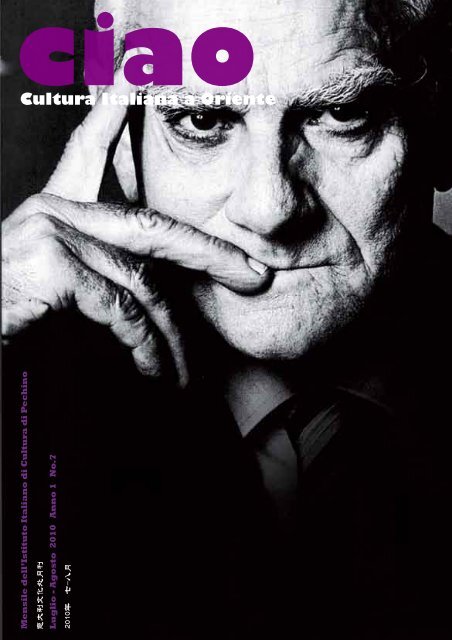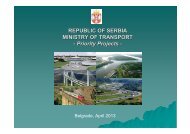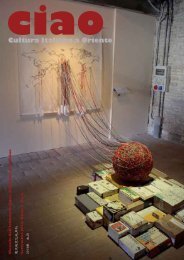Cultura Italiana a Oriente
Cultura Italiana a Oriente
Cultura Italiana a Oriente
- No tags were found...
Create successful ePaper yourself
Turn your PDF publications into a flip-book with our unique Google optimized e-Paper software.
<strong>Cultura</strong> <strong>Italiana</strong> a <strong>Oriente</strong>Mensile dell’Istituto Italiano di <strong>Cultura</strong> di Pechino意 大 利 文 化 处 月 刊Luglio - Agosto 2010 Anno 1 No.72010 年 七 - 八 月1
《 莫 拉 维 亚 小 说 集 》 译 者 序1990 年 9 月 26 日 , 举 世 瞩 目 的 意 大 利 文 学 巨匠 阿 尔 贝 托 · 莫 拉 维 亚 与 世 长 辞 了 。莫 拉 维 亚 是 个 永 不 衰 老 的 “ 斗 士 ”, 他 身 上似 乎 总 有 用 之 不 尽 的 旺 盛 的 精 力 , 孜 孜 不 倦 地 在文 学 园 地 上 常 年 耕 耘 , 在 他 长 达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艰苦 卓 绝 的 文 学 创 作 生 涯 中 , 留 下 了 意 大 利 社 会 各个 时 期 兴 衰 沉 浮 的 痕 记 , 可 以 说 , 莫 拉 维 亚 和 他的 作 品 是 意 大 利 从 法 西 斯 专 政 到 抵 抗 运 动 和 战 后几 十 年 发 展 变 化 的 最 好 见 证 。 他 那 近 40 部 的 各 种体 裁 的 不 朽 之 作 中 , 凝 聚 了 他 非 凡 的 智 慧 和 对 文学 艺 术 的 笃 信 和 倾 注 。 莫 拉 维 亚 一 生 总 共 写 了 17部 长 篇 小 说 ,12 部 短 篇 小 说 ,10 部 剧 作 ,10 部 评论 集 和 游 记 。 他 的 作 品 至 今 已 被 翻 译 成 37 种 语 言在 世 界 各 国 广 泛 流 传 。 灵 魂 的 虚 伪 、 沉 沦 和 堕 落而 触 动 了 法 西 斯 赖 以 生 存 的 土 壤 , 为 此 , 在 第 6版 即 将 开 印 时 就 遭 到 了 当 局 的 查 禁 。 用 6 年 的 心血 写 成 的 第 二 部 小 说 《 错 误 的 野 心 》(1935) 也同 样 遭 到 了 当 局 的 查 禁 。1941 年 问 世 的 《 假 面 舞会 》 是 投 向 业 已 岌 岌 可 危 的 墨 索 里 尼 政 权 的 一 支锋 利 的 投 枪 , 它 指 桑 骂 槐 地 嘲 讽 了 意 大 利 的 法 西斯 政 权 , 因 而 在 它 出 第 二 版 时 又 遭 到 当 局 的 查封 。 从 此 , 莫 拉 维 亚 的 名 字 就 作 为 “ 颠 覆 分 子 ”被 列 人 了 警 方 的 黑 名 单 。被 迫 远 走 他 乡 、 颠 沛 流 离 的 莫 拉 维 亚 对 文学 的 崇 高 信 念 并 未 从 此 混 灭 。 在 南 方 避 难 时 创作 的 《 阿 戈 斯 蒂 诺 》(1944)、《 罗 马 女 人 》(1947)、《 违 命 》(1948)、《 随 波 逐 流 》(1950) 相 继 问 世 。 沉 醉 在 家 乡 光 复 喜 悦 之 中 的莫 拉 维 亚 重 又 燃 起 新 的 创 作 热 情 , 在 新 现 实 主 义热 潮 的 鼓 舞 下 , 眼 光 深 邃 才 思 敏 捷 的 莫 拉 维 亚 发表 了 一 系 列 以 反 映 罗 马 社 会 下 层 平 民 的 命 运 和遭 遇 的 作 品 。 我 们 所 翻 译 的 这 部 《 罗 马 故 事 》(1954) 是 其 中 的 一 部 , 描 写 和 刻 划 了 战 罗 马 社会 底 层 小 人 物 的 辛 酸 际 遇 , 从 题 材 的 选 取 到 表 现手 法 以 及 语 言 的 适 用 , 都 颇 具 特 色 , 可 说 是 作 者的 一 部 力 作 。以 文 学 为 手 段 与 法 西 斯 较 量 中 所 表 现 的 坚 强不 屈 的 意 志 与 战 胜 了 困 扰 他 长 达 9 年 的 病 魔 中 所显 示 出 的 惊 人 的 毅 力 , 是 决 定 莫 拉 维 亚 辉 煌 的 艺术 成 就 的 两 个 基 本 要 素 。9 岁 时 因 患 骨 结 核 而 被迫 卧 床 休 养 因 而 中 断 了 正 规 学 业 的 莫 拉 维 亚 , 在患 病 期 间 , 攻 读 了 大 量 的 欧 洲 和 意 大 利 的 古 典 文学 名 著 , 从 而 为 其 后 来 的 文 学 创 作 奠 定 了 坚 实 的基 础 , 成 为 自 学 成 才 者 的 一 位 楷 模 。在 诸 多 的 文 学 先 行 者 中 ,19 世 纪 的 也 出 生 在罗 马 的 讽 刺 诗 人 焦 阿 基 诺 · 贝 利 (1791-1863)引 起 了 莫 拉 维 亚 极 大 的 兴 趣 。 那 是 一 位 以 深 送 的洞 察 力 直 面 他 所 处 时 代 的 悲 惨 和 人 世 炎 凉 的 现 实主 义 诗 人 。 他 发 表 的 数 量 众 多 的 14 行 短 诗 , 既 大众 化 , 又 富 有 强 烈 的 现 实 性 和 浓 厚 的 抒 情 性 , 像是 一 幅 巨 型 壁 画 鲜 活 地 勾 画 出 了 在 教 皇 格 里 戈 里奥 十 六 世 统 治 下 的 罗 马 城 中 处 于 社 会 底 层 的 贫 民百 姓 “ 仅 仅 为 能 每 天 吃 到 一 块 面 包 而 疲 于 奔 命 ”的 贫 困 境 遇 , 并 展 示 了 罗 马 古 城 当 时 的 风 貌 和 习俗 。1907 年 出 生 在 罗 马 的 一 个 画 家 和 建 筑 师 家 庭的 莫 拉 维 亚 自 小 就 喜 欢 读 贝 利 的 诗 作 , 并 深 为 其作 品 所 具 有 的 艺 术 魅 力 所 感 染 。 诗 人 在 1848 年 对当 时 平 民 反 对 教 会 滥 用 职 权 举 行 的 暴 动 深 表 同情 , 其 作 品 具 有 一 定 的 民 主 自 由 思 想 , 但 他 “ 犹如 一 只 习 惯 于 黑 暗 的 猫 头 鹰 , 骤 然 见 到 光 明 , 不知 往 何 处 飞 翔 , 也 看 不 清 眼 前 事 物 ”。 战 后 的 莫拉 维 亚 就 像 当 年 在 自 由 思 想 感 召 下 的 罗 马 诗 人 贝利 一 样 , 开 始 把 目 光 投 向 四 周 围 的 罗 马 城 的 各 种公 共 场 所 : 车 站 、 市 场 、 咖 啡 厅 、 饭 馆 、 教 堂 、公 园 和 广 场 , 细 致 入 微 地 观 察 日 常 生 活 中 各 种 平凡 的 人 物 的 形 形 色 色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各 种 心 态 。“ 我 要 给 罗 马 平 民 百 姓 留 下 一 块 丰 碑 ”。 那位 19 世 纪 的 罗 马 抒 情 诗 人 用 他 呕 心 沥 血 谱 写 的 2千 多 首 14 行 诗 篇 , 实 现 了 他 生 前 豪 迈 的 誓 言 。而 一 个 世 纪 后 的 小 说 家 莫 拉 维 亚 也 以 其 精 辟 的 语言 , 鲜 明 的 人 物 形 象 和 富 有 戏 剧 性 的 幽 默 感 , 先后 完 成 了 《 罗 马 故 事 》(1954) 和 《 罗 马 故 事 新编 》(1959) 两 部 短 篇 小 说 集 , 为 战 后 生 活 在 罗马 社 会 最 底 层 的 贫 民 又 竖 立 一 座 文 学 艺 术 丰 碑 ,这 两 部 脍 炙 人 口 的 佳 作 , 与 一 百 年 前 的 焦 阿 基 诺· 贝 利 的 诗 作 有 着 异 曲 同 工 之 妙 , 也 是 那 么 引 人入 胜 , 那 么 扣 人 心 弦 。在 莫 拉 维 亚 用 他 一 生 的 精 力 建 立 的 艺 术 丰 碑上 , 除 了 幽 默 风 趣 地 展 示 了 一 幅 鲜 活 的 罗 马 底 层社 会 的 画 卷 外 , 还 用 其 锐 利 的 雕 刀 无 情 地 剖 析 他所 出 身 的 本 阶 级 和 资 产 阶 级 社 会 。 那 是 另 一 种 令人 窒 息 的 画 面 , 展 示 了 现 代 社 会 中 人 与 人 之 间 无法 交 流 和 沟 通 的 现 实 , 画 面 上 的 人 物 在 充 斥 着 追求 物 欲 的 虚 伪 的 现 实 社 会 中 显 得 都 是 那 么 冷 漠 、麻 木 、 自 私 、 茫 然 和 空 虚 。60 年 代 后 他 发 表 了一 系 列 揭 示 现 代 社 会 异 化 的 作 品 , 其 中 有 《 鄙视 》(1954)、《 烦 闷 》(1960)、《 注 意 》(1965)、《 我 和 它 》(1971)、《 内 心 生 活 》(1979) 和 5 部 短 篇 小 说 集 。 他 笔 下 的 人 物 往 往都 是 由 于 在 生 活 中 难 以 寻 求 自 身 的 真 实 存 在 而 烦闷 和 苦 恼 。包 括 了 61 个 短 篇 的 这 部 《 罗 马 故 事 》 中 的 主人 公 们 都 是 生 活 在 战 后 的 罗 马 大 都 市 中 的 贫 苦 的劳 动 大 众 , 他 们 之 中 有 的 是 流 动 小 贩 , 有 的 是 酒吧 跑 堂 , 有 的 是 卡 车 司 机 , 有 的 是 工 人 、 清 道夫 , 有 的 是 裁 缝 、 理 发 师 , 还 有 流 浪 汉 和 仆 役 ,他 们 多 因 生 活 所 迫 千 方 百 计 地 、 有 时 甚 至 是 不 择手 段 地 为 自 己 的 生 存 而 寻 找 各 种 出 路 。 那 雄 伟 的古 罗 马 斗 兽 场 、 那 带 有 美 丽 的 神 话 传 说 的 台 伯河 、 那 神 秘 的 天 使 古 堡 、 那 寂 静 的 古 罗 马 水 道 ,都 冷 漠 地 观 望 着 他 们 的 遭 遇 , 目 睹 他 们 在 饥 饿 和贫 困 线 上 挣 扎 , 即 使 到 了 穷 途 末 路 也 无 法 帮 他 们改 变 悲 惨 、 困 苦 的 命 运 。莫 拉 维 亚 的 《 罗 马 故 事 》 充 满 了 人 生 哲 学 ,通 过 描 写 小 人 物 日 常 所 遭 受 的 种 种 经 历 , 幽 默 地嘲 讽 现 实 生 活 对 他 们 的 不 公 正 , 读 后 令 人 哑 然 失笑 , 却 又 从 那 些 可 怜 、 可 笑 而 又 可 恨 的 人 物 身上 , 看 到 了 存 在 于 现 实 生 活 中 某 些 人 物 形 象 的 缩影 。 作 品 的 幽 默 还 表 现 在 对 其 笔 下 人 物 的 种 种 遭遇 , 总 是 带 着 善 意 的 同 情 和 谅 解 。 对 于 他 们 的 恶习 不 是 鞭 挞 而 是 善 意 的 嘲 讽 , 对 于 他 们 所 采 取 的各 种 伎 俩 不 是 谴 责 , 而 是 含 蓄 地 启 示 开 导 , 并 以成 功 的 对 人 物 心 理 的 细 腻 贴 切 的 描 写 和 刻 画 , 揭示 了 从 事 各 种 职 业 的 人 物 那 种 无 奈 、 无 力 、 无助 、 无 谓 的 生 存 方 式 和 绝 望 的 心 态 。 每 篇 小 说 最后 那 些 独 具 匠 心 的 戏 剧 性 结 尾 妙 趣 横 生 、 恰 到 好处 , 往 往 起 到 画 龙 点 睛 的 作 用 , 更 增 添 了 作 品 的艺 术 感 染 力 , 起 到 了 令 人 意 想 不 到 的 效 果 。……我 们 花 了 近 一 年 的 业 余 时 间 翻 译 了 莫 拉 维 亚的 这 部 短 篇 小 说 集 , 深 深 地 叹 服 这 位 文 学 巨 匠 深厚 的 文 学 功 底 和 高 超 的 艺 术 表 现 力 。 感 谢 上 海 译文 出 版 社 的 合 作 , 使 我 们 能 在 这 位 伟 大 的 小 说家 所 开 辟 的 浩 瀚 的 艺 术 海 洋 中 沐 浴 而 感 到 欣 悦 。考 虑 到 莫 拉 维 亚 这 部 作 品 中 所 采 用 的 罗 马 地 方 语言 的 特 点 , 在 翻 译 中 我 们 也 适 当 地 采 用 了 一 些 地道 的 北 京 话 , 以 更 好 地 传 达 原 著 的 地 方 语 言 色 彩和 基 调 。 关 于 方 言 的 使 用 , 莫 拉 维 亚 曾 这 样 评 述道 :“ 从 句 法 和 修 辞 方 面 来 看 , 我 的 语 言 趋 向罗 马 方 言 , 一 种 ‘ 粗 俗 ’ 的 语 言 …… 方 言 的 运 用是 随 着 官 方 语 言 危 机 的 出 现 而 应 运 而 生 的 ; 经历 了 一 场 灾 难 性 的 法 西 斯 统 治 后 , 产 生 了 偏 好 使用 方 言 的 倾 向 , 从 而 使 文 明 的 官 方 语 言 的 运 用 出现 了 危 机 。 某 些 作 家 采 用 方 言 是 为 了 更 直 接 地 反映 现 实 , 他 们 排 斥 使 用 官 方 语 言 不 仅 出 于 语 言 上的 原 因 , 还 有 政 治 和 社 会 原 因 -- 标 志 着 统 治 阶 级和 文 化 , 知 识 分 子 和 资 产 阶 级 之 间 的 一 种 严 重 分裂 。” 引 自 《 罗 马 故 事 》 前 言 )莫 拉 维 亚 对 古 老 的 中 国 和 中 国 人 民 怀 有 深 厚的 感 情 , 曾 先 后 于 1936 年 、1968 年 、1986 年 三 次来 到 中 国 。 最 后 一 次 应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的 邀 请 到 中国 来 访 时 , 他 已 年 近 八 旬 , 本 书 译 者 之 一 沈 萼梅 女 士 有 幸 作 为 翻 译 陪 同 他 作 了 长 达 两 周 的 正 式访 问 , 参 观 了 北 京 、 西 安 、 广 州 、 桂 林 、 内 蒙 古等 地 。 考 虑 到 他 年 事 已 高 , 作 家 协 会 没 有 能 满 足他 要 去 西 藏 的 宿 愿 , 记 得 他 当 时 深 表 遗 憾 地 说 :“ 我 离 80 还 差 1 岁 呢 !” 当 他 神 采 奕 奕 地 拄 着 拐杖 漫 步 在 成 吉 思 汗 陵 墓 前 的 宽 阔 的 市 道 上 时 ,关 切 地 向 沈 萼 梅 女 士 问 到 《 罗 马 女 人 》 和 《 乔恰 里 亚 女 人 》 在 中 国 有 没 有 译 本 , 说 那 是 两 部 反映 罗 马 下 层 贫 苦 妇 女 悲 惨 命 运 的 力 作 , 并 答 应 回意 大 利 后 直 接 寄 书 给 她 。1986 年 10 月 中 旬 的 一 个下 午 , 满 载 莫 拉 维 亚 主 要 著 作 的 一 箱 书 运 到 了 北京 , 其 中 就 有 我 们 所 译 的 《 罗 马 故 事 》。 每 当 我们 翻 阅 这 些 凝 聚 着 这 位 文 学 巨 匠 毕 生 精 力 的 经 典著 作 时 , 对 莫 拉 维 亚 在 那 次 访 问 过 程 中 所 表 现 出的 惊 人 的 精 力 和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浓 厚 兴 趣 , 以及 他 那 幽 默 风 趣 的 谈 吐 , 至 今 还 记 忆 犹 新 。 印 象最 深 的 是 他 在 西 安 饺 子 馆 用 完 晚 餐 后 , 写 在 留 言簿 上 那 句 不 落 俗 套 的 题 词 :“ 青 蛙 从 盘 子 里 跳 出来 了 ”。 原 来 , 晚 餐 的 菜 谱 上 有 青 椒 炒 青 蛙 ……( 沈 萼 梅 刘 锡 荣 ,1998 年 3 月 于 北 京 )2 3
Prefazione alla Raccolta dei romanzi di MoraviaIl 26 settembre 1990 morì il grande scrittoreitaliano Alberto Moravia, intellettuale militante, cheha coltivato con inesauribile energia la passione perla letteratura. Del mezzo secolo della sua difficilecarriera letteraria restano le tracce delle alternevicende della società italiana, la testimonianza deicambiamenti e degli sviluppi avvenuti nei decennidel Fascismo, della Resistenza e del Dopoguerra.Nella varietà stilistica dei suoi circa 40 scritti, traromanzi, racconti, opere teatrali, saggi critici ememorie di viaggio, tradotti in 37 lingue, Moraviacondensa una straordinaria cultura unita a un forteimpegno per le lettere. Per i temi trattati, l’ipocrisia,il degrado e la degenerazione dell’animo in epocafascista, di alcuni di essi venne vietata la ristampa,come il romanzo Le ambizioni sbagliate (1935),frutto di sei anni di lavoro, e la seconda edizionedi La mascherata del 1941, che facendosi beffadell’ormai instabile governo di Mussolini fucensurato del governo. Da quel momento il nome diMoravia entrò nella lista nera dei “sovversivi”.Costretto alla fuga, Moravia non abbandonòla scrittura. Appartengono al periodo dell’esilioal sud Agostino (1944), La romana (1947), Ladisubbidienza (1948), Il conformista (1950). Feliceper la ritrovata libertà del suo Paese, Moravia trovònuova ispirazione pubblicando una serie di opere suldestino degli strati sociali più poveri della capitale,tra esse Racconti romani, capolavoro tradotto incinese.Attraverso la letteratura Moravia dimostral’irriducibile volontà di combattere il fascismo e lasorprendente perseveranza nell’affrontare la malattiache lo aveva afflitto fin da bambino. Questi sonodue dei fattori fondamentali che hanno determinatoil successo di Moravia. La tubercolosi ossea, chelo aveva colpito all’età di nove anni, lo portò adabbandonare gli studi, costringendolo a letto. Iclassici italiani e stranieri che leggeva avidamentedurante il periodo della malattia diventarono deimodelli per la sua formazione da autodidatta.Tra i pionieri della letteratura, Moravia siinteressò a Gioacchino Belli (1791-1863), il poetasatirico romano del XIX secolo che ritrasse nei suoicomponimenti in stile popolare realista le difficilicondizioni di vita delle classi sociali più povereche, durante l’egemonia di Papa Gregorio XVI,lavoravano duramente per un “tozzo di pane algiorno”.Moravia era nato a Roma nel 1907 da unafamiglia di pittori e architetti e fin da piccolo fuaffascinato dalla profondità delle poesie di Belli.Dopo la guerra, influenzato dal poeta romano, iniziòa prestare attenzione ai luoghi pubblici di Roma:stazioni, mercati, caffetterie, ristoranti, chiese,parchi e piazze, osservando i diversi stili di vita e lamentalità della gente comune nel quotidiano.“Voglio lasciare un monumento ai romani”,questa l’eroica promessa del poeta mantenuta inpiù di duemila poesie. Un secolo più tardi Moravia,con lingua incisiva, personaggi estremamentecaratterizzati, spesso grotteschi, portò a terminele due raccolte Racconti romani (1954) e Nuoviracconti romani (1959), monumenti letterari dellasocietà civile romana del dopoguerra. Oltre adescrivere con sarcasmo le condizioni degli stratipiù umili della società romana, Moravia analizzacon dovizia di dettagli la sua stessa classe sociale,la borghesia, dando un’immagine sconvolgentedell’incomunicabilità dell’uomo nella realtàcontemporanea. I suoi personaggi si muovonoindifferenti, intorpiditi, egoisti e vuoti in una societàavida e falsa.Dopo gli anni Sessanta Moravia pubblica una seriedi opere sull’alienazione della società moderna, tracui Il disprezzo (1954), La noia (1960), L’attenzione(1965), Io e lui (1971), La vita interiore (1979)e cinque raccolte di racconti. I personaggi di cuiscrive sono depressi ed angosciati per le difficoltàincontrate nella loro ricerca di una reale esistenza.I personaggi principali dei sessantuno Raccontiromani sono tutti umili lavoratori nella Romadel dopoguerra: venditori ambulanti, camerieri,camionisti, operai, spazzini, parrucchieri, servi esenzatetto. Si affannano per sopravvivere ricorrendoa qualsiasi mezzo per tirare avanti. Il grandiosoColosseo dell’antica Roma, il leggendario Tevere,il misterioso Castel Sant’Angelo, i canali silenziosidella capitale assistono indifferenti all’incontro diquesti personaggi, diventando testimoni della lorolotta per sconfiggere fame e povertà ma incapaci dicambiare il loro tragico destino.I Racconti romani di Moravia sono pregni dellasua filosofia di vita: nel descrivere la sofferenzaquotidiana di personaggi comuni, l’autore scherniscecon ironia l’ingiustizia della vita nei loro confronti.È difficile per il lettore non lasciarsi sfuggire unsorriso di fronte a personaggi tanto miseri, ridicolie patetici, sebbene proprio essi gli consentano diavere una visione d’insieme della varietà di tipologieumane. Dall’umorismo delle sue opere trasparealtresì l’empatia e la comprensione che Moraviaprova per i suoi personaggi. Non c’è castigo neiconfronti dei loro vizi ma solo un bonario sarcasmo,non c’è critica verso certi comportamenti ma soloun’implicita indicazione della strada da percorrere.L’autore riesce a descriverne con dovizia diparticolari la psicologia umana. Sono uomini chenon nutrono più speranze, che non hanno scelta,inutili e impotenti.Abbiamo impiegato un anno per tradurre questaraccolta di racconti di Moravia, restando ammiratidallo spessore culturale e dalla straordinaria forzaespressiva di questo maestro della letteratura… Perrendere la particolarità e certe caratteristiche deldialetto romano abbiamo fatto ricorso ad espressionitipiche del dialetto pechinese.L’uso di una lingua molto vicina al dialetto, unalingua “volgare” seguiva per Moravia la crisi dellalingua ufficiale. L’esperienza disastrosa del regimefascista aveva dato luogo a una tendenza a preferirel’uso di forme dialettali. “È così che alcuni autoriutilizzano il dialetto per rappresentare in manieradiretta la realtà; essi rigettano l’utilizzo della linguaufficiale non solo per motivi linguistici, ma anchepolitici e sociali, per simboleggiare cioè la nettarottura tra classe dominante e cultura, tra intellettualie borghesia” (tratto da Racconti romani).Moravia si reca in Cina ben tre volte, nel 1936,nel 1968 e nel 1986, invitato nel suo ultimo viaggiodall’Associazione degli scrittori cinesi, quandoaveva ormai quasi ottant’anni. Durante le duesettimane di soggiorno, la sottoscritta, Shen Emei,gli fece da interprete accompagnandolo a Pechino,Xi’an, Canton, Guilin e in Mongolia interna. L’unicatappa che l’Associazione escluse dall’itinerariotemendo per l’età avanzata dello scrittore fu il Tibet.In seguito, ricordando il dispiacere per quel mancatoviaggio, Moravia disse: “Mi mancava ancora unanno prima degli ottanta!”. Moravia volle sapere seLa romana e La ciociara fossero state tradotte incinese, e mi promise di inviarmene copia non appenatornato in Italia.Un pomeriggio di metà ottobre del 1986 venneconsegnata a Pechino una scatola contenente alcunedelle più importanti opere di Moravia, tra le quali iltesto da noi tradotto, Racconti romani. Di Moraviaricordiamo il profondo interesse per la letteraturacinese tradizionale e il grande senso dell’umorismo.Un giorno, al termine di una cena in un ristorantedi jiaozi a Xi’an, scrisse sul libro dei visitatori: “Lerane saltano fuori dal piatto”. Una delle specialitàdel locale erano rane saltate al pepe verde….Shen Emei, Liu Xirong, marzo 1998, Pechino4 5
I viaggi di Moravia in CinaConferenza di Wei Yi all’Associazione degli Italianisti, a Roma nel 2008I. IntroduzioneIl viaggiare è sempre stato e tutt’ora rimane unargomento affascinante, ma non tutti sono fortunatiquanto Moravia, che ha compiuto i primi viaggiavventurosi in Europa già da adolescente, finanziatodal padre, e poi successivamente ha viaggiato comeinviato speciale di giornali o semplice viaggiatorescrittoresu quattro continenti del mondo, eccettoquello australiano. Nella sua autobiografia ches’intitola Vita di Moravia (pubblicata nel 1990, incui ha raccontato ad Alain Elkann della sua vitadagli anni Dieci alla fine degli anni Ottanta delsecolo scorso), ha scritto: “Il mio modello di vitaera Lawrence, che viaggiava sempre e scriveva neiluoghi più diversi...”ancora “...viaggiare mi distrae,mi sblocca, e mi arricchisce”. In questi viaggi,ha incontrato i capi di stato più leggendari, qualiNehru, il primo presidente della Repubblica indiana,poi Tito, Arafat, e Castro, che Moravia chiamava“uomini d’azione”, e per i quali provava una certasimpatia. Le esperienze acquisite percorrendo Paesidiversi l’hanno reso uno degli scrittori italianipiù a contatto con il mondo esterno, e per questomotivo dotato di una visione più ampia. I frutti diquesti viaggi sono gli articoli pubblicati su diversigiornali, cominciando dalla “Gazzetta del Popolo”negli anni Trenta, per continuare con “L’Espresso”e soprattutto “Il Corriere della Sera” dagli anniCinquanta. Moravia ha scritto anche saggi di viaggiodi particolare rilevanza, perché completano gliarticoli pubblicati sui giornali, nei quali l’autoredoveva svolgere il suo compito di giornalista e nonaveva sempre abbastanza spazio per le osservazionipersonali.Moravia definiva se stesso “scrittore turista”, valea dire uno che “è capace di fornire più informazionidegli esperti”. Quando viaggiava, teneva una speciedi diario in cui raccontava le esperienze delle singolegiornate, precisando a volte perfino l’ora esatta deidiversi movimenti, e leggeva le opere degli scrittoriillustri del Paese che stava visitando per trovarnei luoghi più suggestivi. Diceva Moravia nella suaautobiografia: “La mia patria era ed è la letteratura.Viaggiavo con la testa avvolta in una nube diletteratura. Vivevo le avventure del mondo moderno,intanto leggevo dei classici.” (Vita di Moravia, p.82).Moravia non ha vissuto le sue esperienzeall’estero solo viaggiando e leggendo, ma anchecercando delle avventure, e quelle avventure nonhanno coinvolto soltanto compagni di viaggio, qualiElsa Morante per prima, e successivamente DaciaMaraini e Pasolini, e altri scrittori sia italiani chestranieri, ma anche i capi di Stato sopraccitati, evarie figure femminili.Quando una cosa o un fenomeno non è conosciuto,è capace che ad esso venga attribuito un aspettomitico. Ma chi non si accontenta di mitizzare e sipuò permettere di svelare il mito, si mette in azione.Negli innumerevoli viaggi che hanno segnato tuttala vita di Moravia, instancabile scrittore-viaggiatoretestimone,assumono una particolare importanza lesue tre visite in Cina, il Paese che ha suscitato millefantasie in Italia, dai letterati dell’antichità fino alpubblico odierno.II. I tre viaggi in Cina:Moravia visitò la Cina tre volte in contesti bendiversi. Arrivò in Cina per la prima volta nel 1937,alla vigilia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quandodominava il Vecchio Regime, il quale fu costrettoad allearsi al Partito comunista contro gli invasorigiapponesi, dopo il famoso colpo di Stato di Xi’andel 12 dicembre 1937. Nel 1967 Moravia ritornò inCina tra i tumultuosi movimenti della Rivoluzione<strong>Cultura</strong>le, la quale sarebbe stata chiamata dai cinesii dieci anni di catastrofe. Al suo terzo viaggio nel1986 invece, la Cina aveva cominciato a praticare,da quasi dieci anni, la politica dell’apertura, grazie aDeng Xiaoping.In questi viaggi lo sguardo di Moravia, checercava sempre una civiltà intatta, come tral’altro fanno quasi tutti i giornalisti e intellettualioccidentali che viaggiano in contesti particolari esoprattutto orientali, sembrava attirato da temi qualila povertà, la tradizione o meglio il confucianesimo,e alla fine i monumenti storici.1. Il Viaggio del 1937A proposito del motivo di questo viaggio, nellaVita di Moravia scrive: “A Roma mi annoiavo, ladonna inglese era scomparsa dalla mia vita, avevofinito di scrivere i racconti e fu così che decisi dipartire per la Cina” (p.88). Si recò dal direttoredella Gazzetta del Popolo per farsi pagare ilbiglietto di viaggio, e con la promessa di vendergligli articoli, partì da Trieste con un battello che sichiamava Conte Rossi ed arrivò a Shanghai, dopoaver conosciuto tante altre città misteriose qualiBombay, Ceylon, Singapore, Manila. Prima diraggiungere Shanghai, passò per Canton, la cittàdalle mille barche, sul Fiume delle Perle, sullequali viveva parte della sua popolazione; e subitodopo Hong Kong, dominato dai grattacieli, dovesi fermarono tutti i suoi compagni di bordo italianiper raggiungere i “night-club più belli del mondo”.In questo primo viaggio Moravia visitò Nanchino,Suzhou, e Pechino, poi da Pechino ritornò aShanghai per andare a Hong Kong via mare, e dopobrevi visite a Canton e Macao, ripartì da Hong Kongper l’Italia sempre in battello.Agli occhi di Moravia, Shanghai era un pessimoesempio della modernità in Cina, simile ad una cittàamericana, città di divertimenti semplici e monotoni,che consistevano in sale da gioco e sale da ballo.Ed era anche una città cosmopolita dove i palazzidi stile occidentale convivevano con le capannemodeste, i ricchi con i poveri di diverse nazioni, ele ballerine straniere, soprattutto russe, con quellecinesi. Ma se ci si spostava un po’ verso i sobborghidella città, si vedevano subito donne e bambineche lavoravano nelle filande di seta. Concludevanell’articolo pubblicato sulla Gazzetta del Popolo:“Shanghai è una città schiettamente americana; unacittà dove gomito a gomito vivono la più abbiettamiseria e la ricchezza più sfacciata, e dove unristretto numero di persone guadagnano enormisomme di denaro durante il giorno e cercano durantela notte di sperperarne una minima parte.”Dopo fece due brevi gite vicino a Shanghai,durante le quali visitò prima Nanchino, la nuovacapitale del governo del partito nazionalista, chegli lasciò un’impressione negativa, poi Suzhou chechiamava Soochow, la cosiddetta Venezia della Cina,o Città dei giardini.Se Shanghai era la città di divertimenti, eNanchino “un grosso villaggio”, Pechino perMoravia era la città dove “tutto era enorme”.All’arrivo a Pechino dopo un viaggio di due giornicon il treno Shanghai Espress, vide “un’alta, grossa,grigia, merlata, vecchia muraglia, una porta arcorotondo dagli enormi battenti di ferro rugginosoe bullonato...”, immagini che sarebbero sparite alsuo ritorno a Pechino nel 1967, perché la vecchiamuraglia, cintura della città, veniva demolita percostruire larghe strade e per far circolare i veicoli.Ciò che colpì Moravia, fu l’aspetto della vita diPechino. Scrisse nell’articolo uscito il primo luglio1937 sulla Gazzetta del Popolo, che Pechino, nellosfondo confuso dei cosiddetti signori di guerra, stavaancora in “un mondo settecentesco, con i monumentiantichi intatti, con gli artigiani che lavorano amano”. Sulle strade della città che era stata per secolicapitale delle ultime dinastie del Celeste Impero sivedevano “...tanti poveri, con vestiti e modi ancoratradizionali, ma gentili, umani e innocenti”.Era proprio questo il fascino di Pechino, unacittà che “non viveva nel presente”, ma davantialla quale Moravia non riusciva a frenare la suaimmaginazione, diceva appunto che:quando la Cina sarà quel paese moderno eindustriale che gli inglesi vorrebbero che diventasse,sarà certamente più barbara di ora...basta guardareche cosa siano diventati a Shanghai, sola cittàdavvero moderna della Cina, gli antichi gentilicostumi e la vecchia saggezza dei cinesi.Un’avventura del viaggio: gli fu chiesto dalconsolato italiano di Canton di portare un pacco,nel quale c’erano delle carte geografiche dei fondalimarini di Hainan, una grande isola non lontanada Hong Kong. Si capiva che Mussolini volevaimpadronirsi di quell’isola e farne una colonia.Però la giornata più affascinante di questoviaggio rimaneva quello in cui Moravia alloggiò inun albergo nella città di Kalgan, nel deserto dellaMongolia, terra in cui sarebbe tornato Moravianell’ultimo viaggio in Cina per una visita vera epropria. Mangiava il pollo con il riso ascoltandouna bambina di dieci anni che cantava e suonava lachitarra, mentre la città di argilla stava diventando6 7
ionda di sabbia.Tornato a Roma, dopo due mesi in Cina e duemesi sul mare tra l’andata e il ritorno, cominciò apubblicare degli articoli sulla Gazzetta del popolo,raccontando del suo viaggio in Cina, dicendo che fu“un’esperienza importante”, perché cercava, comenegli altri viaggi, una civiltà intatta, e di questarimaneva sicuramente soddisfatto e nostalgico.Questa immobilità della Cina, di cui Moravia èstato uno dei primi testimoni italiani, continuavafino agli anni 50, quando vennero altri scrittori estudiosi italiani, per i quali la Cina rimaneva unpaese misterioso e la patria dei grandi poeti. Questoviaggio è stato importante per Moravia anche perchétrovò, per caso, in una libreria di Pechino, TheWaste Land di T.S.Eliot, che avrebbe letto con moltoentusiasmo.2. Il viaggio del 1967Moravia scrisse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cinese di allora, Zhou Enlai, il quale era anchePresidente del Consiglio, ricordandogli che eragià stato in Cina nel 1937, ed espresse il desideriodi vedere la Cina nuova. Ottenuto il visto, si recòin Cina con Dacia Maraini (mentre la prima voltaviaggiava da solo) per proseguire il viaggio fino alGiappone e alla Corea del Sud.È opportuno ricordare che dopo la fondazionedella nuova Cina negli anni Cinquanta, la Cinasuscitò un vivo interesse negli intellettuali italiani.Nel 1954 si recò in Cina la prima delegazioneculturale italiana, guidata da Francesco Flora, laquale fu seguita, nel 1955, dalla seconda delegazionea cui parteciparono Carlo Cassola, Franco Fortini eCarlo Bernari. Nel 1956 il senatore Ferruccio Parriguidò la terza delegazione, molto più numerosa edi partecipazione più varia: parlamentari, sinologi,professori universitari e altri uomini di cultura, trai quali figuravano Gianfranco Vigorelli e CurzioMalaparte. I loro saggi di viaggio presentavano laCina al pubblico italiano che rimaneva affascinato,perché rendevano più vicino questo Paese dallastoria millenaria ma distante dall’Italia diecimilachilometri. I saggi più importanti sono: Viaggio inCina di Carlo Cassola, Asia Maggiore di FrancoFortini, che è stato ristampato nel 2007, Cara Cinadi Goffredo Parise, Domande e risposte per lanuova Cina di Gianfranco Vigorelli, e Io in Russiae in Cina di Curzio Malaparte, tutti pubblicatialla fine degli anni Cinquanta, seguiti dalle altrepubblicazioni significative, quale Liriche cinesi percui Eugerio Montale scrisse l’introduzione. Taleimpegno degli intellettuali italiani continua fino adoggi.2.1 Le visite e gli incontriDiversamente dal primo viaggio, Moravia passòla dogana tra Hong Kong e la Cina continentale, poiprese il treno per andare a Canton, e da Canton aPechino in aereo.L’orizzonte dello scrittore fu limitato dalprogramma di visite, preparato dall’Ufficio delturismo cinese. Ciononostante Moravia riuscì astabilire più contatti umani diretti rispetto al viaggioprecedente, intervistando personaggi di diversecategorie, i quali comparvero anche nel saggio chededicò al secondo viaggio, vale a dire La Rivoluzione<strong>Cultura</strong>le in Cina (1968).Il panorama della Rivoluzione <strong>Cultura</strong>le, ilmovimento politico di massa che caratterizzò la Cinadegli anni Sessanta e Settanta, si costituì pian piano,cominciando dal ballo di propaganda cui Moraviaassistè prima di prendere il volo per Pechino, edall’abbigliamento dei cinesi: “un tipo di uniformitàassoluta fatta di una tunica abbottonata fino al collo,senza differenza tra gli individui, nemmeno tra isessi”. In questa moltitudine blu o grigia si vedevanodonne coi pantaloni come gli uomini, perché lagonna era “segno di corruzione borghese”. Poi siconcretizzò quando Moravia raggiunse Pechino evide le processioni delle guardie rosse in onore del“grande condottiero”, che secondo lui segnaronoun’epoca nella storia cinese. Mentre i dimostrantiche si allinearono davanti al treno che andava versoHong Kong, sotto la pensilina della stazione, conil libretto di Mao in mano e protestavano controla colonizzazione inglese, furono un’altra prova diquanto fosse coinvolgente la Rivoluzione <strong>Cultura</strong>le,a cui nessun cinese poteva rimanere indifferente.Impressionante fu anche il culto personale peril grande leader che aveva salvato il popolo cinesedalla miseria che era durata per secoli. Sul voloda Canton a Pechino, si offrivano varie fogge conle testa di Mao, e le statue di Mao si vedevanodappertutto, anche nei ristoranti. La particolaritàdi questo culto personale era il libretto di citazionidi Mao che i cinesi tenevano sempre in mano ecitavano prima di parlare su ogni cosa, il qualeattribuì anche al “carattere religioso” dellarivoluzione. È opportuno sottolineare che durante ilmovimento studentesco italiano, il libretto rosso diMao fu molto apprezzato e conobbe varie versioni.Nel quadro generale che ci dipinse Moravia suquesto movimento che coinvolse la popolazionepiù numerosa del mondo, spiccano alcuni cinesiesemplari: uno scrittore famoso e quarantenne, unoperaio pensionato, le Guardie Rosse che erano iragazzi ventenni, la guida che era sempre triste senzamotivo.Il primo personaggio che Moravia incontrò era unoscrittore famoso di Shanghai, giovane e massiccio,dall’aspetto paesano, sempre sorridente, ma portaval’aria di un“insegnante che sta di fronte allo scolarodistratto”. Le loro conversazioni si svolgevano informa di un duello pedantesco, medievale, a basedi citazioni di Mao, e parlavano quasi unicamentedel rapporto tra l’arte e la politica. Per lo scrittorecinese, l’arte doveva servire il popolo, ed era regolauniversale che il criterio politico stava sempre al disopra di quello artistico, mentre Moravia sostenevache l’arte doveva ridpondere sulla base della sualibera scelta. Rispetto al primo viaggio, Moravia eramolto più preparato. Scrisse:“Capisco che debborispondere nello stesso modo: con Mao. Senzaesitare apro anch’io il libro di Mao, annunzio ilnumero della pagina, e appena loro l’hanno trovato,leggo con violento tono didascalico...”(p.65).Moravia voleva continuare il dialogo parlandodegli scrittori famosi occidentali, ma l’amico cinesene sapeva ben poco, come tra l’altro gli scrittorioccidentali rispetto a quelli cinesi antichi e moderni.Lo scrittore cinese si dimostrò non solo ignorantema soprattutto indifferente verso tale argomento,perché nella Cina di Mao anche la letteratura fupoliticizzata, come facevano i russi.L’immediata riflessione suscitata dall’incontro conil giovane scrittore cinese fu: “..la letteratura saràpur l’arte che rivelerà maggiormente le differenzetra la nostra cultura e quella cinese”; poi scrisseMoravia: “La Cina, dicono i cinesi, deve liberarsidell’influenza sovietica. Ma prima di tutto, secondome, dovrebbe liberarsi del realismo socialista,dell’arte di propaganda”(pp.141-142).Il secondo personaggio che Moravia ebbel’occasione di conoscere in modo più approfonditoera un Operaio Modello, sicuramente preparato,il quale diceva che nella sua vita da pensionato,non faceva altro che leggere i libri rivoluzionari,soprattutto quelli di Mao. Ma alla fine dell’intervistateneva a mostrare agli ospiti, con orgoglio, ilsuo fornello a gas, l’unico oggetto di lusso chepossedeva.Rispetto a questi due personaggi, i cinesi cheMoravia conobbe nel secondo viaggio e cheavrebbero colpito la sua immaginazione, erano lecosiddette Guardie Rosse, cioè i giovani studentiche abbandonarono per forza lo studio per farela rivoluzione. Erano poveri e indossavano ivestiti puliti ma bucati e non stirati. Non potevanopermettersi neanche di comprare il té che costavapochissimo e bevevano solo l’acqua calda. Maera la parte del popolo cinese più convinta dellarivoluzione di Mao. Per Moravia invece sono“bambini per la qualità candidamente religiosadella loro credenza”, sono “fanciulli in crociata”.Tra i ragazzi poveri, la guida triste, l’odoredel cavolo che si sentiva dappertutto, e i dazibaoattaccati sui muri su cui si leggevano slogan,denunce, accuse, sentenze, Moravia fu invitato acena, con Dacia Maraini, per assaggiare la famosaanatra di Pechino; ma con un senso di colpa, perchéla Cina di allora era: “un paese che si nutre inprevalenza di riso, di miglio e di cavolo”.2.2 Le riflessioni sulla Rivoluzione culturaleLa Rivoluzione culturale è caratterizzatainnanzitutto dal culto personale verso il grandeleader, considerato “l’uomo eponimo”, vale adire chi dà il proprio nome a tutta un’epoca. Era unculto da parte di tutti i cinesi, tanto che, nel saggiodi Moravia del 1968 veniva attribuito a questomovimento di massa un aspetto religioso. Un cultosoprattutto dei giovani studenti, a cui Mao feceappello. Lo consideravano Mao il loro maestro, e larivoluzione era la loro scuola politica. Le GuardieRosse dicevano appunto che è una rivoluzionedella gioventù. In questo movimento asuscalanazionale, avvenuto quasi vent’anni dopo avervinto la guerra civile contro il Partito nazionalista,Mao ritrovò il contatto diretto con le masse e anchela forza di una volta, tornò coi piedi per terra econdannò violentemente il confucianesimo comeconservatorismo cinese che riteneva il nemicofondamentale. Il simbolo di questo culto era il librodi citazioni che all’epoca tutti i cinesi tenevano inmano e citavano prima di fare qualunque discorso,un fenomeno cui Moravia vedeva una “religiositàcontadina e primitiva”.L’aspetto religioso e primitivo della Rivoluzione<strong>Cultura</strong>le si completava con“...l’estensionealla vita urbana dei valori e dei costumi dellacampagna... in tutta la Cina urbana, si è diffusala ‘pruderi’contadina e antisessuale...ispirandosialla sobrietà dei contadini..”(p155). La prova piùimmediatamente visibile era che gli uomini e ledonne cinesi indossavano lo stesso costume sobrio,e che quasi tutti i ristoranti venivano chiusi. L’unicoristorante sopravvissuto doveva svolgere la funzioneeducativa, e gli occidentali che ci mangiavanodovevano sentirsi in colpa......Sfogliamo velocemente il diario di Moravia pervedere i monumenti visitati, e le riflessioni che gli8 9
suscitano a proposito:Innanzitutto la Grande Muraglia, il simbolo delconservatorismo, che da una parte serviva ai cinesiper proteggersi contro le invasioni barbariche, mad’altra impedì lo sviluppo e i cambiamenti, e fecedella Cina un Paese aragosta, cioè duro fuori, molledentro.In secondo luogo il Palazzo d’estate e le Tombedei Ming, altri simboli del feudalesimo cinese,che suscitavano dalla parte dei cinesi solo l’odiodel passato. Il senso del bello in Cina oggi è statosostituito dal senso di buono”,scrive Moravia.(p.152). Tali monumenti non sono belli perché nonsono buoni, e possono servire solo per educare eistruire.Fu questa l’interpretazione di Moravia sulsentimento dei cinesi verso il loro passato, quandovide la distruzione tragica dei monumenti storici .Malgrado le condizioni umane penose e laconfusione sociale che testimoniò, Moravia provò“sollievo”, e vide in Cina un’“utopia realizzata”,una utopia che consisteva nella povertà del popolo ela castità. Si aspettavano dalla Cina delle“soluzioniutopistiche”, che avrebbero dovuto far sentire laricchezza come peccato, come colpa, come delitto”.Fu necessario un terzo viaggio perché potesse capirefinalmente la crudeltà di questa rivoluzione con tuttele conseguenze tragiche.3 Il viaggio del 1986Sul suo terzo viaggio che effettuò dall’ottobreal dicembre del 1986, ci sono poche tracce, cinquearticoli soltanto sul Corriere della Sera, in cuiMoravia descrisse i cambiamenti nella città diPechino, dicendo che nel suo primo viaggio del1936, Pechino rimaneva una città asiatica nella qualei grandi stradoni imperiali somigliavano a “lettiasciutti di torrenti”; mentre nel secondo viaggio del1967, venne colpito dalle processioni delle GuardieRosse in onore di Mao, tutti in uniforme blu, colpiccolo libro di Mao stretto in pugno; e quando tornòa Pechino per l’ultima volta nel 1986, ciò che glisaltò agli occhi furono i grattacieli di tipo americano,costruiti recentemente con capitali e tecnologiestraniere. Quando attraversava la Piazza Tiananmenin macchina e guardava fuori dal finestrino, pensavache la città stesse diventando senza carattere, “nonc’era nulla di memorabile”, fino a quando non videla marea di biciclette che gli suscitarono un nuovointeresse.3.1 Le visiteRealizzò finalmente il sogno nato dal primoviaggio di visitare la Mongolia. A Huhehot,capoluogo della regione autonoma della Mongoliainterna, visitò due luoghi antichi, un tempio lamaistaquasi intatto, e il Mausoleo di Gengis Khan, nelcuore del deserto di Gobi, distrutto dalle GuardieRosse (solo allora cominciò a capire questa forzadistruttiva, e l’amarezza che provavano i cinesi perquella rivoluzione tragica che aveva suscitato tantidanni alle opere d’arte, e tante conseguenze fisiche emorali a tutti). Era in via di restauro, però a Moraviasembrava “qualcosa tra Disneyland e Le mille e unanotte”.Rispetto all’immenso deserto che da soloassumeva un fascino irresistibile, la città di Pechinogli sembrava, a prima vista, senza carattere, fino aquando lo sguardo cadde sulla gente in bicicletta:“pedalano calmi, riflessivi, composti e dignitosi,danno l’impressione di una folla che abbia adottatala bici non già per necessità ma per libera scelta.La bici è silenziosa, inodore, elegante”. L’infinitapazienza che gli risultava anche ad un certo modoincomprensibile, dimostrata dai ciclisti in bicicletta,l’oggetto che simbolizzava il momento storico,veniva subito associata alla cultura millenaria cinesee al confucianesimo, senza tenere in considerazioneche i cinesi volevano proprio lasciarsi alle spalle ilpatrimonio medievale, considerato conservatore, percorrere verso la modernità, e che la rivalutazione delconfucianesimo doveva ancora arrivare.3.2 Le riflessioniDiversa dai primi due viaggi, la Cina divennemolto meno affascinante per Moravia, che nondedicò nessuna parola in Vita di Moravia al terzoviaggio, ma ci dimostrò, nell’articolo pubblicato sulCorriere della sera, la sua nostalgia e l’amarezzaverso un’antica civiltà distrutta: “Pechino di alloraera una meraviglia, adesso non è più niente. Alloracome era stata per secoli, un groviglio di vicolipittoreschi simili alle calli veneziane. Adesso è comese Roma fosse rimasto soltanto il Colosseo, piazzaSan Pietro e basta”.Le mura alte e i vicoli pittoreschi cedettero lospazio alla metropolitana e ai grattacieli di stileamericano, e i ragazzi in processioni venivanosostituiti dagli operai docili che si recavano al postodi lavoro in bicicletta; le università furono riaperte,però alle domande di Moravia, gli studenti sapevanosolo rispondere in modo univoco, seguendo lapropaganda ufficiale, “sorridendo e ridacchiandoma senza fare obbiezioni e prendere posizioniindividuali”. L’unica cosa che rimaneva era lapovertà. In Mongolia interna, Moravia fu invitatoa un banchetto, caratterizzato da un agnello interoda distribuire secondo la qualità della carne el’importanza del commensale, e animato da danzee canzoni locali. Ma fuori dalla yurta di lusso dovealloggiava, vide un’anziana che prendeva l’acquadal pozzo, fu per lui il simbolo della povertàcontadina. Più sorprendente fu la riflessione sulsocialismo reale cinese, mettendo a paragone la CittàProibita di Pechino, simbolo del potere feudale, e unalbergo di lusso a Guangzhou , in cui alloggiavanoo mangiavano i funzionari cinesi e i turisti stranieri,e dove un’anatra costava 40 yuan, mentre fuori daquesta “nuova Città Proibita” lo stipendio mediocinese era di 100 yuan. Scrisse sul Corriere dellaSera : “Il potere cambia e come. Ma i mezzi di cuisi serve sono pochi e sempre i stessi”.III ConclusioneMoravia è sempre convinto che “un intellettualenon è altro che il testimone del suo tempo”, ein tutti i suoi saggi le testimonianze sono sempreaccompagnate da riflessioni e osservazioni. Quandoscrive sull’India parla quasi sempre della religione,una religione primitiva, mentre l’Africa è perMoravia un Paradiso. Nel caso della Cina, Moraviaè costretto a parlare della sua storia millenaria.I temi che gli stanno più al cuore rimangonoquelli esistenziali: la povertà, l’influenza delconfucianesimo sulla vita dei cinesi, e lo sviluppoa passi stentati e a volte sanguinosi, con sacrificiculturali irragionevoli e irrecuperabili.Un testimone di mentalità sicuramenteintellettuale-occidentale, che associa un movimentodi massa caratterizzato dal culto personale ad unareligione, e che preferisce case e palazzi antichi aigrattacieli, la gente semplice e umile piuttosto airicchi. Ma anche un testimone con un obiettivo bendeterminato, perché la sua riflessione sull’esistenzaumana va sempre a finire per l’attaccare la societàborghese, la battaglia che Moravia ha lanciato nel1929 con il romanzo d’esordio Gli Indifferenti.Cosicché nell’introduzione della Rivoluzione<strong>Cultura</strong>le in Cina, partendo dalla realtà della Cinacomunista, il discorso prosegue pian piano versole riflessioni sulla società occidentale, e ci fornisceun quadro perfetto di questa società di consumo, laquale è diventata disumana e difettosa a causa dellaricchezza. “Questa cultura è consumata nello stessomodo che sono consumati i prodotti industriali...Ilconsumo culturale non produce che sterco culturale,niente altro”(La Rivoluzione <strong>Cultura</strong>le in Cina,p.18). Invece la Cina con la sua povertà generale,è per lui un esempio della condizione normaledell’uomo, perché “la superfluità non lo rende piùuomo di quanto non faccia appunto la povertà”. Daqui nasce la ricetta che Moravia propone per guarirela società borghese corrotta: innanzitutto la povertà,ed anche la castità, prendendo come modello l’utopiadella Cina di Mao, che “stava copiando dei valorie dei costumi della campagna”.Purtroppo le “soluzioni utopistiche” non sisono realizzate in Cina e Moravia, come gli altriscrittori italiani, rimane sempre più incantato dallaterra sperduta dell’Africa, dove i paesaggi bellied autentici attirano non solo il nostro scrittorema anche i suoi lettori. Mentre la Cina continua ilsuo cammino verso una modernità che all’epocadell’ultimo viaggio di Moravia era ancora difficileda immaginare.10 11
ARRIVO A PECHINO CON LO SCIANGAI-EXPRESSA Pechino ci arrivai dopo due giorni di viaggioattraverso uno dei paesaggi più tristi e piatti cheavessi mai veduto in vita mia. Il lento treno cinesedalla lugubre e rauca sirena, lo Sciangai-Expressreso famoso da un film altrettanto menzognero checonvenzionale, attraversò ad una media di 30-40chilometri all’ora una buona metà della Cina per tuttala sua lunghezza; più province, alcune delle qualigrandi come nazioni europee, vennero percorse;eppure, in quei due giorni non vidi mai altro cheun’infinita pianura ancora invernale nonostantela primavera inoltrata, gialla, senza alberi, senzaalture, senza corsi d’acqua, polverosissima, sparsadappertutto dei tumuli delle tombe.Il treno, sebbene si fosse in pianura, procedevacon quella faticosa lentezza con la quale da noi iconvogli avanzano in salita, dentro i pesanti vagonile cerniere, i gangheri, le connessure, ogni cosagemeva e cigolava come per uno sforzo penoso,attraverso i doppi vetri la campagna restava adistanza di ore così immutabile che se ne perdevail senso del tempo e dello spazio. Ma più che lapiattezza del paesaggio e la lentezza del treno, quelche dava al viaggio un suo carattere ossessivo erail gran numero di tombe di cui appariva sparsa ladeserta campagna.È questa una delle caratteristiche più originalidel paesaggio cinese: le montagnole delle tombeche, senza ordine né alcuna specie di recinto, quae là tumefanno i campi arati, rompono le righe deisolchi, e allignano dappertutto così numerose chesulle prime addirittura si pensa ad una specialeconformazione del terreno. E in verità la Cinaintera si potrebbe paragonare ad un’immensa facciapiatta e bonaria tutta coperta di foruncoli, e in ogniforuncolo un cadavere già polverizzato o ancorafresco.La religione pagana degli antenati vuolequeste inumazioni situate di solito presso la casae il podere dove il morto penò e lavorò da vivo;sorgono le tombe così numerose e con così pocoriguardo dell’economia da rendere improduttivauna vasta estensione del suolo cinese; diviso tra lavenerazione per gli antenati e la fame che l’assediasenza tregua, il contadino spinge l’aratro piùvicino che può a questi tumuli, e i più antichi, giàdisfatti dalle intemperie, cerca di far scomparire orarosicchiandone un angolo ora un altro di stagione instagione.Come ho detto questa vista ripetuta delle tombequasi mi ossessionò. Vedevo un tumulo solitario nelmezzo di un gran campo arato a perdita d’occhio epensavo: “Ecco, lì riposa alfine colui che per annie anni si ruppe la schiena sotto la pioggia, la nevee il vento per tracciare questi solchi lunghissimi edirittissimi”; contavo sette, otto o dieci tumuli, l’unostretto all’altro, quali più grossi e alti, quali piùpiccoli, non lontani da certe casupole di fango seccoe mi dicevo: “Ecco i nonni che ebbero la venturadi mangiare riso fino ai sessanta o ai settant’anni, ipadri meno fortunati che schiattarono a quaranta, ledonne morte nelle doglie del parto e i piccolini cosìbelli con le facce tonde e gli occhi stretti e obliquia cui la dissenteria o altra febbre non permise dipassare il quinto anno di età”; finalmente in vista allemura merlate di qualche città mi si presentavano agliocchi, allineate tra i fossi e i terreni vaghi, centinaiae centinaia di montagnole tutte uguali; serrate,pullulanti come i mucchi delle saline, disciplinate, eallora non potevo fare a meno di pensare:“Ecco i giovanotti, contadini e figli di contadiniche si arruolarono negli eserciti allora nemici delgenerale Wang e del generale Li; qui avvenne labattaglia che secondo segreti accordi avrebbe dovutoessere incruenta ma che per un errore tattico risultòsanguinosissima; ora giacciono, poveri eroi stupiti,e i loro capi Wang e Li messisi d’accordo governanoinsieme la provincia.”Così pensavo mentre il treno arrancava; e se nonavessi saputo che la Cina è la più prolifica e vitalenazione che ci sia al mondo, la vista di tante tombemi avrebbe convinto di attraversare un lugubre edeserto paese abitato ormai soltanto da morti.Ma i vivi non mancavano. Ogni due ore, talvoltapiù spesso, la corsa rallentava, e in un gran cigoliodi freni, con certi bruschi contraccolpi che facevanocozzare l’un contro l’altro i viaggiatori, il trenosi fermava davanti il marciapiede di una stazionecampagnuola.Una folla aspettava il treno, una folla ne scendeva;tutta gente rustica, dalle facce stolide, infagottata ingiubbe e pantaloni di cotone nero foderato di ovattao di pelliccia; donne con gabbie e ceste, uominicon casse e sacchi, e i bambini gonfi di troppi panniaggrappati alle gambe.Le stazioni erano casette quadrate di poveramuratura, tutt’intorno in una luce scialba si stendevala pianura deserta, i villaggi dovevano essere lontanicome l’attestavano dietro le tristi palizzate dicemento, attaccati a piccoli carri dalle ruote ferratee dai tetti a gronda, certi bruni cavallucci pelosi. Inqueste stazioni il treno sostava a lungo, senza motivoapparente; poi la sirena rauca e querula gridava, euno dopo l’altro i vagoni si scuotevano; mentre isoldati rimasti soli sul marciapiede presentavano learmi come se fosse stato un corteo funebre.Altre volte il treno passava accanto a un villaggio.Vedevo, appena distinte con righe di luce dalgiallume circostante, le casupole di fango seccocoi tetti di paglia impoltigliata e scurita dallepiogge, costruite sulla sponda di un largo lettoasciutto di torrente; nel quale i cani magri e arruffatirovistavano tra i ciottoli e le immondizie; tuttointorno terre sgretolate che da certe tracce comedi solchi pareva che un tempo fossero state campicoltivati; in tanto eguale e abbagliante gialloresole macchie erano i maiali neri che nei piazzali sirotolavano nella polvere come se fosse stata mota eacqua.Una caligine livida e gonfia offuscava il cielosenza nubi e il sole vi faceva un alone quasi verdesimile ad uno sputo; tant’era l’aridità del paesaggioche non agli occhi faceva male, ma alle nariciche ne risentivano una irrespirabile e spasimosasecchezza come di polvere. Vidi un contadino chezappava ai margini di un immenso campo in cuiogni traccia di aratura si era disfatta e cancellatain una sola granulosa farina; ad ogni zappata unanuvola di polvere si levava sotto il ferro della vangae l’avvolgeva tutto. Ancora vidi una donna che stavaseduta sull’orlo della massicciata con le gambe daipantaloni neri penzolanti nel vuoto; dava il pettoa un bambino, un involto di cenci; mi sorpreseche potesse farlo, l’aridità della terra mi daval’impressione che ogni umore, anche negli uomini,si fosse rasciugato. Dovevano essere mesi che noncadeva una sola gocciola di pioggia e tirava quelvento che vedevo all’orizzonte sollevare dei granturbini scuri; io ne provavo sete e non facevo chebere.Tale monotonia, come ho detto, durò due giorni;le stazioni si seguivano alle stazioni, i soldatipresentavano le armi, i contadini salivano con i lorocesti, il treno fischiava e ripartiva. Al terzo giorno siarrivò a Pechino.Pechino sta con le sue mura tirate a filo di squadranel mezzo della gran pianura asciutta come una granfortezza. Tutte le città cinesi sono cinte di mura e,certo, sotto quest’aspetto Pechino è la più cinesedelle città.Come da noi un treno entra nella galleria chefora una collina, così la locomotiva dell’espresso di12 13
Sciangai improvvisamente si addentrò fischiandodentro l’enorme spessore delle mura. Il fumo nerosaliva ai merli che si staccavano contro il cieloazzurro, uno dopo l’altro i vagoni s’infilavanonella porta lunata con un fracasso di ferraglie cheecheggiava sotto la volta, come si riuscì all’aperto siprese a correre lungo il fossato erboso, stampandonel sole blando l’ombra labile del treno sulla lisciamuraglia.Poi, uscito dalla stazione per un sottopassaggio,questa fu la prima vista di Pechino: una alta, grossa,grigia, merlata, vecchia muraglia, una porta ad arcorotondo dagli enormi battenti di ferro rugginoso ebullonato spalancati, e sopra la porta, giganteggiantecontro il cielo, una torre rettangolare con tre file difinestre profonde sormontata da un triplice tetto dallepunte rialzate e dalle tegole verdi. Tale porta con icontrafforti a sghembo e i tetti massicci a barchettal’avevo già osservata in altre città cinesi; ma maicosì enorme e imponente, così barbarica e regolare.E questa poi doveva essere la mia costantesensazione a Pechino: di vedere tutto quello cheavevo visto fin allora moltiplicato più volte ingrossezza, pesantezza, solidità, magnificenza. Lamedesima sensazione di chi non avendo visto cheserpentelli e biscioline possa finalmente osservareun pitone lungo dodici metri. Una sensazione,strano a dirsi, di stupita ammirazione per le capacitàdigestive così della bestia come dell’opera umana;la quale ispira soprattutto questo pensiero: “Quantapreda viva serve a nutrire questo mostro, quantapietra, quanta fatica, quanta civiltà c’è voluta pertirar su questa porta!”E in verità Pechino è tra le città cinesi quelloche il pitone è tra i serpenti. Le mura che altrovegiungono appena ai sette metri qui sorpassano iquindici. Nei templi le colonne fatte d’un solo troncodi albero tek della Birmania non le abbraccianodue uomini mentre altrove hanno la grossezza diun nostro pino. Le strade sono larghe come fiumi elunghe fino al limite dell’orizzonte. Le tartarughevotive nelle lamaserie sono grandi quanto elefanti;e i padiglioni che le proteggono alti come case. Ilcinese di solito così avaro di spazio, qui s’è esaltatoin cortili vasti come piazze nella Città proibita o inprospettive lunghe e diritte come moli nel Tempiodel Cielo. I leoncelli, che a Canton sono grossicome gatti o tutt’al più come leoni, qui diventanobestie mitologiche della grandezza di bufali e stannoa guardia non di portoncini o di portoni bensì dispettacolari ingressi situati in cima a scalinate dimarmo.Eppure per quella medesima divina proporzionedelle parti nel tutto che nella Basilica di San Pietronon fa parere eccessiva l’enormità degli angeli chesorreggono le pile dell’acqua santa, anche a Pechino,passata la prima sorpresa, non ci si accorge più divivere tra cose immense e insolite. Di modo che ilcolossale, altrove tanto oppressivo, in questa cittàunica risulta armonioso e dolcemente esaltante.[“Gazzetta del Popolo”, 25 giugno 1937]乘 上 海 特 快 来 到 北 京经 过 两 天 的 旅 行 , 我 来 到 了 北 京 。 沿 途 的 风景 是 我 一 生 中 所 见 到 的 令 人 伤 感 和 平 淡 无 奇 的 风景 之 一 。 中 国 的 火 车 行 驶 缓 慢 , 并 且 响 着 凄 凉 而沙 哑 的 汽 笛 。 上 海 特 快 因 为 一 部 既 不 真 实 而 很老 套 的 电 影 而 出 了 名 。 它 以 每 小 时 30-40 公 里 的时 速 , 穿 越 了 大 半 个 中 国 。 这 列 火 车 途 径 很 多 省份 , 其 中 有 一 些 和 欧 洲 的 国 家 一 样 大 。 尽 管 春 天已 至 , 在 这 两 天 的 行 程 中 , 我 满 眼 都 是 冬 季 笼 罩下 的 一 望 无 际 的 黄 色 平 原 , 没 有 树 木 , 没 有 高山 , 没 有 水 流 , 而 且 非 常 贫 穷 , 坟 冢 随 处 可 见 。尽 管 行 驶 在 平 原 上 , 火 车 仍 旧 举 步 维 艰 , 就如 同 在 我 们 那 里 火 车 上 坡 的 时 候 那 样 。 在 这 些 用合 页 、 铰 链 连 接 的 沉 重 的 车 厢 里 , 每 样 东 西 都 在呻 吟 着 , 发 出 吱 吱 呀 呀 的 响 声 , 仿 佛 不 堪 重 负 。透 过 双 层 玻 璃 的 车 窗 , 乡 村 永 远 是 在 距 离 几 个 小时 以 外 的 地 方 , 以 至 于 人 失 去 了 空 间 和 时 间 感 。不 过 , 比 平 淡 无 奇 的 风 景 和 火 车 的 缓 慢 更 加 令 人难 以 忍 受 的 , 是 遍 布 在 广 阔 的 田 野 上 的 那 些 为 数众 多 的 坟 冢 。这 是 中 国 最 具 特 色 的 风 景 : 一 个 个 坟 冢 , 既没 有 秩 序 , 也 没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围 栏 。 它 们 在 田 间隆 起 , 切 断 了 犁 地 留 下 的 沟 辙 。 这 些 坟 冢 四 处 繁衍 , 而 且 为 数 众 多 , 以 至 于 人 们 会 认 为 它 们 是 一种 特 殊 的 地 貌 形 式 。 事 实 上 , 可 以 把 整 个 中 国 比作 一 张 巨 大 、 扁 平 、 和 善 , 却 长 满 疥 疮 的 脸 , 在每 一 个 疥 疮 里 躺 着 一 具 业 已 化 为 尘 土 , 或 者 仍 然新 鲜 的 尸 体 。作 为 一 种 非 基 督 徒 的 宗 教 , 对 于 先 人 的 这 种崇 拜 希 望 将 先 人 们 埋 葬 在 居 家 的 附 近 , 也 就 是 逝者 从 前 劳 动 的 地 方 。 如 此 为 数 众 多 而 又 简 陋 的 坟墓 , 使 得 中 国 广 大 的 土 地 不 能 用 于 生 产 。 出 于 对先 人 的 崇 拜 , 这 个 国 家 处 于 无 休 止 的 饥 饿 当 中 。农 民 扶 着 犁 在 尽 可 能 靠 近 这 些 坟 冢 的 地 方 经 过 。那 些 最 老 的 坟 冢 已 经 随 着 岁 月 的 流 逝 而 毁 坏 。 农民 们 尝 试 着 在 每 个 季 节 里 一 个 角 一 个 角 地 将 它 们蚕 食 。正 如 我 前 面 所 说 的 , 这 些 坟 冢 的 不 断 出 现 使我 几 乎 感 到 一 种 折 磨 。 看 到 一 大 片 犁 过 的 土 地 上树 立 着 一 个 孤 零 零 的 坟 冢 , 我 想 :“ 就 在 这 儿 ,这 里 长 眠 着 一 位 曾 经 年 复 一 年 在 雨 雪 、 寒 风 中弯 着 腰 , 在 田 地 上 留 下 一 条 条 又 长 又 直 的 沟 辙 的人 ”; 我 数 着 七 个 , 八 个 , 或 者 十 个 坟 冢 , 一 个紧 挨 着 另 一 个 。 其 中 的 一 些 不 太 高 , 但 是 很 大 ,另 外 一 些 则 规 模 偏 小 。 它 们 距 离 一 些 用 土 坯 建 成的 小 茅 屋 非 常 近 。 我 心 中 于 是 想 :“ 这 就 是 那 些有 幸 在 60 或 者 70 岁 的 高 龄 还 能 吃 大 米 的 爷 爷 奶 奶们 , 那 些 在 四 十 岁 就 暴 死 的 不 幸 的 父 亲 们 , 还 有因 难 产 死 去 的 母 亲 , 以 及 长 着 如 此 漂 亮 的 , 浑 圆的 小 脸 , 细 长 的 眼 睛 , 却 因 为 痢 疾 或 者 其 它 热病 没 有 能 够 活 过 5 岁 的 孩 子 ”。 最 后 , 我 的 眼 前又 出 现 了 某 座 城 市 筑 有 城 池 的 围 墙 外 , 排 列 在壕 沟 和 广 袤 的 土 地 之 间 的 那 些 坟 冢 。 它 们 成 千 上万 , 形 式 完 全 一 致 , 密 密 麻 麻 地 紧 挨 在 一 起 , 如同 盐 场 的 一 个 个 整 齐 的 盐 堆 。 我 禁 不 住 想 :“ 这 就 是 那 些 年 轻 人 , 农 民 的 儿 子 。 他 们 应征 入 伍 , 去 和 当 时 的 敌 人 作 战 , 那 个 什 么 王 将 军或 者 李 将 军 。 这 里 发 生 了 战 斗 。 根 据 秘 密 协 定 ,这 些 战 役 都 应 该 兵 不 血 刃 。 但 是 , 由 于 某 种 战 略上 的 失 误 , 却 演 变 成 了 一 场 血 战 。 现 在 , 这 里 长眠 着 那 些 可 怜 而 愚 蠢 的 英 雄 , 而 他 们 的 长 官 , 王将 军 和 李 将 军 , 却 商 定 要 共 同 统 治 这 个 省 份 。”如 此 , 火 车 一 路 艰 难 前 行 , 我 的 思 绪 也 随 着火 车 浮 想 联 翩 。 假 如 我 不 是 已 经 得 知 中 国 是 世 界上 最 为 物 产 丰 富 和 富 于 活 力 的 国 家 , 见 到 如 此 多的 坟 冢 , 我 会 觉 得 自 己 是 在 一 个 唯 有 死 人 居 住 的悲 伤 而 荒 凉 的 国 度 旅 行 。事 实 上 , 这 里 并 不 缺 少 活 人 。 每 隔 两 个 小时 , 火 车 就 会 放 慢 速 度 。 随 着 巨 大 的 吱 吱 呀 呀 的车 闸 声 , 以 及 旅 客 之 间 碰 撞 发 出 的 窸 窸 窣 窣 的 声响 , 火 车 停 靠 在 一 个 乡 间 小 站 的 站 台 上 。一 群 人 在 下 面 等 车 , 另 外 一 群 人 则 要 下 车 。他 们 都 是 些 乡 下 人 , 呆 头 呆 脑 , 表 情 迟 钝 , 裹 在棉 大 衣 、 黑 色 棉 裤 或 者 毛 皮 裤 里 。 女 人 手 里 提 着笼 子 和 篮 子 , 男 人 提 着 箱 子 和 袋 子 , 就 连 孩 子 们也 穿 得 十 分 臃 肿 , 抱 着 大 人 的 膝 盖 。火 车 站 是 一 些 墙 壁 简 陋 , 四 四 方 方 的 小 房子 , 笼 罩 在 平 淡 的 阳 光 里 的 荒 芜 的 平 原 在 它 的 四周 延 伸 开 来 。 凄 凉 的 水 泥 砌 成 的 栏 杆 后 面 , 停 放着 一 些 带 有 倾 斜 顶 棚 的 铁 轮 的 小 车 , 车 上 拴 着 浑身 是 毛 的 褐 色 丑 马 。 它 们 仿 佛 证 明 村 庄 距 离 这 里很 远 。 在 这 些 车 站 , 火 车 要 停 留 很 久 , 却 看 不 出有 什 么 理 由 。 随 后 , 沙 哑 而 哀 怨 的 汽 笛 再 次 响起 , 火 车 车 厢 开 始 一 个 接 一 个 地 晃 动 起 来 。 士 兵们 孤 独 地 留 在 站 台 上 , 握 着 武 器 , 仿 佛 是 一 个 送葬 的 队 伍 。另 外 一 些 时 候 , 火 车 会 从 一 个 村 庄 的 旁 边 经过 。 借 着 四 周 微 弱 的 灯 光 , 我 可 以 依 稀 看 见 用 土坯 建 成 的 小 茅 屋 。 这 些 房 子 建 在 一 条 长 长 的 已 经干 枯 的 河 床 边 上 , 屋 顶 上 铺 的 茅 草 因 为 下 雨 而 布满 灰 尘 , 黑 乎 乎 的 。 一 些 瘦 削 而 毛 发 凌 乱 的 野 狗在 鹅 卵 石 和 垃 圾 间 翻 找 着 。 房 屋 的 四 周 是 龟 裂 的田 地 。 从 犁 留 下 的 辙 来 看 , 这 里 曾 经 是 可 以 耕 种的 田 地 。 在 一 成 不 变 的 耀 眼 光 线 下 , 唯 一 的 斑 点是 几 只 黑 色 的 猪 。 它 们 在 尘 土 中 打 滚 , 仿 佛 那 是泥 和 水 。一 大 团 青 黑 色 的 烟 雾 遮 蔽 了 晴 朗 的 天 空 , 太阳 的 光 环 几 乎 变 成 了 绿 色 , 如 同 一 口 痰 。 反 正 乡间 的 景 色 索 然 无 味 , 所 以 烟 雾 对 于 视 觉 并 没 有 产生 什 么 损 失 , 不 过 鼻 孔 却 嗅 到 一 股 难 闻 的 干 涩 ,像 是 灰 尘 。 我 看 见 一 个 农 民 在 一 片 辽 阔 的 田 野 边上 锄 地 , 田 地 里 犁 留 下 的 痕 迹 被 一 片 颗 粒 状 的 东西 所 淹 没 。 他 每 锄 一 下 , 铁 锹 下 面 就 会 扬 起 一 阵14 15
灰 尘 , 把 他 完 全 包 裹 在 内 。 我 还 看 见 一 位 妇 人 坐在 路 基 的 边 上 , 裤 腿 在 空 中 悬 着 。 她 正 在 给 孩 子喂 奶 , 孩 子 被 裹 在 破 布 里 面 。 我 很 吃 惊 她 还 能 这样 做 , 因 为 干 燥 的 尘 土 让 我 觉 得 任 何 的 体 液 , 甚至 是 男 人 的 , 也 已 经 干 枯 了 。 很 可 能 已 经 几 个 月都 没 有 下 过 一 滴 雨 了 , 风 在 地 平 线 处 卷 起 黑 暗 的漩 涡 。 我 感 到 口 渴 , 于 是 不 停 地 喝 水 。正 像 我 先 前 所 说 的 , 如 此 的 单 调 持 续 了 两天 。 我 们 经 过 一 个 接 一 个 的 车 站 。 士 兵 佩 戴 着 武器 , 农 民 挎 着 他 们 的 篮 子 上 车 , 火 车 鸣 笛 出 发 。第 三 天 , 我 来 到 了 北 京 。位 于 广 阔 而 干 旱 的 平 原 中 央 的 北 京 , 围 绕 在方 方 正 正 的 城 墙 中 间 , 如 同 一 个 巨 大 的 要 塞 。 中国 所 有 的 城 市 都 有 城 墙 。 当 然 , 从 这 个 角 度 来讲 , 北 京 是 所 有 城 市 中 最 中 国 的 一 个 。如 同 在 我 们 那 里 火 车 钻 进 山 丘 上 开 的 隧 道 一样 , 上 海 特 快 的 火 车 头 突 然 响 着 汽 笛 钻 进 一 个 巨大 而 厚 重 的 城 墙 。 黑 烟 升 上 了 蓝 天 下 矗 立 的 墙垛 , 一 个 个 车 厢 钻 入 月 亮 形 的 城 门 , 拱 门 下 回 响着 破 烂 的 火 车 发 出 的 巨 大 声 响 。 进 入 城 门 后 , 火车 开 始 沿 着 沾 满 杂 草 的 城 墙 奔 跑 起 来 , 柔 和 的 阳光 将 火 车 匆 匆 的 身 影 投 射 在 光 滑 的 城 墙 上 。随 后 , 我 从 一 个 地 下 道 出 了 火 车 站 。 这 是 北京 展 现 在 我 眼 前 的 第 一 幅 景 象 : 一 座 高 大 、 厚重 、 灰 色 、 筑 有 城 池 的 城 墙 ; 一 个 拱 形 的 城 门 ,敞 开 的 巨 大 铁 质 门 扇 锈 迹 斑 斑 , 上 面 钉 着 螺 栓 。在 城 门 上 方 , 长 方 形 的 巨 大 塔 楼 直 冲 云 霄 。 塔 楼侧 面 开 着 三 列 幽 深 的 窗 户 , 顶 上 是 三 层 绿 色 瓦 片的 飞 檐 。 如 此 筑 有 倾 斜 的 扶 垛 和 厚 重 的 船 型 屋 檐的 城 门 , 我 已 经 在 其 他 中 国 城 市 见 过 , 不 过 都 没有 这 里 的 巨 大 和 宏 伟 , 也 没 有 这 么 野 蛮 和 规 则 。对 于 北 京 的 这 种 感 觉 将 一 直 持 续 下 去 : 在 这里 所 见 到 的 一 切 , 都 要 比 在 别 处 见 到 的 庞 大 、 厚重 、 坚 固 和 宏 伟 好 几 倍 。 这 种 感 觉 就 好 像 只 见 过小 蛇 的 人 终 于 见 到 了 十 二 米 的 巨 蟒 一 样 。 很 奇怪 , 这 种 感 觉 , 是 对 像 人 类 这 样 的 野 兽 具 有 如 此消 化 能 力 的 一 种 吃 惊 与 钦 佩 。 这 种 感 受 尤 其 会 使人 产 生 如 此 的 联 想 :“ 要 想 养 活 如 此 的 魔 鬼 , 需要 多 少 猎 物 、 石 头 、 辛 苦 , 又 需 要 多 少 文 明 才 能开 启 这 扇 大 门 呀 !”事 实 上 , 北 京 对 于 中 国 其 它 的 城 市 来 说 就 如同 一 条 巨 蟒 之 于 小 蛇 。 别 处 的 城 墙 勉 强 能 够 达 到七 米 高 , 而 这 里 的 城 墙 却 超 过 了 十 五 米 。 在 这 些寺 庙 里 , 用 一 根 缅 甸 檀 木 制 成 的 柱 子 , 两 个 人 合抱 都 很 困 难 , 而 他 处 却 只 有 我 们 的 松 树 那 么 粗 。这 里 的 道 路 像 河 流 一 样 宽 广 , 长 长 的 一 直 延 伸 到地 平 线 。 喇 嘛 庙 里 的 许 愿 乌 龟 体 大 如 象 , 庇 护 它们 的 亭 阁 则 如 同 房 屋 一 样 高 大 。 通 常 情 况 下 在 空间 上 如 此 吝 啬 的 中 国 人 , 在 这 座 城 市 里 却 建 造 了像 紫 禁 城 里 的 广 场 那 样 宽 阔 的 庭 院 , 或 者 是 天 坛里 那 样 漫 长 而 笔 直 的 堤 道 。 把 门 的 小 石 狮 子 在 广东 只 有 猫 那 么 大 , 或 者 最 多 像 只 狮 子 , 在 北 京 却变 成 了 如 同 水 牛 一 样 巨 大 的 神 话 中 的 野 兽 。 它 们不 是 在 守 候 那 些 门 , 而 是 守 护 着 位 于 大 理 石 台 阶顶 上 的 入 口 。同 样 是 气 势 宏 伟 的 建 筑 , 圣 彼 得 大 教 堂 里 擎着 圣 水 槽 的 天 使 并 不 显 得 格 外 庞 大 。 在 北 京 也 是这 样 。 在 经 历 了 最 初 的 惊 奇 之 后 , 就 再 也 不 会 觉得 是 生 活 在 庞 大 和 不 寻 常 的 东 西 中 间 了 。 以 至 于那 份 巨 大 , 在 其 它 的 地 方 显 得 如 此 令 人 压 抑 , 在这 座 独 一 无 二 的 城 市 里 却 显 得 如 此 和 谐 而 温 柔 。《 人 民 报 》,1937 年 6 月 25 日ASPETTI SETTECENTESCHI DELLA VITA DI PECHINOGran parte delle critiche che di solito vengonomosse dai viaggiatori stranieri in Cina hanno tutteuna medesima origine: che codesti viaggiatorivivono in paesi moderni, cioè paesi che hanno giàattraversato la fase dell’industrialesimo; mentre laCina, per ragioni economiche e storiche, è rimastaferma ad una condizione di vita che non esito achiamare settecentesca.II Settecento, è risaputo, fu un secolo di grandee umana civiltà. Ma non occorre uno sforzo troppointenso della fantasia per immaginare cosa fosseParigi verso la fine del Settecento. Strade senzaselciato, fangose e con carraie profonde; dameeleganti e incipriate, ma sotto quelle cianfrusagliee quei belletti la sporcizia e il sudore; case ornate,piene di belle cose complicatamente decorativee squisitamente scomode, ma nello stesso tempol’assenza o peggio la presenza inadeguata einefficace di quei bagni, di quelle sistemazionimeccaniche, di quegli apparecchi igienici che pernoi, certo a torto, sono diventati ormai sinonimo diciviltà.È risaputo che a Downing Street la casa del primoministro inglese non ebbe un bagno fin dopo la metàdell’Ottocento: il grave Gladstone e il gaio Disraelisi lavavano poco. Figuriamoci cosa doveva essereParigi cinquanta o sessant’anni addietro. Quantopoi alla vita, essa si svolgeva con molte cerimoniee molte raffinatezze di etichetta ma senza alcunafretta; rapidità non c’era né era richiesta; era unavita davvero poco turbinosa, in un silenzio di strademalselciate e maleodoranti dove non risuonavanoche gli schiocchi delle fruste, il rotolare delle ruote egli zoccoli dei cavalli.Socialmente la gente agiata non aveva neppure ilsospetto delle sofferenze del popolo; e quest’ultimosoffriva senza protestare, o se protestava non lofaceva per accampare diritti ma per chiedere ilfavore di un trattamento migliore: popolo riottosoe scontento ma non desideroso di prendere il postodei padroni, non organizzato, come si dice ora, noncosciente. Tali con semplicità le condizioni di Parigisettecentesca; e anche quelle della Cina di oggi.I disastri della Cina vengono in gran parte daquesto stacco di secoli che la divide dagli altri paesi.Per questo sono ingiuste le critiche degli stranieri,specialmente degli anglo-sassoni i quali, scambiandouna differenza di civiltà per barbarie, parlano spessodella Cina come se fosse uno stato negro dell’Africa.E aggiungiamo che, a parer nostro, quando la Cinasarà quel paese moderno e industriale che gli inglesivorrebbero che diventasse, sarà certamente piùbarbara di ora; per convincersene, basta guardare checosa siano diventati a Sciangai, sola città davveromoderna della Cina, gli antichi gentili costumi e lavecchia saggezza dei cinesi.Ma a Pechino siamo ancora in un mondosettecentesco. La città non è molto cambiata daitempi degli imperatori Manciù; si è sgretolata, èdecaduta, lentamente si disfà, ma trasformazionivere e proprie per fortuna non ne ha subite.L’incanto della vita a Pechino, incanto un po’amaroe malinconico, sta proprio in questo sentimento dinon vivere nel presente, bensì in uno dei passati piùillustri e più civili che ci siano mai stati. Non parlodei monumenti che sopravviveranno; parlo di quellecento minute cose della vita quotidiana che unavolta compiuta l’inevitabile trasformazione dellaCina in paese moderno sono destinate certamente ascomparire.Del resto i termini di Asia e di civiltà orientalein contrapposto con Europa e civiltà occidentalepossono infondo venire adoperati soltanto percerte fondamentali attitudini dello spirito. Ma peril costume e per gli aspetti spiccioli della vita,16 17
十 八 世 纪 风 格 的 北 京 生 活大 部 分 对 于 这 个 国 家 的 评 价 来 自 于 曾 经 到 中国 旅 行 的 外 国 人 , 而 且 都 有 同 样 的 来 源 : 这 些 旅行 者 都 生 活 在 现 代 化 国 家 , 也 就 是 已 经 经 历 了 工业 化 的 国 家 。 中 国 则 由 于 经 济 和 历 史 的 原 因 仍 旧处 于 停 滞 的 状 态 。 这 里 的 条 件 会 令 人 毫 不 犹 豫 地将 它 称 为 十 八 世 纪 式 的 生 活 。众 所 周 知 , 十 八 世 纪 是 一 个 拥 有 伟 大 而 人 性化 文 明 的 世 纪 。 但 是 , 无 需 绞 尽 脑 汁 就 可 以 想 象到 十 八 世 纪 末 的 巴 黎 是 个 什 么 样 子 : 没 有 砌 石 的路 面 上 布 满 了 泥 泞 和 深 深 的 车 辙 。 优 雅 的 贵 夫 人们 脸 上 扑 着 香 粉 。 不 过 , 在 那 些 无 用 的 胭 脂 香 粉下 面 , 是 肮 脏 和 汗 臭 。 装 饰 豪 华 的 房 子 里 布 满 了繁 琐 而 又 华 而 不 实 的 装 饰 。 与 此 同 时 , 还 有 那 些不 相 称 而 且 不 好 用 的 卫 生 间 、 机 械 装 置 , 那 些 如今 已 经 成 为 文 明 的 同 义 词 的 卫 生 设 施 。我 们 知 道 , 在 唐 宁 街 英 国 首 相 的 府 邸 , 十 九世 纪 末 才 有 了 卫 生 间 。 格 拉 斯 顿 和 狄 斯 里 都 很 少洗 漱 。 五 十 或 者 六 十 年 以 前 的 巴 黎 是 副 什 么 模 样可 想 而 知 。 当 时 的 生 活 充 满 了 各 种 社 交 活 动 和 繁文 缛 节 , 不 过 并 不 忙 碌 。 不 存 在 也 不 要 求 速 度 。那 是 一 种 绝 少 纷 扰 的 生 活 。 没 有 砌 砖 , 味 道 也 不太 好 闻 的 街 道 静 悄 悄 的 , 只 有 鞭 子 的 劈 啪 声 , 车轮 的 转 动 声 , 还 有 马 蹄 声 。从 社 会 角 度 来 讲 , 富 人 甚 至 根 本 想 象 不 到 人民 的 苦 难 ; 而 后 者 承 受 着 巨 大 的 痛 苦 却 并 不 反抗 ; 或 者 即 使 反 抗 , 也 仅 限 于 要 求 一 些 权 利 , 以便 得 到 更 好 的 待 遇 。 人 民 倔 强 而 不 满 , 但 并 没 有取 代 他 们 主 人 的 愿 望 。 他 们 没 有 组 织 , 正 像 现 在所 说 的 , 没 有 意 识 。 这 就 是 十 八 世 纪 巴 黎 的 状况 , 也 就 是 今 天 中 国 的 现 状 。中 国 的 灾 难 大 部 分 来 自 几 个 世 纪 以 来 与 其 它国 家 的 脱 离 。 因 此 外 国 人 的 批 评 是 不 公 正 的 , 尤其 是 英 国 人 。 他 们 把 对 文 明 的 漠 视 当 作 是 野 蛮 ,谈 起 中 国 时 就 好 像 它 是 非 洲 的 某 个 国 家 。 还 要 指出 的 是 , 在 我 们 看 来 , 当 中 国 变 成 像 英 国 人 期 望的 那 样 一 个 现 代 的 工 业 化 国 家 时 , 无 疑 会 比 现 在更 加 野 蛮 。 要 说 明 这 一 点 , 只 需 看 看 那 些 古 老 而优 雅 的 习 俗 和 中 国 人 古 老 的 智 慧 , 在 时 下 的 上 海变 成 了 什 么 样 子 。 那 里 是 中 国 唯 一 真 正 现 代 化 的城 市 。不 过 , 北 京 还 是 一 个 十 八 世 纪 的 世 界 。 从 满族 那 些 皇 帝 统 治 开 始 到 现 在 , 这 座 城 市 并 没 有 多少 变 化 : 破 败 , 坍 塌 , 然 后 慢 慢 地 瓦 解 。 不 过 ,幸 好 没 有 发 生 什 么 真 正 的 变 化 。 北 京 生 活 的 迷 人之 处 , 那 种 稍 显 苦 涩 和 伤 感 的 魅 力 , 就 在 于 一 种不 生 活 在 现 实 中 的 感 觉 。 尽 管 过 去 它 有 着 最 为 灿烂 的 文 明 。 我 所 说 的 不 是 那 些 幸 存 下 来 的 建 筑 ,而 是 生 活 琐 事 。 一 旦 中 国 不 可 避 免 地 过 渡 为 一 个现 代 化 的 国 家 , 这 些 东 西 一 定 会 消 失 。另 外 , 亚 洲 与 东 方 文 明 , 欧 洲 和 西 方 文 明 ,这 些 字 眼 说 到 底 只 能 用 来 表 达 精 神 中 某 些 基 本 态度 。 对 于 习 俗 和 日 常 琐 事 , 最 好 是 用 时 代 这 个词 。 现 在 的 北 京 仍 旧 处 于 手 工 业 时 代 。 欧 洲 的 这个 时 代 具 有 同 样 的 特 征 , 而 且 无 疑 已 经 结 束 了 。因 此 , 对 于 中 国 人 生 活 中 表 现 出 的 某 些 现 象 , 欧洲 人 并 不 觉 得 那 么 陌 生 , 因 此 也 不 像 面 对 一 个 完全 不 同 的 世 界 那 么 激 动 。“ 我 们 也 曾 经 是 这 样的 ,” 他 们 总 是 这 样 想 ,“ 而 且 我 们 永 远 也 不 会再 那 样 了 。”北 京 是 一 个 手 工 业 的 城 市 , 进 城 的 那 一 幕 已经 说 明 了 这 一 点 。 这 里 没 有 令 世 界 上 那 些 大 都 市窒 息 的 工 业 郊 区 , 也 没 有 高 高 的 烟 囱 , 或 者 是 伦敦 和 巴 黎 常 见 的 砖 头 建 成 的 低 矮 厂 房 。 正 像 工 业革 命 之 前 的 欧 洲 那 样 , 北 京 被 封 闭 在 带 有 城 池 的厚 重 的 城 墙 里 面 , 乡 村 则 位 于 城 外 。 走 出 北 京 ,立 刻 就 可 以 看 到 犁 过 的 田 地 和 四 处 散 落 的 农 舍 。郊 区 里 充 斥 着 乞 丐 , 手 艺 人 , 菜 农 。 那 里 到 处 尘土 飞 扬 , 恶 狗 横 行 , 破 烂 而 粗 野 。 到 处 是 衣 衫 褴褛 的 人 , 牧 羊 人 , 牲 口 圈 , 赶 骆 驼 的 人 , 士 兵 ,和 流 动 商 贩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北 京 是 一 个 慵 懒 的 城 市 , 只 不过 那 里 的 工 人 还 没 有 工 业 化 , 仍 旧 居 住 在 祖 传 的老 房 子 里 , 到 作 坊 里 去 做 工 。 只 要 在 街 上 转 一转 就 会 发 现 这 一 特 点 。 无 论 是 尽 头 耸 立 着 城 门 的塔 楼 的 大 街 , 还 是 各 个 街 区 中 弯 曲 的 小 巷 里 , 都布 满 了 完 全 是 十 八 世 纪 风 格 的 店 铺 。 那 里 不 只 进行 销 售 , 而 且 从 事 生 产 活 动 。 在 花 街 , 玉 街 , 首饰 悬 挂 在 橱 窗 的 后 面 。 在 店 铺 后 面 昏 暗 狭 窄 的 房子 里 , 年 轻 人 们 整 天 工 作 , 雕 刻 , 切 割 石 头 和 银器 。 常 见 的 店 铺 主 要 是 铜 器 和 白 镴 器 店 。 这 些 东西 都 在 自 家 店 铺 里 制 作 出 来 的 。从 那 里 经 过 的 时 候 , 我 们 发 现 北 京 的 店 铺 和欧 洲 的 一 样 , 也 是 按 照 它 们 的 种 类 排 列 的 , 同 样的 店 铺 或 者 都 坐 落 于 同 一 条 街 , 或 者 都 在 另 外 一条 街 上 。 也 就 是 说 一 条 街 上 都 是 首 饰 店 , 另 一 条街 上 则 都 是 布 店 , 下 一 条 又 都 是 铜 器 店 , 第 四 条街 都 是 瓷 器 , 以 此 类 推 。 狭 窄 的 街 道 上 , 每 家 店铺 里 都 回 响 着 无 线 电 和 留 声 机 中 传 出 的 单 调 而 刺耳 的 歌 声 。 店 铺 里 悬 挂 着 有 历 史 故 事 画 装 饰 的 旗帜 , 仿 佛 栽 种 在 一 条 大 街 两 旁 的 垂 柳 的 叶 子 。 在这 条 街 上 , 从 早 到 晚 行 人 和 人 力 车 熙 来 攘 往 。这 些 店 铺 仍 旧 保 持 从 前 的 样 子 。 美 国 人 还 没有 来 教 他 们 如 何 使 用 镀 铬 的 金 属 器 具 、 水 晶 、 空旷 的 空 间 , 漆 布 , 以 及 间 接 光 。 所 有 的 东 西 都排 列 在 玻 璃 下 面 的 柜 台 上 , 密 集 而 布 满 灰 尘 。 商品 不 论 新 旧 或 者 美 丑 , 都 混 杂 在 一 起 。 客 人 进 去的 时 候 , 老 板 和 三 、 四 个 售 货 员 会 站 起 身 , 小 心地 注 视 着 顾 客 的 每 一 个 举 动 。 在 商 店 里 , 柜 台 非常 拥 挤 , 人 只 能 勉 强 移 动 , 头 顶 几 乎 碰 到 了 天 花板 。 在 这 里 , 我 们 以 东 方 的 方 式 讨 价 还 价 了 很 长时 间 。 通 常 情 况 下 , 他 们 会 以 物 品 最 终 售 价 的 两倍 甚 至 是 三 倍 开 价 。 尽 管 如 此 , 他 们 开 出 的 最 高价 格 比 起 欧 洲 的 价 格 来 通 常 要 低 得 多 。那 些 流 动 小 贩 也 是 十 八 世 纪 风 格 的 。 卖 水 的人 清 晨 就 推 着 巨 大 而 且 晃 晃 悠 悠 的 手 推 车 走 街 串巷 , 车 上 装 着 很 多 木 制 的 容 器 。 他 不 叫 嚷 , 因 为手 推 车 那 滴 答 流 水 的 轮 子 颤 抖 的 尖 叫 声 , 足 以 通知 家 庭 妇 女 们 他 的 到 来 。 同 样 的 尖 叫 声 也 可 以 用来 驱 散 鬼 魂 , 每 个 中 国 人 认 为 有 鬼 魂 在 跟 随 着 他们 。 不 过 , 有 一 些 走 街 串 巷 的 小 贩 会 大 声 吆 喝 。他 们 的 肩 上 挑 着 一 根 竹 竿 , 竹 竿 的 两 端 各 悬 挂 着一 个 大 木 桶 。 我 不 知 道 他 们 在 卖 什 么 东 西 。 有 的时 候 , 他 们 会 在 那 些 灰 暗 , 而 且 象 蛇 一 样 弯 曲的 , 狭 窄 的 街 道 围 墙 之 间 现 身 , 靠 在 一 扇 钉 着 黄金 球 饰 的 红 色 大 门 上 , 一 只 手 凑 到 嘴 边 , 面 朝 天空 喊 出 他 们 疲 惫 、 抑 扬 顿 挫 、 哀 怨 的 祈 求 。 几 个肮 脏 的 孩 子 坐 在 门 槛 上 吃 惊 地 望 着 他 们 。 永 不 停息 的 风 吹 起 一 阵 灰 尘 , 把 他 们 包 裹 在 了 里 面 ,然 后 带 着 他 们 渐 渐 远 离 , 走 到 大 街 上 。 另 一 些人 用 手 推 车 艰 难 地 推 着 一 个 热 气 腾 腾 的 大 锅 , 炉子 里 的 火 熊 熊 地 燃 烧 。 锅 里 的 汤 晃 来 晃 去 , 洒 到了 外 面 。 那 个 可 怜 人 把 车 停 住 , 把 白 米 饭 盛 在 碗里 , 然 后 蹲 在 地 上 贪 婪 地 吃 起 来 。 又 有 一 些 人 收集 破 布 , 然 后 用 一 个 小 锤 在 一 块 核 桃 木 上 拍 打 。那 啪 嗒 的 声 音 从 远 处 就 能 听 得 见 。在 这 个 世 界 里 , 满 眼 都 是 穷 人 。 不 过 , 这 种贫 穷 是 和 善 、 天 真 、 人 性 化 的 , 而 不 是 工 业 化 背景 下 工 人 的 那 种 沮 丧 和 负 罪 的 悲 惨 。 北 京 大 街上 的 乞 丐 是 如 此 之 多 , 如 果 不 带 上 两 、 三 兜 铜 币最 好 不 要 出 门 。 铜 币 在 这 里 被 叫 做 铜 板 。 这 些 乞丐 在 街 道 的 各 个 角 落 里 伸 手 乞 讨 。 他 们 的 动 作 、表 情 、 言 语 都 可 能 令 人 发 笑 , 而 且 流 露 出 一 种 天真 的 狡 黠 。 我 说 “ 可 能 ”, 因 为 尽 管 他 们 采 用 一些 天 真 而 狡 黠 的 计 谋 , 但 人 们 还 是 不 能 不 被 如 此谦 卑 , 没 有 自 卫 能 力 , 而 且 如 此 彻 底 的 贫 穷 所 感动 。 强 壮 而 衣 衫 褴 褛 的 母 亲 们 脸 上 的 表 情 是 如 此疲 惫 、 衰 老 和 哀 怨 , 婴 儿 就 伏 在 她 半 裸 的 胸 前 。老 人 们 满 脸 皱 纹 而 且 有 点 疯 疯 癫 癫 , 男 人 们 骨 瘦如 柴 , 身 上 穿 着 过 于 肥 大 而 破 烂 的 衣 衫 。 所 有 这些 乞 丐 表 情 都 如 此 悲 壮 , 好 像 需 要 用 他 们 乞 讨 来的 那 很 少 的 几 个 钱 维 持 全 部 的 生 命 。 仿 佛 在 你 们前 面 或 者 后 面 经 过 的 任 何 人 都 不 会 去 怜 悯 他 们 。在 如 此 紧 急 的 状 况 面 前 , 拒 绝 是 非 常 困 难 的 , 而且 不 可 能 知 道 他 们 的 这 种 做 法 中 有 几 分 出 于 本 身极 端 的 需 要 , 又 有 几 分 出 于 他 们 的 职 业 。 他 们 气喘 嘘 嘘 地 跟 在 人 力 车 后 面 跑 , 大 声 地 乞 讨 , 固 执地 伸 着 手 , 得 到 钱 以 后 又 用 那 些 比 乞 讨 更 感 人 的古 老 而 人 性 化 的 表 演 来 致 谢 。 我 看 见 一 个 饥 饿 的妇 人 , 臂 弯 里 抱 着 一 个 刚 刚 几 个 月 大 的 婴 儿 。 在接 受 施 舍 的 时 候 , 她 会 深 深 鞠 躬 两 三 次 。 那 姿 势如 此 优 雅 , 如 同 某 个 古 老 宫 廷 里 的 屈 膝 礼 。不 过 , 北 京 十 八 世 纪 的 风 格 表 现 最 充 分 的 ,还 是 在 饭 店 里 。 与 美 洲 的 反 差 在 那 里 表 现 得 淋 漓尽 致 。 美 国 餐 馆 的 大 厅 宽 敞 拥 挤 , 而 且 要 和 不 认识 的 人 拼 桌 吃 饭 。 吃 的 是 盒 子 里 或 者 冰 柜 里 的 食品 。 因 为 要 赶 着 换 乘 公 共 汽 车 和 地 铁 的 空 当 匆 匆就 餐 。 北 京 的 情 况 完 全 相 反 , 而 且 是 正 确 的 。 大部 分 情 况 下 , 那 些 饭 店 位 于 两 层 的 房 子 里 。 人 们在 乞 丐 的 目 视 下 跨 过 门 槛 , 进 入 昏 暗 而 肮 脏 的 院子 , 那 里 放 满 了 破 旧 而 零 落 的 家 什 。 随 后 , 客 人20 21
进 入 某 个 惨 白 的 房 间 , 里 面 坐 着 一 些 在 玩 或 者 交谈 的 中 国 人 , 然 后 是 洗 碗 工 和 炉 灶 所 在 的 厨 房 。不 过 , 会 有 一 个 木 制 的 楼 梯 通 向 上 面 的 一 层 , 里面 有 一 些 走 廊 , 非 常 像 我 们 那 里 男 士 理 发 的 发廊 , 有 很 多 彼 此 独 立 , 用 木 头 和 布 料 隔 开 的 隔断 。 那 些 隔 断 有 一 个 白 色 粗 布 的 帘 子 , 门 框 上 还有 一 个 小 黑 板 或 者 牌 子 , 上 面 写 着 您 的 名 字 。 这样 , 假 如 您 在 等 待 什 么 客 人 , 后 者 就 不 会 因 为 寻找 您 而 破 坏 其 他 小 房 间 里 客 人 的 隐 私 。客 人 坐 下 来 以 后 , 帘 子 马 上 垂 下 , 服 务 生 拿来 一 个 小 盒 硬 墨 和 一 支 毛 笔 。 于 是 , 你 的 朋 友 拿起 毛 笔 , 从 上 向 下 用 那 些 复 杂 的 汉 字 迅 速 写 下 晚餐 要 点 的 菜 。 服 务 生 于 是 消 失 , 随 即 就 端 来 很 多的 大 小 菜 肴 。 即 使 是 最 简 朴 的 中 国 晚 餐 , 也 总 是丰 盛 而 充 足 。 同 时 , 从 其 它 的 隔 断 里 传 来 客 人 的笑 声 , 玩 猜 拳 的 人 叫 喊 着 划 拳 , 为 食 客 们 助 兴 的演 奏 者 带 来 的 尖 利 而 单 调 的 乐 曲 , 歌 手 们 唱 着 赞美 诗 , 服 务 生 大 声 对 着 楼 下 的 厨 子 叫 喊 , 告 诉 他们 所 点 的 菜 肴 。 在 中 国 餐 馆 里 , 上 演 着 一 首 私 密与 扰 人 的 声 音 与 喧 嚣 交 织 的 交 响 曲 。中 国 人 喜 欢 美 食 , 并 且 要 有 好 的 陪 伴 。 另外 , 由 于 他 们 谨 慎 而 又 不 善 社 交 , 所 以 希 望 与 自己 的 女 人 和 朋 友 单 独 相 处 。 因 此 也 就 没 有 公 用 的大 厅 。 当 主 人 在 吃 饭 和 娱 乐 的 时 候 , 拉 车 的 坐 在车 辕 上 , 在 寒 冷 中 等 待 几 个 小 时 ; 或 者 会 在 温 暖的 厨 房 里 闲 聊 。 这 些 仆 人 在 说 些 什 么 呢 ? 通 常 是在 说 他 们 的 主 人 , 他 们 怎 么 吃 , 怎 么 睡 , 怎 么说 , 怎 么 爱 , 怎 么 花 钱 。 某 些 消 息 会 通 过 秘 密 途径 传 播 , 传 到 意 想 不 到 或 者 遥 远 的 地 方 。 所 以 ,在 上 海 会 很 快 得 知 古 老 的 首 都 发 生 的 事 情 。晚 上 的 北 京 昏 暗 , 沉 寂 , 没 有 生 气 , 就 像 威尼 斯 在 沉 寂 的 季 节 里 一 样 。 灯 光 昏 暗 的 街 道 上 行人 稀 少 。 在 阴 影 里 , 人 力 车 的 灯 笼 摇 晃 向 前 。沿 着 掩 藏 在 黑 暗 中 的 厚 重 的 城 墙 , 只 能 听 到 苦 力们 光 着 的 脚 发 出 的 轻 轻 的 、 幽 灵 般 的 脚 步 声 。 他们 不 知 疲 倦 地 拉 着 车 , 车 上 坐 着 裹 在 裘 皮 大 衣 和被 子 里 的 主 人 。 人 力 车 高 大 的 轮 子 沉 默 而 满 是 泥泞 , 又 黑 又 亮 如 同 乌 木 。 车 上 配 有 手 柄 、 灯 笼 和铜 质 的 车 闸 , 装 饰 而 且 加 工 得 如 同 一 个 小 小 的 马车 。 车 夫 移 动 着 两 条 腿 在 泥 泞 中 行 走 , 令 人 想 到贡 多 拉 船 。夜 间 , 人 力 车 黑 色 的 轮 廓 与 那 些 车 灯 相 比 显得 奇 怪 而 古 老 , 令 人 回 想 起 具 有 魔 力 的 灯 笼 的 影子 , 以 及 十 八 世 纪 的 剪 影 。 这 里 还 有 轿 子 , 以及 另 外 一 种 干 脆 而 合 理 的 非 人 行 为 , 一 种 古 老 制度 : 妇 人 们 会 让 那 些 气 喘 吁 吁 而 且 筋 疲 力 尽 的 穷人 抬 她 们 走 上 好 几 公 里 。 而 后 者 却 仍 旧 保 持 着 古代 那 种 耐 心 、 愉 快 而 善 意 的 态 度 。如 同 每 个 尚 未 经 历 工 业 化 的 城 市 一 样 , 北 京人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 白 天 光 彩 美 丽 , 夜 晚 了无 生 机 。 在 美 国 化 的 上 海 , 白 天 令 人 恐 惧 , 夜 晚则 借 助 那 些 黑 暗 中 闪 烁 的 霓 虹 灯 呈 现 出 一 种 虚 假的 美 丽 。《 人 民 报 》,1937 年 7 月 1 日IL CONFORMISTAPrimo capitoloNel tempo della sua fanciullezza, Marcello eraaffascinato dagli oggetti come una gazza. Forseperché, a casa, più per indifferenza che per austerità,i genitori non avevano mai pensato a soddisfare ilsuo istinto di proprietà; o, forse, perché altri istintipiù profondi e ancora oscuri si mascheravano in luida avidità; egli era continuamente assalito da vogliefuriose per gli oggetti più diversi. Una matita conil puntale di gomma, un libro illustrato, una fionda,un regolo, un calamaio portatile di ebanite, qualsiasinonnulla sollevava il suo animo, prima ad undesiderio intenso e irragionevole della cosa agognatae poi, una volta la cosa entrata in suo possesso, aduno stupefatto, stregato, insaziabile compiacimento.Marcello aveva in casa una camera tutta per luidove dormiva e studiava. Qui, tutti gli oggetti sparsisulla tavola o chiusi nei cassetti, avevano per lui ilcarattere di cose ancora sacre o appena sconsacratesecondo che il loro acquisto fosse recente o antico.Non erano, insomma, oggetti simili agli altri che sitrovavano in casa, bensì frantumi di un’esperienzada farsi o già fatta, tutta la carica di passione e dioscurità. Marcello si rendeva conto, a modo suo, diquesto carattere singolare della proprietà e, mentrene traeva un godimento ineffabile al tempo stessone soffriva, come di una colpa che si rinnovavacontinuamente e non lasciava neppure il tempo diprovarne rimorso.Tra tutti gli oggetti, però, quelli che lo attraevanodi più, forse perché gli erano proibiti, erano le armi.Non già le armi finte con cui giocano i bambini, ifucili di latta, le rivoltelle a detonazione, i pugnalidi legno, bensì le armi vere, nelle quali l’idea dellaminaccia, del pericolo e della morte non è affidataad una mera somiglianza di forme, bensì è ragioneprima e ultima della loro esistenza. Con la rivoltelladei bambini si giocava alla morte senza alcunapossibilità di provocarla davvero, ma con le rivoltelledei grandi la morte era non soltanto possibile maincombente, come una tentazione frenata dalla solaprudenza. Marcello aveva avuto qualche volta trale mani queste armi vere, un fucile da caccia incampagna, la vecchia rivoltella del padre che costui,un giorno, gli aveva mostrato in un cassetto, e, ognivolta, aveva provato un brivido di comunicazione,come se la sua mano avesse finalmente trovato unnaturale prolungamento nell’impugnatura dell’arma.Marcello aveva amici numerosi tra i bambinidel quartiere, e ben presto si era accorto che ilsuo gusto per le armi aveva origini più profonde eoscure delle loro innocenti infatuazioni militari. Essigiocavano ai soldati fingendo spietatezza e ferociama in realtà perseguendo il gioco per amore de1gioco e scimmiottando quei crudeli atteggiamentisenza alcuna vera partecipazione; in lui, invece,avveniva il contrario: era la spietatezza e la ferociache cercavano uno sfogo nel gioco dei soldati e,in mancanza del gioco in altri passatempi tuttiintonati al gusto della distruzione e della morte.In quel tempo Marcello era crudele senza rimorsoné vergogna, del tutto naturalmente, perché dallacrudeltà gli venivano i soli piaceri che non glisembrassero insipidi e questa crudeltà era ancoraabbastanza puerile per non destare sospetti in luistesso o negli altri. Gli accadeva, per esempio, discendere nel giardino, ad un’ora calda, in quell’iniziod’estate. Era un giardino angusto ma folto nel quale,in gran disordine, crescevano numerose piante ealberi abbandonati da anni al loro naturale rigoglio.Marcello scendeva nel giardino armato di un giuncosottile e flessibile che aveva strappato in soffitta daun vecchio battipanni; e per un poco si aggiravatra le ombre scherzose degli alberi e i raggi ardentidel sole, per i vialetti ghiaiati, osservando le piante.Sentiva che i propri occhi scintillavano, che tutto ilcorpo gli si apriva ad una sensazione di benessereche pareva confondersi con la generale vitalità delgiardino rigoglioso e pieno di luce, e si sentivafelice. Ma di una felicità aggressiva e crudele, quasivogliosa di misurarsi al paragone dell’infelicitàaltrui. Come vedeva nel mezzo di un’aiuola unbel cespo di margherite gremito di fiori bianchi egialli, oppure un tulipano dalla corolla rossa rittasul gambo verde, oppure ancora una pianta di calledagli alti fiori bianchi e carnosi, Marcello vibrava unsol colpo col giunco, facendolo fischiare per l’ariacome una spada. I1 giunco tagliava di netto fiori efoglie che cadevano pulitamente a terra presso lapianta, lasciando ritti gli steli decapitati. Provavacosì facendo, un raddoppiamento di vitalità, e quasiil compiacimento delizioso che ispira lo sfogo diun’energia troppo a lungo compressa; ma al tempostesso non sapeva che sentimento esatto di potenzae di giustizia. Come se quelle piante fossero statecolpevoli e lui le avesse punite e avesse insiemesentito che era in suo potere punirle. Ma il carattereproibito e colpevole di questo passatempo non gliera del tutto ignoto. Ogni tanto, quasi suo malgrado,rivolgeva sguardi furtivi alla villa, timoroso che lamadre dalla finestra del salotto o la cuoca da quelladella cucina potessero osservarlo. E si rendeva22 23
conto che temeva non tanto il rimprovero quantola semplice testimonianza di atti che lui stessoavvertiva anormali e misteriosamente intrisi dicolpevolezza.Dai fiori e dalle piante agli animali, il passaggiofu insensibile, come lo è in natura. Marcello nonavrebbe potuto dire quando si accorse che quellostesso piacere che provava nello schiantare le piantee nel decapitare i fiori, gli si rivelava più intensoe più profondo nell’infliggere le stesse violenzeagli animali. Forse fu soltanto il caso che lo spinsesu questa via, un colpo di giunco che, invece distorpiare un arbusto, colpì sulla schiena una lucertolaaddormentata su un ramo o forse un principio dinoia e di sazietà che gli suggerì di cercare nuovamateria sulla quale esercitare la crudeltà ancorainconsapevole. Comunque, un pomeriggio silenziosoche tutti in casa dormivano, Marcello si ritrovò adun tratto, come colpito da una folgore di rimorsoe di vergogna, davanti ad una strage di lucertole.Erano cinque o sei lucertole che con varii modi erariuscito a scovare sui rami degli alberi o sulle pietredel muro di cinta, fulminandole con un solo colpodi giunco proprio nel momento in cui, insospettitedalla sua presenza immobile, cercavano di fuggireverso qualche riparo. Come fosse giunto a questonon avrebbe saputo dire o meglio preferiva nonricordarlo, ma ormai tutto era finito e non restavache il sole ardente e impuro sui corpi sanguinolentie lordi di polvere delle lucertole morte. Egli stavain piedi davanti al marciapiede di cemento sul qualegiacevano le lucertole, il giunco stretto in pugno; esentiva ancora per il corpo e sul viso l’eccitazioneche l’aveva invaso durante la strage, ma non piùpiacevolmente fervida, come era stata allora, bensìgià trascolorante nel rimorso e nella vergogna. Sirendeva conto, inoltre, che al solito sentimentodi crudeltà e di potenza si era aggiunto questavolta un turbamento particolare, nuovo per lui,inspiegabilmente fisico; e, insieme con la vergognae il rimorso, provava un confuso senso di spavento.Come a scoprire in se stesso un carattere del tuttoanormale, di cui dovesse vergognarsi, che dovessemantenere segreto per non vergognarsi oltre che conse stesso anche con gli altri e che, di conseguenza,lo avrebbe per sempre separato dalla società deicoetanei. Non c’era dubbio, egli era diverso dairagazzi della sua età che, loro, non si dedicavanoné insieme né soli a simili passatempi; e per giuntadiverso in maniera definitiva. Perché le lucertoleerano morte, su questo non c’era dubbio e questamorte e gli atti da lui compiuti, crudeli e folli, perprovocarla, erano irreperibili. Egli era, insomma,quegli atti, come in passato era stato altri atti deltutto innocenti e normali.Quel giorno, a conferma di questa scoperta cosìnuova e così dolorosa della propria anormalità,Marcello volle confrontarsi con un suo piccoloamico, Roberto, che abitava nel villino attiguo alsuo. Verso il crepuscolo, Roberto, dopo aver finitodi studiare, scendeva in giardino; e fino all’oradella cena, per mutuo consenso delle famiglie, idue ragazzi giocavano insieme, ora nel giardinodell’uno ora in quello dell’altro. Marcello aspettòquel momento con impazienza, per tutto il lungopomeriggio silenzioso, solo in camera sua, distesosul letto. I genitori erano usciti, in casa non c’erache la cuoca di cui, ogni tanto, udiva la voce checantarellava sommessamente nella cucina, alpianterreno. Di solito, il pomeriggio, studiava ogiocava, solo nella propria camera; ma quel giornoné gli studi né il gioco lo attraevano; si sentivaincapace di fare quel che sia e al tempo stessofuriosamente insofferente dell’ozio: lo paralizzavanoe, insieme, lo spazientivano lo sgomento dellascoperta che gli pareva di aver fatto e la speranzache questo sgomento venisse dissipato dal prossimoincontro con Roberto.Se Roberto gli avesse detto che anche luiuccideva le lucertole e che gli piaceva ucciderle enon vedeva alcun male nell’ucciderle, gli sembravache ogni senso di anormalità sarebbe scomparso eche egli avrebbe potuto guardare con indifferenzaalla strage delle lucertole come ad un incidenteprivo di significato e senza conseguenze. Nonavrebbe saputo dire perché attribuisse tanta autoritàa Roberto; oscuramente pensava che se ancheRoberto faceva di queste cose e in quel modo econ quei sentimenti, questo voleva dire che tutti lefacevano; e quel che tutti facevano era normale ossiabene. Queste riflessioni non erano, d’altronde, benchiare nella mente di Marcello e gli si presentavanopiuttosto come sentimenti e impulsi profondi checome pensieri precisi. Ma di un fatto gli pareva diessere sicuro: dalla risposta di Roberto dipendeva latranquillità del suo animo.In questa speranza e in questo sgomento, aspettòcon impazienza l’ora del crepuscolo. Stava quasiper assopirsi, quando, dal giardino, gli giunse unlungo fischio modulato: era il segnale convenutocon il quale Roberto avvertiva della sua presenza.Marcello si levò dal letto e, senza accender luci,nella penombra del tramonto, uscì dalla camera,discese la scala e si affacciò al giardino.Nella luce bassa del crepuscolo estivo gli alberistavano immobili e aggrondati; sotto i rami, l’ombraappariva già notturna. Esalazioni floreali, odor dipolvere, irradiazioni solari emananti dalla terrariscaldata stagnavano per l’aria immobile e densa.La cancellata che divideva il giardino di Marcello daquello di Roberto scompariva completamente sottoun’edera gigantesca, folta e profonda, simile ad unmuro di foglie sovrapposte. Marcello andò dritto adun angolo in fondo al giardino dove l’edera e l’ombraerano più fitte, salì in piedi su un grosso sasso e conun solo gesto deliberato scostò tutta una massa dirampicante. Era stato lui ad inventare quella speciedi sportello nel fogliame dell’edera, per un sensodi gioco segreto e avventuroso. Spostata l’edera,apparvero le sbarre della cancellata e, tra le sbarre, ilviso fine e pallido, sotto i capelli biondi, dell’amicoRoberto. Marcello si alzò in punta di piedi sul sassoe domandò: “Nessuno ci ha visti?”Era la formula d’inizio di questo loro gioco,Roberto rispose come recitando una lezione: “No,nessuno...” E poi dopo un momento: “Hai studiato,tu?”Parlava sussurrando altro procedimentoconvenuto. Sussurrando anche lui, Marcello rispose:“No, oggi non ho studiato... non avevo voglia... diròalla maestra che mi sentivo male.”“Io ho scritto il compito di italiano,” mormoròRoberto, “e ho fatto anche uno dei problemi diaritmetica... me ne resta un altro... perché non haistudiato?”Era la domanda che Marcello si aspettava: “Nonho studiato”, rispose, “perché ho dato la cacciaalle lucertole.” Sperava che Roberto gli dicesse:“Ah davvero... anch’io qualche volta do la cacciaalle lucertole,” o qualche cosa di simile. Ma il visodi Roberto non esprimeva alcuna complicità eneppure curiosità. Soggiunse con sforzo, cercandodi dissimulate il proprio imbarazzo: “Le ho uccisetutte.”Roberto prudentemente domandò: “Quante?”“Sette in tutto,” rispose Marcello. E poi,sforzandosi ad una vanteria tecnica e informativa:“Stavano sui rami degli alberi e sui sassi... io hoaspettato che si muovessero e poi le ho colte alvolo... con un solo colpo di questo giunco... un colpoper una.” Fece una smorfia di compiacimento emostrò il giunco a Roberto.Vide l’altro guardarlo con una curiosità nondisgiunta da una specie di meraviglia: “Perché le haiammazzate?”“Così,” egli esitò, stava sul punto di dire:“perché mi faceva piacere,” poi non sapeva neppurlui perché, si trattenne e rispose: “Perché sonodannose... non lo sai che le lucertole sono dannose?”“No,” disse Roberto, “non lo sapevo... dannose ache cosa?”“Mangiano l’uva,” disse Marcello, “l’altr’anno,in campagna, hanno mangiato tutta l’uva dellapergola.”“Ma qui non c’è uva.”“E poi,” egli continuò senza curarsi di raccoglierel’obbiezione, “sono cattive... una, come mi ha visto,invece di scappare, mi è venuta addosso con labocca spalancata... se non l’avessi fermata a tempo,mi saltava addosso...” Egli tacque un momento poi,più confidenzialmente, soggiunse: “Tu non ne haimai ammazzate?”Roberto scosse il capo e rispose: “No, mai.”Quindi abbassando gli occhi, compunto in viso:“Dicono che non bisogna far male agli animali.”“Chi lo dice?”“La mamma.”“Dicono tante cose...” disse Marcello sempremeno sicuro di sé, “ma tu prova, stupido... ti assicuroche è divertente.”“No, non proverò.”“E perché?”“Perché è male.”Così non c’era niente da fare, pensò Marcellocon disappunto. Gli venne un impeto d’ira control’amico che, senza rendersene conto, lo inchiodavaalla propria anormalità. Riuscì tuttavia a dominarsie propose: “Guarda, domani rifaccio la caccia allelucertole… se tu vieni a dar la caccia con me, tiregalo il mazzo delle carte del Mercante in Fiera.”Sapeva che per Roberto l’offerta era tentante:aveva più volte espresso il desiderio di possederequel mazzo. E infatti Roberto, come illuminato dauna subita ispirazione, rispose: “Io vengo a cacciama a un patto: che le prendiamo vive e poi lechiudiamo in una scatolina e poi le lasciamo libere…e tu mi dai il mazzo.”“Questo no,” disse Marcello, “il bello sta proprionel colpirle con questo giunco… scommetto che nonne sei capace.”L’altro non disse nulla. Marcello proseguì: “Alloravieni... siamo intesi… ma cercati anche tu ungiunco.”“No,” disse Roberto con ostinazione, “non verrò.”“Ma perché? È nuovo quel mazzo.”“No, è inutile,” disse Roberto, “io le lucertole nonle ammazzo… neppure se,” egli esitò cercando unoggetto di un valore proporzionato, “neppure se midai la tua pistola.”Marcello comprese che non c’era niente da faree tutto ad un tratto, si lasciò andare all’ira che glibolliva da qualche momento nel petto: “Non vuoi24 25
perché sei un vigliacco,” disse, “perché hai paura.”“Ma paura di che? Mi fai proprio ridere.”“Hai paura,” ripetè Marcello adirato, “sei unconiglio… un vero coniglio.” Improvvisamente,sporse una mano attraverso le sbarre della cancellatae afferrò l’amico per un orecchio. Roberto avevaorecchie sporgenti, rosse, e non era la prima voltache Marcello gliele afferrava; ma mai con tantarabbia e con un desiderio così preciso di fargli male.“Confessa che sei un coniglio.”“No, lasciami,” cominciò a lamentarsi l’altrotorcendosi, “ahi... ahi.”“Confessa che sei un coniglio.”“No... lasciami.”“Confessa che sei un coniglio.”Nella sua mano l’orecchio di Roberto bruciava,caldo e sudato; lacrime apparvero negli occhi azzurridel tormentato. Egli balbettò: “Sì, va bene, sono unconiglio,” e Marcello lo lasciò subito. Roberto saltògiù dalla cancellata e correndo via gridò “Non sonoun coniglio… mentre lo dicevo ho pensato: non sonoun coniglio… te l’ho fatta.” Scomparve, e la suavoce, lacrimosa e beffarda, si perse lontano, oltre iboschetti del giardino attiguo.Gli restò da questo dialogo un senso di malessereprofondo. Roberto, insieme con la sua solidarietà,gli aveva negato l’assoluzione che egli cercava eche gli sembrava legata a quella solidarietà. Così erarespinto nell’anormalità, ma non senza aver primamostrato a Roberto quanto gli premesse uscirne,ed essersi lasciato andare, come si rendeva contoperfettamente, alla menzogna e alla violenza. Adessoalla vergogna e al rimorso di aver ucciso le lucertole,si aggiungeva la vergogna e il rimorso di avermentito a Roberto circa i motivi che lo spingevanoa chiedergli la sua complicità e di essersi tradito conquel movimento d’ira, quando l’aveva afferrato perl’orecchio. Alla prima colpa se ne aggiungeva unaseconda; e lui non poteva disfarsi in alcun modo nédell’una né dell’altra.Ogni tanto, tra queste riflessioni amare, riandavacon la memoria alla strage delle lucertole, quasisperando di ritrovarla depurata di ogni rimorso,un semplice fatto come un altro. Ma subito siaccorgeva che avrebbe voluto che le lucertole nonfossero mai morte; e, insieme, vivo e, forse non deltutto spiacevole ma, appunto per questo, tanto piùripugnante, gli tornava quel senso di eccitazione edi turbamento fisico che aveva provato mentre davala caccia; tanto forte da fargli persino dubitare cheavrebbe resistito nei giorni prossimi alla tentazionedi ripetere la strage. Questo pensiero lo atterri:così non soltanto egli era anormale, ma, nonché disopprimere l’anormalità, non era neanche capacedi controllarla. Era in quel momento in camera sua,seduto al tavolino, davanti un libro aperto, in attesadella cena. Impetuosamente si alzò, andò a letto, egettandosi in ginocchio sullo scendiletto, come erasolito fare quando recitava le preghiere, disse ad altavoce, giungendo le mani, con accento che gli parvesincero: “Giuro davanti a Dio che non toccherò maipiù né i fiori, né le piante, né le lucertole.”Tuttavia, il bisogno di assoluzione che l’avevaspinto a ricercare la complicità di Roberto sussisteva,cambiato adesso nel suo contrario, in un bisogno dicondanna. Roberto, mentre avrebbe potuto salvarlodal rimorso schierandosi al suo fianco, non avevaabbastanza autorità per confermare la fondatezzadi questo rimorso e metter ordine nella confusionedella sua mente con un verdetto inappellabile. Eraun ragazzo come lui, accettabile come complice mainadeguato come giudice. Ma Roberto, rifiutando lasua proposta aveva addotto, a sostegno della propriaripugnanza, l’autorità materna. Marcello pensò che sisarebbe appellato anche lui a sua madre. Lei soltantopoteva condannarlo o assolverlo e, comunque, farrientrare il suo atto in un ordine purchessia. Marcelloche conosceva sua madre, prendendo questadecisione, ragionava in astratto, come riferendosiad una madre ideale, quale avrebbe dovuto essere enon qual era. In realtà, dubitava del buon esito delsuo appello. Ma tant’era, egli non aveva che quellamadre e d’altronde il suo impulso a rivolgersi a leiera più forte di qualsiasi dubbio.Marcello aspettò il momento in cui la madre,dopo che si era coricato, veniva in camera a darglila buonanotte. Era questo uno dei pochi momentiche gli riusciva di vederla da solo a solo: il più dellevolte, durante i pasti o nelle rare passeggiate coigenitori, il padre era sempre presente. Marcello,sebbene non avesse, d’istinto, molta fiducia nellamadre, l’amava, e forse, anche più che amarla,l’ammirava in maniera perplessa e invaghita, come siammira una sorella maggiore dalle abitudini singolarie dal carattere estroso. La madre di Marcello, che siera sposata giovanissima, era rimasta moralmentee anche fisicamente una fanciulla; inoltre, pur nonavendo alcuna confidenza con il figlio di cui sioccupava pochissimo a causa dei numerosi impegnimondani, ella non aveva mal separato la propria vitada quella di lui. Così Marcello era cresciuto in uncontinuo tumulto di entrate ed uscite precipitose,di vestiti provati e gettati via, di interminabiliquanto frivole conversazioni al telefono, di bizzecon sarti e fornitori, di dispute con la cameriera, dicontinue variazioni di umore per i più futili motivi.Marcello poteva entrare in camera di sua madre inqualsiasi momento, spettatore curioso e ignorato diun’intimità in cui non aveva alcun posto. Qualchevolta la madre, come riscuotendosi dall’inerzia perun improvviso rimorso, decideva di dedicarsi alfiglio e se lo portava dietro da una sarta o da unamodista. In queste occasioni, costretto a passarelunghe ore seduto sopra uno sgabello, mentre lamadre provava cappelli e vestiti, Marcello quasirimpiangeva la solita turbinosa indifferenza.Quella sera, come comprese subito, la madreaveva più fretta del solito; e infatti, prima ancorache Marcello avesse avuto il tempo di sormontare lapropria timidezza, ella gli voltò le spalle avviandosiattraverso la camera buia, alla porta rimastasocchiusa. Ma Marcello non intendeva aspettareancor un giorno il giudizio di cui aveva bisogno.Tirandosi a sedere sul letto, chiamò con voce forte:“Mamma.”La vide voltarsi dalla soglia, con gesto quasiinfastidito. “Che c’è Marcello?” ella domandò, poi,avvicinandosi di nuovo al letto.Ora stava in piedi presso di lui, in controluce,bianca e esile nel nero abito scollato. Il viso finee pallido incorniciato di capelli neri era in ombra,non tanto però che Marcello non vi distinguesseun’espressione scontenta, frettolosa e impaziente.Tuttavia, trasportato dal suo impulso, egli annunziò:“Mamma, debbo dirti una cosa.”“Sì Marcello, ma fa presto… la mamma deveandar via... il papà sta aspettando.” Intanto con ledue mani armeggiava sulla nuca, intorno il fermagliodella collana.Marcello voleva rivelare alla madre la strage dellelucertole e domandarle se aveva fatto male. Mala fretta materna gli fece cambiar idea. O meglio,modificare la frase che aveva preparato in mente.Le lucertole gli parvero ad un tratto animali troppopiccoli e insignificanti per poter fermare l’attenzionedi una persona così distratta. Lì per lì, non sapevaneppure lui perché, inventò una bugia ingrandendoil proprio delitto. Sperava con l’enormità della colpadi riuscire a colpire la sensibilità materna che, inmaniera oscura, indovinava ottusa e inerte. Dissecon sicurezza che lo meravigliò: “Mamma, ho uccisoil gatto.”In quel momento la madre era riuscita finalmentea fare incontrare le due parti del fermaglio. Le maniriunite sulla nuca, il mento inchiodato sul petto,ella guardava a terra e ogni tanto, per l’impazienza,batteva il tacco sul pavimento. “Ah, sì,” dissecon voce incomprensiva, come svuotata di ogniattenzione dallo sforzo che stava facendo. Marcelloribadì malsicuro: “L’ho ucciso con la fionda.”Vide la madre scuotere il capo con disappuntoe poi togliere le mani dalla nuca, tenendo in unala collana che non era riuscita a chiudere. “Questomaledetto fermaglio,” ella proferì con rabbia.“Marcello... da bravo… aiutami a mettere lacollana.” Ella sedette sul letto, di sbieco, le spalleal figlio, soggiungendo con impazienza: “Ma sta’attento a far scattare il fermaglio… altrimenti siaprirà di nuovo.”Pur parlando, gli presentava le spalle magre,nude fino alle reni, bianche come la carta nella luceche veniva dalla porta. Le mani sottili dalle unghieaguzze e scarlatte tenevano il monile sospeso sullanuca delicata, ombreggiata di peluria ricciuta.Marcello si disse che, una volta attaccata la collana,ella l’avrebbe ascoltato con maggiore pazienza;sporgendosi, prese i due capi e li saldò con un soloscatto. Ma la madre si levò subito in piedi e dissechinandosi a sfiorargli il viso con un bacio: “Grazie...ora dormi… buonanotte.” Prim’ancora che Marcelloavesse potuto trattenerla con un gesto o con ungrido, era già scomparsa.II giorno dopo il tempo era caldo e rannuvolato.Marcello, dopo aver mangiato in silenzio tra i due26 27
genitori silenziosi scivolò di soppiatto giù dallaseggiola e, per la portafinestra, uscì nel giardino.Come il solito, la digestione provocava in lui untorbido malessere tutto mischiato di turgida eriflessiva sensualità. Camminando piano, quasi inpunta di piedi, sulla ghiaia scricchiolante, all’ombradegli alberi fervida di insetti, andò fino al cancelloe guardò di fuori. Gli apparve la strada così nota,in leggera pendenza, fiancheggiata da due filedi alberi del pepe, di un verde piumoso e quasilattescente, deserta a quell’ora e stranamente buiaper via delle basse nuvole nere che ingombravanoil cielo. Dirimpetto, si intravvedevano altri cancelli,altri giardini, altre ville simili alla sua. Dopo averosservato con attenzione la strada, Marcello si staccòdal cancello, trasse di tasca la fionda e si chinòverso terra. Tra la ghiaia minuta, erano frammistialcuni ciottoli bianchi più grossi. Marcello ne preseuno della grandezza di una noce, lo inserì nel discodi cuoio della fionda e prese a passeggiare lungoil muro che separava il suo giardino da quello diRoberto. La sua idea, o meglio il suo sentimento, erache egli si trovava in stato di guerra con Roberto eche doveva sorvegliare con la massima attenzionel’edera che ricopriva il muro di cinta e al minimomovimento far fuoco, ossia scagliare il sasso chestringeva nella fionda. Era un gioco in cui esprimevainsieme il rancore contro Roberto che non avevavoluto essergli complice nella strage delle lucertolee l’istinto belluino e crudele che l’aveva spinto allastrage medesima. Naturalmente Marcello sapevabenissimo che Roberto, solito a dormire a quell’ora,non lo spiava da dietro il fogliame dell’edera;e tuttavia, pur sapendolo, agiva con serietà econseguenza, come se fosse stato sicuro che inveceRoberto ci fosse. L’edera, vecchia e gigantesca,saliva fino alle punte delle picche della cancellata,e le foglie, sovrapposte le une alle altre, grandi,nere, polverose, simili a volanti di trina su un pettotranquillo di donna, stavano ferme e flosce nell’ariapesante e senza vento. Un paio di volte, gli parve cheun leggerissimo fremito facesse palpitare il fogliameo meglio inventò a se stesso di aver veduto questofremito e tosto, con soddisfazione intensa, scagliò ilsasso nel fitto dell’edera.Subito dopo il colpo si chinava in fretta,raccoglieva un altro sasso e si rimetteva in posizionedi combattimento, le gambe larghe, le bracciastese in avanti, la fionda pronta a scattare: non sipoteva mai sapere, Roberto poteva essere dietro lefoglie, in atto di prender la mira contro di lui, con ilvantaggio di essere nascosto, mentre lui, invece, eracompletamente allo scoperto. Così, in questo gioco,giunse in fondo al giardino, là dove aveva ritagliatolo sportello nel fogliame dell’edera. Qui si fermò,guardando con attenzione al muro di cinta. Nellasua fantasia, la casa era un castello, la cancellatanascosta dal rampicante le mura fortificate, eil pertugio una breccia pericolosa e facilmentevalicabile. Allora, improvvisamente e questa voltasenza possibilità di dubbio, vide le foglie muoversida destra a sinistra, tremando e oscillando. Sì, neera certo, le foglie si muovevano e qualcuno dovevapur farle muovere. Tutto in un sol momento pensòche Roberto non c’era, che era un gioco e che,visto che era un gioco, lui poteva tirare il sasso; eal tempo stesso che Roberto c’era e lui non dovevatirare il sasso se non voleva ammazzarlo. Poi, consubitanea e spensierata decisione, tese gli elastici escagliò il sasso nel folto delle foglie. Non contento,si chinò, febbrilmente incastrò un altro sasso nellafionda, lo tirò, ne prese un terzo, tirò anche quello.Ormai aveva messo da parte scrupoli e timori enon gli importava più che Roberto ci fosse o nonci fosse: provava soltanto un senso di eccitazioneilare e bellicoso. Finalmente, ansimante, dopo averben bene sforacchiato il fogliame, lasciò cadere lafionda in terra e si inerpicò fino al muro di cinta.Come aveva preveduto e sperato, Roberto non c’era.Ma le sbarre della cancellata erano molto larghee permettevano di sporgere il capo nel giardinoattiguo. Punto da non sapeva che curiosità, siaffacciò e guardò in basso.Dalla parte del giardino di Roberto, non c’erarampicante, bensì un’aiuola coltivata a iris checorreva tra il muro e il vialetto ghiaiato. Allora,proprio sotto i suoi occhi tra il muro e la fila di irisbianchi e violetti, disteso su un fianco, Marcellovide un grosso gatto grigio. Un terrore insensato glitagliò il respiro poichè notò la posizione innaturaledella bestia: coricata di lato, con le zampe allungatee rilasciate, il muso abbandonato sul terriccio. I1pelo, folto e di un grigio azzurrognolo, apparivaleggermente irto e arruffato e insieme inerte, comele piume di certi uccelli morti che aveva osservatotempo addietro sul tavolo di marmo della cucina.Ora il terrore cresceva: balzò a terra, sfilò da unroseto la canna di sostegno, tornò ad inerpicarsi,e, sporgendo il braccio tra le sbarre, si ingegnò dipungere il fianco al gatto con la punta terrosa dellacanna. Ma il gatto non si mosse, tutto ad un trattogli iris dagli altri gambi verdi, dalle corolle bianchee violette inclinate intorno il grigio corpo immobile,gli parvero mortuarii, come tanti fiori disposti da unamano pietosa intorno un cadavere. Gettò via la cannae, senza curarsi di rimettere a posto l’edera, saltò aterra.Si sentiva in preda a diversi terrori e il suo primoimpulso fu di correre a chiudersi in un armadio,in un ripostiglio, dovunque, insomma, ci fossebuio e clausura, per sfuggire a se stesso. Provavaterrore prima di tutto per aver ucciso il gatto e poi,forse in misura maggiore, per avere annunziatoquest’uccisione alla madre, la sera prima: segnoindubbio che, in un modo misterioso e fatale, erapredestinato a compiere atti di crudeltà e di morte.Ma il terrore che destavano in lui la morte del gattoe la premonizione significativa di questa morte, eradi gran lunga superato dal terrore che gli ispiraval’idea che uccidendo il gatto, in realtà, aveva avutointenzione di uccidere Roberto. Soltanto il casoaveva voluto che il gatto fosse morto in luogodell’amico. Un caso, però, non privo di senso; chenon si poteva negare che ci fosse stata progressionedai fiori alle lucertole, dalle lucertole al gatto edal gatto all’omicidio di Roberto pensato e volutoseppure non eseguito, ma tuttora eseguibile e,forse, inevitabile. Così egli era un anormale, nonpoteva fare a meno di pensare, o meglio di sentire,con una viva, fisica consapevolezza di questaanormalità, un anormale segnato da un destinosolitario e minaccioso e ormai avviato per una stradasanguigna sulla quale nessuna forza umana avrebbepotuto fermarlo. Tra questi pensieri si aggiravafreneticamente nel breve spazio tra la casa e ilcancello levando ogni tanto gli occhi alle finestredel villino quasi con desiderio di vedervi apparirela figura della sua frivola e stordita madre: maormai ella non poteva più far nulla per lui, se pureera mai stata capace di fare qualche cosa. Quindi,con subitanea speranza, corse di nuovo in fondoal giardino, si arrampicò fino al muro e si affacciòtra le sbarre della cancellata. Quasi si illudeva diritrovare vuoto il luogo dove prima aveva veduto ilgatto esanime. Invece il gatto non se ne era andato,era sempre là, grigio e immobile nella coronafuneralesca degli iris bianchi e violetti. E la morteera accusata, con un senso macabro di carogna inputrefazione, da una nera striscia di formiche chepartendo dal viale risalivano l’aiuola fino al muso,anzi agli occhi della bestia. Guardava e, tutto adun tratto, quasi per sovraimpressione, gli parve divedere in luogo del gatto, Roberto, anche lui distesotra gli iris, anche lui esanime, con le formiche cheandavano e venivano dagli occhi spenti e dallabocca semiaperta. Con un brivido di raccapriccio, sitolse da questa orribile contemplazione e saltò giù.Ma questa volta ebbe cura di tirare al suo posto losportello di edera. Che adesso, insieme al rimorsoe al terrore di se stesso affiorava anche la paura diessere scoperto e punito.Tuttavia, mentre le temeva, sentiva che altempo stesso desiderava questa scoperta e questapunizione; se non altro per essere fermato a temposulla china sdrucciolevole in fondo alla qualegli sembrava inevitabile che dovesse aspettarlol’omicidio. Ma i genitori non l’avevano mai punito,che egli ricordasse; e questo non tanto per unconcetto educativo che escludesse la punizione,quanto, come capiva vagamente, per indifferenza.Così alla sofferenza di sospettarsi autore di undelitto e soprattutto capace di commetterne altripiù gravi, si aggiungeva quella di non sapere a chirivolgersi per farsi punire e di ignorare persino qualepotesse essere la punizione. Marcello si rendevaconto oscuramente che Io stesso meccanismoche l’aveva spinto a confidare la propria colpa aRoberto nella speranza di sentirsi dire che non erauna colpa ma una cosa comune che tutti facevano,adesso gli suggeriva di fare la stessa rivelazione aigenitori nell’opposta speranza di vederli esclamarecon indignazione che aveva commesso un crimineorrendo per il quale doveva espiare una penaadeguata. E poco gli importava che nel primo casol’assoluzione di Roberto l’avrebbe incoraggiato aripetere l’azione che, nel secondo caso, gli avrebbeinvece, attirato una severa condanna. In realtà,come capiva, in ambedue i casi egli voleva usciredall’isolamento terrificante dell’anormalità a tutti icosti e con qualsiasi mezzo.Forse si sarebbe deciso a confessare ai genitoril’uccisione del gatto se, quella stessa sera, a cena,non avesse avuto la sensazione che sapevano giàogni cosa. Come, infatti, si fu seduto a tavola,notò con un senso misto di sgomento e di malcertosollievo, che il padre e la madre parevano ostili e dicattivo umore. La madre, il viso puerile atteggiatoad un’espressione di esagerata dignità, se ne stavadritta, gli occhi bassi, in un silenzio chiaramentesdegnoso. Di fronte a lei, il padre mostrava per segnidiversi ma non meno parlanti, analoghi sentimentidi malumore. I1 padre, di molti anni più vecchiodella moglie, dava spesso a Marcello la sensazionesconcertante di essere accomunato insieme con suamadre in una stessa aria infantile e soggetta, come seella non gli fosse stata madre ma sorella. Era magro,con un viso secco e rugoso, raramente illuminatoda brevi risate senza gioia, nel quale erano notevolidue tratti legati da un nesso indubbio: lo scintillioinespressivo, quasi minerale delle pupille sporgenti eil guizzo frequente, sotto la pelle tirata della guancia,di non si capiva che nervo frenetico. Forse dai molti28 29
anni passati nell’esercito egli aveva conservatoil gusto per i gesti precisi, per gli atteggiamenticontrollati. Ma Marcello sapeva che quando suopadre era adirato, precisione e controllo diventavanoeccessivi, cangiandosi nel contrario, ossia in unastrana violenza contenuta e puntuale rivolta, sisarebbe detto, a caricare di significato i gesti piùsemplici. Ora, quella sera, a tavola, Marcello notòsubito che il padre sottolineava con forza, quasia richiamarvi sopra l’attenzione, azioni abitualie di nessuna importanza. Prendeva, per esempio,il bicchiere, beveva un sorso e poi lo rimetteva aposto con un colpo forte sulla tavola; cercava lasaliera, ne toglieva un pizzico di sale e poi giù,deponendola, un altro colpo; afferrava il pane, lospezzava e quindi lo riposava con un terzo colpo.Oppure, come invaso da una subitanea smania disimmetria, si dava a inquadrare, coi soliti colpi, ilpiatto tra le posate, in modo che coltello, forchettae cucchiaio si incontrassero ad angolo retto intornoil circolo della scodella. Se Marcello fosse statomeno preoccupato dalla propria colpevolezza sisarebbe accorto facilmente che questi gesti cosìdensi di energia significativa e patetica erano rivoltinon già a lui ma a sua madre; la quale, infatti, adognuno di quei colpi, si rinsaccava nella propriadignità con certi sospiri di sufficienza e certe alzatedi sopracciglia piene di sopportazione. Ma la suapreoccupazione lo accecava, così che non dubitòche i genitori sapessero ogni cosa: certamenteRoberto da quel coniglio che era, aveva fatto la spia.Aveva desiderato la punizione, ma adesso vedendoi genitori così corrucciati, gli venne un improvvisoribrezzo della violenza di cui sapeva capace suopadre in simili circostanze. Come le manifestazionidi affetto della madre erano sporadiche, casuali,dettate evidentemente più dal rimorso che dall’amormaterno, così le severità paterne erano improvvise,ingiustificate, eccessive, suggerite, si sarebbe detto,piuttosto dal desiderio di rimettersi in pari dopolunghi periodi di distrazione che da una intenzioneeducativa. Tutto ad un tratto, su una lagnanza dellamadre o della cuoca, il padre ricordava di averun figlio, urlava, dava in smanie, lo percuoteva.Soprattutto le percosse spaventavano Marcelloperchè il padre aveva al mignolo un anello con uncastone massiccio che, durante queste scene, non sisa come, si trovava sempre voltato dalla parte dellapalma, aggiungendo così, alla durezza umiliantedello schiaffo, un dolore più penetrante. Marcellosospettava che il padre voltasse apposta in dentro ilcastone, ma non ne era sicuro.Intimidito, spaventato, incominciò ad architettarein fretta e in furia una bugia plausibile: lui non avevaucciso il gatto, era stato Roberto, e, infatti, il gattosi trovava nel giardino di Roberto, e come avrebbefatto lui ad ammazzarlo attraverso l’edera e il murodi cinta? Ma poi, improvvisamente, ricordò che lasera avanti aveva annunziato alla madre l’uccisionedel gatto che poi, in effetti, era avvenuta il giornodopo, e capì che qualsiasi bugia gli era preclusa.Per quanto distratta, sua madre aveva certamenteriferito la sua confessione al padre e questi, nonmeno certamente, aveva stabilito un nesso tra laconfessione e le accuse di Roberto; e così non c’eraalcuna possibilità di smentita. A questo pensiero,passando da l’uno all’altro estremo, con rinnovatoimpulso desiderò la punizione, purchè venisse prestoe fosse decisiva. Quale? Ricordò che Roberto, ungiorno, aveva parlato di collegi come di luoghi dovei genitori mettevano i figli discoli per punizione, esi sorprese a desiderare vivamente questo generedi pena. Era l’inconsapevole stanchezza dellavita familiare disordinata e poco affettuosa chesi esprimeva in questo desiderio; non soltantofacendogli vagheggiare ciò che i genitori avrebberoconsiderato un castigo, ma anche inducendolo atruffare se stesso e il proprio bisogno di questocastigo, con il calcolo quasi furbo che in tal modoavrebbe al tempo stesso calmato il proprio rimorsoe migliorato il proprio stato. Questo pensiero glisuggerì subito delle immagini che avrebbero dovutoessere scuoranti e invece gli riuscivano grate: unsevero, freddo edificio grigio dai finestroni sbarratida inferriate; camerate gelide e disadorne con file diletti, allineati sotto alti muri bianchi; aule smorte,piene di banchi, con la cattedra in fondo; corridoinudi, scale buie, porte massicce, cancelli invalicabili:tutto insomma, come in una prigione eppure tuttopreferibile alla libertà inconsistente, angosciosa,insostenibile della casa paterna. Persino l’idea diportare un’uniforme di rigatino e di aver la testarasata, come i collegiali che gli accadeva talvoltadi incontrare incolonnati per le strade; perfinoquest’idea umiliante e quasi ripugnante gli riuscivagrata nella sua presente disperata aspirazione ad unordine e ad una normalità purchessia.Tra queste fantasticherie non guardava più alpadre ma alla tovaglia abbagliante di luce bianca sucui, ogni tanto, si abbattevano gli insetti notturni chedalla finestra spalancata venivano a cozzare controil paralume della lampada. Poi alzò gli occhi e feceappena in tempo a vedere, proprio dietro suo padre,sul davanzale della finestra, il profilo di un gatto. Mala bestia, prima che egli avesse potuto distinguerneil colore, saltò giù, attraversò la sala da pranzo escomparve dalla parte della cucina. Sebbene non nefosse del tutto sicuro, tuttavia il cuore gli si gonfiòdi gioiosa speranza al pensiero che potesse essereil gatto che poche ore prima aveva veduto stesoimmobile tra gli iris, nel giardino di Roberto. E fucontento di questa speranza, segno che dopo tuttogli premeva più la vita dell’animale che il propriodestino. “I1 gatto,” esclamò con voce forte. E poigettando il tovagliolo sulla tavola e stendendo unagamba fuori della seggiola: “Papà, ho finito, possoalzarmi?”“Tu stai al tuo posto,” disse il padre con voceminacciosa. Marcello, intimidito, arrischiò: “Ma ilgatto è vivo...”“Ti ho già detto di stare al tuo posto,” ribadìil padre. Quindi, come se le parole di Marcelloavessero infranto anche per lui il lungo silenzio, sivoltò verso la moglie dicendo: “Allora di’ qualchecosa, parla.”“Non ho nulla da dire,” ella ripose con ostentatadignità, le palpebre basse, la bocca sdegnosa. Eravestita da sera, con un abito nero scollato; Marcellonotò che stringeva tra le dita magre un piccolofazzoletto che portava frequentemente al naso; conl’altra mano afferrava e lasciava ricadere sulla tavolaun pezzo di pane, ma non con le dita, bensì con lepunte delle unghie, come un uccello.“Ma di’ quello che hai da dire… parla…perbacco.”“Con te non ho nulla da dire.”Marcello cominciava appena a capire che nonera l’uccisione del gatto il motivo del malumoredei genitori quando, improvvisamente, tutto parveprecipitare. II padre ripetè ancora una volta: “Parla,perdio,” la madre, per tutta risposta, alzò le spalle;allora il padre prese il bicchiere a calice davantial piatto e, gridando forte: “Vuoi parlare sì o no?”lo sbattè con violenza sulla tavola. I1 bicchiere siruppe, il padre con un’imprecazione portò la manoferita alla bocca, la madre spaventata si levò dallatavola e si avviò in fretta verso la porta. I1 padre sisucchiava il sangue della mano quasi con voluttà,inarcando le sopracciglia al disopra della mano; mavedendo la moglie andarsene, interruppe di succhiaree le gridò: “Ti proibisco di andartene… hai capito.”Come risposta venne il colpo della porta sbattutacon violenza. Il padre si alzò anche lui e si slanciòverso la porta. Eccitato dalla violenza della scena,Marcello lo seguì.I1 padre si era già avviato su per la scala,una mano sulla balaustrata, senza scomporsi nè,apparentemente, affrettarsi; ma Marcello che gliveniva dietro vide che saliva gli scalini due a due,quasi volando silenziosamente verso il pianerottolo;come, pensò, un orco da favola calzato degli stivalidelle sette leghe; e non dubitò un momento chequesta ascesa calcolata e minacciosa avrebbe avutoragione della fretta disordinata della madre chepoco più su scappava per gli scalini, uno per uno,con le gambe impacciate dalla gonna stretta. “Oral’ammazza,” pensò seguendo il padre. Giunta sulpianerottolo, la madre fece una piccola corsa finoalla sua camera, non tanto rapida però da impedire almarito di insinuarsi dietro di lei per la fessura dellaporta. Tutto questo Marcello lo vide ascendendola scala con le sue gambe corte di bambino chenon gli consentivano nè di salire due gradini pervolta come il padre nè di saltellare in fretta comela madre. Come arrivò al pianerottolo, notò che alfracasso dell’inseguimento, era, adesso, subentrato,stranamente un silenzio improvviso. La porta dellacamera della madre era rimasta aperta. Marcello, unpo’ titubante, si affacciò sulla soglia.Dapprima non vide, in fondo alla camera inpenombra, ai due lati del largo letto basso, che ledue grandi tende vaporose delle finestre, sollevate dauna corrente di vento dentro la stanza, su su verso ilsoffitto, fin quasi a sfiorare il lume centrale.Queste tende silenziose, biancheggianti amezz’aria nella camera buia, davano un sensodi deserto, come se, inseguendosi, i genitori diMarcello si fossero involati fuori dalle finestrespalancate, nella notte estiva. Poi, nella striscia diluce che dal corridoio, attraverso la porta, giungevafino al letto, scorse finalmente i genitori. O meglio,non vide che il padre, di schiena, sotto il quale lamadre scompariva quasi completamente, salvo cheper i capelli sparsi sul guanciale e per un bracciolevato verso la spalliera del letto. Questo bracciocercava, convulsamente, di aggrapparsi con lamano alla spalliera, senza però riuscirvi; e intanto ilpadre, schiacciando sotto il proprio corpo il corpodella moglie, faceva con le spalle e con le mani deigesti come se avesse voluto strangolarla. “La staammazzando,” pensò Marcello convinto, fermandosisulla soglia. Provava in quel momento unasensazione insolita di eccitazione pugnace e crudelee insieme un desiderio forte di intervenire nellalotta, non sapeva neppur lui se per dar mano forteal padre o difendere la madre. Nello stesso tempo,quasi gli sorrideva la speranza di vedere, attraversoquesto delitto tanto più grave, cancellato il proprio:che era infatti l’uccisione di un gatto in confrontodi quella di una donna? Ma proprio nel momento incui, vincendo l’ultima esitazione, affascinato e pienodi violenza, si muoveva dalla soglia, la voce della30 31
madre, per niente strozzata, anzi quasi carezzevole,mormorò piano: “lasciami,” e, in contraddizionecon questa preghiera, il braccio che ella aveva tenutosino allora alzato a cercare l’orlo della spalliera, siabbassò a cingere la nuca del marito. Meravigliato,quasi deluso, Marcello indietreggiò e uscì nelcorridoio.Pian piano, procurando di non far rumore sugliscalini, discese a pianterreno e si diresse verso lacucina. Adesso lo pungeva di nuovo la curiosità disapere se il gatto che era saltato giù dalla finestranella sala da pranzo fosse quello che temeva di avereucciso. Spinta la porta della cucina, gli apparve untranquillo quadro casalingo: la cuoca matura e lagiovane cameriera, sedute alla tavola di marmo inatto di mangiare, nella cucina bianca, tra il fornelloelettrico e la ghiacciaia. E, in terra, sotto la finestra,il gatto intento a leccare con la lingua rosea il lattedi una ciotola. Ma, come si accorse subito condelusione, non era il gatto grigio bensì un gattostriato del tutto diverso.Non sapendo come giustificare la propria presenzanella cucina, andò al gatto, si abbassò e lo accarezzòsul dorso. I1 gatto, pur senza interrompere di leccareil latte, prese a far le fusa. La cuoca si alzò e andòa chiudere la porta. Poi aprì la ghiacciaia, ne trasseun piatto con una fetta di dolce, lo posò sulla tavolae, accostando una seggiola, disse a Marcello: “Vuoiun po’ del dolce di ieri sera?... L’ho messo appostada parte per te.” Marcello, senza dir parola, lasciòil gatto, sedette e cominciò a mangiare il dolce. Lacameriera disse: “Io però certe cose non le capisco…hanno tanto tempo durante la giornata, hanno tantoposto in casa e, invece, proprio a tavola, in presenzadel bambino, debbono litigare.”La cuoca rispose sentenziosamente: “Quandonon si ha voglia di occuparsi dei figli, è meglio nonmetterli al mondo.”La cameriera, dopo un breve silenzio, osservò:“Lui per l’età potrebbe essere suo padre… si capisceche non vanno d’accordo...”“Fosse soltanto questo...” disse la cuoca con unosguardo pesante in direzione di Marcello.“E poi,” continuò la cameriera, “secondo mequell’uomo non è normale...”Marcello, a questa parola, pur continuando amangiare lentamente il dolce, drizzò l’orecchio.“Anche lei la pensa come me,” proseguì lacameriera, “sai che mi ha detto l’altro giorno mentrela spogliavo per andare a letto? Giacomina, ungiorno o l’altro, mio marito mi uccide… io le horisposto: ma signora che aspetta a lasciarlo? E lei...”“Sss...” la interruppe la cuoca indicando Marcello.La cameriera comprese e domandò a Marcello:“Dove sono papà e mamma?”“Su, in camera,” rispose Marcello. E poi tutto adun tratto, come spinto da un impulso irresistibile: “èproprio vero che papa non è normale. Lo sapete cosaha fatto?”“No, che cosa?”“Ha ammazzato un gatto,” disse Marcello.“Un gatto, e come?”“Con la mia fionda... L’ho visto io, nel giardino,seguire un gatto grigio che camminava sul muro…poi ha preso un sasso e ha tirato al gatto e l’hacolpito in un occhio… il gatto è caduto nel giardinodi Robertino e poi io sono andato a vedere e hovisto che era morto.” Via via che parlava, si erainfervorato, senza tuttavia abbandonare il tonodell’innocente che con ignara e candida ingenuitàracconta qualche misfatto al quale abbia assistito.“Ma pensa un po’” “disse la cameriera giungendo lemani, “un gatto… un uomo di quell’età, un signore,prendere la fionda del figlio e ammazzare un gatto...e poi non bisogna dire che è un anormale.“Chi è cattivo con le bestie, è anche cattivo con icristiani,” disse la cuoca, “si comincia con un gatto epoi si ammazza un uomo.”“Perché?”, domandò ad un tratto Marcellolevando gli occhi dal piatto.“Si dice così,” rispose la cuoca facendogli unacarezza. “Sebbene,” soggiunse rivolta alla cameriera,“non sia sempre vero… quello che ammazzò tuttaquella gente a Pistoia...l’ho letto nel giornale… saicosa fa adesso, in prigione? Alleva un canarino.”II dolce era finito. Marcello si alzò e usci dallacucina.同 流 者序 幕 一马 尔 切 洛 在 他 的 童 年 时 期 , 常 像 一 只 喜 鹊 似的 , 叽 叽 喳 喳 地 为 种 种 东 西 着 迷 。 这 也 许 是 因 为在 家 里 , 父 母 更 多 地 是 出 于 冷 漠 , 而 不 是 出 于 严厉 , 从 来 没 有 想 到 来 满 足 他 那 占 有 欲 的 本 能 ;要 么 则 也 许 是 因 为 其 他 一 些 更 深 刻 的 、 依 然 处 于蒙 昧 状 态 的 本 能 , 在 他 的 身 上 还 戴 着 贪 得 无 厌 的面 具 ; 他 一 直 是 持 续 不 断 地 被 一 些 想 要 占 有 形 形色 色 的 东 西 的 强 烈 愿 望 所 冲 击 。 一 枝 带 有 橡 皮 头的 铅 笔 , 一 本 有 插 图 的 书 籍 , 一 把 弹 弓 , 一 把 尺子 , 一 个 可 携 带 的 硬 橡 胶 制 的 墨 水 瓶 , 任 何 一 个无 足 轻 重 的 小 玩 意 儿 , 都 曾 使 他 的 心 灵 为 之 一振 , 先 是 感 到 一 种 想 要 占 有 这 个 被 他 渴 慕 的 东 西的 炽 烈 而 又 毫 无 道 理 的 欲 望 , 随 后 则 是 一 旦 占 有了 这 个 东 西 , 就 感 到 一 种 喜 出 望 外 的 、 心 驰 神 往的 、 难 以 抑 制 的 得 意 洋 洋 。 马 尔 切 洛 在 家 里 自 己拥 有 整 整 一 个 房 间 , 用 来 睡 觉 和 学 习 。 在 这 里 ,所 有 那 些 乱 放 在 桌 子 上 的 、 或 是 放 进 抽 屉 里 的 东西 , 对 他 来 说 , 都 有 各 自 的 特 性 : 有 些 东 西 依 然是 神 圣 的 , 有 些 东 西 则 是 刚 刚 遭 到 贬 低 , 这 要 看这 些 东 西 是 新 近 买 来 的 , 还 是 已 经 买 来 很 久 了 。总 之 , 这 些 东 西 和 家 里 的 其 他 东 西 不 一 样 , 虽 然是 以 后 会 使 用 或 现 在 已 用 过 的 一 些 七 零 八 碎 的 东西 , 却 又 是 他 十 分 喜 爱 而 又 弄 不 清 楚 的 全 部 家当 。 马 尔 切 洛 以 他 自 己 的 方 式 来 了 解 占 有 欲 的 这种 特 殊 性 质 , 他 在 从 中 汲 取 难 以 言 传 的 乐 趣 的 同时 , 却 也 为 此 而 受 到 痛 苦 的 折 磨 , 就 像 是 犯 了 什么 过 错 , 而 且 这 个 过 错 在 不 断 地 一 犯 再 犯 , 甚 至不 让 他 来 得 及 对 此 感 到 懊 悔 。但 是 , 在 所 有 这 些 东 西 当 中 , 对 他 吸 引 力 最大 的 东 西 ( 也 许 是 因 为 这 些 东 西 是 禁 止 他 拥 有 的吧 ), 那 就 是 武 器 。 这 可 不 是 小 孩 子 们 用 来 玩 耍的 假 武 器 : 什 么 铁 皮 步 枪 啊 , 起 爆 手 枪 啊 , 木 制匕 首 啊 , 而 是 真 正 的 武 器 , 因 为 一 旦 有 了 真 正 的武 器 , 威 胁 、 危 险 、 死 亡 的 念 头 就 不 是 依 据 武 器在 形 体 上 的 完 全 似 真 而 产 生 的 了 , 而 是 成 为 这 些真 正 的 武 器 之 所 以 存 在 的 首 要 的 和 最 终 的 理 由 。人 们 可 以 用 小 孩 子 们 的 手 枪 来 玩 死 亡 的 游 戏 , 而又 不 会 有 真 正 造 成 死 亡 的 任 何 可 能 , 但 是 , 用 大人 们 的 手 枪 , 死 亡 就 不 仅 是 可 能 的 , 而 且 还 是 就要 临 头 的 , 就 像 是 一 种 只 是 出 于 谨 慎 才 能 加 以 遏制 的 尝 试 。 马 尔 切 洛 曾 有 过 几 次 , 把 这 些 真 正 的武 器 拿 在 手 里 , 那 是 一 把 农 村 用 的 猎 枪 , 是 父 亲的 一 把 旧 手 枪 : 有 一 天 , 父 亲 曾 拉 开 一 个 抽 屉 让他 看 过 这 把 手 枪 ; 他 每 一 次 都 会 感 到 一 阵 受 感 染似 的 战 慄 , 就 仿 佛 他 的 手 在 紧 握 那 个 武 器 的 同 时终 于 自 然 而 然 地 变 长 了 。马 尔 切 洛 在 这 个 街 区 的 那 些 孩 子 当 中 , 有 许多 朋 友 , 而 他 很 早 就 发 现 , 他 对 武 器 的 喜 好 有 一些 比 他 们 那 种 天 真 无 邪 的 对 军 事 的 着 迷 要 更 加 深刻 、 更 加 晦 暗 的 缘 由 。 他 们 玩 当 兵 的 游 戏 , 装出 一 副 残 忍 凶 狠 的 模 样 , 但 是 , 实 际 上 , 他 们 都仍 然 是 在 做 着 为 爱 游 戏 而 做 的 游 戏 , 他 们 像 猴 子那 样 模 仿 那 种 残 酷 无 情 的 姿 态 , 却 根 本 没 有 真 正投 入 ; 然 而 , 在 他 身 上 , 情 况 则 恰 恰 相 反 : 他 的那 种 残 忍 和 凶 狠 是 要 在 玩 当 兵 的 游 戏 中 寻 求 发 泄的 , 而 且 在 从 事 其 他 一 些 消 遣 时 , 尽 管 不 是 在 玩当 兵 的 游 戏 , 那 种 残 忍 和 凶 狠 也 都 透 露 出 对 毁 灭和 死 亡 的 喜 好 。 在 那 个 时 候 , 马 尔 切 洛 总 是 残 酷无 情 的 , 既 不 会 懊 悔 , 又 不 会 羞 愧 , 完 全 自 然 得很 , 因 为 这 种 残 酷 无 情 只 会 使 他 感 到 乐 趣 , 而 且这 种 乐 趣 在 他 看 来 似 乎 并 不 索 然 无 味 ; 这 种 残 酷无 情 当 时 尚 属 相 当 幼 稚 , 不 致 引 起 他 自 己 或 其 他人 的 猜 疑 。 比 如 说 吧 , 在 夏 初 时 节 , 在 天 正 热 的时 候 , 他 常 下 楼 到 花 园 里 去 。 这 个 花 园 很 狭 小 ,但 是 却 草 木 葱 郁 , 花 园 里 漫 无 秩 序 地 生 长 着 许 多植 物 和 树 木 , 多 年 来 无 人 照 看 , 听 任 它 们 自 然 地茂 密 繁 生 。 马 尔 切 洛 拿 着 一 根 细 而 有 弹 性 的 藤 条作 武 器 , 下 楼 到 花 园 里 来 , 这 根 藤 条 是 他 从 阁 楼上 的 一 把 拍 打 衣 物 的 藤 拍 上 拔 下 来 的 ; 他 常 在 树木 的 那 些 戏 弄 人 的 阴 影 和 太 阳 的 那 些 灼 热 的 光 线中 间 , 沿 着 那 些 鹅 卵 石 铺 成 的 林 荫 小 路 , 转 悠 一会 儿 , 一 边 观 察 着 那 些 植 物 。 他 感 到 , 自 己 的 眼睛 在 闪 闪 发 光 , 他 的 整 个 身 体 都 豁 然 舒 展 开 来 ,产 生 一 种 畅 快 惬 意 的 感 觉 , 这 种 感 觉 似 乎 和 充满 阳 光 的 繁 茂 的 花 园 的 一 片 欣 欣 向 荣 的 生 机 混 合在 一 起 , 他 感 到 自 己 很 幸 福 。 但 是 , 这 是 一 种 侵犯 性 的 、 残 酷 无 情 的 幸 福 , 几 乎 是 在 强 烈 地 渴 望要 与 他 人 的 不 幸 一 决 高 低 。 当 马 尔 切 洛 看 到 一 个花 坛 中 央 , 有 一 簇 开 满 黄 白 两 色 花 朵 的 漂 亮 的 雏菊 , 或 是 一 朵 带 有 挺 立 在 绿 色 茎 干 上 的 红 色 花 冠的 郁 金 香 , 再 或 是 一 根 长 着 高 高 的 白 色 丰 腴 花 朵的 马 蹄 莲 的 时 候 , 他 总 是 会 把 那 藤 条 挥 动 一 下 ,让 那 藤 条 在 空 气 中 发 出 嗖 的 一 声 响 , 就 像 一 把 宝剑 似 的 。 那 藤 条 干 脆 利 落 地 砍 掉 了 花 叶 , 那 花 叶干 干 净 净 地 落 在 那 棵 植 物 旁 边 的 地 上 , 留 下 那 些被 斩 首 的 茎 梗 依 然 挺 立 着 。 这 样 一 来 , 他 就 感 到自 己 的 生 命 力 增 加 了 一 倍 , 几 乎 有 一 种 无 比 酣 畅的 得 意 心 情 , 这 种 心 情 正 是 由 一 种 被 压 抑 过 久 的精 力 的 痛 快 发 泄 引 起 的 ; 但 是 与 此 同 时 , 他 也 感到 有 一 种 他 也 说 不 上 是 怎 样 的 饱 含 威 力 和 裁 决 权的 确 切 情 感 。 这 就 好 像 那 些 植 物 是 有 罪 的 , 而 他呢 , 则 是 对 它 们 作 了 惩 罚 , 同 时 他 还 感 到 , 他 是有 权 力 惩 罚 它 们 的 。 但 是 , 这 种 消 遣 法 的 应 被 禁止 和 罪 不 容 恕 的 性 质 , 却 并 不 是 他 全 然 不 晓 的 。他 不 时 , 几 乎 是 不 由 自 主 地 , 朝 别 墅 偷 偷 地 看 上几 眼 , 因 为 他 害 怕 , 母 亲 可 能 会 从 客 厅 的 窗 户 ,32 33
或 是 厨 娘 可 能 会 从 厨 房 的 窗 户 , 看 到 他 。 而 且 他也 知 道 , 他 害 怕 的 倒 不 只 是 责 骂 , 而 是 尤 其 是 对他 所 作 所 为 的 简 单 鉴 证 , 因 为 他 自 己 也 发 觉 他 的所 作 所 为 是 反 常 的 , 是 莫 名 其 妙 地 浸 透 着 罪 恶 因素 的 。从 鲜 花 和 植 物 转 到 动 物 , 这 个 过 渡 是 不 知 不觉 的 , 正 像 在 自 然 界 中 也 恰 是 如 此 。 马 尔 切 洛 也说 不 出 他 何 时 发 现 : 他 在 摧 残 植 物 和 砍 掉 花 朵 方面 所 感 到 的 那 种 乐 趣 , 竟 然 在 对 动 物 施 加 暴 力方 面 , 向 他 显 示 出 是 更 为 强 烈 , 更 为 深 刻 的 。 也许 他 被 迫 走 上 这 条 道 路 , 仅 仅 是 事 出 偶 然 : 他挥 动 了 一 下 藤 条 , 不 是 打 坏 了 一 株 灌 木 , 而 是打 中 了 一 只 睡 在 一 根 枝 蔓 上 的 蜥 蜴 的 脊 背 ; 或者 造 成 这 个 结 果 的 也 许 是 : 他 开 始 感 到 某 种 烦腻 , 这 就 使 他 寻 找 新 的 物 质 , 以 便 对 这 个 物 质 施加 那 尚 属 不 自 觉 的 残 酷 折 磨 。 不 论 如 何 , 在 一 个寂 静 的 下 午 , 家 里 所 有 的 人 都 在 睡 觉 , 马 尔 切 洛突 然 间 像 被 懊 悔 和 羞 愧 电 击 般 地 打 了 一 下 , 面 对着 对 蜥 蜴 的 一 场 屠 杀 。 有 五 六 只 蜥 蜴 曾 被 他 用 种种 不 同 的 方 式 , 从 树 木 的 枝 蔓 上 或 是 围 墙 的 石 块上 捅 了 出 来 , 他 在 恰 恰 是 这 些 蜥 蜴 已 经 猜 疑 到 他一 动 不 动 地 等 在 那 里 、 因 而 设 法 逃 向 一 些 避 难 所的 那 一 刻 , 仅 仅 挥 动 了 一 下 藤 条 , 便 把 这 些 蜥 蜴抽 死 了 。 他 是 怎 样 做 到 这 一 点 的 , 他 也 说 不 明白 , 或 者 说 得 更 确 切 些 , 他 是 宁 可 不 回 忆 这 一点 , 但 是 , 如 今 一 切 都 做 完 了 , 只 剩 下 炎 热 而 不干 净 的 太 阳 在 晒 着 那 些 死 去 的 蜥 蜴 的 血 淋 淋 的 、着 满 尘 土 的 身 体 。 他 站 在 水 泥 便 道 前 面 , 而 便 道上 则 躺 着 那 些 蜥 蜴 , 他 手 里 还 紧 握 着 那 根 藤 条 ;他 的 全 身 和 脸 上 还 感 到 在 屠 杀 蜥 蜴 时 曾 席 卷 他 的那 股 冲 动 情 绪 , 但 是 , 这 情 绪 已 经 不 再 是 那 么 热烈 而 令 他 兴 奋 了 , 就 像 在 当 时 那 样 , 相 反 都 是 黯然 失 色 , 转 变 为 懊 悔 和 羞 愧 。 此 外 , 他 也 明 白 ,在 素 常 那 种 残 酷 无 情 和 作 威 作 福 的 情 感 上 , 这 一次 又 增 添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困 惑 , 这 种 困 惑 对 他 来 说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并 且 是 无 法 说 明 的 一 种 肉 体 上 的感 觉 ; 与 羞 愧 和 懊 悔 一 并 具 来 的 是 : 他 还 有 一 种模 糊 的 恐 惧 感 。 这 就 好 像 他 从 自 己 身 上 发 现 了 一种 完 全 反 常 的 个 性 , 对 此 他 是 应 该 感 到 羞 愧 的 ,而 且 他 应 该 对 此 保 密 , 以 求 不 致 愧 对 自 己 , 而 且还 愧 对 他 人 , 因 此 , 这 种 反 常 的 个 性 将 会 把 他 永远 和 他 同 龄 人 的 社 会 群 体 分 割 开 来 。 不 容 置 疑 ,他 是 不 同 于 和 他 年 纪 相 仿 的 那 些 孩 子 的 , 那 些 孩子 , 他 们 , 不 论 是 全 体 , 还 是 个 别 , 都 不 曾 专 门去 做 类 似 的 消 遣 ; 况 且 , 他 和 他 们 的 不 同 是 彻 头彻 尾 的 。 因 为 那 些 蜥 蜴 是 已 经 死 掉 了 , 在 这 个 问题 上 ,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 这 种 死 亡 以 及 他 为 了 造 成这 种 死 亡 而 做 出 的 残 酷 而 疯 狂 的 行 为 , 也 是 绝 无仅 有 的 。 总 而 言 之 , 他 是 与 那 些 行 为 恰 相 一 致 ,这 就 像 在 过 去 , 他 曾 与 那 些 完 全 天 真 、 完 全 正 常的 行 为 恰 相 一 致 一 样 。那 一 天 , 为 了 证 实 对 自 己 的 反 常 状 态 的 这 个如 此 新 鲜 、 如 此 痛 苦 的 发 现 , 马 尔 切 洛 想 要 使 自己 和 他 的 一 个 小 朋 友 罗 贝 托 做 个 比 较 , 罗 贝 托 是住 在 他 的 那 所 小 别 墅 旁 边 的 小 别 墅 里 的 。 在 将近 黄 昏 的 时 分 , 罗 贝 托 总 是 在 学 习 完 毕 后 , 下 楼到 花 园 里 来 ; 经 过 双 方 家 庭 的 互 相 同 意 , 这 两 个小 男 孩 常 在 一 起 玩 , 一 直 玩 到 吃 晚 饭 的 时 候 , 时而 是 在 这 个 孩 子 的 花 园 里 玩 , 时 而 是 在 另 一 个 孩子 的 花 园 里 玩 。 马 尔 切 洛 在 整 个 漫 长 而 寂 静 的 下午 , 急 不 可 耐 地 等 待 这 个 时 刻 的 到 来 , 他 独 自 待在 他 的 房 间 里 , 躺 在 床 上 。 父 母 已 经 出 门 了 , 家里 只 有 厨 娘 一 人 , 他 不 时 可 以 听 见 她 在 底 层 厨 房里 低 声 哼 唱 的 声 音 。 平 常 , 下 午 , 他 总 是 独 自 在自 己 的 房 间 里 学 习 或 玩 耍 ; 但 是 , 那 一 天 , 不 论是 学 习 还 是 玩 耍 都 对 他 没 有 吸 引 力 ; 他 感 到 自 己无 法 去 干 任 何 事 , 同 时 , 又 觉 得 心 情 急 躁 , 无 法忍 受 无 所 事 事 : 使 他 懒 得 动 弹 、 同 时 又 心 情 烦 躁的 是 他 觉 得 自 己 已 经 做 出 的 那 个 发 现 所 引 起 的 震惊 , 以 及 企 盼 他 就 要 和 罗 贝 托 相 见 这 件 事 能 打 消这 种 震 惊 的 希 望 。 如 果 罗 贝 托 对 他 说 : 他 也 常 杀害 蜥 蜴 , 他 喜 欢 杀 害 蜥 蜴 , 他 看 不 出 杀 害 蜥 蜴 有什 么 不 好 , 那 么 , 他 就 会 觉 得 , 一 切 反 常 的 感 觉都 烟 消 雾 散 了 , 他 也 就 可 以 漠 不 关 心 地 看 待 屠 杀蜥 蜴 这 件 事 , 把 它 看 成 和 一 件 无 足 轻 重 、 不 计 后果 的 意 外 事 故 一 样 。 他 说 不 出 为 什 么 他 赋 予 罗 贝托 这 么 大 的 权 威 ; 他 模 模 糊 糊 地 认 为 , 如 果 罗 贝托 也 干 这 些 事 , 也 用 这 种 方 式 和 怀 着 这 种 心 情 干这 些 事 , 这 就 是 说 , 所 有 的 人 都 是 这 样 干 的 ; 而所 有 的 人 都 干 的 那 件 事 , 也 便 是 正 常 的 亦 即 好 事了 。 再 说 , 这 种 想 法 在 马 尔 切 洛 的 头 脑 中 也 并 不是 十 分 清 楚 的 , 这 种 想 法 在 他 的 头 脑 中 出 现 , 与其 说 是 明 确 的 思 想 , 倒 不 如 说 是 剧 烈 的 感 触 和 冲动 。 但 是 , 有 一 件 事 , 他 觉 得 自 己 对 它 是 有 把 握的 : 他 的 心 灵 的 安 宁 要 取 决 于 罗 贝 托 的 回 答 。他 抱 着 这 种 希 望 , 带 着 这 种 震 惊 心 情 , 急 不可 耐 地 等 待 黄 昏 时 分 的 到 来 。 他 几 乎 就 要 打 起 瞌睡 来 了 , 这 时 , 从 花 园 里 传 来 了 一 阵 长 长 的 抑 扬口 哨 声 : 这 是 他 和 罗 贝 托 商 定 的 信 号 , 罗 贝 托 正是 用 它 来 告 诉 他 : 他 来 了 。 马 尔 切 洛 从 床 上 站 起身 来 , 也 没 有 开 灯 , 在 半 明 半 暗 的 暮 色 中 从 房 间里 出 来 , 下 了 楼 梯 , 来 到 花 园 。在 夏 日 黄 昏 的 低 暗 光 照 下 , 树 木 纹 丝 不 动 ,愁 云 深 锁 ; 枝 蔓 下 , 阴 影 已 经 显 得 像 是 黑 夜 了 。鲜 花 喷 吐 的 芳 香 , 尘 土 的 气 味 , 从 晒 热 的 土 地 里散 发 出 来 的 阳 光 的 辐 射 , 都 在 凝 重 而 浓 密 的 空 气中 陷 于 呆 滞 状 态 。 那 扇 把 马 尔 切 洛 的 花 园 和 罗 贝托 的 花 园 隔 开 的 铁 栅 栏 门 , 在 一 片 巨 大 、 茂 密 而深 邃 的 常 春 藤 —— 它 简 直 就 像 一 堵 由 重 叠 的 叶 子构 成 的 墙 壁 —— 底 下 , 完 全 消 失 了 。 马 尔 切 洛 径直 去 到 花 园 深 处 的 一 个 角 落 , 那 里 , 常 春 藤 和 阴影 更 为 浓 密 , 他 登 上 一 块 大 石 头 , 仅 用 手 坚 决 地动 了 一 下 , 便 把 一 整 块 攀 缘 植 物 拨 开 。 正 是 他 在从 事 一 种 秘 密 和 冒 险 的 游 戏 的 感 觉 驱 使 下 , 从 常春 藤 的 叶 丛 中 发 明 这 样 一 种 小 门 的 。 把 常 春 藤 移开 之 后 , 便 露 出 了 铁 栅 栏 门 的 那 些 铁 棍 , 而 在 那些 铁 棍 中 间 , 则 又 露 出 了 朋 友 罗 贝 托 的 金 黄 头 发底 下 的 细 嫩 而 苍 白 的 脸 。 马 尔 切 洛 在 石 头 上 跷 起脚 尖 , 问 道 :“ 没 有 人 看 见 我 们 吧 ?”这 是 他 们 这 个 游 戏 开 端 的 程 式 , 罗 贝 托 像背 诵 一 段 课 文 似 的 答 道 :“ 没 有 , 一 个 人 也 没有 ……” 过 了 一 会 儿 , 他 随 即 说 道 :“ 你 学 习 了吗 ?”他 放 低 声 音 , 悄 悄 说 着 , 这 又 是 一 个 商 定 的做 法 。 马 尔 切 洛 也 放 低 声 音 , 悄 悄 答 道 :“ 没有 , 我 今 天 没 有 学 习 …… 我 没 有 心 思 …… 我 会 跟 那位 女 老 师 说 : 我 感 到 不 舒 服 。”“ 我 做 了 意 大 利 文 的 功 课 ,” 罗 贝 托 低 声 说道 ,“ 我 还 做 了 几 道 算 术 题 里 的 一 道 …… 我 现 在还 剩 下 一 道 算 数 题 要 做 了 …… 为 什 么 你 没 有 学 习呢 ?”这 正 是 马 尔 切 洛 期 待 的 问 题 :“ 我 没 有 学习 ,” 他 答 道 ,“ 是 因 为 我 刚 才 打 蜥 蜴 了 。”他 希 望 罗 贝 托 对 他 说 :“ 啊 , 真 的 吗 …… 我有 时 也 打 蜥 蜴 呢 ,” 或 者 说 一 些 类 似 的 话 。 但是 , 罗 贝 托 的 脸 却 没 有 做 出 任 何 不 谋 而 合 的 表示 , 甚 至 连 好 奇 也 没 有 。 他 勉 强 又 说 了 一 句 , 一边 力 求 掩 饰 自 己 的 难 堪 :“ 我 把 它 们 全 杀 了 。”罗 贝 托 谨 慎 地 问 道 :“ 有 多 少 ?”“ 一 共 七 只 ,” 马 尔 切 洛 答 道 。 接 着 , 他 又尽 力 从 技 术 上 自 吹 自 擂 , 说 道 :“ 它 们 当 时 待 在树 枝 上 和 石 头 上 …… 我 等 待 它 们 移 动 身 子 , 接 着我 就 随 手 把 它 们 抓 住 …… 用 这 根 藤 条 只 抽 了 一 下…… 一 只 抽 一 下 。” 他 得 意 地 做 了 一 个 怪 相 , 拿出 那 根 藤 条 给 罗 贝 托 看 。他 看 到 对 方 带 着 一 种 并 非 不 包 含 某 种 类 似 惊讶 的 好 奇 神 情 注 视 着 他 :“ 你 为 什 么 把 它 们 都 杀了 ?”“ 不 为 什 么 ,” 他 犹 豫 了 一 下 , 差 一 点 要说 :“ 因 为 我 喜 欢 ,” 再 说 , 他 自 己 也 不 知 道 是为 什 么 , 他 把 话 咽 下 去 了 , 随 即 答 道 :“ 因 为 它们 有 害 …… 你 难 道 不 知 道 蜥 蜴 是 有 害 的 吗 ?”“ 不 ,” 罗 贝 托 说 道 ,“ 我 不 知 道 …… 那么 , 它 们 对 什 么 有 害 呢 ?”“ 它 们 吃 葡 萄 啊 ,” 马 尔 切 洛 说 道 ,“ 前年 , 在 乡 下 , 它 们 把 葡 萄 架 上 的 所 有 葡 萄 都 吃 光了 。”“ 可 这 里 没 有 葡 萄 啊 。”“ 再 说 呢 ,” 他 继 续 说 下 去 , 全 然 不 顾 听 取对 方 的 异 议 ,“ 它 们 很 坏 …… 刚 才 有 一 只 , 看 见我 , 它 不 但 不 逃 开 , 还 冲 着 我 跑 来 , 把 嘴 巴 张 得大 大 的 …… 要 是 我 没 有 及 时 把 它 挡 住 , 它 本 来 会跳 到 我 身 上 来 呢 ……” 他 沉 默 了 一 会 儿 , 接 着 ,用 更 机 密 的 口 气 说 道 :“ 你 从 来 没 有 杀 过 蜥 蜴吗 ?”罗 贝 托 摇 了 摇 头 , 答 道 :“ 没 有 , 从 来 没有 。” 接 着 , 他 放 低 了 眼 睛 , 脸 上 显 出 痛 心 的 样子 :“ 人 家 说 , 不 该 伤 害 动 物 。”“ 谁 说 的 ?”“ 妈 妈 。”“ 人 家 说 的 话 也 太 多 了 ……” 马 尔 切 洛 说道 , 他 的 自 信 心 越 来 越 少 了 ,“ 可 你 该 试 试 嘛 ,傻 瓜 …… 我 向 你 保 证 , 这 可 好 玩 了 。”“ 不 , 我 才 不 试 呢 。”“ 那 为 什 么 ?”“ 因 为 这 是 坏 事 。”这 样 , 就 一 点 办 法 也 没 有 了 , 马 尔 切 洛 扫 兴地 想 道 。 他 猛 然 感 到 自 己 对 这 位 朋 友 有 一 股 怒 气涌 上 心 头 , 因 为 对 方 竟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把 他 钉 在 他自 己 的 反 常 状 态 上 了 。 然 而 , 他 还 是 控 制 住 自己 , 提 议 道 :“ 你 看 , 明 天 , 我 还 要 打 蜥 蜴 呢…… 要 是 你 来 跟 我 一 起 打 , 我 就 把 《 集 市 商 人 》那 副 纸 牌 送 给 你 。”他 知 道 , 对 罗 贝 托 来 说 , 这 个 建 议 可 是 有 诱惑 力 的 : 罗 贝 托 曾 多 次 表 示 想 要 得 到 这 副 纸 牌 。果 然 , 罗 贝 托 像 是 突 然 灵 机 一 动 , 答 道 :“ 我 可以 来 打 , 不 过 , 有 一 个 条 件 : 我 们 要 抓 活 的 ,然 后 把 它 们 放 到 一 个 小 盒 子 里 , 然 后 再 放 了 它 们…… 你 呢 , 就 把 纸 牌 给 我 。”“ 这 可 不 行 ,” 马 尔 切 洛 说 道 ,“ 妙 就 妙 在用 这 根 藤 条 抽 它 们 …… 我 打 赌 , 你 没 有 能 力 这 样干 。”对 方 什 么 话 也 没 有 说 。 马 尔 切 洛 又 说 下 去 :“ 那 么 , 你 就 来 吧 …… 我 们 一 言 为 定 …… 但 是 , 你也 得 找 一 根 藤 条 。”“ 不 ,” 罗 贝 托 固 执 地 说 道 ,“ 我 不 会 来的 。”“ 可 为 什 么 呢 ? 那 副 纸 牌 可 是 新 的 啊 。”“ 不 , 这 也 没 用 ,” 罗 贝 托 说 道 ,“ 我 可 不杀 蜥 蜴 …… 就 算 ,” 他 犹 豫 了 一 下 , 因 为 他 在 寻觅 一 件 价 值 相 当 的 东 西 ,“ 你 把 你 的 手 枪 给 我 ,我 也 不 干 。”马 尔 切 洛 明 白 , 确 是 一 点 办 法 也 没 有 了 , 猛然 间 , 他 让 憋 在 胸 中 好 一 会 儿 的 怒 气 迸 发 出 来 :“ 你 不 想 干 , 是 因 为 你 是 个 胆 小 鬼 ,” 他 说 道 ,“ 是 因 为 你 害 怕 。”“ 可 又 害 怕 什 么 呢 ? 你 真 让 我 好 笑 。”“ 你 害 怕 ,” 马 尔 切 洛 怒 气 冲 冲 地 又 重 复 了一 遍 ,“ 你 是 一 只 兔 子 …… 一 只 真 正 的 兔 子 。”突 然 间 , 他 穿 过 铁 栅 栏 门 的 那 些 铁 棍 伸 出 一 只 手来 , 一 把 揪 住 这 位 朋 友 的 一 只 耳 朵 。 罗 贝 托 有 一对 招 风 耳 , 红 红 的 , 而 且 这 也 不 是 头 一 次 马 尔 切洛 揪 他 的 耳 朵 了 ; 但 是 , 马 尔 切 洛 过 去 揪 他 的 耳朵 , 从 来 没 有 如 此 火 冒 三 丈 , 如 此 明 确 地 想 要 弄痛 他 。“ 你 承 认 你 是 只 兔 子 。”“ 不 , 放 开 我 ,” 对 方 扭 曲 着 身 体 , 开 始 大呼 小 叫 起 来 ,“ 哎 哟 …… 哎 哟 。”“ 你 承 认 你 是 只 免 子 。”“ 不 …… 放 开 我 。”“ 你 承 认 你 是 只 免 子 。”罗 贝 托 的 耳 朵 在 他 的 手 里 火 辣 辣 地 发 疼 , 又34 35
热 又 流 汗 ; 那 受 折 磨 的 人 的 蔚 蓝 色 眼 睛 里 已 经 出现 了 泪 水 。 他 结 结 巴 巴 地 说 道 :“ 是 的 , 好 吧 ,我 是 只 兔 子 ,” 于 是 , 马 尔 切 洛 马 上 就 放 了 他 。罗 贝 托 从 铁 栅 栏 门 上 跳 下 去 , 边 跑 开 边 喊 道 :“ 我 才 不 是 兔 子 呢 …… 我 刚 才 说 那 句 话 的 时 候 ,想 的 却 是 : 我 不 是 兔 子 …… 我 哄 了 你 了 。” 他 一溜 烟 跑 得 无 影 无 踪 , 他 那 哭 哭 啼 啼 而 又 冷 嘲 热 讽的 声 音 也 消 失 在 远 处 , 消 失 在 隔 壁 花 园 的 那 一 片片 小 树 林 以 外 的 地 方 。这 番 对 话 留 给 马 尔 切 洛 的 只 是 一 种 异 常 不 安的 感 觉 。 罗 贝 托 拒 绝 把 他 所 追 求 的 宽 恕 连 同 他 的友 好 情 谊 赋 予 他 , 而 他 本 来 觉 得 , 这 种 宽 恕 是 该和 那 种 友 好 情 谊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 这 样 , 他 就 是遭 到 了 唾 弃 , 被 抛 到 反 常 状 态 当 中 , 尽 管 事 先 他也 不 是 没 有 向 罗 贝 托 表 示 : 他 是 多 么 迫 切 希 望 摆脱 这 种 反 常 状 态 的 , 不 是 没 有 听 任 自 己 说 了 一 番谎 话 , 并 且 使 用 了 一 番 暴 力 的 , 这 一 点 他 十 分 清楚 。 现 在 , 除 了 原 来 因 为 杀 死 蜥 蜴 而 感 到 的 羞 愧和 懊 悔 之 外 , 又 加 上 了 新 的 羞 愧 和 懊 悔 , 那 就是 : 他 曾 在 说 明 他 之 所 以 要 求 罗 贝 托 和 他 串 通 一气 的 原 因 方 面 , 向 罗 贝 托 撒 了 谎 , 并 且 还 揪 了 罗贝 托 的 耳 朵 , 大 发 了 一 通 脾 气 , 从 而 违 背 了 自 己的 初 衷 。 在 第 一 个 过 错 上 边 , 又 加 上 了 第 二 个 过错 ; 而 他 又 毫 无 办 法 , 既 不 能 去 掉 第 一 个 过 错 ,又 不 能 去 掉 第 二 个 过 错 。在 这 些 苦 痛 的 思 索 当 中 , 他 不 时 回 忆 起 对 晰蜴 的 屠 杀 , 他 几 乎 希 望 能 发 现 这 种 屠 杀 已 经 不 会引 起 任 何 懊 悔 , 它 不 过 像 别 的 事 情 一 样 , 是 一 件简 单 的 事 情 。 但 是 , 他 却 总 是 马 上 发 觉 : 他 似 乎希 望 , 那 些 蜥 蜴 永 远 不 要 死 掉 ; 而 与 此 同 时 , 他在 打 蜥 蜴 时 所 产 生 的 那 种 既 兴 奋 又 手 足 无 措 的 感觉 也 又 回 到 他 的 身 上 来 , 这 种 感 觉 是 那 么 强 烈 ,也 许 并 不 是 完 全 令 他 不 快 的 , 但 是 也 正 因 如 此 ,却 又 令 他 感 到 更 加 恶 心 ; 这 种 感 觉 竟 然 如 此 强烈 , 甚 至 使 他 不 禁 怀 疑 起 来 : 在 今 后 几 天 里 , 他是 否 会 经 受 得 住 再 次 进 行 屠 杀 的 诱 惑 。 这 个 想 法把 他 吓 住 了 : 如 此 说 来 , 他 不 仅 是 反 常 的 , 而 且还 是 无 力 消 除 这 种 反 常 状 态 的 , 甚 至 连 控 制 这 种反 常 状 态 也 无 力 做 到 。 这 时 , 他 待 在 自 己 的 房 间里 , 坐 在 书 桌 前 , 面 对 着 一 本 掀 开 的 书 , 等 待 吃晚 饭 。 他 猛 地 站 了 起 来 , 去 到 床 边 , 扑 身 跪 倒 在床 前 的 小 地 毯 上 , 正 像 他 在 做 祈 祷 时 通 常 所 做 的那 样 , 他 双 手 合 十 , 用 他 觉 得 是 诚 心 诚 意 的 语 气高 声 说 道 :“ 我 在 上 帝 面 前 发 誓 : 我 永 远 不 再 去 碰 鲜花 、 植 物 和 蜥 蜴 了 。”然 而 , 曾 经 驱 使 他 去 寻 求 罗 贝 托 与 他 同 谋 共犯 的 那 种 求 得 宽 恕 的 需 要 , 却 依 然 存 在 , 这 时 不过 是 变 成 它 的 反 面 , 变 成 领 受 谴 责 的 需 要 罢 了 。当 罗 贝 托 还 能 拯 救 他 、 让 他 免 受 懊 悔 之 苦 、 并且 跟 他 站 在 一 起 的 时 候 , 罗 贝 托 并 没 有 足 够 的 权威 来 证 实 这 种 懊 悔 是 有 根 有 据 的 , 也 没 有 足 够 的权 威 来 用 最 终 的 判 决 把 他 的 头 脑 混 乱 整 理 有 序 。罗 贝 托 像 他 一 样 , 是 一 个 孩 子 , 只 可 以 做 同 谋 ,却 不 适 于 当 法 官 。 但 是 , 罗 贝 托 却 拒 绝 了 他 的 建议 , 并 且 为 了 支 持 自 己 对 这 个 建 议 感 到 厌 恶 的 态度 , 还 借 用 了 母 亲 的 权 威 。 马 尔 切 洛 想 道 , 自 己也 可 以 求 助 于 母 亲 嘛 。 只 有 母 亲 才 能 谴 责 他 或 是宽 恕 他 , 不 论 如 何 , 只 有 母 亲 才 能 使 他 的 行 为 重新 就 范 , 恢 复 到 不 论 是 哪 一 种 秩 序 中 去 。 马 尔 切洛 是 了 解 他 的 母 亲 的 , 但 是 他 既 然 拿 定 这 个 主意 , 也 便 只 好 从 抽 象 方 面 进 行 推 理 , 就 像 是 拿 一位 理 想 母 亲 做 靠 山 似 的 : 这 位 母 亲 是 理 应 如 此 ,而 不 是 实 际 如 此 。 其 实 , 他 对 自 己 的 这 种 求 助 能否 取 得 良 好 结 果 , 也 是 有 疑 虑 的 。 但 是 , 事 已 如此 , 他 又 只 有 那 位 母 亲 可 求 , 再 说 , 他 那 想 要 求助 于 她 的 冲 动 情 绪 , 也 是 比 任 何 疑 虑 都 要 更 强 烈的 。马 尔 切 洛 等 待 这 样 一 个 时 刻 : 母 亲 在 他 上 床躺 下 之 后 , 总 要 来 到 房 间 里 向 他 道 晚 安 。 这 是 他能 单 独 和 母 亲 见 面 的 少 数 时 刻 中 的 一 个 时 刻 : 在更 多 的 时 间 里 , 在 吃 一 日 三 餐 或 是 与 父 母 一 起散 步 时 , 父 亲 则 总 是 在 场 的 。 马 尔 切 洛 固 然 从 本能 上 , 对 母 亲 不 很 信 任 , 但 是 却 很 爱 她 , 而 且 也许 甚 至 是 比 爱 她 更 甚 , 他 是 困 惑 而 又 迷 恋 地 仰 慕她 , 就 如 同 仰 慕 一 个 习 惯 特 殊 、 脾 气 古 怪 的 大 姐姐 似 的 。 马 尔 切 洛 的 母 亲 在 非 常 年 轻 的 时 候 便 结了 婚 , 她 在 精 神 上 , 甚 至 是 在 肉 体 上 , 始 终 还 是个 女 孩 子 ; 此 外 , 她 虽 然 跟 这 个 儿 子 一 点 也 不 亲密 , 而 且 因 为 社 交 活 动 频 繁 , 她 也 极 少 照 顾 这 个儿 子 , 但 是 , 她 却 从 来 没 有 把 自 己 的 生 活 和 儿 子的 生 活 分 开 。 因 此 , 马 尔 切 洛 是 在 一 种 持 续 不 断的 乱 乱 哄 哄 的 环 境 下 长 大 的 : 母 亲 总 是 匆 匆 忙 忙地 进 进 出 出 , 总 是 在 试 衣 服 , 随 即 又 把 这 些 衣 服扔 掉 , 总 是 没 完 没 了 而 又 随 随 便 便 地 打 电 话 聊天 , 总 是 跟 裁 缝 和 供 应 商 使 性 耍 赖 , 跟 女 佣 吵 吵闹 闹 , 并 且 为 了 一 些 鸡 毛 蒜 皮 的 小 事 , 情 绪 不 断变 化 无 常 。 马 尔 切 洛 不 论 在 任 何 时 候 都 可 以 到 他母 亲 的 房 间 里 去 , 可 以 成 为 一 个 好 奇 而 又 无 知 的隐 私 旁 观 者 , 然 而 , 他 在 这 隐 私 中 却 又 是 没 有 任何 地 位 的 。 有 时 , 母 亲 像 是 突 然 感 到 内 疚 而 从 麻木 不 仁 中 惊 醒 过 来 , 于 是 决 定 要 关 照 一 下 儿 子 ,便 把 他 带 到 自 己 的 身 后 , 到 一 家 裁 缝 店 或 是 女 帽店 去 。 在 这 种 场 合 下 , 马 尔 切 洛 就 只 好 坐 在 一 个板 凳 上 , 度 过 好 几 个 钟 头 , 而 母 亲 则 在 试 着 帽 子和 衣 服 , 这 样 , 他 就 总 是 不 禁 怀 念 通 常 那 种 乱 糟糟 的 一 片 冷 漠 的 境 遇 了 。那 天 晚 上 , 正 像 他 马 上 懂 得 的 那 样 , 母 亲 比平 常 更 匆 忙 些 ; 的 确 , 马 尔 切 洛 还 没 有 来 得 及 克服 自 己 的 羞 怯 , 她 就 朝 他 背 转 身 去 , 穿 过 黑 暗 的房 间 , 走 到 始 终 是 虚 掩 着 的 房 门 。 但 是 , 马 尔 切洛 却 不 打 算 让 他 所 需 要 的 裁 决 再 等 上 一 天 了 。 他在 床 上 坐 起 身 来 , 大 声 叫 了 一 下 :“ 妈 妈 。”他 见 她 从 门 槛 上 转 过 身 来 , 做 了 一 个 几 乎 是厌 烦 的 手 势 。“ 怎 么 了 , 马 尔 切 洛 ?” 她 问 道 ,随 后 又 走 到 床 边 。这 时 , 她 站 在 他 的 身 旁 , 背 着 光 , 穿 着 一 件袒 胸 露 肩 的 黑 衣 服 , 显 得 那 么 白 , 那 么 瘦 。 她 那被 黑 头 发 围 拢 着 的 细 腻 而 苍 白 的 脸 , 隐 在 阴 影 当中 , 但 是 还 不 致 使 马 尔 切 洛 从 上 面 看 不 出 有 一 种不 悦 、 匆 忙 、 急 不 可 耐 的 表 情 。 然 而 , 他 在 自 己的 冲 动 情 绪 推 动 下 , 却 还 是 说 出 :“ 妈 妈 , 我 得跟 你 说 一 件 事 。”“ 好 吧 , 马 尔 切 洛 , 不 过 , 你 得 快 点 …… 妈妈 得 出 去 …… 爸 爸 在 等 着 呢 。” 这 时 , 她 用 两 只手 在 后 颈 上 , 在 项 链 的 链 扣 周 围 , 瞎 摸 乱 动 着 。马 尔 切 洛 想 要 向 母 亲 透 露 屠 杀 蜥 蜴 的 事 , 想要 问 她 : 他 这 样 做 是 不 是 很 坏 。 但 是 , 母 亲 急 匆匆 的 样 子 令 他 改 变 了 想 法 。 或 者 说 得 更 确 切 些 ,是 令 他 改 换 了 他 在 脑 海 中 酝 酿 好 的 那 句 话 。 他 突然 间 觉 得 , 那 些 蜥 蜴 无 非 是 一 些 过 于 渺 小 、 过 于无 足 轻 重 的 动 物 而 已 , 它 们 无 法 引 起 一 个 如 此 心不 在 焉 的 人 的 注 意 。 一 时 间 , 他 竟 编 造 出 一 句 谎话 ( 连 他 自 己 也 不 知 道 为 什 么 要 这 样 ), 夸 大 自己 的 罪 行 。 他 希 望 能 用 这 个 滔 天 的 罪 过 来 打 动 母亲 的 敏 感 性 , 因 为 他 模 模 糊 糊 地 猜 测 , 母 亲 的 敏感 性 是 很 迟 钝 的 , 很 麻 木 的 。 他 用 连 他 自 己 也 感到 惊 讶 的 自 信 语 气 说 道 :“ 妈 妈 , 我 杀 死 了 一 只猫 。”在 这 时 刻 , 母 亲 终 于 让 链 扣 的 两 个 部 分 对 到一 起 了 。 她 把 两 只 手 合 在 后 颈 上 , 下 巴 死 死 在 压在 胸 前 , 她 盯 视 着 地 上 , 不 时 , 由 于 急 躁 , 还 用鞋 跟 跺 着 地 板 。“ 啊 , 是 吗 ,” 她 用 毫 不 在 意的 声 音 说 道 , 这 声 音 像 是 因 为 她 在 努 力 扣 链 扣 而把 所 有 的 注 意 力 都 剔 除 掉 了 。 马 尔 切 洛 这 时 信 心不 足 了 , 他 又 说 了 一 句 :“ 我 是 用 弹 弓 打 死 它的 。”他 见 母 亲 灰 心 地 摇 了 摇 头 , 随 即 把 两 只 手 从后 颈 上 拿 下 来 , 一 只 手 里 还 握 着 那 条 她 没 有 能 够扣 上 的 项 链 。“ 这 该 死 的 链 扣 ,” 她 气 呼 呼 地 说道 。“ 马 尔 切 洛 …… 好 孩 子 …… 帮 我 把 这 条 项 链 戴上 吧 。” 她 坐 到 床 边 , 斜 着 身 子 , 背 向 着 儿 子 ,又 不 耐 烦 地 说 道 :“ 可 你 得 注 意 让 链 扣 扣 紧 ……不 然 , 它 会 又 翘 开 的 。”她 虽 然 在 说 着 话 , 却 把 那 瘦 瘦 的 肩 膀 摆 在 他的 面 前 , 那 肩 膀 赤 裸 裸 的 , 一 直 裸 露 到 腰 部 , 在来 自 房 门 的 光 线 映 照 下 , 白 得 像 纸 。 两 只 纤 细 的手 , 指 甲 又 尖 又 红 , 攥 住 那 条 悬 在 被 鬈 曲 的 茸 毛遮 掩 着 的 细 嫩 后 颈 上 的 宝 石 项 链 。 马 尔 切 洛 自 忖道 , 一 旦 把 项 链 扣 好 , 她 一 定 会 更 耐 心 地 听 他 讲话 ; 他 把 身 子 伸 过 去 , 拿 住 项 链 的 两 头 , 只 一 按就 把 两 头 接 上 了 。 但 是 , 母 亲 却 立 即 站 立 起 来 ,弯 下 身 来 , 用 一 个 亲 吻 轻 拂 了 一 下 他 的 脸 , 说道 :“ 谢 谢 …… 现 在 , 你 睡 觉 吧 …… 晚 安 。” 不 等马 尔 切 洛 能 够 用 一 个 动 作 或 一 声 叫 喊 把 她 留 住 ,她 就 已 经 跑 得 不 见 踪 影 了 。次 日 , 天 气 很 热 , 又 多 云 。 马 尔 切 洛 在 一 言不 发 的 父 母 中 间 静 静 地 吃 完 了 饭 之 后 , 悄 悄 地 从椅 子 上 溜 下 来 , 穿 过 落 地 窗 走 了 出 去 , 来 到 花园 。 像 往 常 一 样 , 消 化 使 他 感 到 浑 身 发 懒 , 很 不舒 服 , 同 时 又 觉 得 感 觉 迟 钝 , 有 些 反 胃 。 他 缓 缓地 走 着 , 差 不 多 是 在 踮 着 脚 尖 , 在 吱 吱 嘎 嘎 作 响的 鹅 卵 石 上 , 在 热 火 朝 天 地 爬 满 小 虫 子 的 树 荫下 走 着 , 他 一 直 走 到 铁 栅 栏 门 前 , 便 朝 下 面 望去 。 呈 现 在 他 眼 前 的 是 那 条 如 此 熟 悉 的 街 道 ,街 道 略 有 坡 度 , 两 旁 是 两 排 绿 茸 茸 的 、 几 乎 带 有乳 汁 色 的 胡 椒 树 , 街 道 在 这 个 时 候 没 有 任 何 行人 , 而 由 于 满 布 天 空 的 低 矮 乌 云 , 又 显 得 出 奇 地昏 暗 。 对 面 , 可 以 瞥 见 其 他 一 些 铁 栅 栏 门 、 其 他一 些 花 园 、 其 他 一 些 类 似 他 家 的 别 墅 。 马 尔 切 洛在 仔 细 地 观 察 了 一 下 这 条 街 道 之 后 , 便 离 开 铁 栅栏 门 , 从 衣 袋 里 拿 出 弹 弓 , 朝 地 面 俯 下 身 去 。 在那 些 细 小 的 鹅 卵 石 当 中 , 也 参 杂 着 一 些 较 大 的 白色 石 子 。 马 尔 切 洛 从 中 捡 起 一 块 有 核 桃 大 小 的 石子 , 把 它 放 到 弹 弓 的 皮 盘 上 , 他 开 始 顺 着 那 堵 把他 的 花 园 和 罗 贝 托 的 花 园 隔 开 的 墙 信 步 走 起 来 。他 的 想 法 , 或 者 说 得 更 确 切 些 , 是 他 的 情 感 , 这时 是 : 他 觉 得 自 己 是 和 罗 贝 托 处 于 战 争 状 态 , 他应 该 以 最 大 的 注 意 力 来 监 视 那 片 覆 盖 着 那 道 围 墙的 常 春 藤 , 稍 有 动 静 , 就 该 开 火 , 也 就 是 把 他 紧握 在 弹 弓 里 的 那 块 石 子 打 出 去 。 这 是 一 种 游 戏 ,但 他 在 其 中 却 既 表 达 对 罗 贝 托 的 怨 恨 ( 因 为 罗 贝托 不 愿 意 做 他 屠 杀 蜥 蜴 的 帮 凶 ), 又 表 达 那 种 驱使 他 对 晰 蝎 大 加 屠 戮 的 残 暴 的 兽 性 本 能 。 当 然 ,马 尔 切 洛 十 分 清 楚 , 罗 贝 托 是 习 惯 于 在 这 个 时 候睡 觉 的 , 因 此 , 他 不 会 从 那 片 常 春 藤 的 叶 丛 后 面偷 窥 自 己 ; 然 而 , 他 即 使 知 道 这 一 点 , 也 要 认 真而 彻 底 地 行 动 , 就 仿 佛 他 确 信 , 罗 贝 托 恰 恰 是 待在 那 里 的 。 那 片 常 春 藤 年 头 很 久 , 体 积 巨 大 , 一直 攀 援 到 铁 栅 栏 门 的 矛 形 装 饰 物 的 尖 端 , 那 些 叶片 , 相 互 重 叠 , 又 大 又 黑 , 满 是 尘 土 , 就 像 是 铺在 女 人 的 恬 静 胸 脯 上 的 圈 圈 花 边 饰 带 , 这 些 叶 片在 浓 重 而 无 风 的 空 气 中 静 止 不 动 , 松 松 软 软 。 有两 次 , 他 觉 得 , 似 乎 有 一 阵 极 为 轻 微 的 抖 动 使 叶丛 颤 动 起 来 , 或 者 说 得 更 确 切 些 , 是 他 无 中 生 有地 硬 让 自 己 以 为 是 看 见 了 这 个 抖 动 , 于 是 , 他 马上 就 抱 着 强 烈 的 满 意 心 情 , 把 石 子 打 进 常 春 藤 的密 叶 中 去 。打 出 之 后 , 他 就 赶 紧 俯 下 身 去 , 捡 起 另 一 块石 子 , 他 重 又 摆 好 战 斗 的 架 势 , 张 开 双 腿 , 双 臂前 伸 , 弹 弓 随 时 准 备 好 弹 射 : 人 们 永 远 无 法 知道 , 罗 贝 托 可 能 是 待 在 那 些 叶 子 后 面 , 正 在 向 他瞄 准 , 利 用 躲 在 暗 处 的 优 势 , 而 他 则 相 反 , 却 是完 全 暴 露 在 明 处 的 。 这 样 , 他 在 这 场 游 戏 中 , 就一 直 去 到 花 园 的 尽 头 , 在 那 里 , 他 曾 在 常 春 藤 的叶 丛 当 中 拨 出 那 扇 小 门 。 在 这 里 , 他 停 了 下 来 ,一 边 注 意 盯 视 着 那 堵 围 墙 。 在 他 的 幻 想 中 , 房 屋就 是 一 座 城 堡 , 被 攀 缘 植 物 隐 藏 起 来 的 铁 栅 门 就是 加 固 设 防 的 城 墙 , 而 那 个 门 洞 则 是 危 险 的 、 容易 被 人 穿 过 的 一 个 缺 口 。 这 时 , 他 突 然 看 见 ——这 一 回 是 没 有 任 何 怀 疑 的 可 能 了 —— 那 些 叶 子 在从 右 到 左 地 动 着 , 在 颤 抖 和 摇 晃 。 是 的 , 他 确 信36 37
这 一 点 , 那 些 叶 子 是 在 动 , 有 人 想 必 也 在 使 那 些叶 子 动 来 动 去 。 只 是 在 一 个 瞬 息 之 间 , 他 竟 想 到了 一 切 : 他 想 到 , 罗 贝 托 不 在 那 里 , 这 不 过 是 一场 游 戏 , 而 既 然 是 一 切 游 戏 , 他 就 可 以 把 石 子 打出 去 了 ; 与 此 同 时 , 他 又 想 到 , 罗 贝 托 恰 恰 就 在那 里 , 如 果 他 不 想 杀 死 罗 贝 托 , 就 不 该 把 石 子打 出 去 。 接 着 , 他 又 未 加 思 考 地 骤 然 拿 定 主 意 ,拉 直 两 条 皮 筋 , 把 石 子 打 进 茂 密 的 叶 丛 。 他 还 不满 足 , 便 俯 下 身 去 , 兴 奋 地 又 把 一 块 石 子 夹 到 弹弓 里 , 打 了 出 去 , 随 即 又 拿 起 第 三 块 石 子 , 也 把它 打 了 出 去 。 这 时 , 他 已 经 把 顾 虑 和 恐 惧 搁 置 一旁 , 对 他 来 说 , 罗 贝 托 在 不 在 那 里 , 已 经 不 再 重要 了 : 他 只 有 一 种 快 活 和 好 斗 的 冲 动 感 觉 。 最后 , 在 把 那 片 叶 丛 打 成 千 疮 百 孔 之 后 , 他 才 气 喘吁 吁 地 把 弹 弓 扔 到 地 上 , 一 直 爬 到 围 墙 上 面 。 正像 他 所 预 料 和 希 望 的 那 样 , 罗 贝 托 不 在 那 里 。 但是 , 铁 栅 栏 门 的 那 些 铁 棍 距 离 是 很 宽 的 , 能 让 人把 脑 袋 伸 到 隔 壁 的 花 园 里 。 他 在 他 也 不 知 道 是 什么 好 奇 心 的 激 发 下 , 便 把 脸 探 了 过 去 , 并 且 朝 下面 看 了 看 。在 罗 贝 托 的 花 园 那 一 边 , 没 有 攀 缘 植 物 , 而是 有 一 个 种 植 着 蝴 蝶 兰 的 花 坛 , 这 个 花 坛 在 围 墙和 鹅 卵 石 林 荫 小 路 之 间 伸 展 开 来 。 这 时 , 马 尔 切洛 恰 恰 从 他 的 眼 睛 底 下 , 在 围 墙 和 一 排 白 紫 两 色的 蝴 蝶 兰 中 间 , 看 见 有 一 只 灰 色 的 大 猫 侧 身 倒 卧着 。 一 阵 无 名 的 恐 怖 打 断 了 他 的 呼 吸 , 因 为 他 看出 , 那 只 猫 的 姿 态 是 很 不 自 然 的 : 它 侧 在 一 边 躺倒 , 四 只 爪 子 伸 长 并 放 松 , 嘴 脸 瘫 在 地 面 上 。 猫毛 很 密 , 呈 蓝 灰 色 , 略 显 竖 立 和 蓬 乱 , 同 时 还 显得 呆 滞 , 就 像 某 些 死 禽 的 羽 毛 , 他 以 前 在 厨 房 的大 理 石 桌 子 上 曾 见 识 过 。 这 时 , 恐 怖 在 增 长 : 他跳 到 地 上 , 从 一 个 玫 瑰 花 圃 里 抽 出 一 根 支 杆 , 随即 重 又 爬 到 墙 上 , 他 把 胳 臂 从 铁 棍 中 间 伸 过 去 ,设 法 用 支 杆 的 沾 满 泥 土 的 尖 头 捅 捅 猫 的 侧 身 。 但是 , 猫 没 有 动 , 突 然 间 , 那 些 围 绕 着 那 个 一 动 不动 的 灰 色 身 体 、 有 高 高 的 绿 色 茎 秆 、 斜 垂 着 白 紫两 色 花 冠 的 蝴 蝶 兰 , 在 他 看 来 , 竟 像 是 用 于 丧 葬的 花 圈 , 像 是 由 一 只 怜 悯 的 手 放 到 一 个 尸 体 周 围的 许 许 多 多 的 鲜 花 。 他 马 上 扔 掉 那 根 支 杆 , 也 顾不 得 把 常 春 藤 恢 复 原 状 , 便 跳 到 地 上 。他 感 到 自 己 被 形 形 色 色 的 恐 怖 所 吞 噬 , 而 他首 先 产 生 的 冲 动 情 绪 就 是 要 跑 到 一 个 衣 橱 里 , 一个 储 藏 室 里 , 总 之 , 要 跑 到 任 何 一 个 有 黑 暗 、 能禁 闭 的 地 方 , 把 自 己 关 起 来 , 以 求 逃 避 自 己 。他 之 所 以 感 到 恐 怖 , 首 先 是 因 为 他 杀 了 那 只 猫 ,其 次 则 是 —— 也 许 是 在 更 大 的 程 度 上 是 如 此 ——因 为 他 昨 天 晚 上 曾 向 母 亲 说 过 : 他 杀 死 一 只 猫 :这 无 疑 是 一 个 迹 象 : 说 明 他 是 神 秘 莫 测 、 无 法 避免 地 命 定 要 做 出 残 暴 杀 戮 的 事 情 来 的 。 但 是 , 这只 猫 的 死 以 及 这 样 的 无 所 预 示 的 意 昧 深 长 的 警 告在 他 身 上 引 起 的 恐 怖 , 却 远 远 超 过 这 样 一 个 想法 促 使 他 产 生 的 那 种 恐 怖 : 他 想 到 , 在 杀 死 猫的 同 时 , 他 实 际 上 是 打 算 杀 死 罗 贝 托 。 只 是 因 为事 出 偶 然 , 这 只 猫 才 代 替 这 位 朋 友 而 一 命 呜 呼 。不 过 , 这 种 偶 然 性 却 并 非 没 有 其 含 义 的 ; 无 法 否认 的 是 : 这 是 一 个 渐 进 的 过 程 , 从 鲜 花 到 蜥 蜴 ,从 蜥 蝎 到 猫 , 从 猫 又 到 罗 贝 托 , 杀 死 罗 贝 托 是 他想 到 的 和 希 望 的 , 尽 管 他 没 有 做 到 , 然 而 却 是 可以 做 到 的 , 也 许 还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 如 此 说 来 , 他确 是 一 个 反 常 的 人 , 他 不 能 不 想 到 , 或 者 说 得 更确 切 些 , 是 不 能 不 带 着 对 这 种 反 常 状 态 的 强 烈 而具 体 的 觉 悟 感 受 到 : 他 是 一 个 注 定 要 有 一 个 孤 单奋 战 和 屡 逢 凶 险 的 命 运 、 并 且 已 经 走 上 一 条 血 腥道 路 的 反 常 的 人 , 没 有 任 何 人 力 能 使 他 在 这 条 血腥 道 路 上 停 下 来 。 他 这 样 前 思 后 想 着 , 兀 自 发 狂似 的 在 房 屋 和 铁 栅 栏 门 中 间 的 那 块 小 小 的 空 间 里转 来 转 去 , 不 时 还 抬 起 眼 睛 , 看 看 那 座 小 别 墅 的一 个 个 窗 户 , 几 乎 是 盼 望 能 从 那 里 看 到 他 的 那 位轻 率 而 冒 失 的 母 亲 的 身 影 出 现 : 不 过 , 如 今 , 她已 经 不 再 能 为 他 做 任 何 事 了 , 即 使 她 原 本 是 有 能力 做 些 什 么 。 接 着 , 他 突 然 又 抱 起 希 望 , 再 次 跑到 花 园 的 尽 头 , 一 直 爬 到 围 墙 , 从 铁 栅 栏 门 的 那些 铁 棍 中 间 探 过 脸 去 。 他 几 乎 是 幻 想 能 发 现 , 原来 他 看 见 有 那 只 没 有 生 气 的 猫 的 地 方 , 现 在 则 是空 荡 荡 的 了 。 相 反 , 那 只 猫 却 没 有 走 掉 , 它 一 直待 在 那 里 , 在 那 些 白 紫 两 色 蝴 蝶 兰 的 吊 唁 花 圈 的围 拢 下 , 仍 是 灰 灰 的 , 一 动 不 动 。 那 死 亡 已 经 给人 一 种 正 在 腐 烂 的 兽 尸 那 样 的 可 怖 感 觉 , 这 从 一条 由 蚂 蚁 拼 成 的 黑 色 带 子 得 到 证 实 , 因 为 这 些 蚂蚁 从 林 荫 小 路 出 发 , 逐 渐 爬 上 花 坛 , 一 直 爬 到 这个 畜 牲 的 嘴 脸 , 甚 至 爬 到 眼 睛 上 。 他 在 注 视 着 ,突 然 之 间 , 几 乎 像 是 出 现 叠 印 效 果 似 的 , 他 觉 得自 己 看 见 的 不 是 那 只 猫 , 而 是 罗 贝 托 , 他 也 躺 倒在 那 些 蝴 蝶 兰 中 间 , 他 也 是 毫 无 生 气 , 而 且 那 群蚂 蚁 也 从 他 那 失 神 的 眼 睛 和 半 张 的 嘴 巴 上 来 来 去去 , 走 个 不 停 。 他 顿 觉 毛 发 竖 立 , 打 了 一 个 寒噤 , 他 不 再 让 自 己 把 这 种 可 怕 的 景 象 看 下 去 了 ,他 跳 了 下 去 。 但 是 , 这 一 回 , 他 却 注 意 把 那 扇 常春 藤 小 门 拉 到 原 处 。 因 为 这 时 , 除 了 他 自 身 的 懊悔 和 恐 怖 之 外 , 他 还 害 怕 会 被 人 发 现 , 遭 到 惩处 。然 而 , 他 虽 然 害 怕 被 发 现 被 惩 处 ; 却 也 感到 , 自 己 同 时 又 渴 望 被 发 现 被 惩 处 ; 这 不 过 是 为了 让 人 及 时 地 把 自 己 在 滑 坡 上 阻 挡 住 , 因 为 他 觉得 , 在 这 滑 坡 的 尽 头 , 不 可 避 免 地 必 然 有 杀 人 的罪 行 在 等 待 他 。 但 是 , 根 据 他 的 记 忆 , 父 母 是 从来 没 有 惩 罚 过 他 的 ; 这 倒 不 是 出 于 什 么 排 除 惩 罚的 教 育 理 念 , 而 是 , 像 他 模 模 糊 糊 地 了 解 的 那样 , 是 出 于 漠 不 关 心 。 这 样 一 来 , 除 了 他 因 为 怀疑 自 己 是 一 桩 罪 行 的 元 凶 、 特 别 是 怀 疑 自 己 还 会犯 下 其 他 更 严 重 的 罪 行 而 感 到 的 那 种 痛 苦 之 外 ,又 增 添 了 另 一 种 痛 苦 : 那 就 是 , 他 不 知 道 要 去找 谁 , 来 让 对 方 惩 罚 自 己 , 他 甚 至 不 晓 得 这 惩 罚可 能 会 是 什 么 样 的 。 马 尔 切 洛 含 含 糊 糊 地 明 白 ,曾 推 动 过 他 的 那 股 动 力 , 亦 即 推 动 他 把 自 己 的 罪过 向 罗 贝 托 吐 露 出 来 、 从 而 希 望 听 到 对 方 告 诉 自己 这 不 算 是 什 么 罪 过 、 而 是 一 件 大 家 都 在 干 的 普通 的 事 的 那 股 动 力 , 现 在 则 是 在 启 示 他 去 向 父 母做 同 样 的 吐 露 , 不 过 , 他 所 抱 的 希 望 却 应 该 是 相反 的 : 那 就 是 希 望 看 到 父 母 能 愤 怒 地 呼 叫 起 来 ,说 他 犯 了 一 个 可 怕 的 罪 行 , 因 此 , 他 应 该 受 到 适当 的 惩 处 。 而 对 他 来 说 , 这 两 种 情 况 都 是 无 所 谓的 : 尽 管 在 第 一 种 情 况 下 , 罗 贝 托 对 他 的 宽 恕 是会 鼓 励 他 再 重 复 干 他 所 干 的 那 件 事 , 而 在 第 二 种情 况 下 , 他 所 干 的 那 件 事 却 相 反 会 使 他 受 到 严 厉的 谴 责 。 其 实 , 他 很 明 白 , 在 这 两 种 情 况 下 , 他都 是 想 要 不 惜 一 切 代 价 , 不 择 任 何 手 段 , 来 摆 脱反 常 这 种 可 怕 的 孤 立 状 态 的 。如 果 就 在 那 当 天 晚 上 , 他 没 有 感 到 父 母 已 经知 道 所 有 的 事 情 的 话 , 他 本 来 也 许 会 下 决 心 向 他们 坦 白 交 待 杀 猫 这 件 事 的 。 的 确 , 当 他 坐 到 饭 桌前 的 时 候 , 他 曾 带 着 混 杂 着 惊 骇 和 很 不 放 心 的感 觉 , 看 出 父 亲 和 母 亲 似 乎 都 满 怀 敌 意 , 情 绪 恶劣 。 母 亲 的 那 张 天 真 灿 烂 的 脸 摆 出 一 种 过 分 庄 重的 样 子 , 她 挺 直 腰 板 , 双 眼 下 垂 , 傲 气 十 足 , 一言 不 发 。 在 她 的 对 面 , 父 亲 则 通 过 种 种 不 同 的 、却 都 能 同 样 说 明 问 题 的 迹 象 , 表 现 出 类 似 的 恶 劣心 情 。 父 亲 比 母 亲 年 长 许 多 岁 , 他 往 往 使 马 尔切 洛 惊 慌 失 措 地 感 到 , 自 己 是 和 母 亲 归 到 一 起的 , 都 有 同 样 的 一 种 幼 稚 的 和 受 人 辖 制 的 神 情 ,就 好 像 她 不 是 他 的 母 亲 , 而 是 他 的 姐 姐 。 父 亲 很瘦 , 一 张 脸 又 干 又 布 满 皱 纹 , 很 少 能 因 为 并 非 真正 高 兴 地 短 短 笑 上 几 声 而 焕 发 出 光 彩 , 在 这 张 脸上 , 有 两 个 被 一 种 不 容 置 疑 的 纽 带 联 系 在 一 起 的特 点 十 分 惹 人 注 目 : 一 个 是 那 双 突 出 的 眼 珠 的 毫无 表 情 、 几 乎 像 是 矿 物 质 的 闪 闪 发 光 , 一 个 则 是人 们 弄 不 清 楚 是 哪 根 紧 张 的 神 经 在 一 个 面 颊 的 紧绷 皮 肤 底 下 的 频 频 抽 动 。 也 许 他 有 许 多 年 是 在 军队 里 度 过 的 , 因 此 , 他 保 留 了 对 准 确 的 动 作 、 对有 节 制 的 姿 态 的 爱 好 。 但 是 , 马 尔 切 洛 知 道 , 当他 的 父 亲 发 起 怒 来 的 时 候 , 准 确 和 节 制 就 会 变 得过 火 了 , 从 而 变 成 其 反 面 , 也 就 是 说 , 变 成 一 种受 到 控 制 、 动 作 得 当 的 奇 特 的 粗 暴 态 度 , 有 人 会说 , 这 种 粗 暴 态 度 是 要 使 那 些 最 简 单 的 动 作 也 有其 涵 义 。 因 而 , 那 天 晚 上 , 在 饭 桌 上 , 马 尔 切 洛马 上 看 出 , 父 亲 是 在 用 力 强 调 一 些 平 常 的 、 没 有任 何 重 要 意 义 的 行 动 , 几 乎 像 是 要 把 别 人 的 注 意力 吸 引 到 这 些 行 动 上 去 。 比 如 说 吧 , 他 拿 起 杯子 , 喝 了 一 口 , 然 后 重 重 地 在 桌 子 上 敲 了 一 下 ,放 回 原 处 ; 他 寻 找 盐 罐 子 , 从 里 面 拿 出 一 丁 点 盐来 , 然 后 , 在 放 罐 子 的 时 候 , 又 是 重 重 的 一 下 ,放 下 去 ; 他 抓 起 面 包 , 把 它 撕 成 碎 片 , 接 着 来 了一 个 重 重 的 第 三 下 , 把 它 放 下 。 要 么 则 是 , 他 像是 突 然 热 衷 于 求 得 对 称 , 于 是 一 个 劲 地 用 那 种 砰砰 摔 东 西 的 惯 常 动 作 , 把 碟 子 端 端 正 正 地 放 到 餐具 中 间 , 让 刀 、 叉 和 勺 子 围 绕 着 那 圆 圆 的 盘 子 连成 直 角 。 如 果 马 尔 切 洛 不 是 因 为 自 己 的 罪 过 而 感到 十 分 忧 虑 的 话 , 他 本 来 会 不 难 发 现 , 这 些 如 此意 味 深 长 和 装 腔 作 势 的 强 硬 动 作 , 并 不 是 冲 着 他来 的 , 而 是 针 对 他 的 母 亲 ; 果 然 , 在 那 些 砰 砰 摔东 西 的 动 作 每 做 一 次 的 时 候 , 她 都 再 度 拿 起 自 己的 庄 重 架 势 , 并 且 还 得 意 地 叹 叹 气 , 带 着 容 忍 冒犯 的 神 情 抬 抬 眉 毛 。 但 是 , 马 尔 切 洛 的 忧 虑 心 情却 使 他 视 而 不 见 , 因 此 , 他 毫 不 怀 疑 : 父 母 是 已经 知 道 所 有 的 事 情 了 : 可 以 肯 定 , 罗 贝 托 从 他 原来 作 为 的 兔 子 , 已 经 变 成 了 奸 细 。 马 尔 切 洛 本 来是 希 望 受 到 惩 罚 的 , 但 是 现 在 , 他 既 然 看 见 父 母是 如 此 愠 怒 , 便 突 然 间 想 起 他 的 父 亲 在 这 种 情 况下 会 采 取 什 么 暴 力 行 为 而 不 禁 战 慄 起 来 。 正 像 母亲 的 温 情 表 现 总 是 不 稳 定 的 , 偶 然 的 , 很 明 显 是更 多 地 出 于 内 疚 而 不 是 出 于 母 爱 , 同 样 , 父 亲 的严 厉 作 风 也 是 突 然 的 , 无 理 的 , 过 分 的 , 有 人 会说 , 之 所 以 有 这 种 作 风 , 与 其 说 是 因 为 父 亲 打 算教 育 他 , 倒 不 如 说 是 因 为 父 亲 在 长 期 对 他 漠 不 关心 之 后 , 想 要 重 新 调 整 一 下 自 己 的 态 度 。 往 往 是突 然 之 间 , 由 于 母 亲 或 厨 娘 说 了 什 么 抱 怨 的 话 ,父 亲 就 会 想 起 自 己 还 有 一 个 儿 子 , 于 是 便 吼 叫 起来 , 大 动 肝 火 , 把 儿 子 痛 打 一 顿 。 尤 其 令 马 尔 切洛 害 怕 的 是 那 一 下 一 下 的 殴 打 , 因 为 父 亲 的 小 指上 戴 着 一 只 戒 指 , 戒 指 上 有 一 个 镶 大 宝 石 的 地方 , 在 父 亲 发 火 揍 他 时 , 也 不 知 道 是 怎 么 回 事 ,那 镶 宝 石 的 地 方 总 是 会 转 到 手 掌 这 一 边 , 这 样 一来 , 就 在 凌 辱 人 的 重 重 一 记 耳 光 之 上 又 平 添 了 一阵 更 加 钻 心 的 痛 楚 。 马 尔 切 洛 常 怀 疑 , 父 亲 是 故意 把 那 个 镶 宝 石 的 地 方 转 到 里 面 来 的 , 但 是 , 他对 此 却 又 没 有 什 么 把 握 。出 于 惊 吓 和 恐 惧 , 他 开 始 急 匆 匆 地 编 造 一 个说 得 过 去 的 谎 言 : 他 没 有 杀 死 那 只 猫 , 杀 死 猫 的是 罗 贝 托 , 本 来 嘛 , 那 只 猫 是 在 罗 贝 托 的 花 园 里的 , 而 他 又 怎 么 能 穿 过 常 春 藤 和 围 墙 去 把 那 只猫 杀 死 呢 ? 但 是 , 接 着 他 又 突 然 想 起 , 头 一 天 晚上 , 他 曾 向 母 亲 说 过 杀 猫 的 事 , 后 来 第 二 天 , 这件 事 果 然 就 发 生 了 , 于 是 , 他 明 白 , 无 论 什 么 谎言 , 对 他 来 说 , 都 是 行 不 通 的 。 他 的 母 亲 , 尽 管是 心 不 在 焉 , 却 肯 定 已 经 把 他 向 她 坦 白 交 代 的 话告 诉 了 父 亲 , 而 父 亲 , 可 以 同 样 肯 定 , 已 经 在 他的 坦 白 交 代 和 罗 贝 托 的 告 状 二 者 之 间 建 立 了 某 种联 系 ; 这 样 , 就 没 有 任 何 矢 口 否 认 的 可 能 了 。 想到 这 里 , 他 又 从 一 个 极 端 转 到 另 一 个 极 端 , 他 再次 冲 动 起 来 , 希 望 受 到 惩 罚 , 只 要 这 个 惩 罚 来 得快 些 , 并 且 是 决 定 性 的 。 是 什 么 惩 罚 呢 ? 他 想起 , 罗 贝 托 有 一 天 曾 谈 到 寄 宿 学 校 , 说 那 里 是 父母 把 调 皮 的 儿 女 送 去 受 惩 罚 的 地 方 , 而 且 他 感 到吃 惊 , 竟 发 现 自 己 是 热 切 地 盼 望 去 受 这 种 处 罚 。从 这 种 盼 望 中 表 达 出 来 的 正 是 对 混 乱 无 序 、 缺 少温 情 的 家 庭 生 活 所 感 到 的 那 种 不 自 觉 的 厌 倦 ; 这使 他 不 仅 渴 望 得 到 被 父 母 看 成 是 一 种 惩 罚 的 那 个东 西 , 而 且 还 促 使 他 欺 骗 自 己 , 欺 骗 他 自 己 对 这种 惩 罚 的 需 要 , 因 为 他 几 乎 是 在 狡 猾 地 盘 算 着 :这 样 一 来 , 他 就 会 同 时 做 到 : 既 平 息 自 己 的 内疚 , 又 改 善 自 己 的 处 境 。 这 个 想 法 马 上 使 他 联 想到 一 些 情 景 , 这 些 情 景 本 来 应 该 是 令 他 沮 丧 的 ,38 39
然 而 却 令 他 很 高 兴 , 这 些 情 景 就 是 : 一 座 有 安 装着 铁 条 的 大 窗 户 的 严 肃 而 阴 险 的 灰 色 建 筑 物 ; 一些 在 高 高 的 白 墙 下 面 摆 着 一 排 排 床 的 冰 冷 而 没 有任 何 装 饰 的 宿 舍 ; 一 些 摆 满 了 课 桌 、 讲 台 则 设 在尽 头 的 黯 淡 萧 索 的 教 室 ; 一 些 光 秃 秃 的 过 道 、 黑黢 黢 的 楼 梯 、 大 而 笨 重 的 房 门 、 无 法 逾 越 的 铁 栅栏 门 : 总 而 言 之 , 像 是 在 一 个 监 狱 里 , 不 过 , 这个 监 狱 却 比 父 亲 家 里 的 那 种 不 牢 靠 的 、 令 人 提 心吊 胆 的 、 难 以 维 持 长 久 的 自 由 要 胜 强 多 多 。 甚 至那 种 关 于 要 穿 上 带 一 道 道 条 纹 的 制 服 、 要 剃 光 脑袋 、 如 同 他 有 时 在 街 上 遇 见 的 排 成 纵 队 的 寄 宿 学校 学 生 的 想 法 , 甚 至 这 种 令 人 感 到 凌 辱 、 几 乎 是令 人 感 到 恶 心 的 想 法 , 也 使 他 觉 得 高 兴 , 因 为 他现 在 是 那 么 近 乎 绝 望 地 憧 憬 任 何 一 种 秩 序 和 任 何一 种 正 常 状 态 。在 这 种 胡 思 乱 想 当 中 , 他 不 再 去 看 父 亲 了 ,而 是 注 视 着 那 发 射 着 耀 眼 的 白 光 的 台 布 , 在 那 台布 上 , 不 时 有 从 那 扇 大 开 的 窗 户 飞 进 来 、 撞 上 电灯 的 灯 罩 的 夜 蛾 在 挣 扎 着 。 接 着 , 他 又 抬 起 眼睛 , 恰 好 及 时 地 看 到 正 是 在 他 的 父 亲 后 面 , 在 窗台 上 , 有 一 只 猫 的 侧 影 。 但 是 , 那 畜 牲 却 在 他 能辨 出 它 的 颜 色 之 前 就 跳 下 来 了 , 它 穿 过 餐 厅 , 消失 在 厨 房 那 一 边 。 虽 然 他 对 此 没 有 完 全 的 把 握 ,然 而 他 的 心 却 充 满 了 愉 快 的 希 望 , 因 为 他 想 道 ,这 可 能 就 是 那 只 几 个 钟 头 以 前 他 看 到 一 动 不 动 地倒 在 罗 贝 托 花 园 里 的 那 些 蝴 蝶 兰 当 中 的 猫 。 他 因为 有 了 这 个 希 望 而 感 到 高 兴 , 这 表 明 : 不 论 如何 , 那 只 动 物 的 生 命 , 要 比 他 自 己 的 命 运 , 更 令他 感 到 关 切 。“ 那 猫 ,” 他 大 声 惊 呼 起 来 。 他 随即 把 餐 巾 扔 到 饭 桌 上 , 把 一 条 腿 伸 到 椅 子 外 面 :“ 爸 爸 , 我 吃 完 了 , 我 可 以 起 来 吗 ?”“ 你 就 待 在 你 的 位 子 上 ,” 父 亲 用 威 吓 的 声音 说 道 。 马 尔 切 洛 被 吓 住 了 , 他 冒 昧 地 说 道 :“ 可 那 猫 还 活 着 呢 ……”“ 我 已 经 跟 你 说 了 : 待 在 你 的 位 子 上 ,” 父亲 又 说 了 一 句 。 接 着 , 就 好 像 马 尔 切 洛 的 话 似 乎对 他 来 说 , 也 算 是 打 破 了 长 时 间 的 缄 默 , 他 便 朝着 妻 子 转 过 身 去 , 说 道 :“ 那 么 , 你 就 说 些 什 么吧 , 说 吧 。”“ 我 没 有 什 么 可 说 的 ,” 她 有 意 摆 出 一 副 庄重 的 姿 态 答 道 , 眼 皮 下 垂 , 撇 着 嘴 巴 。 她 身 穿 一件 夜 礼 服 , 黑 色 的 , 袒 胸 露 肩 ; 马 尔 切 洛 注 意到 , 她 那 瘦 瘦 的 手 指 中 间 紧 握 着 一 条 小 手 帕 , 她屡 屡 地 把 手 绢 放 到 鼻 子 上 ; 她 用 另 一 只 手 掌 抓 起一 片 面 包 , 随 即 又 扔 到 桌 子 上 , 不 过 , 她 抓 面 包并 不 是 用 手 指 , 而 是 用 指 甲 尖 , 那 指 甲 尖 简 直 就像 一 只 鸟 儿 。“ 可 你 该 把 你 要 说 的 说 出 来 嘛 …… 说 吧 ……嗨 。”“ 跟 你 我 没 有 什 么 话 可 说 。”马 尔 切 洛 这 才 开 始 明 白 , 杀 猫 并 不 是 父 母 情绪 不 好 的 原 因 , 而 这 时 , 突 然 间 , 一 切 都 似 乎 在急 转 直 下 。 父 亲 又 一 次 重 复 一 遍 :“ 说 吧 , 哎呀 ”, 母 亲 呢 , 作 为 全 部 回 答 , 却 只 是 耸 了 耸肩 ; 于 是 , 父 亲 拿 起 了 摆 在 碟 子 前 面 的 高 脚 杯 ,大 声 喊 道 :“ 你 到 底 想 不 想 说 ?” 随 即 用 力 把 杯子 放 到 桌 子 上 。 杯 子 碰 碎 了 , 父 亲 骂 了 一 声 , 把受 伤 的 手 放 到 嘴 上 , 母 亲 吓 了 一 大 跳 , 忙 从 桌 前站 了 起 来 , 匆 匆 走 向 门 口 。 父 亲 几 乎 像 是 津 津 有味 地 吸 着 手 上 的 血 , 他 在 手 的 上 方 扬 起 两 条 眉毛 ; 但 是 , 他 看 到 妻 子 正 在 走 开 , 便 不 再 吸 血 ,向 她 喊 道 :“ 我 不 准 你 走 …… 你 明 白 的 。” 作 为回 答 的 却 是 用 力 摔 门 的 砰 的 一 声 。 父 亲 也 站 起 身来 , 向 门 口 冲 去 。 马 尔 切 洛 在 这 番 情 景 的 猛 烈 冲击 下 , 也 激 动 起 来 , 便 跟 着 父 亲 跑 过 去 。父 亲 这 时 已 经 走 上 楼 梯 , 一 只 手 扶 着 楼 梯 扶手 , 他 不 动 声 色 , 表 面 上 也 不 慌 不 忙 ; 但 是 , 马尔 切 洛 跟 在 他 的 后 面 , 却 眼 见 他 是 在 两 级 两 级 地迈 上 楼 梯 , 几 乎 像 是 在 默 默 地 飞 向 楼 道 ; 他 不 禁想 道 , 父 亲 简 直 就 像 一 个 穿 着 有 七 里 格 长 的 靴 子的 童 话 里 的 吃 人 妖 怪 ; 他 片 刻 也 不 曾 怀 疑 , 这 种盘 算 好 的 、 步 步 进 逼 的 上 楼 法 必 将 胜 过 母 亲 的 那种 急 忙 而 凌 乱 的 步 法 , 而 母 亲 却 只 是 稍 微 在 上 面一 些 , 正 在 一 级 一 级 地 迈 着 梯 阶 逃 跑 呢 , 况 且 ,她 那 瘦 窄 的 裙 子 还 绊 着 她 的 双 腿 。“ 现 在 , 他 要宰 了 她 了 ,” 他 紧 跟 着 父 亲 , 一 边 想 道 。 母 亲 来到 楼 道 , 一 阵 小 跑 , 跑 到 她 的 房 间 , 但 是 , 她 却跑 得 不 够 迅 速 , 没 有 能 够 阻 挡 住 丈 夫 跟 在 她 背 后从 门 缝 里 钻 进 去 。 所 有 这 些 情 况 马 尔 切 洛 都 看 到眼 里 , 尽 管 他 是 用 他 那 小 孩 子 的 一 双 短 腿 上 楼的 , 这 双 短 腿 既 不 容 许 他 像 父 亲 那 样 一 步 迈 两 级地 上 楼 , 又 不 容 许 他 像 母 亲 那 样 急 匆 匆 地 跳 跳 蹦蹦 上 楼 。 等 他 来 到 楼 道 时 , 他 才 注 意 到 , 刚 才 那种 乱 糟 糟 的 追 踪 声 响 , 现 在 却 奇 怪 地 被 突 然 的 一片 寂 静 所 取 代 了 。 母 亲 房 间 的 房 门 在 敞 开 着 。 马尔 切 洛 有 点 犹 豫 不 决 地 来 到 门 口 。起 初 , 他 只 看 见 在 半 明 半 暗 的 房 间 尽 头 , 在那 宽 阔 而 低 矮 的 床 两 边 , 有 那 两 扇 窗 户 的 两 大 幅朦 朦 胧 胧 的 窗 帘 , 这 两 幅 窗 帘 被 吹 进 房 间 里 的 一阵 风 掀 起 , 朝 上 掀 啊 掀 , 掀 向 天 花 板 , 甚 至 几 乎要 拂 到 位 于 中 央 的 那 盏 灯 。 这 两 幅 窗 帘 是 那 么 静悄 悄 的 , 在 黑 暗 的 房 间 里 , 在 半 空 中 发 着 白 光 ,从 而 使 人 产 生 一 种 荒 凉 的 感 觉 , 就 好 像 马 尔 切 洛的 父 母 在 你 逃 我 追 的 同 时 , 竟 然 从 大 开 的 窗 户 里飞 到 外 面 去 , 飞 到 夏 日 的 夜 色 当 中 。 接 着 , 在 那束 从 过 道 穿 过 房 门 、 一 直 射 到 床 上 的 光 芒 里 , 他终 于 发 现 了 父 母 。 或 者 说 得 更 确 切 些 , 他 是 只 看见 父 亲 的 脊 背 , 在 父 亲 下 面 , 母 亲 几 乎 完 全 消 失了 , 除 了 因 为 有 那 些 披 散 在 枕 头 上 的 头 发 和 一 条抬 向 床 头 板 的 胳 臂 。 这 条 胳 臂 在 痉 挛 地 设 法 用 手抓 住 床 头 板 , 但 是 却 没 有 抓 住 ; 而 这 时 , 父 亲 则用 力 把 妻 子 的 身 体 压 在 自 己 的 身 体 下 面 , 用 双 肩和 双 手 做 出 一 些 动 作 , 就 好 像 他 要 把 妻 子 扼 死 。“ 他 是 在 杀 死 她 啊 ,” 马 尔 切 洛 确 信 无 疑 地 想道 , 他 一 直 站 在 门 口 。 就 在 那 一 刻 , 他 竟 感 到 一阵 非 同 寻 常 的 凶 狠 残 暴 的 冲 动 , 同 时 还 产 生 一 种想 要 参 与 斗 殴 的 强 烈 愿 望 , 连 他 自 己 也 不 知 道 是要 给 父 亲 帮 大 忙 还 是 要 保 卫 母 亲 。 与 此 同 时 , 又有 一 种 希 望 在 向 他 微 笑 : 他 希 望 能 通 过 这 个 更 严重 得 多 的 罪 行 , 看 到 自 己 的 罪 行 被 一 笔 抹 煞 : 的确 , 和 杀 死 一 个 女 人 相 比 , 杀 死 一 只 猫 又 算 得 了什 么 呢 ? 但 是 , 恰 恰 在 他 克 服 了 最 后 一 点 犹 豫 、被 暴 力 弄 得 迷 迷 糊 糊 、 一 心 只 想 跃 跃 欲 试 、 正 在离 开 门 槛 的 那 一 刻 , 他 却 听 见 母 亲 的 声 音 , 那 声音 丝 毫 没 有 被 掐 住 , 反 而 几 乎 像 是 十 分 柔 和 , 它慢 慢 地 悄 悄 说 了 一 句 :“ 放 开 我 吧 。” 而 与 这 个请 求 相 反 的 却 是 , 刚 才 一 直 被 她 抬 起 来 摸 索 床 头板 边 缘 的 那 条 胳 臂 , 这 时 却 放 了 下 来 , 搂 住 了 丈夫 的 后 颈 。 马 尔 切 洛 感 到 很 惊 奇 , 甚 而 几 乎 是 感到 失 望 , 他 后 退 了 几 步 , 走 出 房 间 , 来 到 过 道 。他 轻 而 又 轻 地 , 力 求 在 楼 梯 上 不 弄 出 响 声 ,下 到 底 层 , 并 且 朝 着 厨 房 走 去 。 现 在 , 原 来 那 个好 奇 心 —— 即 想 知 道 方 才 在 餐 厅 里 从 窗 口 跳 下 的那 只 猫 是 否 就 是 他 害 怕 被 自 己 一 手 杀 死 的 那 只猫 —— 又 在 刺 激 着 他 了 。 他 推 开 厨 房 的 门 , 出 现在 他 眼 前 的 是 一 派 安 详 的 家 庭 景 象 : 那 已 到 中 年的 厨 娘 和 那 青 春 年 少 的 女 佣 正 坐 在 大 理 石 桌 前 ,在 洁 白 的 厨 房 里 , 在 电 气 炉 灶 和 冰 箱 之 间 吃 着 东西 。 而 在 地 上 , 在 窗 户 底 下 , 那 只 猫 则 在 一 心 一意 地 用 粉 红 色 舌 头 舔 着 一 个 小 碗 里 的 牛 奶 。 但是 , 正 像 他 马 上 就 失 望 地 看 出 来 的 , 这 不 是 那 只灰 色 的 猫 , 而 是 一 只 完 全 不 同 的 带 花 纹 的 猫 。因 为 他 不 知 道 如 何 来 说 明 他 来 厨 房 的 理 由 ,他 便 去 到 猫 的 跟 前 , 蹲 下 来 , 摸 了 摸 猫 的 背 。 那猫 虽 然 没 有 停 止 舔 奶 , 却 开 始 呼 噜 呼 噜 地 发 起 怒来 。 厨 娘 站 起 身 来 , 去 把 房 门 关 上 。 接 着 , 她开 开 冰 箱 , 从 里 面 拿 出 一 个 摆 着 一 片 点 心 的 碟子 , 她 把 碟 子 放 在 桌 上 , 移 过 来 一 把 椅 子 , 对 马尔 切 洛 说 道 :“ 你 想 不 想 吃 一 点 昨 天 晚 上 的 点心 ?…… 我 是 专 门 给 你 留 着 的 。” 马 尔 切 洛 话 也没 有 说 , 便 坐 下 来 , 开 始 吃 起 点 心 来 。 女 佣 说道 :“ 不 过 , 有 些 事 我 还 是 真 不 明 白 …… 他 们 一天 里 有 那 么 多 的 时 间 , 在 家 里 有 那 么 多 的 地 方 ,却 偏 偏 在 饭 桌 上 , 当 着 孩 子 的 面 , 非 吵 一 通 架 不可 。”厨 娘 煞 有 介 事 地 说 道 :“ 要 是 没 有 心 思 照 看孩 子 , 最 好 就 不 要 生 孩 子 。”女 佣 沉 默 了 一 会 儿 又 指 出 :“ 他 呢 , 从 年 龄来 说 , 本 来 可 以 做 她 的 父 亲 了 …… 很 明 显 , 他 们合 不 来 ……”“ 要 是 只 是 这 样 就 好 了 ……” 厨 娘 说 道 , 她朝 马 尔 切 洛 深 沉 地 看 了 一 眼 。“ 再 说 呢 ,” 女 佣 继 续 说 道 ,“ 依 我 看 , 那男 人 不 正 常 ……”马 尔 切 洛 一 听 此 话 , 虽 然 仍 在 慢 慢 地 吃 着 点心 , 却 把 耳 朵 竖 了 起 来 。“ 她 也 像 我 一 样 这 样 想呢 ,” 女 佣 又 说 下 去 ,“ 你 知 道 , 那 天 我 在 给 她脱 衣 服 上 床 睡 觉 的 时 候 , 她 跟 我 说 了 什 么 吗 ? 贾科 米 娜 , 总 有 一 天 , 我 丈 夫 会 把 我 杀 了 的 …… 我回 答 她 说 : 可 太 太 , 您 应 该 离 开 他 , 您 还 等 什 么呢 ? 而 她 ……”“ 嘘 ……” 厨 娘 打 断 了 她 的 话 , 指 了 指 马 尔切 洛 。 女 佣 明 白 了 , 便 问 马 尔 切 洛 道 :“ 爸 爸 和妈 妈 在 哪 里 呢 ?”“ 在 楼 上 , 房 间 里 ,” 马 尔 切 洛 答 道 。 接着 , 猛 然 间 , 他 像 是 受 到 一 种 不 可 抗 拒 的 冲 动 情绪 的 推 动 , 又 说 :“ 这 确 是 真 的 : 爸 爸 不 正 常 。你 们 知 道 , 他 干 了 什 么 吗 ?”“ 不 知 道 , 他 干 了 什 么 ?”“ 他 杀 了 一 只 猫 ,” 马 尔 切 洛 说 道 。“ 一 只 猫 , 那 么 , 是 怎 么 杀 的 ?”“ 用 我 的 弹 弓 …… 我 亲 眼 看 见 他 在 花 园 里 跟着 一 只 灰 色 的 猫 , 那 只 猫 在 墙 上 走 着 …… 接 着 ,他 就 拿 起 一 个 石 子 , 朝 猫 打 去 , 打 中 了 猫 的 一 只眼 睛 …… 那 猫 掉 到 小 罗 贝 托 的 花 园 里 了 , 后 来 ,我 去 看 了 一 下 , 我 看 出 来 它 是 死 了 。” 他 一 边 慢慢 讲 着 , 一 边 变 得 激 动 起 来 , 然 而 他 却 没 有 抛 弃一 个 无 辜 的 人 在 以 无 知 和 单 纯 的 天 真 口 气 讲 述 他所 亲 眼 看 到 的 什 么 坏 事 的 那 种 语 调 。“ 可 你 该 想想 看 啊 ,” 女 佣 双 手 合 十 , 说 道 ,“ 一 只 猫 啊…… 一 个 有 这 把 年 纪 的 男 人 , 一 位 老 爷 , 拿 起 儿子 的 弹 弓 , 杀 死 一 只 猫 …… 那 就 不 必 说 了 , 他 就是 个 反 常 的 人 。”“ 对 畜 牲 不 好 的 人 , 对 基 督 徒 也 是 好 不 了的 ,” 厨 娘 说 道 ,“ 开 始 是 杀 猫 , 然 后 就 是 杀人 。”“ 为 什 么 呢 ?” 马 尔 切 洛 把 眼 睛 从 碟 子 里 抬起 , 突 然 问 道 。“ 人 家 就 是 这 么 说 的 嘛 ,” 厨 娘 答 道 , 顺 手抚 摩 了 他 一 下 。“ 尽 管 这 种 说 法 并 不 总 是 对 的……” 她 随 即 又 转 向 女 佣 说 道 ,“ 那 个 在 皮 斯 托亚 杀 了 所 有 那 些 人 的 人 …… 我 是 在 报 纸 上 看 到 的…… 你 知 道 他 如 今 在 监 狱 里 干 什 么 呢 ? 他 竟 养 了一 只 金 丝 雀 。”点 心 吃 完 了 。 马 尔 切 洛 站 起 身 来 , 走 出 了 厨房 。黄 文 捷 译译 文 选 自 译 林 出 版 社 《 莫 拉 维 亚 作 品 》鸣 谢 译 林 出 版 社 对 本 刊 的 支 持40 41
GLI INDIFFERENTIPrimo capitoloEntrò Carla; aveva indossato un vestito di lanettamarrone con la gonna così corta, che bastò quelmovimento di chiudere l’uscio per fargliela saliredi buon palmo sopra le pieghe lente che le facevanole calze intorno alle gambe; ma ella non se neaccorse e si avanzò con precauzione guardandomisteriosamente davanti a sé, dinoccolata emalsicura; una sola lampada era accesa e illuminavale ginocchia di Leo seduto sul divano; un’oscuritàgrigia avvolgeva il resto del salotto.“Mamma sta vestendosi,” ella disse avvicinandosi“e verrà giù tra poco”.“L’aspetteremo insieme,” disse l’uomo curvandosiin avanti; “vieni qui Carla, mettiti qui”. Ma Carlanon accettò questa offerta; in piedi presso il tavolinodella lampada, cogli occhi rivolti verso quel cerchiodi luce del paralume nel quale i gingilli e gli altrioggetti, a differenza dei loro compagni morti einconsistenti sparsi nell’ombra del salotto, rivelavanotutti i loro colori e la loro solidità, ella provava coldito la testa mobile di una porcellana cinese: unasino molto carico sul quale tra due cesti sedeva unaspecie di Budda campagnolo, un contadino grassodal ventre avvolto in un kimono a fiorami; la testaandava in su e in giù, e Carla, dagli occhi bassi, dalleguance illuminate, dalle labbra strette, pareva tuttaassorta in questa occupazione.“Resti a cena con noi?” ella domandò alfine senzaalzare la testa.“Sicuro,” rispose Leo accendendo una sigaretta;“forse non mi vuoi?” Curvo, seduto sul divano,egli osservava la fanciulla con un’attenzione avida;gambe dai polpacci storti, ventre piatto, una piccolavalle di ombra fra i grossi seni, braccia e spallefragili, e quella testa rotonda così pesante sul collosottile.“Eh che bella bambina” egli ripetè “che bellabambina.” La libidine sopita per quel pomeriggiosi ridestava, il sangue gli saliva alle guance, daldesiderio avrebbe voluto gridare.Ella diede ancora un colpo alla testa dell’asino: “Tisei accorto quanto fosse nervosa mamma oggi al tè?Tutti ci guardavano.”“Affari suoi” disse Leo; si protese e senza parer dinulla, sollevò un lembo di quella gonna:“Sai che hai delle belle gambe, Carla?” dissevolgendole una faccia stupita ed eccitata sulla qualenon riusciva ad aprirsi un falso sorriso di cordialità;ma Carla non arrossì e con un colpo secco abbattè laveste:“Mamma è gelosa di te” disse guardandolo; “per questo ci fa a tutti la vita impossibile.” Leo feceun gesto che significava: “E che ci posso fare io?”;poi si rovesciò daccapo sul divano e accavalciò legambe.“Fai come me” disse freddamente; “appena vedoche il temporale sta per scoppiare, non parlo più…Poi passa e tutto è finito.”“Per te, finito” ella disse a voce bassa e fu come sequelle parole dell’uomo avessero ridestato in lei unarabbia antica e cieca; “per te... ma per noi... per me”proruppe con labbra tremanti e occhi dilatati dall’ira,puntandosi un dito sul petto; “per me che ci vivoinsieme non è finito nulla ...”. Un istante di silenzio.“Se tu sapessi”, ella continuò con quella voce bassaa cui il risentimento marcava le parole e prestavaun singolare accento come straniero, “quanto tuttoquesto sia opprimente e miserabile e gretto, e qualevita sia assistere tutti i giorni, tutti i giorni...”. Daquell’ombra, laggiù, che riempiva l’altra metà delsalotto, l’onda morta del rancore si mosse, scivolòcontro il petto di Carla, disparve, nera e senzaschiuma, ella restò cogli occhi spalancati, senzarespiro, resa muta da questo passaggio di odio.Si guardarono: “Diavolo” pensava Leo un po’stupito da tanta violenza, la cosa è seria. Si curvò,tese l’astuccio: “Una sigaretta” propose consimpatia; Carla accettò, accese e tra una nuvola difumo gli si avvicinò ancora di un passo.“E così” egli domandò guardandola dal bassoin alto “proprio non ne puoi più?” La vide annuireun poco impacciata dal tono confidenziale cheassumeva il dialogo. “E allora”, soggiunse “sai cosasi fa quando non se ne può più? Si cambia.”“È quello che finirò per fare” ella disse con unacerta teatrale decisione; ma le pareva di recitareuna parte falsa e ridicola; così, era quello l’uomoa cui questo pendìo di esasperazione l’andavainsensibilmente portando? Lo guardò: né meglioné peggio degli altri, anzi meglio senza alcundubbio, ma con in più una certa sua fatalità cheaveva aspettato dieci anni che ella si sviluppasse ematurasse per insidiarla ora, in quella sera, in quelsalotto oscuro.“Cambia”, le ripeté; “vieni a stare con me.”Ella scosse la testa: “Sei pazzo...”“Ma sì!” Leo si protese, l’afferrò per la gonna:“Daremo il benservito a tua madre, la manderemoal diavolo, e tu avrai tutto quel che vorrai, Carla...”:tirava la gonna, l’occhio eccitato gli andava daquella faccia spaventata ed esitante a quel po’ digamba nuda che s’intravedeva là, sopra la calza.“Portarmela a casa”; pensava “possederla ...” Ilrespiro gli mancava: “Tutto quel che vorrai... vestiti,molti vestiti, viaggi ... ; viaggeremo insieme ... ; è unvero peccato che una bella bambina come te sia cosìsacrificata ...: vieni a stare con me Carla …”.“Ma tutto questo è impossibile”, ella dissetentando inutilmente di liberare la veste da quellemani; “c’è mamma... è impossibile.”“Le daremo il benservito ...” ripeté Leoafferrandola questa volta per la vita; la manderemoa quel paese, è ora che la finisca.., e tu verrai a starecon me, è vero? Verrai a stare con me che sono iltuo solo vero amico, il solo che ti capisca e sappiaquel che vuoi.” La strinse più davvicino nonostantei suoi gesti spaventati; “Essere a casa mia” pensava,e queste rapide idee erano come lucidi lampi nellatempesta della sua libidine: “Le farei vedere allorache cosa vuole.” Alzò gli occhi verso quella facciasmarrita e provò un desiderio, per rassicurarla, didirle una tenerezza qualsiasi: “Carla, amor mio...”Ella fece di nuovo il vano gesto di respingerlo, maancor più fiaccamente di prima, ché ora la vincevauna specie di volontà rassegnata; perché rifiutareLeo? Questa virtù l’avrebbe rigettata in braccio allanoia e al meschino disgusto delle abitudini; e lepareva inoltre, per un gusto fatalistico di simmetriemorali, che questa avventura quasi familiare fosseil solo epilogo che la sua vita meritasse; dopo, tuttosarebbe stato nuovo; la vita e lei stessa; guardavaquella faccia dell’uomo, là, tesa verso la sua:“Finirla”, pensava “rovinare tutto...” e le girava latesta come a chi si prepara a gettarsi a capofitto nelvuoto.Ma invece supplicò: “Lasciami”, e tentò dinuovo di svincolarsi; pensava vagamente prima direspingere Leo e poi di cedergli, non sapeva perché,forse per avere il tempo di considerare tutto il rischioche affrontava, forse per un resto di civetteria; sidibatté invano; la sua voce sommessa, ansiosa esfiduciata ripeteva in fretta la preghiera inutile:“Restiamo buoni amici Leo, vuoi? Buoni amici comeprima” ma la veste tirata le discopriva le gambe,e c’era in tutto il suo atteggiamento renitente e inquei gesti che faceva per coprirsi e per difendersi, ein quelle voci che le strappavano le strette libertinedell’uomo, una vergogna, un rossore, un disonoreche nessuna liberazione avrebbe potuto più abolire.“Amicissimi” ripeteva Leo quasi con gioia,e torceva in pugno quella vesticciola di lana;“amicissimi Carla ... “ Stringeva i denti, tutti i suoisensi si esaltavano alla vicinanza di quel corpodesiderato: “Ti ho alfine” pensava torcendosi tuttosul divano per fare un posto alla fanciulla, e già stavaper piegare quella testa, là, sopra la lampada, quandodal fondo oscuro del salotto un tintinnìo della porta avetri l’avvertì che qualcheduno entrava.Era la madre; la trasformazione che questapresenza portò nell’atteggiamento di Leo fusorprendente: subito, egli si rovesciò sullo schienaledel divano, accavalciò le gambe e guardò la fanciullacon indifferenza; anzi spinse la finzione fino alpunto di dire col tono importante di chi conclude undiscorso incominciato: “Credimi Carla, non c’è altroda fare.”La madre si avvicinò; non aveva cambiato ilvestito ma si era pettinata e abbondantementeincipriata e dipinta; si avanzò, là, dalla porta, conquel suo passo malsicuro; e nell’ombra la facciaimmobile dai tratti indecisi e dai colori vivaci parevauna maschera stupida e patetica.“Vi ho fatto molto aspettare?” domandò. “Di checosa stavate parlando?”Leo additò con un largo gesto Carla diritta in piedinel mezzo del salotto: “Stavo appunto dicendo a suafiglia che questa sera non c’è altro da fare che restarein casa.”“Proprio nient’altro”; approvò la madre consussiego e autorità sedendosi in una poltrona, infaccia all’amante; “al cinema siamo già state oggi enei teatri danno tutte cose che abbiamo già sentite...42 43
Non mi sarebbe dispiaciuto di andare a vedere ‘Seipersonaggi’ della compagnia di Pirandello...: mafrancamente come si fa?... è una serata popolare.”“E poi le assicuro che non perde nulla” osservòLeo.“Ah, questa poi no” protestò mollemente lamadre: “Pirandello ha delle belle cose... : come sichiamava quella sua commedia che abbiamo sentitopoco tempo fa?... Aspetti... ah sì, ‘La maschera e ilvolto’: mi ci sono tanto divertita.”“Mah, sarà ... “ disse Leo rovesciandosi soprail divano; “però io mi ci sono sempre annoiato amorte.” Mise i pollici nel taschino del panciotto eguardò prima la madre e poi Carla.Dritta dietro la poltrona della madre, la fanciullaricevette quell’occhiata inespressiva e pesante comeun urto che fece crollare in pezzi il suo stupore divetro; allora, per la prima volta, si accorse quantovecchia, abituale e angosciosa fosse la scena cheaveva davanti agli occhi: la madre e l’amanteseduti in atteggiamento di conversazione l’uno infaccia all’altra; quell’ombra, quella lampada, quellefacce immobili e stupide, e lei stessa affabilmenteappoggiata al dorso della poltrona per ascoltare eper parlare. “La vita non cambia”, pensò, “non vuolcambiare.” Avrebbe voluto gridare; abbassò le duemani e se le torse, là, contro il ventre, così forte che ipolsi le si indolenzirono.“Possiamo restare in casa”, continuava la madre“tanto più che abbiamo tutti i giorni della settimanaimpegnati… : domani ci sarebbe quel tè danzantepro infanzia abbandonata ... ; dopodomani il ballomascherato al Grand Hotel ... ; negli altri giornisiamo invitate un po’ qua un po’ là... E, Carla... hoveduto oggi la signora Ricci ... : è invecchiata a untal punto ... ; l’ho osservata con attenzione ... : hadue rughe profonde che le partono dagli occhi e learrivano alla bocca ...., e i capelli non si sa più di checolore siano ... : un orrore! ..” Ella storse la bocca eagitò le mani in aria.“Non è poi questo orrore” disse Carla facendosiavanti e sedendosi presso l’uomo; una leggeradolorosa impazienza la pungeva; prevedeva cheper vie indirette e tortuose la madre sarebbe alfinearrivata a fare, come sempre, la sua piccola scenadi gelosia all’amante; non sapeva quando e in chemodo ma ne era certa come del sole che avrebbebrillato all’indomani e della notte che l’avrebbeseguito; e questa chiaroveggenza le dava un sensodi paura; non c’era rimedio, tutto era inamovibile edominato da una meschina fatalità.“Mi ha fatto una quantità di chiacchiere”; continuòla madre “mi ha detto che hanno venduto la vecchiaautomobile e ne hanno comprata una nuova... unaFiat... ‘Sa’ mi fa ‘mio marito è diventato il bracciodestro di Paglioni, alla Banca Nazionale... Paglioninon può fare a meno di lui, Paglioni lo indica comeil suo più probabile socio;’ Paglioni qui, Paglioni là... : ignobile! ...”“Perché ignobile?” osservò Leo contemplandola donna tra le sue palpebre socchiuse. “Cosa c’è diignobile in tutto questo?”“Lei sa” domandò la madre fissandolo acutamente,come per invitarlo a soppesare bene le parole, “chePaglioni è l’amico della Ricci?”“Tutti lo sanno” disse Leo, e pesantemente queisuoi occhi torpidi si posarono su Carla trasognata erassegnata.“E lei sa anche” insistette Mariagrazia distaccandole sillabe, “che prima di conoscere Paglioni i Riccinon avevano un soldo... e ora hanno l’automobile?”Leo voltò la testa: “Ah, è per questo”; esclamò “eche male c’è?... Povera gente, s’industriano.”Fu come se avesse dato fuoco a una micciaaccuratamente preparata.“Ah, è così”, disse la madre spalancandoironicamente gli occhi; “lei giustifica unasvergognata, e neppure bella, un mucchio d’ossa,che sfrutta senza scrupoli l’amico e si fa pagarele automobili ed i vestiti e trova anche modo dimandare avanti quel suo marito non si sa se piùimbecille o più furbo... Lei ha di questi principi? Ahbenissimo proprio benissimo... allora non c’è piùnulla da dire... tutto si spiega... a lei evidentementepiacciono quelle donne …”“Ecco” pensò Carla; un leggero tremito diinsofferenza corse per le sue membra, socchiuse gliocchi e rovesciò la testa fuori da quella luce e daquei discorsi; nell’ombra.Leo rise: “No, francamente non sono quelle ledonne che mi piacciono.” Gettò una rapida, cupidaocchiata alla fanciulla, là, al suo fianco ... : pettoflorido, guance in fiore, anatomia giovane: “Eccole donne che mi piacciono” avrebbe voluto gridareall’amante.“Lo dice ora”, insistette la madre “lo dice ora...ma chi disprezza compra... ma quando le è vicino,l’altro giorno, per esempio, in casa Sidoli, si prodigain complimenti; allora le dice una quantità disciocchezze ... ; eh vada là, la conosco... Sa cos’èlei?... Un bugiardo...”“Ecco” si ripeté Carla; quella conversazionepoteva continuare; ma ella aveva riconosciutoche la vita incorreggibile e abitudinaria noncambiava; e questo le bastava; si alzò: “vadoa mettermi un golf e torno”, e senza voltarsiindietro, ché sentiva gli sguardi di Leo incollarsial suo dorso come due sanguisughe, uscì.Nel corridoio incontrò Michele: “C’è Leo di là?”egli le domandò; Carla guardò il fratello: “C’è.”“Vengo proprio ora dall’amministratore di Leo”;continuò tranquillamente il ragazzo. “Ho saputoun monte di belle cose... e prima di tutto che siamorovinati.”“Vorrebbe dire?” chiese la fanciulla interdetta.“Vorrebbe dire” spiegò Michele “che dovremocedere la villa a Leo, in pagamento di quell’ipoteca,e andarcene, senza un soldo, andarcene altrove.”Si guardarono; un sorriso forzato squallido passòsulla faccia del ragazzo: “Perché sorridi?” elladomandò. “Ti par cosa da sorridere?”“Perché sorrido?” egli ripeté. “Perché tutto questomi è indifferente... e anzi quasi mi fa piacere.”“Non è vero.”“Sicuro che è vero” egli ribatté, e senzaaggiungere parola, lasciandola lì stupita evagamente spaventata, entrò nel salotto.La madre e Leo disputavano ancora; Micheleebbe il tempo di percepire un tu che si trasformòin lei alla sua entrata, e ne sorrise di disgustatapietà: “Credo che sia ora di cena” disse allamadre, senza salutare, senza neppure guardarel’uomo; ma questo suo freddo contegno nonsconcertò Leo: “Oh chi si vede”, egli gridò conla consueta giovialità “il nostro Michele... vieniqui Michele... è tanto tempo che non ci vediamo.”“Due giorni soltanto” disse il ragazzo guardandolofissamente; si sforzava di parer freddo e vibrantebenché non si sentisse che indifferente; avrebbevoluto soggiungere: “E meno ci vediamo meglio è”o qualcosa di simile, ma non ne ebbe la prontezza néla sincerità.“E ti par nulla due giorni?” gridò Leo. “Sipossono far tante cose in due giorni.” Chinò la sualarga faccia trionfale nel lume della lampada: “Eheh, che bel vestito che hai... chi te lo ha fatto?...”Era un vestito di stoffa turchina di buon taglio mamolto usato, che Leo doveva avergli veduto addossoalmeno cento volte; ma colpito da questo direttoattacco alla sua vanità, Michele dimenticò in un soloistante tutti i suoi propositi di odio e di freddezza.“Ti pare?...” domandò non nascondendo un mezzosorriso di compiacimento; “è un vecchio vestito...è tanto tempo che lo porto, me lo ha fatto Nino,sai?...” E istintivamente si girò per mostrare il dorsoall’uomo e con le mani tirò i bordi della giaccaaffinché aderisse al torso; vide la sua immagine nellospecchio di Venezia appeso alla parete di faccia; iltaglio era perfetto, su questo non c’era dubbio, magli parve che il suo atteggiamento fosse pieno d’unaridicola e fissa stupidità simile a quella dei fantocciben vestiti esposti col cartello del prezzo sul petto,nelle vetrine dei negozi; una leggera inquietudineserpeggiò nei suoi pensieri.“Buono... proprio buono.” Ora, curvandosi, Leopalpava la stoffa; poi si rialzò: “E bravo il nostroMichele” disse battendogli la mano sul braccio;“sempre inappuntabile, non fa che divertirsi e nonha pensieri di nessuna sorta.” Allora dal tono diqueste parole e dal sorriso che le accompagnava,Michele capì troppo tardi di essere stato astutamentelusingato e in definitiva canzonato; dove eranol’indignazione, il risentimento che aveva immaginatodi provare in presenza del suo nemico? Altrove, nellimbo delle sue intenzioni; odiosamente impacciatoda questo suo vano atteggiamento, egli guardò suamadre:“Peccato che tu non fossi oggi con noi”; ella disse“abbiamo visto un film magnifico.”“Ah sì” fece il ragazzo; e poi voltandosi versol’uomo, colla voce più secca e più vibrante che poté:“Sono stato dal tuo amministratore, Leo...”Ma con un gesto netto della mano l’altro lointerruppe: “Ora no... ho capito ... ne parleremodopo... dopo cena... ogni cosa nel suo momento.”“Come vuoi” disse il ragazzo con istintivamansuetudine, e subito si accorse di essere statodominato per la seconda volta. “Dovevo dire:subito”, pensò, “chiunque avrebbe fatto così ... ;subito e discutere e magari ingiuriare”: dalla rabbiaavrebbe voluto gridare; vanità e indifferenza,nel giro di pochi minuti Leo aveva saputo farlocadere in ambedue queste sue meschine voragini.Quei due, la madre e l’amante, si erano alzati.“Ho appetito”, diceva Leo abbottonandosila giacca; “un appetito...” La donna rideva;macchinalmente Michele li seguì. “Madopo cena”, pensava tentando invano dimettere dell’acredine in queste sue ideequasi distratte, “non la passerai così liscia.”Alla porta si fermarono: “Prego” disse Leo; e lamadre uscì; restarono l’uno in faccia all’altro,l’uomo e il ragazzo, e si guardarono: “Avanti avanti”insistette Leo complimentosissimo posandogli unamano sulla spalla; “cediamo il posto al padronedi casa ... “ E con gesto paterno, con un sorrisotanto amichevole da parere canzonatorio spinsedolcemente il ragazzo. “Il padrone di casa”, pensòquesti senz’ombra d’ira, “eccone una bella ... : ilpadrone di casa sei tu.” Ma non disse nulla e uscì nelcorridoio dietro la madre.44 45
卡 尔 拉 进 来 了 。 她 身 穿 一 件 褐 色 的 粗 呢 子 短上 衣 , 下 套 一 条 裙 子 , 裙 子 很 短 , 关 门 时 裙 裾 撩起 , 高 出 腿 上 那 双 长 统 袜 宽 松 的 袜 口 足 有 一 掌 。但 她 没 发 现 这 点 , 只 顾 向 前 踽 踽 而 行 , 同 时 带 着迟 疑 的 神 情 , 用 神 秘 的 目 光 看 着 前 方 。 只 有 一 盏灯 亮 着 , 灯 光 照 着 坐 在 长 沙 发 上 的 莱 奥 的 膝 头 。一 片 灰 暗 笼 罩 着 客 厅 的 其 余 部 分 。“ 妈 妈 在 换 衣 服 ,” 她 一 面 说 , 一 面 渐 渐 走近 。“ 过 一 会 儿 就 下 来 。”“ 我 们 一 起 等 她 吧 ,” 莱 奥 朝 前 俯 过 身 来说 。“ 到 这 儿 来 , 卡 尔 拉 , 坐 在 这 儿 。” 但 卡 尔拉 没 有 接 受 他 的 提 议 。 她 伫 立 在 放 着 那 盏 灯 的 茶几 旁 边 , 目 光 投 向 灯 罩 下 的 光 环 。 位 于 光 环 中 的那 些 小 玩 意 儿 及 其 他 物 品 , 跟 分 散 在 黑 暗 的 客 厅里 的 没 有 生 气 和 不 成 形 的 东 西 不 同 , 它 们 充 分 显露 出 自 己 的 绚 丽 色 彩 和 结 实 外 形 。 她 伸 出 一 个 手指 , 贸 然 碰 了 碰 一 件 中 国 瓷 器 上 的 那 个 会 动 的 脑袋 : 这 是 一 头 驮 满 货 物 的 驴 子 , 背 上 的 两 只 筐 子中 间 端 坐 着 一 个 身 穿 花 长 袍 的 大 腹 便 便 的 农 民 ,活 像 乡 间 供 养 的 佛 。 驴 子 的 脑 袋 上 下 晃 动 , 卡 尔拉 两 眼 低 垂 , 双 唇 紧 闭 , 脸 颊 被 灯 光 照 亮 ; 她 似乎 正 全 神 贯 注 于 拨 弄 驴 子 的 脑 袋 。“ 你 留 下 和 我 们 一 起 吃 晚 饭 吗 ?” 她 终 于 提了 个 问 题 , 但 没 抬 头 。“ 当 然 喽 ,” 莱 奥 一 边 回 答 , 一 边 点 起 一支 烟 。“ 你 大 概 不 愿 意 我 留 下 吧 ?” 他 坐 在 沙 发上 , 身 子 往 前 倾 , 专 注 、 贪 婪 地 打 量 着 这 位 妙 龄少 女 : 肌 腱 发 达 的 双 腿 , 扁 平 的 腹 部 , 高 耸 的 乳峰 , 胸 部 中 间 的 深 谷 , 纤 弱 的 胳 臂 和 双 肩 , 还 有细 长 的 脖 子 上 的 那 颗 沉 甸 甸 的 圆 脑 袋 。“ 唔 , 多 标 致 的 姑 娘 ,” 他 反 复 想 道 ,“ 多标 致 的 姑 娘 。” 当 天 下 午 被 抑 制 住 的 欲 火 重 新 燃起 来 了 。 热 血 涌 上 他 的 面 颊 。 他 欲 火 中 烧 , 真 想大 叫 一 声 。她 又 碰 了 一 下 驴 子 的 脑 袋 :“ 今 天 喝 茶 的 时候 , 妈 妈 的 脾 气 多 暴 躁 , 你 看 出 来 了 吗 ? 所 有 的人 都 看 着 我 们 。”“ 这 是 她 的 事 。” 莱 奥 说 , 他 凑 上 前 来 , 漫不 经 心 地 掀 起 她 的 裙 子 的 一 角 。“ 你 知 道 自 己 有 一 双 漂 亮 的 大 腿 吗 , 卡 尔 拉?” 他 说 , 同 时 向 她 转 过 一 张 愚 蠢 和 激 动 的 脸 ;他 想 装 出 一 个 欢 快 的 微 笑 , 但 没 有 成 功 。 卡 尔 拉既 没 脸 红 , 也 不 答 话 , 只 是 猛 地 一 甩 手 , 把 裙 子放 下 。“ 妈 妈 为 你 吃 醋 ,” 她 看 着 他 说 。“ 因 为 这个 缘 故 , 她 使 得 大 家 的 日 子 都 不 好 过 。” 莱 奥 摆摆 手 , 意 思 是 :“ 我 又 有 什 么 办 法 ?” 接 着 他 往冷 漠 的 人一后 一 仰 身 , 重 新 靠 在 沙 发 上 , 跷 起 了 二 郎 腿 。“ 你 可 以 像 我 这 样 ,” 他 冷 冰 冰 地 说 ,“ 一见 暴 风 雨 即 将 来 临 , 就 赶 紧 闭 上 嘴 巴 …… 事 情 过去 后 , 一 切 就 结 束 了 。”“ 对 你 来 讲 是 结 束 了 ,” 她 低 声 说 。 莱 奥 的话 仿 佛 重 新 燃 起 了 她 心 头 的 那 股 由 来 已 久 的 无 名怒 火 。“ 对 你 来 讲 是 这 样 …… 可 是 , 对 我 们 来 说…… 对 我 来 说 ……” 她 嚷 了 起 来 。 由 于 愤 怒 , 她 的嘴 唇 不 住 抖 动 , 眼 睛 瞪 得 滚 圆 。 她 用 手 指 顶 着 自己 的 胸 口 。“ 我 是 和 她 住 在 一 起 的 , 对 我 来 说 ,事 情 根 本 没 有 结 束 ……” 沉 默 片 刻 。“ 你 要 是 知道 ,” 她 接 下 去 说 ; 嗓 门 倒 是 压 低 了 , 但 愤 懑 却使 她 把 每 个 词 都 咬 得 很 清 楚 , 而 且 还 赋 予 它 们 一种 特 别 的 腔 调 , 像 是 外 国 口 音 。“ 这 一 切 可 悲 透顶 , 卑 俗 至 极 , 看 了 真 叫 人 难 受 。 每 天 看 着 这种 场 面 , 这 是 一 种 什 么 生 活 啊 ……” 一 股 死 气 沉沉 的 怨 恨 的 浪 潮 从 笼 罩 着 客 厅 的 另 一 半 的 黑 影中 涌 来 , 碰 到 卡 尔 拉 的 胸 膛 后 消 遁 了 , 重 新 归 于黑 暗 , 连 一 丝 浪 花 也 没 留 下 。 她 睁 大 眼 睛 , 屏 住呼 吸 : 怨 愤 情 绪 的 这 种 传 递 方 式 , 使 她 说 不 出 话来 。他 们 相 视 无 言 。“ 见 鬼 ,” 莱 奥 寻 思 道 ; 卡尔 拉 的 口 气 这 么 激 烈 , 他 颇 觉 惊 诧 。“ 事 情 挺严 重 。” 他 俯 过 身 , 递 给 她 一 包 烟 。“ 抽 支 烟吧 。” 他 和 颜 悦 色 地 提 了 个 建 议 。 卡 尔 拉 接 受了 。 她 燃 起 烟 , 喷 出 一 团 烟 雾 , 又 朝 他 走 近 一步 。“ 这 么 说 ,” 他 从 下 向 上 看 着 她 问 ,“ 你 确实 再 也 无 法 忍 受 了 ?” 他 看 见 她 微 微 点 了 点 头 。他 讲 话 时 用 的 亲 昵 语 调 使 她 感 到 非 常 尴 尬 。“ 既然 这 样 ,” 他 补 充 道 ,“ 你 知 道 , 当 一 个 人 再 也无 法 忍 受 的 时 候 , 应 该 怎 么 办 吗 ? 换 个 方 式 。”“ 我 最 后 准 会 那 样 做 的 。” 她 斩 钉 截 铁 地说 , 似 乎 在 演 戏 ; 然 而 , 她 觉 得 自 己 扮 演 的 是 一个 虚 伪 和 可 笑 的 角 色 。 她 难 道 正 沿 着 愤 激 的 斜坡 , 不 知 不 觉 地 滑 进 这 个 男 人 的 怀 抱 吗 ? 她 瞟 了他 一 眼 : 他 既 不 比 别 人 好 , 也 不 比 别 人 坏 ; 嗯 ,不 , 他 比 别 人 要 好 些 , 这 是 毫 无 疑 问 的 。 此 外 ,有 一 件 事 是 命 中 注 定 的 : 他 等 了 十 年 , 盼 着 她 发育 成 熟 、 长 大 成 人 , 此 时 此 刻 , 就 在 这 天 晚 上 ,就 在 这 个 昏 暗 的 客 厅 中 , 她 将 掉 进 他 的 罗 网 。“ 换 个 方 式 ,” 他 又 说 了 一 遍 ;“ 你 和 我 一起 生 活 吧 。”她 摇 摇 头 :“ 你 疯 了 ……”“ 不 , 应 该 这 样 ,” 莱 奥 凑 过 去 , 一 把 拽 住她 的 裙 子 。“ 我 们 把 你 母 亲 撵 走 , 把 她 赶 到 魔 鬼那 儿 去 。 你 将 得 到 你 想 要 的 一 切 , 卡 尔 拉 ……”他 拽 着 裙 子 , 激 动 的 目 光 从 她 那 张 惊 恐 和 犹 豫的 脸 上 移 到 露 在 长 统 袜 上 方 的 那 一 小 截 赤 裸 的 大腿 上 。“ 把 她 带 回 我 家 ,” 他 盘 算 道 ,“ 占 有她 ……” 他 喘 不 过 气 来 了 :“ 你 想 要 的 一 切 …… 衣服 , 许 许 多 多 衣 服 , 旅 行 …… 我 们 一 块 儿 去 旅 行…… 像 你 这 么 一 个 漂 亮 姑 娘 竟 做 出 了 这 种 牺 牲 ,真 可 惜 …… 和 我 一 起 生 活 吧 , 卡 尔 拉 ……”“ 可 是 , 这 一 切 是 办 不 到 的 ,” 她 一 边 说 ,一 边 徒 劳 无 益 地 试 图 使 裙 子 摆 脱 他 的 那 双 手 。“ 有 妈 妈 在 …… 办 不 到 。”“ 我 们 把 她 撵 走 ……” 莱 奥 又 说 了 一 遍 。 他这 回 搂 住 了 她 的 腰 。“ 把 她 赶 到 乡 下 去 , 该 结 束了 …… 你 将 和 我 住 在 一 起 , 对 不 对 ? 你 将 和 我 住 在一 起 , 因 为 我 是 你 唯 一 真 正 的 朋 友 , 只 有 我 能 理解 你 , 知 道 你 想 要 什 么 。” 他 不 顾 她 做 出 的 许 多惊 恐 动 作 , 把 她 抱 得 更 紧 了 。“ 到 了 我 家 后 ,”他 寻 思 道 ; 他 的 欲 念 如 同 一 场 暴 风 雨 , 这 些 匆 匆出 现 的 念 头 便 是 暴 风 雨 中 的 耀 眼 闪 电 ,“ 我 就 会让 她 知 道 , 她 想 要 的 到 底 是 什 么 。” 他 抬 眼 望 着她 那 张 惶 惑 的 脸 , 产 生 了 一 种 对 她 随 便 说 句 情 意绵 绵 的 话 、 让 她 定 下 心 来 的 愿 望 :“ 卡 尔 拉 , 我的 爱 ……”她 又 徒 然 做 出 一 个 推 开 他 的 动 作 , 但 比 刚 才还 要 软 弱 无 力 , 因 为 她 现 在 已 被 某 种 听 天 由 命 的意 愿 制 服 了 。 为 什 么 要 拒 绝 莱 奥 呢 ? 类 似 的 美 德只 会 使 她 重 新 陷 入 苦 闷 , 使 生 活 又 走 上 习 俗 的 平庸 乏 味 和 令 人 生 厌 的 轨 道 。 此 外 , 她 对 道 德 对 称论 有 一 种 致 命 的 嗜 好 , 她 觉 得 , 这 种 几 乎 是 在 家里 发 生 的 艳 遇 是 她 的 生 活 的 应 得 结 局 ; 事 情 过 去后 , 一 切 都 将 焕 然 一 新 : 生 活 将 焕 然 一 新 , 她 自己 也 将 焕 然 一 新 。 她 凝 视 着 莱 奥 那 张 朝 她 凑 过 来的 脸 。“ 让 一 切 都 结 束 吧 ,” 她 心 想 ,“ 毁 掉 一切 ……” 她 像 打 算 从 高 空 跳 下 的 人 那 样 , 感 到 头晕 脑 涨 。然 而 , 她 却 央 求 道 :“ 放 开 我 。” 她 再 次 试图 挣 脱 。 她 模 糊 地 想 道 : 先 拒 绝 莱 奥 , 以 后 再 顺从 他 。 她 不 知 道 为 什 么 要 这 样 , 或 许 是 为 了 有 时间 考 虑 面 临 的 全 部 危 险 , 或 许 是 为 了 最 后 卖 弄一 下 风 情 。 她 毫 无 用 处 地 挣 扎 着 。 她 那 压 得 低 低的 、 焦 虑 忧 愁 的 和 缺 乏 自 信 的 声 音 匆 匆 重 复 着 这个 徒 劳 无 益 的 请 求 :“ 我 们 还 是 作 为 好 朋 友 吧 ,莱 奥 , 你 愿 意 吗 ? 和 以 前 一 样 , 是 好 朋 友 。” 可是 , 裙 子 被 撩 上 去 了 , 大 腿 统 统 露 了 出 来 。 在 她的 全 部 推 拒 姿 势 中 , 在 她 为 遮 住 身 体 和 保 护 自 己而 做 的 那 些 动 作 中 , 以 及 在 她 由 于 莱 奥 的 放 肆 拥抱 而 脱 口 发 出 的 叫 声 中 , 有 一 种 羞 耻 感 和 一 种 即使 挣 脱 他 的 搂 抱 也 无 法 消 除 的 受 辱 感 ; 她 脸 红了 。“ 最 好 的 朋 友 ,” 莱 奥 带 着 一 种 几 乎 是 欢 快的 声 调 反 复 说 道 ; 同 时 , 他 攥 紧 拳 头 , 使 劲 揉 着她 的 粗 呢 裙 子 ,“ 最 好 的 朋 友 , 卡 尔 拉 ……” 他咬 紧 牙 齿 , 他 的 全 部 激 情 由 于 这 个 渴 望 中 的 躯 体近 在 身 旁 而 沸 腾 起 来 。“ 我 终 于 得 到 了 你 。” 他一 面 这 么 想 着 , 一 面 在 沙 发 上 扭 了 扭 身 子 , 给 姑娘 腾 出 个 地 方 。 他 正 要 把 那 个 仰 得 比 灯 还 高 的 脑袋 往 下 按 的 时 候 , 从 黑 漆 漆 的 客 厅 那 端 传 来 了 玻璃 门 开 启 的 “ 叮 咚 ” 声 , 这 表 明 有 人 进 来 了 。是 卡 尔 拉 的 母 亲 ; 她 的 出 现 使 莱 奥 的 姿 势 发生 了 令 人 惊 异 的 变 化 : 他 立 即 向 后 一 仰 , 靠 在 沙发 背 上 , 一 条 腿 往 另 一 条 腿 上 一 搁 , 用 冷 漠 的 目光 扫 了 姑 娘 一 眼 。 这 还 不 够 , 他 甚 至 装 出 正 在 把一 句 开 了 头 的 话 讲 完 的 样 子 , 用 一 本 正 经 的 腔 调说 :“ 相 信 我 吧 , 卡 尔 拉 , 没 别 的 事 可 干 。”母 亲 渐 渐 走 近 ; 她 没 换 衣 服 , 但 梳 理 了 头发 , 扑 了 许 多 香 粉 , 还 抹 了 胭 脂 口 红 。 她 步 态 蹒跚 地 离 开 门 口 走 上 前 来 。 在 黑 影 中 , 她 那 张 表 情呆 滞 、 线 条 不 清 、 浓 妆 艳 抹 的 脸 盘 , 恍 若 一 个 傻里 傻 气 但 又 忧 愁 伤 感 的 面 具 。“ 我 让 你 们 久 等 了 吧 ?” 她 问 。“ 你 们 在 谈些 什 么 ?”莱 奥 一 挥 胳 臂 , 指 指 在 客 厅 中 部 挺 立 着 的 卡尔 拉 :“ 我 正 在 对 您 女 儿 说 , 今 晚 没 别 的 事 可干 , 只 好 留 在 家 里 。”“ 确 实 没 别 的 事 可 干 ,” 母 亲 用 庄 重 和 权 威的 口 吻 表 示 赞 同 , 随 即 坐 在 情 人 对 面 的 一 把 软 椅中 。“ 我 们 今 天 已 经 去 过 电 影 院 了 , 而 剧 场 里上 演 的 则 全 是 已 经 看 过 的 东 西 …… 我 倒 很 乐 意 去看 看 皮 蓝 德 娄 剧 团 演 出 的 《 六 个 剧 中 人 》…… 可是 , 坦 率 地 说 , 怎 么 搞 票 呢 ?…… 今 天 是 为 一 般 观众 演 出 。”“ 我 可 以 向 您 担 保 , 您 不 去 不 会 有 任 何 损 失的 。” 莱 奥 指 出 。“ 唔 , 这 话 不 对 ,” 母 亲 稍 加 反 驳 ,“ 皮蓝 德 娄 的 有 些 东 西 很 精 彩 …… 不 久 前 我 们 看 过 的那 出 喜 剧 叫 什 么 来 着 ?…… 等 一 等 …… 噢 , 对 了 ,46 47
《 面 具 和 脸 膛 》。 我 看 得 津 津 有 味 。”“ 嗬 , 但 愿 如 此 ……” 莱 奥 一 面 说 , 一 面 在沙 发 上 把 身 子 往 后 一 仰 。“ 不 过 , 我 却 从 头 到 尾厌 烦 得 要 死 。” 他 把 两 手 的 大 拇 指 插 进 西 服 背 心口 袋 , 先 看 看 母 亲 , 后 来 又 看 了 卡 尔 拉 一 眼 。卡 尔 拉 站 在 母 亲 的 软 椅 后 面 , 接 受 了 这 一 瞥毫 无 表 情 的 沉 重 目 光 。 她 的 诧 异 心 情 如 同 一 块 玻璃 , 在 他 的 目 光 的 冲 击 下 成 了 碎 块 。 她 第 一 次 发现 , 眼 前 的 这 个 场 面 由 来 已 久 , 已 经 成 了 习 惯 ,着 实 令 人 焦 虑 : 面 对 面 坐 在 那 儿 交 谈 的 母 亲 和 情人 , 黑 影 , 那 盏 灯 , 那 两 张 静 止 和 愚 蠢 的 面 孔 ,以 及 温 顺 地 倚 靠 在 椅 背 上 讲 话 和 听 着 他 们 讲 话 的她 自 己 。“ 生 活 没 有 改 变 ,” 她 思 忖 道 ,“ 也 不会 改 变 。” 她 真 想 喊 出 声 来 。 她 垂 下 双 手 , 贴 着腹 部 互 相 揉 搓 ; 她 使 的 劲 很 大 , 腕 部 开 始 隐 隐 作痛 。“ 我 们 可 以 留 在 家 里 ,” 母 亲 接 着 说 ,“ 何况 这 星 期 我 们 天 天 有 事 …… 明 天 有 个 茶 会 , 将 有舞 蹈 表 演 , 为 弃 婴 们 募 捐 …… 后 天 在 大 饭 店 有 化装 舞 会 …… 前 几 天 我 们 四 处 应 邀 …… 唔 , 卡 尔 拉…… 今 天 我 看 见 了 里 奇 太 太 …… 老 到 那 种 程 度 ……我 留 心 观 察 了 她 …… 两 道 深 深 的 皱 纹 从 眼 角 一 直连 到 嘴 边 …… 还 有 头 发 , 简 直 不 晓 得 成 了 什 么 颜色 …… 可 怕 !……” 她 努 努 嘴 , 双 手 在 空 中 挥 了 一下 。“ 可 怕 的 不 是 这 个 。” 卡 尔 拉 边 说 边 走 上 前来 , 挨 着 莱 奥 坐 下 。 一 种 轻 微 而 痛 苦 的 不 耐 烦 刺激 着 她 。 她 预 见 到 , 母 亲 旁 敲 侧 击 、 指 桑 骂 槐 一阵 之 后 , 最 终 会 像 往 常 那 样 , 在 情 人 面 前 妒 意 发作 , 闹 上 一 场 。 什 么 时 候 , 以 何 种 方 式 发 作 , 她心 中 无 数 ; 但 她 确 信 母 亲 肯 定 会 发 作 , 如 同 确 信第 二 天 明 亮 的 太 阳 将 升 起 , 然 后 又 让 位 给 黑 夜 一样 。 这 种 清 醒 的 预 见 给 她 带 来 了 一 种 恐 惧 感 。 没有 补 救 办 法 , 一 切 都 是 不 可 推 移 的 , 都 被 一 种 卑俗 的 天 数 主 宰 着 。“ 她 对 我 闲 扯 了 一 大 堆 事 ,” 母 亲 继 续 说 。“ 她 告 诉 我 , 他 们 把 旧 汽 车 卖 了 , 买 回 一 辆 新的 …… 一 辆 菲 亚 特 ……‘ 您 知 道 吗 ,’ 她 对 我 说 ,‘ 我 丈 夫 在 国 民 银 行 里 成 了 帕 里 奥 尼 的 左 右 手…… 帕 里 奥 尼 缺 了 我 丈 夫 不 行 , 帕 里 奥 尼 认 为 我丈 夫 最 有 可 能 成 为 他 的 合 股 人 。’ 左 一 个 帕 里 奥尼 , 右 一 个 帕 里 奥 尼 …… 卑 鄙 !……”“ 为 什 么 说 她 卑 鄙 ?” 莱 奥 说 , 一 面 从 眯 缝着 的 眼 皮 中 间 打 量 着 这 个 女 人 。“ 这 一 切 当 中 有什 么 称 得 上 是 卑 鄙 的 ?”“ 您 知 道 吗 ,” 母 亲 紧 盯 着 他 说 , 似 乎 请 他仔 细 斟 酌 一 下 词 句 ,“ 帕 里 奥 尼 是 里 奇 家 的 朋 友?”“ 人 人 都 知 道 。” 莱 奥 说 。 他 那 混 浊 的 目 光沉 重 地 落 在 心 不 在 焉 和 无 可 奈 何 的 卡 尔 拉 身 上 。“ 您 是 不 是 也 知 道 ,” 玛 丽 阿 格 拉 齐 娅 一 字一 顿 地 追 问 ,“ 里 奇 夫 妇 认 识 帕 里 奥 尼 之 前 身 无分 文 …… 现 在 却 有 了 小 汽 车 ?”莱 奥 转 过 头 来 :“ 噢 , 原 来 是 为 了 这 事 。”他 大 声 说 道 :“ 这 有 什 么 不 好 的 ?…… 穷 人 嘛 , 各自 找 门 路 。”他 好 像 点 燃 了 一 根 仔 细 准 备 好 的 导 火 线 。“ 啊 , 是 这 样 ,” 母 亲 说 , 她 睁 大 两 眼 , 露出 嘲 讽 的 神 情 ;“ 您 为 一 个 不 知 羞 耻 、 长 相 也 不好 看 的 女 人 辩 解 。 这 个 干 瘪 娘 儿 厚 颜 无 耻 地 敲 诈她 的 朋 友 , 让 他 掏 腰 包 买 汽 车 , 买 衣 服 ; 还 能 想出 办 法 把 丈 夫 蒙 在 鼓 里 。 谁 知 道 她 那 个 丈 夫 是 笨蛋 还 是 滑 头 …… 您 还 有 原 则 吗 ? 哼 , 太 好 了 , 实 在太 好 了 …… 那 就 没 什 么 可 说 的 了 …… 一 切 都 能 解 释…… 显 然 , 您 喜 欢 那 种 女 人 ……”“ 瞧 。” 卡 尔 拉 心 想 。 由 于 忍 无 可 忍 , 她 的四 肢 微 微 哆 嗦 了 一 下 。 她 半 合 上 眼 睛 , 扭 过 头 ,使 脑 袋 离 开 灯 光 进 入 黑 影 中 ; 她 不 想 听 见 这 些话 。莱 奥 笑 了 起 来 :“ 不 , 老 实 说 , 我 喜 欢 的 不是 那 种 女 人 。” 他 向 身 旁 的 少 女 匆 匆 投 射 出 一 瞥贪 婪 的 目 光 …… 丰 满 的 胸 脯 , 鲜 花 般 的 面 颊 , 散发 着 青 春 气 息 的 身 段 。“ 喏 , 这 样 的 女 人 才 讨 我喜 欢 。” 他 想 大 声 对 情 人 这 么 说 。“ 您 现 在 是 这 样 讲 ,” 母 亲 坚 持 己 见 ,“ 您现 在 是 这 样 讲 …… 买 主 总 把 自 己 有 意 买 下 的 东 西贬 得 一 钱 不 值 …… 您 和 她 待 在 一 起 的 时 候 , 比 方说 前 天 在 西 多 利 家 里 , 您 对 她 赞 不 绝 口 。 当 时 您向 她 说 了 一 大 堆 傻 话 …… 嗨 , 算 了 吧 , 我 了 解 您这 个 人 …… 您 是 个 什 么 货 色 , 您 知 道 吗 ?…… 骗 人精 ……”“ 瞧 ,” 卡 尔 拉 再 次 想 道 , 这 场 口 角 会 继 续下 去 ; 她 早 就 晓 得 , 这 种 生 活 已 成 习 惯 , 无 法 纠正 , 无 法 改 变 。 卡 尔 拉 实 在 忍 受 不 下 去 了 。 她 站了 起 来 :“ 我 去 穿 件 毛 衣 , 马 上 就 回 来 。” 她 头也 不 回 地 走 了 出 去 , 因 为 她 感 觉 到 莱 奥 的 目 光 像两 条 水 蛭 似 的 吸 附 在 她 的 后 背 上 。在 过 道 里 , 她 碰 见 了 米 凯 莱 。“ 莱 奥 在 里 面吗 ?” 他 问 她 。 卡 尔 拉 看 了 弟 弟 一 眼 :“ 在 。”“ 我 刚 从 莱 奥 的 财 产 管 理 人 那 儿 来 ,” 小 伙子 接 着 心 平 气 和 地 说 。“ 知 道 了 一 大 堆 有 趣 的 事情 …… 首 先 是 , 我 们 完 了 。”“ 这 是 什 么 意 思 ?” 姑 娘 疑 惑 不 解 地 问 。“ 意 思 是 ,” 米 凯 莱 解 释 道 ,“ 我 们 得 把 别墅 交 给 莱 奥 , 用 来 偿 还 典 当 的 款 子 。 我 们 得 离 开这 里 , 两 手 空 空 地 离 开 这 里 , 到 别 的 地 方 去 。”他 们 相 互 看 看 。 小 伙 子 的 脸 上 掠 过 一 个 勉 强挤 出 来 的 惨 淡 的 微 笑 。“ 你 为 什 么 笑 ?” 她 问 。“ 你 觉 得 这 事 可 笑 吗 ?”“ 我 为 什 么 笑 ?” 他 反 问 道 。“ 因 为 我 对 这一 切 感 到 冷 漠 …… 噢 , 不 , 我 感 到 高 兴 。”“ 不 对 。”“ 没 错 , 正 是 这 样 。” 他 反 驳 道 。 他 没 有 再说 一 句 话 , 径 自 走 进 客 厅 。 卡 尔 拉 站 在 原 地 发愣 , 心 中 有 一 种 隐 隐 约 约 的 焦 虑 感 。母 亲 和 莱 奥 还 在 争 辩 。 米 凯 莱 刚 进 门 , 他 们就 从 以 “ 你 ” 相 称 变 为 以 “ 您 ” 相 称 ; 但 米 凯莱 及 时 听 见 了 。 他 怀 着 厌 恶 和 怜 悯 的 心 情 淡 然一 笑 。“ 我 看 是 吃 晚 饭 的 时 候 了 。” 他 对 母 亲说 。 他 没 跟 莱 奥 打 招 呼 , 甚 至 没 看 那 人 一 眼 。 不过 , 他 的 这 种 冷 淡 态 度 并 未 使 莱 奥 感 到 不 自 在 。“ 嗬 , 看 , 谁 来 了 ,” 莱 奥 用 往 常 那 种 欢 快 的 语调 说 ,“ 我 们 的 米 凯 莱 …… 到 这 儿 来 , 米 凯 莱 ……我 们 好 久 没 见 了 。”“ 只 有 两 天 。” 小 伙 子 直 勾 勾 地 盯 着 莱 奥说 。 他 试 图 装 出 冷 酷 和 愤 怒 的 样 子 , 然 而 他 感 到的 只 是 冷 漠 。 他 想 补 充 说 :“ 我 们 越 少 见 面 越好 。” 或 者 讲 一 句 类 似 的 话 , 可 是 他 既 没 有 敏 捷的 反 应 能 力 , 又 缺 乏 这 样 做 的 真 诚 愿 望 。“ 你 觉 得 两 天 算 不 了 什 么 吗 ?” 莱 奥 大 声说 。“ 两 天 内 可 以 做 出 许 多 事 情 来 。” 他 低 下头 , 灯 光 照 在 他 那 张 得 意 洋 洋 的 大 脸 膛 上 。“ 嘿 , 嘿 , 你 这 件 衣 服 真 好 看 …… 谁 给 你 做 的 ?……”这 是 一 件 用 深 蓝 色 料 子 做 成 的 上 衣 , 裁 剪 得很 合 身 , 但 已 穿 得 很 旧 了 , 莱 奥 起 码 见 他 穿 过一 百 次 。 然 而 , 这 句 直 截 了 当 的 话 打 中 了 米 凯 莱的 虚 荣 心 , 顷 刻 间 , 他 把 自 己 试 图 装 出 愤 怒 和 冷酷 的 样 子 的 所 有 意 愿 统 统 抛 到 了 九 霄 云 外 。“ 你 真 的 认 为 是 这 样 吗 ?……” 他 问 道 , 同 时毫 不 掩 饰 地 露 出 一 个 似 是 而 非 的 得 意 微 笑 。“ 是一 件 旧 衣 服 …… 我 已 穿 了 很 长 时 间 , 是 尼 诺 给 我做 的 , 你 知 道 吗 ?……” 他 本 能 地 转 过 身 , 让 莱 奥看 看 衣 服 的 后 片 , 并 用 双 手 拽 了 拽 衣 襟 , 使 上 衣更 贴 身 。 他 从 挂 在 对 面 墙 上 的 威 尼 斯 镜 子 中 看 见了 自 己 的 形 象 。 裁 剪 得 无 懈 可 击 , 这 是 毫 无 疑 问的 。 不 过 , 他 觉 得 自 己 的 行 为 既 十 分 可 笑 , 又 极为 愚 蠢 , 像 是 陈 列 在 商 店 橱 窗 里 的 木 头 人 : 身 上披 着 华 丽 的 衣 衫 , 胸 前 别 着 价 格 标 签 。 想 到 这儿 , 他 感 到 有 些 不 自 在 。“ 好 …… 真 好 ,” 莱 奥 这 时 弓 着 腰 , 摸 了 摸衣 料 , 然 后 又 直 起 身 子 来 。“ 我 们 的 米 凯 莱 是 好样 的 ,” 他 一 面 说 , 一 面 伸 出 手 拍 拍 米 凯 莱 的 胳臂 。“ 从 来 没 有 什 么 可 指 责 的 地 方 。 老 是 乐 呵 呵的 , 没 有 任 何 烦 人 的 念 头 。” 米 凯 莱 从 这 番 话 的语 气 和 伴 随 着 它 们 的 笑 容 来 判 断 , 知 道 自 己 被 狡猾 地 吹 捧 了 几 句 后 受 到 了 嘲 弄 ; 但 他 明 白 得 太 晚了 。 原 先 打 算 在 自 己 的 敌 人 面 前 发 泄 的 怒 火 和 怨气 眼 下 在 哪 儿 ? 在 别 处 , 停 留 在 他 的 意 愿 中 。 他为 自 己 的 这 种 出 自 虚 荣 心 的 举 动 而 感 到 颇 为 难堪 , 他 恨 自 己 。 他 看 了 母 亲 一 眼 。“ 真 遗 憾 , 今 天 你 没 跟 我 们 在 一 起 ,” 她说 。“ 我 们 看 了 一 部 精 彩 的 电 影 。”“ 唔 , 是 吗 ?” 小 伙 子 说 ; 他 随 即 朝 莱 奥 转过 身 , 竭 力 用 最 生 硬 、 最 愤 慨 的 声 音 说 :“ 我 到 你 的 财 产 管 理 人 那 儿 去 过 了 , 莱 奥……”然 而 对 方 却 猛 地 一 挥 手 , 打 断 了 他 的 话 :“ 现 在 别 谈 这 事 …… 我 明 白 了 …… 以 后 再 说 …… 吃完 晚 饭 后 …… 每 样 事 情 都 有 它 合 适 的 时 机 。”“ 随 你 的 便 ,” 小 伙 子 用 一 种 本 能 的 顺 从 口吻 说 。 他 立 刻 觉 察 到 , 自 己 又 一 次 被 莱 奥 驾 驭了 。“ 我 应 该 说 , 马 上 就 谈 ,” 他 心 里 琢 磨 道 。“ 任 何 人 都 会 这 么 做 的 …… 马 上 就 谈 , 争 论 一番 , 或 者 破 口 大 骂 。” 他 恼 火 得 想 大 嚷 一 声 。 虚荣 和 冷 漠 : 莱 奥 在 几 分 钟 内 就 让 他 掉 进 了 这 两 个可 恶 的 深 渊 。 那 两 个 人 —— 母 亲 和 她 的 情 人 ——站 起 身 来 。“ 我 饿 了 ,” 莱 奥 边 说 边 扣 好 上 衣 扣 子 ,“ 饿 得 ……” 母 亲 笑 吟 吟 的 , 米 凯 莱 机 械 地 跟 着他 们 。“ 晚 饭 后 ,” 他 想 道 , 同 时 徒 劳 无 益 地 企图 使 自 己 这 些 几 乎 是 漫 不 经 心 的 念 头 带 上 一 些 愤懑 的 色 彩 ,“ 不 会 让 你 这 么 便 宜 。”他 们 在 门 口 站 住 。“ 请 ,” 莱 奥 说 。 母 亲 走了 出 去 。 他 们 两 人 —— 莱 奥 和 米 凯 莱 —— 面 对面 待 在 那 儿 , 互 相 看 着 对 方 。“ 你 先 走 , 你 先走 ,” 莱 奥 彬 彬 有 礼 地 坚 持 道 , 他 伸 出 手 搭 在 米凯 莱 肩 上 。“ 主 人 先 请 ……” 他 露 出 一 个 友 好 得像 是 嘲 弄 的 微 笑 , 做 出 一 个 慈 父 般 的 动 作 , 轻 轻推 着 小 伙 子 往 外 走 。“ 主 人 ,” 米 凯 莱 暗 自 思量 , 但 他 心 头 连 一 丝 愤 怒 的 影 子 也 没 有 ,“ 瞧 ,说 得 多 妙 …… 这 个 家 的 主 人 是 你 。” 然 而 他 什 么也 没 说 , 跟 着 母 亲 走 进 了 过 道 。袁 华 清 译译 文 选 自 译 林 出 版 社 《 莫 拉 维 亚 作 品 》鸣 谢 译 林 出 版 社 对 本 刊 的 支 持48 49
NO.7Le recensioni 图 书 推 荐Alberto MoraviaGli IndifferentiBompiani, 2000pp. 340, RMB- Yuan 95Alberto MoraviaLa CiociaraBompiani, 2001pp. 380, RMB- Yuan 95Il sipario si apre in una lussuosa villa di Roma, i riflettori sorprendono gliatteggiamenti finti e abitudinari della famiglia Ardengo. Una storia senzatrama: i personaggi-marionette si lasciano vivere dagli avvenimenti etrascinare dalla lieve corrente di una vita ripetitiva e consunta.Dopo gli avvenimenti dell’8 settembre del 1943 Moravia si rifugia conla moglie a Sant’Agata, un villaggio montano di pastori provenientida Vallecorsa (Ciociaria) presso la famiglia Marrocco-Mirabella; daquesta esperienza e dal rapporto con questa famiglia nasce questo romanzo.Nel La Ciociara, attraverso la maturazione del personaggio diCesira, lo scrittore intende descrivere tutta la confusa e disperata realtàitaliana del periodo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Alberto MoraviaIl ConformistaBompiani, 2002pp. 336, RMB- Yuan 100Il conformista apparentemente è più cose: la storia di un viaggio di nozzea Parigi; quella di un delitto di stato; la biografia di un uomo; la descrizionedi un’epoca e di una società. Ma, a ben guardare, questo romanzoè soprattutto il ritratto di un personaggio e di un atteggiamento moralecaratteristici del nostro tempo: il conformista e il conformismo.Alberto MoraviaViaggi. Articoli 1930- 1990Bompiani, 1994pp. 1836, RMB- Yuan 335Raccolta di articoli apparsi originariamente su varie testate giornalistiche;documentano le impressioni e riflessioni dell’autore nel corsodei numerosissimi viaggi compiuti in tutto il mondo.Alberto MoraviaOpere. 1927-1947Bompiani, 1986pp. 1170, RMB- Yuan 335Il primo volume antologico degli scritti di Moravia. A cura di Geno Pampaloni,con l’autobiografia letteraria dell’autore.ciaoDirettore 主 编 : Barbara Alighiero 巴 尔 巴 拉Caporedattore 责 任 编 辑 : Ombretta Melli 梅 礼Redazione 编 辑 :Patrizia Liberati 李 莎Tiziana Carcich 卡 琪Tang Di 汤 荻Luo Rui 罗 睿Wang Leilei 王 蕾 蕾Rubriche 专 栏 作 者 :Claudio PoetaGrafica 平 面 设 计 :Su Xinxin 苏 欣 欣Pubblicità 广 告 :Yang Xiaoning 杨 晓 宁Tel: +86 10 6532 2187A questo numero hanno collaborato 本 期 合 作 者 :Sara Iaia, Claudia Tabacchino, Federica TagliabueTUTTI I LIBRI SONO DISPONIBILI NELLA LIBRERIA DELL’ISTITUTOTUTTI I LIBRI SONO DISPONIBILI NELLA LIBRERIA DELL’ISTITUTO50www.iicpechino.esteri.itlibreria.iicpechino@esteri.itlibreria.iicpechino@esteri.it51
NO.7Le recensioni 图 书 推 荐丛 书 名 : 莫 拉 维 亚 作 品出 版 社 : 凤 凰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 译 林 出 版 社 ; 第 1 版 (2010 年 5 月 1 日 )《 鄙 视 》 内 容 简 介 :有 志 于 从 事 戏 剧 创 作 的 里 卡 尔 多 · 莫 尔 泰 尼 为 博 得 妻 子 埃 米丽 亚 的 爱 , 违 背 自 己 的 意 愿 , 为 电 影 制 片 人 编 写 电 影 脚 本 , 以 尽快 获 得 金 钱 , 满 足 妻 子 的 物 质 欲 求 。 可 是 , 当 他 满 足 了 妻 子 的 欲求 时 , 妻 子 却 已 不 再 爱 他 , 并 对 他 表 示 出 极 度 的 鄙 视 。 里 卡 尔 多痛 苦 万 分 , 而 当 他 决 定 放 弃 编 剧 工 作 , 不 再 依 附 于 制 片 人 时 , 妻子 却 又 对 他 的 决 定 嗤 之 以 鼻 。 夫 妻 之 间 在 情 感 上 的 无 法 沟 通 , 造成 了 难 以 填 平 的 鸿 沟 。 小 说 通 过 一 对 夫 妻 感 情 生 活 的 破 裂 这 个 侧面 反 映 了 当 代 的 社 会 现 实 和 现 代 人 深 刻 的 精 神 危 机 。《 鄙 视 》 曾被 法 国 著 名 导 演 戈 达 尔 拍 成 电 影 。《 不 由 自 主 》 内 容 简 介 :这 个 短 篇 小 说 集 中 的 四 十 一 篇 作 品 从 不 同 侧 面 表 现 了 意 大 利社 会 中 产 阶 级 在 精 神 上 的 迷 惘 与 困 惑 , 以 及 人 的 异 化 和 扭 曲 。 书中 的 人 物 , 家 庭 背 景 、 职 业 、 生 活 和 行 为 虽 然 各 不 相 同 , 但 他 们都 由 于 一 些 自 己 也 不 明 白 的 原 因 , 不 由 自 主 地 做 着 自 己 并 不 想 做的 事 。 他 们 不 再 是 物 质 的 主 宰 , 而 是 变 成 了 物 质 的 附 属 品 。 甚 至可 以 说 , 人 变 成 了 他 所 拥 有 的 众 多 机 器 中 的 一 台 , 也 像 机 器 那 样在 外 力 的 驱 使 下 做 着 机 械 的 运 动 , 显 得 无 奈 和 不 由 自 主 。《 冷 漠 的 人 》 内 容 简 介 :虚 荣 而 愚 蠢 的 中 年 寡 妇 玛 丽 阿 格 拉 齐 娅 把 全 部 家 庭 事 务 交 给情 人 莱 奥 处 理 , 从 而 导 致 了 家 庭 经 济 状 况 的 日 益 恶 化 , 濒 临 破产 。 莱 奥 则 一 边 敷 衍 着 玛 丽 阿 格 拉 齐 娅 , 从 这 个 家 庭 榨 取 更 多 的钱 财 , 一 边 觊 觎 漂 亮 的 卡 尔 拉 。 女 儿 卡 尔 拉 迫 于 家 庭 的 经 济 情 况以 及 莱 奥 的 引 诱 , 最 终 委 身 于 他 , 以 过 上 所 谓 的 新 生 活 。 儿 子 米凯 莱 内 心 充 满 痛 苦 , 虽 然 仇 恨 莱 奥 , 但 天 生 的 懦 弱 性 格 使 他 只 能冷 漠 地 旁 观 , 并 最 终 与 莱 奥 和 解 。 这 是 一 部 兼 具 小 说 和 戏 剧 特 点的 小 说 , 通 过 对 一 个 岌 岌 可 危 的 家 庭 在 两 天 里 的 活 动 的 描 写 , 揭示 了 人 们 灵 魂 深 处 的 冷 漠 。《 冷 漠 的 人 》 曾 被 意 大 利 著 名 导 演 马塞 利 拍 成 同 名 电 影 。《 注 意 》 内 容 简 介 :这 部 小 说 的 第 一 人 称 主 人 公 是 作 家 兼 记 者 , 出 身 于 资 产 阶 级家 庭 , 他 出 于 对 自 己 阶 级 的 厌 恶 和 对 平 民 阶 级 的 好 感 , 与 出 身 平民 阶 级 的 裁 缝 科 拉 结 了 婚 。 他 决 定 以 日 记 的 形 式 记 录 自 己 的 爱 情经 历 , 以 便 日 后 根 据 日 记 写 作 小 说 。 而 当 他 回 想 与 妻 子 的 爱 情 婚姻 经 历 时 , 却 发 现 自 己 已 经 不 再 爱 科 拉 了 , 而 自 己 过 去 狂 热 追 求的 生 活 也 显 得 不 真 实 。这 是 一 部 手 法 奇 特 的 作 品 , 用 作 者 自 己 的 话 来 说 就 是 , 作 品真 正 的 主 人 公 并 不 是 小 说 的 主 人 公 , 而 是 小 说 的 主 人 公 “ 我 ” 一直 在 写 着 、 准 备 将 来 有 一 天 用 作 某 部 小 说 的 素 材 的 日 记 。《 乔 恰 里 亚 女 人 》 内 容 简 介 :农 民 出 身 的 罗 马 小 店 主 切 西 拉 为 躲 避 战 乱 和 饥 饿 , 带 着 女 儿罗 赛 塔 逃 往 意 大 利 南 方 的 山 区 避 难 。 小 说 通 过 她 们 在 山 中 所 过 的九 个 月 的 艰 苦 生 活 , 揭 示 了 由 意 大 利 法 西 斯 和 德 国 纳 粹 发 动 的 第二 次 世 界 大 战 给 意 大 利 的 普 通 民 众 带 来 的 苦 难 和 对 人 类 文 明 的 破坏 , 以 及 对 人 的 道 德 和 灵 魂 的 摧 残 。 这 部 在 战 争 结 束 十 年 之 后 创作 的 长 篇 小 说 , 有 着 其 他 回 忆 战 争 经 历 的 小 说 所 未 曾 具 有 的 思 想深 度 , 是 公 认 的 意 大 利 战 后 最 杰 出 的 小 说 。 小 说 出 版 后 不 久 即 被意 大 利 著 名 导 演 维 托 里 奥 · 德 西 卡 搬 上 银 幕 , 引 起 世 界 轰 动 , 获得 第 三 十 四 届 奥 斯 卡 最 佳 外 语 片 奖 , 饰 演 切 西 拉 的 索 菲 亚 · 罗 兰获 得 最 佳 女 主 角 奖 。《 同 流 者 》 内 容 简 介 :出 身 于 不 正 常 家 庭 的 马 尔 切 洛 · 克 莱 利 齐 从 小 就 有 意 识 地 追求 正 常 状 态 。 为 了 得 到 同 学 的 尊 重 , 他 从 纠 缠 自 己 的 性 变 态 者 利诺 那 里 得 到 一 把 手 枪 , 并 开 枪 杀 死 利 诺 。 杀 人 罪 带 给 他 的 内 心 折磨 益 加 激 起 了 回 归 正 常 状 态 的 决 心 。 他 加 入 法 西 斯 党 , 成 了 秘 密警 察 , 与 正 常 家 庭 出 身 的 朱 丽 亚 结 婚 。 在 去 巴 黎 的 蜜 月 旅 行 时 ,他 协 助 实 施 对 反 法 西 斯 组 织 领 袖 夸 德 里 教 授 的 谋 杀 。 虽 然 他 把 参与 谋 杀 夸 德 里 视 为 达 到 正 常 状 态 的 必 要 步 骤 , 却 无 法 摆 脱 内 心 深处 的 负 罪 感 。 法 西 斯 政 府 倒 台 了 , 他 突 然 发 现 自 己 一 直 在 追 求 顺应 时 代 、 顺 应 社 会 , 最 终 还 是 被 时 代 和 社 会 抛 弃 。 为 躲 避 惩 罚 ,他 带 着 妻 子 和 女 儿 逃 往 山 区 , 途 中 遭 到 了 美 军 飞 机 的 射 击 ……《 同流 者 》 曾 被 意 大 利 著 名 导 演 贝 尔 托 鲁 奇 拍 成 同 名 电 影 。所 有 图 书 意 大 利 书 屋 有 售所 有 图 书 意 大 利 书 屋 有 售52 libreria.iicpechino@esteri.itlibreria.iicpechino@esteri.it53
DA NON PERDERE IN ITALIASpettacoli9 giugno – 13 luglio, 21o Ravenna Festival, RavennaMusica, balletto, teatro danzawww.ravennafestival.org30 giugno - 8 settembre, Un’Estate al Madre, NapoliSei sere a settimana di Musica, Danza, Arte, Cinema, Teatro e Mostreall’interno degli spazi espositivi del Museo Madre.www.museomadre.it1 luglio – 31 agosto, Teatro dell’Opera di Roma alle Terme di Caracallahttp://www.operaroma.it/1 luglio – 26 settembre, Ravello Festival 2010 La Follia, Ravello(Salerno)www.ravellofestival.com5 – 30 luglio, Rock in Roma, Ippodromo delle Cappanelle di Romawww.rockinroma.com9 – 18 luglio, Umbria Jazz 10, Perugiawww.umbriajazz.com12 luglio – 2 agosto, Milano Jazzin’ Festival, Arena Civica di Milanowww.milanojazzinfestival.it16 luglio – 22 agosto, 56 o Festival Puccini, Torre del Lago Puccini,Viareggio (Lucca)www.puccinifestival.it18 - 31 luglio, 40o Giffoni Film Festival Giffoni Valle Piana (SA)www.giffoni.itMostre24 giugno - 26 settembre, It’s Only Rock ‘n’ Roll Baby!, TriennaleBovisa di MilanoStoria dei musicisti rock che si sono espressi anche attraverso learti visivehttp://www.vogue.it/26 giugno - 15 settembre, Vicoli Sotto le Stelle, Romatrekking urbano seralealla scoperta di luoghi e monumentidi Roma e dei Castelli Romani accompagnati da archeologiprofessionisti.http://www.savethedate.it/fino al 5 settembre L’Età della Conquista: Il fascino dell’arte grecaa RomaPalazzo Caffarelli, Musei Capitolini di Romawww.museicapitolini.orgfino al 17 ottobre, Caravaggio e caravaggeschi a FirenzePalazzo Pitti, Uffizi, Villa Baldini di Firenzehttp://www.unannoadarte.it/caravaggio/fino al 7 gennaio 2011, tagli d’Artista: una storia lunga un secoloGalleria Nazionale d’Arte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di RomaPresentazione di “Ambiente spaziale con tagli” di Lucio Fontana ealtri capolavori del ‘900http://www.gnam.beniculturali.it/22 luglio - 21 agosto, 12o Festival Suono dal Salento 2010, Lecce eCopertinoGrandi nomi della musica nazionale ed internazionalewww.savethedate.it/54 www.beniculturali.itwww.beniculturali.it55
Cinema 电 影 NO.7LUGLIO 2010 - ogni venerdì ore 19.30, ingresso liberoIstituto Italiano di <strong>Cultura</strong> di Pechino七 月 -- 每 周 五 19:30, 免 费 入 场北 京 意 大 利 文 化 处VEN 2 – LA ROMANAAdriana è una ragazza molto bella ma povera che, dopo alcune delusionisentimentali, finisce per darsi alla prostituzione. L’incontro e l’amore perGino, antifascista in clandestinità, sembra darle una nuova speranza di vita.Regista: Luigi ZampaCast: Gina Lollobrigida, Franco Fabrizi, Daniel GélinSott. italiano, 99’, 1955 – bianco e nero7 月 2 日 --《 罗 马 女 人 》亚 德 里 亚 娜 是 一 个 美 丽 而 贫 穷 的 女 孩 , 经 历 过 几 次 感 情 挫 折 后 , 她 走 上了 卖 淫 的 道 路 。 她 遇 见 了 季 诺 并 爱 上 了 他 , 一 个 反 法 西 斯 非 法 移 民 团 伙成 员 , 他 似 乎 给 了 亚 德 里 亚 娜 生 活 的 新 希 望 。导 演 : 路 易 奇 · 赞 巴主 演 : 吉 娜 · 罗 布 里 吉 达 , 弗 朗 科 · 法 布 里 奇 , 丹 尼 尔 · 格 林字 幕 : 意 大 利 文 ,99’,1955’, 黑 白VEN 9 – LA CIOCIARAAnno 1943, l'affacciarsi dei nuovi valori liberali si contrappone ad unpaesaggio culturale fratturato e sconvolto dalla guerra. La storia racconta ladrammatica fuga da Roma di Cesira, giovane vedova, con la figlia tredicenne.Oscar per Sophia Loren e Nastro d’argento 1961.Regia: Vittorio De SicaCast: Sophia Loren, Eleonora Brown, Jean-Paul Belmondo e Renato SalvatoriSott. cinese, 105’, 1960 – bianco e nero7 月 9 日 --《 丘 恰 拉 》1943 年 , 德 国 占 领 意 大 利 的 九 个 月 , 人 们 面 对 的 是 被 战 争 撕 裂 和 颠 覆 的价 值 观 。 年 轻 的 寡 妇 切 西 拉 , 带 着 十 三 岁 的 女 儿 逃 离 罗 马 , 来 到 丘 恰拉 , 一 个 似 乎 可 以 让 他 们 的 生 活 恢 复 安 宁 的 小 城 , 但 盟 军 的 到 来 却 改 变了 一 切 , 造 成 了 无 法 弥 补 的 创 伤 。索 菲 亚 · 罗 兰 凭 借 此 片 奥 斯 卡 封 后 , 同 时 也 赢 得 1961 年 “ 银 丝 带 ” 奖导 演 : 维 多 利 奥 · 德 西 卡主 演 : 索 菲 亚 · 罗 兰 , 埃 莱 奥 诺 拉 · 布 朗 , 让 - 保 罗 · 贝 蒙 德 , 雷 纳德 · 萨 尔 瓦 多字 幕 : 中 文 ,105’,1960, 黑 白VEN 17 – LA PROVINCIALEA casa del professor Vagnuzzi fervono i preparativi per il trasferimento aRoma. Dopo la cena, Gemma, la moglie del professore, si avventa senza unmotivo apparente sull’ospite, la contessa romena Elvira Coceanu ferendolacon un coltello.Regia: Mario SoldatiCast: Gina Lollobrigida, Gabriele Ferzetti e Alda ManginiSott. italiano, 109’, 1963 – bianco e nero7 月 17 日 --《 城 里 来 的 女 人 》瓦 努 奇 教 授 一 家 正 在 准 备 搬 家 到 罗 马 。 晚 餐 后 , 教 授 的 妻 子 杰 玛 不 知何 因 忽 然 暴 怒 , 用 刀 刺 伤 了 伯 爵 夫 人 埃 尔 薇 拉 · 珂 夏 努 。 一 个 秘 密 逐渐 呈 现 在 人 们 面 前 , 这 个 秘 密 把 她 和 伯 爵 夫 人 联 系 在 一 起 , 同 时 也 威胁 着 她 的 婚 姻 。导 演 : 马 里 奥 · 索 达 迪主 演 : 吉 娜 · 洛 洛 布 里 吉 达 , 加 布 里 艾 拉 · 菲 尔 则 迪 , 阿 尔 达 · 曼 吉 尼字 幕 : 意 大 利 文 ,109’,1963, 黑 白VEN 23 – GLI INDIFFERENTIGli Ardegno, una ricca ed annoiata famiglia della borghesia romana èormai in declino. Maria Grazia, vedova con due figli, è da anni l’amantedi Leo Merumeci, un uomo d’affari privo di scrupoli che cura gli interessipatrimoniali della famiglia.Regia: Francesco MaselliCast: Claudia Cardinale, Rod Steiger, Shelley Winters, Tomas MilianSott. italiano, 86’, 1964 – bianco e nero7 月 23 日 --《 要 塞 风 云 》《 冷 漠 的 人 》 讲 述 的 是 一 个 富 有 而 乏 味 的 罗 马 中 产 阶 级 家 庭 的 衰 落 。带 着 两 个 孩 子 的 寡 妇 玛 利 亚 · 格 拉 齐 亚 , 多 年 来 一 直 是 梅 鲁 梅 齐 的 情人 , 梅 是 一 个 无 所 顾 忌 的 商 人 , 负 责 处 理 家 族 财 产 。 他 厌 倦 了 自 己 的情 人 , 却 开 始 勾 引 情 人 的 女 儿 卡 拉 。导 演 : 弗 朗 切 斯 科 · 马 赛 利主 演 : 克 劳 迪 娅 · 卡 尔 迪 娜 莱 , 罗 德 · 斯 德 格 , 雪 莉 · 温 特 斯字 幕 : 意 大 利 文 ,86’,1964, 黑 白VEN 30 – IL CONFORMISTAIl desiderio di normalità trasforma Marcello Clerici in sicario del regimefascista. Va a Parigi ad uccidere un suo professore fuori uscito. Il 25 luglio1943 fa una tremenda scoperta. È il più inventato e liberamente criticodei film tratti da Moravia, di raffinata eleganza figurativa e di trascinanteinvenzione stilistica.Regista: Bernardo BertolucciCast: Stefania Sandrelli, Dominique Sanda e Pierre ClementiSott. cinese, 110’, 19707 月 30 日 --《 同 流 者 》讲 述 了 一 个 意 大 利 年 轻 人 因 为 政 见 不 同 , 而 谋 杀 了 自 己 老 师 的 故 事 。影 片 故 事 流 畅 , 主 题 深 刻 , 演 员 表 演 到 位 , 具 有 Bernardo Bertolucci 早期 电 影 中 将 政 治 与 情 欲 融 为 一 体 的 风 格 。 此 片 为 Bernardo Bertolucci 赢得 奥 斯 卡 最 佳 编 剧 提 名 , 成 就 了 其 国 际 声 望 。导 演 : 伯 纳 多 · 贝 托 鲁 奇主 演 : 斯 黛 法 尼 亚 · 桑 德 莱 利 , 多 梅 尼 克 · 桑 达 , 皮 埃 尔 · 克 莱 门 迪字 幕 : 中 文 ,110’,197056 57
Cinema 电 影 NO.7AGOSTO 2010 - ogni venerdì ore 19.30, ingresso liberoIstituto Italiano di <strong>Cultura</strong> di Pechino八 月 -- 每 周 五 19:30, 免 费 入 场北 京 意 大 利 文 化 处VEN 6 – SarahsaràLiberamente ispirato alla storia vera di Sarah Gadalla Gubara. In Namibia,appiedato per una rottura al motore, un giornalista viene quasi travoltoda un’ambulanza: inseguendo il conducente al pronto soccorso, assiste aldramma di due immigrati indiani la cui figlia di 3 anni, Sarah, resterà zoppaper un’iniezione. Ma nove anni più tardi Sarah è diventata una bravissimanuotatrice…Regia: Renzo MartinelliCast: Lucio Allocca, Giulio BrogiSott. italiano, 105’, 19948 月 6 日 --《 萨 拉 传 奇 》根 据 萨 拉 · 加 达 拉 · 古 巴 拉 的 真 实 故 事 改 编 。 在 纳 米 比 亚 , 由 于 发 动 机故 障 , 救 护 车 差 点 撞 倒 一 名 记 者 : 他 跟 着 司 机 来 到 医 院 急 诊 室 , 亲 眼 看到 一 对 印 度 移 民 夫 妇 三 岁 的 女 儿 萨 拉 由 于 一 次 注 射 的 失 误 变 成 了 跛 子 。而 九 年 后 , 萨 拉 成 为 了 一 名 优 秀 的 游 泳 运 动 员 ...导 演 : 兰 佐 · 马 尔 迪 内 里主 演 : 卢 其 奥 · 阿 洛 卡 , 朱 里 奥 · 布 罗 吉字 幕 : 意 大 利 文 ,105’,1994VEN 20 – Estate RomanaRossella, attrice di teatro di avanguardia, ritorna a Roma dopo anni diassenza, ma nulla le appare più come prima. La accompagnano nel suogirovagare Salvatore, scenografo napoletano, l’assistente Monica e uningombrante mappamondo costruito per uno spettacolo ispirato a GuerreStellari.Dal regista di Gomorra.Regista: Matteo GarroneCast: Rossella Or, Monica Nappo, Salvatore SansoneSott. inglese, 87’, 20008 月 20 日 --《 罗 马 之 夏 》罗 塞 拉 是 一 名 先 锋 戏 剧 演 员 , 离 开 罗 马 多 年 后 再 回 来 , 她 发 觉 一 切 都和 从 前 不 一 样 了 。 来 自 那 不 勒 斯 的 布 景 师 萨 尔 瓦 多 和 助 理 莫 妮 卡 陪 伴着 她 , 他 们 将 演 出 以 《 星 球 大 战 》 为 灵 感 的 一 出 戏 。《 格 莫 拉 》 导 演马 岱 奥 · 加 罗 内 作 品 。导 演 : 马 岱 奥 · 加 罗 内主 演 : 罗 塞 拉 · 奥 尔 , 莫 妮 卡 · 纳 珀 , 萨 尔 瓦 多 · 桑 所 内字 幕 : 英 文 ,87’,2000VEN 13 – Un altro pianetaÈ una mattina d’estate. Salvatore sta percorrendo, tra le dune, il tragitto chelo porta alla spiaggia per trascorrere un po’ di tempo da solo. Contrariamentealle sue aspettative, Salvatore si troverà coinvolto nelle storie di un gruppo dipersone, ritrovando la serenità perduta.Regista: Stefano TummoliniCast: Antonio Merone, Lucia MascinoSott. inglese, 82’, 2008VEN 27 – MarneroDue donne vivono insieme nella stessa casa alla periferia di Firenze. Gemmaè un’anziana da poco rimasta vedova, Angela, la badante, è una giovanerumena da poco in Italia. Entrambe sole, si cercano inconsapevolmente e,giorno dopo giorno, si schiudono una all’altra.Regia: Federico BondiCast: Ilaria Occhini, Dorotheea PetreSott. italiano, 91’, 20098 月 13 日 --《 另 一 个 星 球 》夏 日 的 一 个 清 晨 。 萨 尔 瓦 多 在 沙 丘 中 旅 行 , 他 的 目 的 地 是 海 边 , 独 自 享受 一 个 人 的 假 期 。 然 而 他 没 有 想 到 的 是 , 路 上 遇 到 的 一 群 家 伙 , 却 帮 助他 找 到 了 失 去 的 开 朗 。导 演 : 斯 戴 法 诺 · 图 莫 里 尼主 演 : 安 东 尼 奥 · 麦 罗 内 , 露 琪 亚 · 马 西 诺字 幕 : 英 文 ,82’,20088 月 27 日 --《 黑 海 》两 个 女 人 同 住 在 佛 罗 伦 萨 郊 区 的 一 所 房 子 里 。 年 迈 的 杰 玛 刚 刚 寡 居 , 她的 护 理 安 吉 拉 是 一 个 年 轻 的 罗 马 尼 亚 女 人 , 刚 到 意 大 利 不 久 。 两 个 孤 独的 女 人 , 随 着 日 子 的 推 移 , 逐 渐 对 对 方 敞 开 了 心 扉 。导 演 : 费 得 里 克 · 班 迪主 演 : 伊 拉 莉 亚 · 奥 奇 尼 , 多 萝 西 · 佩 特 雷字 幕 : 意 大 利 语 ,91’,200958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