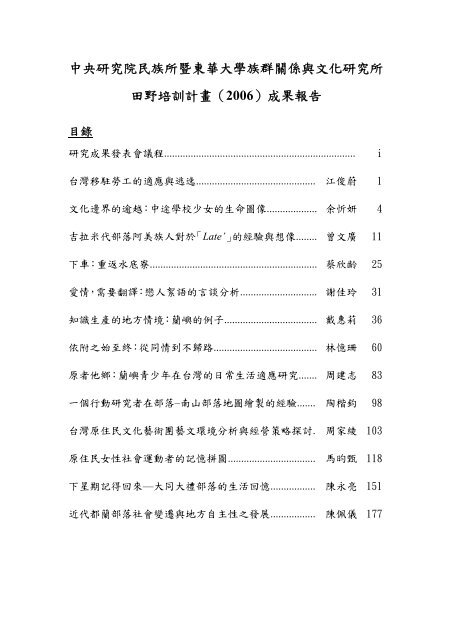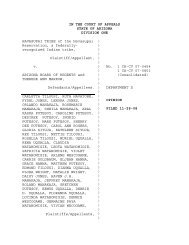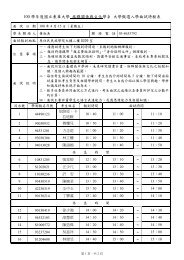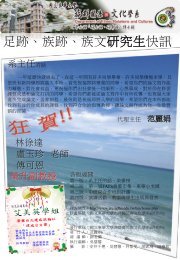Erfolgreiche ePaper selbst erstellen
Machen Sie aus Ihren PDF Publikationen ein blätterbares Flipbook mit unserer einzigartigen Google optimierten e-Paper Software.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暨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br />
目錄<br />
田野培訓計畫(2006)成果報告<br />
研究成果發表會議程........................................................................ i<br />
台灣移駐勞工的適應與逃逸............................................. 江俊蔚 1<br />
文化邊界的逾越:中途學校少女的生命圖像................... 余忻妍 4<br />
吉拉米代部落阿美族人對於「Late’」的經驗與想像........ 曾文廣 11<br />
下車:重返水底寮............................................................... 蔡欣齡 25<br />
愛情,需要翻譯:戀人絮語的言談分析............................. 謝佳玲 31<br />
知識生產的地方情境:蘭嶼的例子................................... 戴惠莉 36<br />
依附之始至終:從同情到不歸路....................................... 林憶珊 60<br />
原者他鄉:蘭嶼青少年在台灣的日常生活適應研究....... 周建志 83<br />
一個行動研究者在部落–南山部落地圖繪製的經驗....... 陶楷鈞 98<br />
台灣原住民文化藝術團藝文環境分析與經營策略探討. 周家綾 103<br />
原住民女性社會運動者的記憶拼圖................................. 馬昀甄 118<br />
下星期記得回來—大同大禮部落的生活回憶................. 陳永亮 151<br />
近代都蘭部落社會變遷與地方自主性之發展................. 陳佩儀 177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暨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br />
田野培訓計畫(2006) 研究成果發表會議程<br />
日期:96 年 11 月 17 日(星期六)<br />
地點:東華大學文一講堂<br />
場次 時間 論文題目 發表人 對話人<br />
∕主持人<br />
開幕 09:00-09:05 羅正心 教授<br />
09:05-09:25 外藉勞工逃逸因素調查 江俊蔚<br />
09:25-09:45 文化邊界的逾越:中途學校少<br />
第一場<br />
女的生命圖像<br />
余忻妍<br />
鄧湘漪<br />
09:45-10:05 阿美族 Lati’ 的經驗與想像 曾文廣<br />
10:05-10:20 討論<br />
茶敘 10:20-10:40<br />
10:40-11:00 下車:重返水底寮 蔡欣齡<br />
11:00-11:20 分手戀人絮語 謝佳玲 許超智<br />
第二場 11:20-11:30 討論<br />
11:30-12:10 原者他鄉:蘭嶼青少年在台灣<br />
的日常生活適應研究<br />
周建志 張志杰<br />
午餐 12:10-13:30<br />
13:30-14:10 原住民女性社會運動者的記憶<br />
第三場<br />
14:10-14:50<br />
拼圖<br />
馬昀甄<br />
台灣原住民文化藝術團藝文環<br />
境分析與經營策略探討<br />
周家綾<br />
黃雅鴻<br />
茶敘 14:50-15:10<br />
15:10-15:50 下星期記得回來 陳永亮<br />
第四場<br />
15:50-16:30 近代都蘭部落社會變遷與地方<br />
自主性之發展<br />
陳佩儀<br />
白皇湧<br />
綜合討論<br />
與閉幕<br />
16:30-17:00 羅正心 教授<br />
發表規則:<br />
1. 本發表會論文分為「田野可行性調查」(江俊蔚、余忻妍、曾文廣、蔡欣齡、<br />
謝佳玲)與「碩士論文田野」(周建志、馬昀甄、周家綾、陳永亮、陳佩儀)<br />
兩類。<br />
2.「田野可行性調查」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20 分鐘,每篇討論時間為 5 分鐘。<br />
3.「碩士論文田野」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30 分鐘,每篇討論時間為 10 分鐘。<br />
i
台灣移駐勞工的適應與逃逸<br />
江俊蔚<br />
本研究以質性訪談的方式探討不同工作性質的移駐勞工(外藉勞工)在台生<br />
活及工作的適應情形,並檢視兩者間的差異是否構成其適應上的不同,進而影響<br />
移工逃逸與否的要素。<br />
原本合法在台工作的移駐勞工,為何要冒著隨時被查緝、遣返的風險,而「主<br />
動」成為非法移工,其原因是被迫或是出之於自願,亦或是源於結構性因素所導<br />
致?在質性研究的期間,不但訪問了移駐勞工,同時也訪問了雇主,試著透過對<br />
勞雇雙方各別的會談來探討彼此的關係,在此同時,為了更進一步瞭解移駐勞工<br />
的工作內容,本研究與移工接觸並非只在受訪者下班後進行訪談,研究者亦在勞<br />
雇雙方同意之下直接參與了移工的工作場所及工作過程,藉此更為深入瞭解移工<br />
的真實面貌。<br />
由於直接與逃逸之外勞接洽實非易事,故本研究以透過深度訪談來訪問在台<br />
外勞針對其友人(非針對受訪者)或已知逃逸情形進行訪談;或者藉以同樣是移工<br />
的角度來思考,在什麼樣的情境下,會產生逃逸的念頭。研究問卷屬開放式問卷,<br />
一方面可能更瞭解其生活的多面向,更希望能透過此方法獲得到更多關於生活適<br />
應與逃逸的資訊。<br />
一、研究目的<br />
本研究試圖以移駐勞工的角度來看待「離開現有體制」的現象,而非一昧地<br />
刑責化他們對於既有社會制度的反抗,並藉此提供一個讓他們發聲的機會,進而<br />
尋求適切的解決之道,以創造勞雇雙贏的局面,然主要目的分述如下:<br />
(一) 瞭解當前國內國際移駐勞工社會適應現況(及潛在的問題)。<br />
(二) 探討結構性因素對國際移駐勞工在社會適應上的影響。<br />
(三) 瞭解事業單位、僱主與國家機器對國際移工在適應上的安排與處遇,並<br />
評估所面臨的困難及需要的協助。<br />
(四) 比較不同工作性質之國際移工,在社會適應上的差異。<br />
(五) 試圖提出具體方案以降低移工逃逸的發生率,進而減少社會成本(如查<br />
緝、犯罪率與民眾觀感等)的支出。<br />
二、研究困境與挑戰<br />
(一) 本研究之資訊一部份探討報導人其自身可能逃逸的潛在原因,另一部份<br />
則透過受訪者轉述其友人逃逸經驗,固在轉述上可能造成內容上的失<br />
真,進而影響本研究之真實性。<br />
(二)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多在受訪者的工作場合,甚至雇主就參與其中,<br />
若論及敏感議題時,例如與雇主之關係、是否曾想過要逃逸等,恐會造<br />
1
(三) 與移駐勞工的訪談過程皆使用普通話,對於不是自己母語的移工而言,<br />
在語意的表達上難免有不夠精確之疑慮,惟研究者依循言談情境之脈胳<br />
予以補足。<br />
三、研究發現<br />
根據與移駐勞工的訪談結果,發現移工逃逸的主要原因如下,本研究希望能<br />
夠有效指出原因並找尋出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法,以降低逃逸的可能。<br />
(一) 實領工資過低:外藉勞工所領的薪資乃是依據我國勞動基準法所規定的<br />
基本工資17,280元 1 ,再加上加班費,每月應領近20,000元左右,但由於高額的仲<br />
介費,以及某些不肖的勞工管理公司,運用多種名目實際扣除或暫時扣壓其薪<br />
資,導致實領工資過少,通常外勞在台灣第一年的平均月收入僅為5000元左右,<br />
在這情況之下,外界非法勞動市場的地下經濟活動便成了外勞逃逸的主要誘因。<br />
(二) 工作壓力過大:關於工作壓力上的問題,可因工作性質而有所區分,一<br />
類為廠/場勞工,她/他們的工作即使輪班、加班亦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但粗重、<br />
繁瑣、及難度的工作內容則不在話下;另一類為則是以家為廠的家庭幫傭及看護<br />
工,這些勞工的工作特性為全天候24小時處於「待機」狀態,沒有固定的休息時<br />
間,她們跟著受照顧者的作息而生活,甚至只要有任何家庭成員是醒著,她們便<br />
隨時要有接受雇主指派工作的準備,身體的勞累是一壓力,但心理上的負擔更是<br />
沒有舒緩的一刻,分分秒秒面對自己的壓力源—雇主,無法透過社交活動尋求傾<br />
訴的對向,何嘗不是一種折磨。我國引進之移駐勞工多屬上述二種性質之勞工,<br />
其工作內容非但低報酬、低技術,更值得我們關切的是,她/他們所從事的內容<br />
皆屬所謂的3D工作(髒、繁重、危險),是台灣勞工不願意做,或是需要更高的代<br />
價才請得到本國籍勞工,然而我國業者/企業主卻能以低廉的費用完成同樣的工<br />
作。移工在面臨如此不平等對待時的心境已不言可喻。<br />
(三) 涉世未深、受騙上當:據報導人表示,許多來到台灣工作的移駐勞工們<br />
年紀都很輕,一些年輕的女性移工 2 因工作之便,認識異性並交往甚密,在台灣<br />
為了男友同居而變成了逃逸外勞,更有些欺騙女性移工為台灣的男性,他們讓這<br />
些女孩以為自己可以從外籍勞工的身份變成外藉新娘,因此甘願鋌而走險,為愛<br />
「走」天涯。<br />
(四) 勞雇關係不佳:移駐勞工來自與我們在文化、語言上相異的國度,長時<br />
間相處之下,難免導致勞雇之間的誤會,但這並不足以構成移工非走不可的理<br />
由,惟有些雇主的心態認為既然花了錢,就應該要有更多的回饋,對於勞工的工<br />
作內容應該可以有無限制的要求,簡直視外傭如下人,在根本上已忽略其「人權」<br />
的存在,除了工作的要求之外,尚有雇主對移工斥責、侮罵、嘲諷,甚至有些不<br />
1<br />
行政院從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實施調高基本工資,除了外籍看護和幫傭因為不適用勞基法,<br />
基本工資仍維持在新台幣 15,840 元,其餘從事廠/場工作之移駐勞工皆能調漲薪資至 17,280。<br />
2<br />
研究者並不認為只有女性才可能產生此現象,然而報導人所提供的資訊為「女性移工」為受騙<br />
上當的對象。<br />
2
肖雇主會將移工視為生財工具,帶著她到親友家打掃家務充當「臨時工」,或帶<br />
至自己的工作場合擔任「自己的」雇員,而使雇主從中牟取不當利益。更有甚者<br />
有些男性雇主會對女性外勞性侵害,若不是報章媒體的批漏,這樣的外勞悲歌不<br />
知還會在多少角落上重演?<br />
(五) 社會支持的誘因:根據報導人指出,在移工的生活圈中,存在著屬於他<br />
們自己的連繫網絡,讓隻身來到異地工作的移工們有個滿足彼此親和需求的管<br />
道,部份非法仲介業者就透過這樣的連絡網,利用己逃逸勞工散佈新工作之訊<br />
息,在利益的誘惑及友人的慫恿,便可能離開現有的工作環境。<br />
(六) 遣返在即:根據我國現行法律,外藉勞工在台工作時間為期三年,申請<br />
得延長二次,共九年 3 ,有些外藉勞工因為契約期限即將屆滿,若回到母國,其<br />
工作所得不如台灣,為了能夠在台灣多賺一些錢,再加上不用被仲介抽成,就乾<br />
脆選擇逃跑,加入非法外勞的行列。另外,由於定期的體檢,若遇不合格者,當<br />
依法遣送回國,移工亦可能走上逃逸一途。<br />
(七) 管理方式不當:某些惡劣的外勞管理顧問公司為了能在為數不少的外勞<br />
身上繼續剝削,就會以代幣發放零用金,兌換時還要被抽兩成,且禁止他們外出<br />
購物,因此外勞完全沒有選擇的購買管理公司內比市價貴的日用品,此種巧立名<br />
目的剝削方式及一些不人道的規範,如:禁用手機、遲到扣薪等,使得外藉勞工<br />
連基本的生活都成問題時,他們會甘願逃跑。<br />
(八) 擔心被遣返:在我國對移工的規定中表示,除非外勞有能力舉證雇主之<br />
不法,否則外勞沒有主動選擇雇主的權利 4 ,也因為這樣不合情理的法規,使得<br />
法律變向的讓雇主對外勞有更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勞工害怕被雇主終止契約而被<br />
遣返,因此而走上逃逸的路。<br />
(九) 求助無門:初到台灣的外藉勞工,對於國內幫助外勞管道的資訊取得並<br />
不清楚,再加上某些工作性質屬於孤立、獨處的狀態,若是長期處在不平等的對<br />
待之中,沒有社會支持且求助無門時,都有可能「被迫」逃離現有的環境。<br />
(十)法規因素:現行的法規僅嚴格規定雇主違約時應該如何受罰,對於外勞的<br />
違約僅施予遣返回國,並未有任何賠償或罰則處分,在此情形之下,無法有效的<br />
規約外勞堅守工作崗作的動機,故有提昇外勞逃跑的可能。<br />
(十一) 移工教育不足:關乎於移工個人權益之維護,我國政府及其相關單位<br />
皆立法予以保障,但研究者在與移工接觸過程中發現,移工對對自身權益的瞭解<br />
相當有限,在面對外在及自身的問題時,能夠以現行的法律途徑或社福機構尋求<br />
解決之道,不用走上逃逸一途,如此便能降低社會成本、創造勞雇雙贏的局面。<br />
3<br />
總統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公布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修正案,將藍領外勞累計在臺工作年限從原<br />
本之 6 年延長為 9 年,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規定,本修正案將於 2007 年 7 月 13 日發生效<br />
力。<br />
4<br />
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由勞雇雙方合意方式決定外勞轉換雇主,外勞轉換雇主的次數也將由<br />
現行的 2 次提高為 3 次。<br />
3
文化邊界的逾越:中途學校少女的生命圖像<br />
余忻妍<br />
本研究試圖透過參與觀察與訪談中途學校女學生,並將少女的身體視為感知<br />
的主體,以探索她們豐富的身體經驗,用當事人的眼光來詮釋她們自己的身體、<br />
自我,及其與社會關係的交互辯證。<br />
民國八十四年,「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制訂之後,法律對於從事性<br />
交易(之虞)的少女規範了明確的處置流程,少女經由警察查獲到中途學校安置,<br />
歷經一連串法律和自我價值的衝擊,少女的身體自由因此被剝奪,展開為期兩年<br />
的特殊教育。筆者身為中途學校教師的角色,和少女共同兩年的學校生活中發<br />
現,少女種種「社會邊緣」的生命歷程,雖有不斷碰撞、抵抗,卻也同時吸納既<br />
存文化價值的規範,呈現層層疊疊的衝突、矛盾,與妥協。<br />
那些曾進入色情產業的少女,青春的身體成為商品交換的報酬,超越文化給<br />
定的文化禮儀版圖,成為主流論述中逸出文化邊界的身體經驗,因此,在此論述<br />
的框架裡,直接否定少女主體的慾求,更「不見」少女多向複雜的感知經驗與行<br />
動意義。研究者認為少女的身體為體現自我的載體,其表現與與社會關係相互作<br />
用,對於這一群離開家、進入性產業的少女而言,鮮明的存在面對規範和自我慾<br />
望的掙扎,這些掙扎表現在身體上,是主體與文化模塑、社會價值、法律規範等<br />
不斷辯證的對話,形成自我面對自己的禁令與責任。<br />
我們想要理解文化邊界與未成年少女行動關係時,本研究試圖透過曾從事性<br />
產業少女,過往逾越文化邊界的生命歷程:離開家、進入性產業與被警察查獲進<br />
入中途學校,少女的身體成為規範與自我的中介亦是展現自我的工具,存在個體<br />
種種社會處境的差異,所展現多樣的行動與生命樣貌,其宗旨在探究她們如何經<br />
驗自己的身體和文化邊界產生關連與互動,進而行塑面對自我的禁令與責任。<br />
一、問題意識<br />
民國九十二年夏天,我在中途學校教師甄試中獲得勝利,進入中途學校任<br />
教,在校園裡扮演一個輔導教師角色,輔導觸犯<br />
的未成年少女。我以為身為一個輔導老師的角色便是積極關懷,並且相信愛能夠<br />
轉化這群已被一般學校教育放棄的孩子。但令我驚訝的是,當她們進到校園,有<br />
人不時以淚洗面、有人終日想要逃跑。她們思念家人、思念在外面的朋友和男友。<br />
她們過著每日倒數的掙扎,期待三個月過後的假期 1 ,逐漸適應校園中的團體生<br />
活。有人開始質疑自己命運「難道我真的錯了嗎?一步錯,就步步錯?」、「我的<br />
家庭需要我,難道我只能在這裡混吃等死,毫無助力?」「我不要被關,壓力好<br />
大!」這失去自由的校園生活,是她們從未意料到的,雖然從前在外從事色情產<br />
1 依照學校校規規定,安置在中途學校三個月後,才能開始放「親子假」,經由學生的導師、輔<br />
導老師及社工等三人共同評估放假的可行性,學生可以擁有兩週一次的假期。<br />
4
業時,因為未成年的身份,會和經紀人、店家有一些默契和保護自己的說法,但<br />
是從未想到,有一天抓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更沒想到,經由法官的判決下,<br />
必須毫無許選擇的進入中途學校,展開為期兩年的安置生活。她們問我:「外面<br />
比我更亂的朋友,為什麼不去抓?」「在這裡只是浪費時間,這裡不屬於我啦!」<br />
「這叫性交易嗎?在外面我只是好玩而已。」我回答不出來,常只能消極的告訴<br />
他們「表現好一點,可以讓你早點出去。」「如果逃跑的話,還不是會被警察抓<br />
回來。」學生在我面前展現面對法律制裁的抵抗、不甘願和無可奈何,而我面對<br />
她們的控訴,彷彿也成為制裁她們的一份子,於是,我發現自己跟獄卒、典獄長<br />
沒什麼兩樣,甚至更無力一些。<br />
然而,學生口口聲聲想念「外面」的生活,究竟是什麼?給了孩子什麼樣的<br />
歷練?那些令我們感到不安、充滿危險的世界,為何成為這一群孩子在衝撞人生<br />
時的歸屬?當主流社會透過法律裁決後,孩子們進入了中途學校,她們脫掉高跟<br />
鞋、抹去臉上的妝容,重新穿起制服,扮演好一個學生的角色的同時,她們又是<br />
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和她人之的關係?我發現不論她們口中「外面」的世界<br />
或是「裡面」的學校生活,對這一群孩子來說,鮮明的存在面對規範和自我慾望<br />
的掙扎,這些掙扎表現在身體上,是主體與文化模塑、社會價值、法律規範等不<br />
斷辯證的對話,並且形成自我面對自己的禁令與責任,其中各個不同的個體呈現<br />
差異的自我認同,通過身體的展現等待著被詮釋。<br />
二、田野的描繪<br />
民國 75 至 76 年間,媒體大幅報導少女被押賣從娼的一件件血淚故事,喚起<br />
社會面對人口販賣的問題。在民間團體「救援雛妓」的高聲疾呼下,政府終於在<br />
民國 84 年 8 月制定了,所保護的對象為未滿十八之兒童或少年從事性交易或有從事之虞 2 。民<br />
國 84 年,以下簡稱為,明確在法<br />
律上定位兒少從事性交易或性交易之虞為受害者,從成人散佈色情或是營業色情<br />
而都有相當程度的裁罰,並且具體從救援、安置保護、追蹤輔導訂立明確的處理<br />
程序。兒童及少年性交易事件處理流程如下:<br />
2 所謂性交易從事之虞在中有條列定義:1.坐檯陪酒伴遊,2.伴唱或伴舞,<br />
3.其他涉及色情之侍應工作。<br />
5
顯無從事性交易<br />
或從事之虞<br />
不予安置<br />
責付家長<br />
表 1 兒少性交易事件之處遇流程(改編自黃巧婷 2002:9)<br />
查獲及救援從事性交易(之虞)之兒童少年<br />
(通知主管機關指派專業人員陪同訓問)<br />
24 小時內安置緊急收容中心(於 72 小時內,提出報告,聲請法院裁定)<br />
其它適當場所<br />
特殊事由不宜安置<br />
短期收容中心<br />
有從事性交易或從事之虞<br />
其它安置場所<br />
短期收容中心<br />
(兩週至一個月內,提出觀察輔導報<br />
告及建議處遇方式,聲請法院裁定<br />
中途學校施予兩年特<br />
殊教育<br />
無從事性交易或從事之虞<br />
不予安置<br />
交付法定代理人<br />
依照處遇流程,少女經由查獲後,在短期急收容中心等待裁定<br />
的過渡階段,對於原先家庭功能不彰,唯恐再從娼之虞的少女,經由社工評估報<br />
告和法官的裁奪,決定是否進入中途學校或是其它民間機構施予約兩年特殊教<br />
育。於是,少女從「外面」的生活到「裡面」的中途學校,歷經查獲、裁定到安<br />
置的流程,啟動社會局、警察局、短期安置中心等多重的規範與馴化機制。中途<br />
學校成為少女回歸主流社會前的教育機構,希冀透過提供多元型態的教育,給予<br />
少女良好身心安頓的學習環境<br />
我所任職的中途學校於民國 87 年成立,於隔年開始招生。學生進入學校之<br />
後必須全年、全日住宿,白天學生都有一位社工、輔導老師和導師共同參與學生<br />
的學習生活;夜間有宿舍媽媽管理群體住宿生活。剛入校前三個月學生,沒有外<br />
出的自由,與外界通訊的電話和信件也必須在導師從旁督導與同意下進行,僅每<br />
週日直系血親 3 能夠進入學校探視學生。因為學校為保護機構,校外各項活動都<br />
必須謹防學校屬性的洩漏,而必須隱姓埋名,學校儼然自成一個隔絕外界,自樹<br />
一格的世界,在這小小的世界裡,卻有聲有色上演各種喜怒哀樂,而且深刻的彼<br />
此照見和牽動,因此,「我們學校最大的秘密就是沒有秘密」成為彼此心照不宣<br />
的心境。<br />
在學校,我的角色是輔導老師同時也是導師,除了教授輔導活動課外,我最<br />
3 直系血親校方規定在二等親內的親友或經導師、輔導老師及社工三方面評估的重要他人。<br />
6
重要的任務便是帶好班上的五位孩子,她們年齡各有不同,來到學校的時間也各<br />
自不同。在孩子尚未來到學校前,學校的社工會先前去短期安置中心瞭解孩子,<br />
法院的裁定文和學校社工的訪查是給我的第一手資料,對於孩子形成初步印象。<br />
當學生進入學校之後,我和她們的方式除了透過課程活動還有個別晤談,藉由學<br />
生提出晤談需求,或是我主動藉由晤談瞭解每個不同孩子的性格和煩惱。在一個<br />
不到 40 位學生的校園環境,擁有超過 20 位教師擔任不同的角色和職責,24 小<br />
時照護學生。學生常主動的叫我「娘」,或者是「媽咪」,也許是校園人數少,和<br />
她們互動關係頻繁,也或許是封閉的校園環境,自然形成的微妙關係,使得成為<br />
中途學校的「老師」,常不只是「老師」這兩個字所能說盡的的責任和角色。<br />
三、三個女孩的故事<br />
我認為這些孩子的獨白,不可能存在,因為這是我的論文、我的觀點,因此<br />
在呈現孩子的聲音時,「我」不可避免的的也參與互動的情境,對這些孩子想法<br />
形成的脈絡也會出現在文字的描述裡,並且藉此呈現我和她們處在同一情境裡相<br />
互參與的多重樣貌。<br />
(一)阿姐<br />
社工告訴我:這孩子來到學校滿懷不滿,因為阿姐的案子被揭開,這一切來<br />
的突然。阿姐妹妹的朋友報警要告孟秋的爸爸家暴,無意間說出阿姐被爸爸媒介<br />
性交易的事情,阿姐的爸爸因此被警察列為被告,這件事情告發之後,奶奶、媽<br />
媽..都覺得是這孩子亂講話不知輕重,因此求阿姐翻供,阿姐想到父親的未來和<br />
成全整個家族的哀求,只好在開庭的時候翻供說自己誣告,就這樣,她多了一條<br />
保護管束的案子,必須定時向保護官報到。因此,社工跟我說,入校初期的阿姐,<br />
狀況十分的不穩定,用盡各種方式逃跑,不過,近來一年,她似乎也認了自己的<br />
命,不跑了。<br />
後來我看到阿姐了,她已經來到學校一年,在班上儼然是大姊,是主動發號<br />
師令的頭,也許是因為她,年齡比較大、在學校的資歷也較久,班上的氣氛常因<br />
為她臉一沈,也沒人敢笑了。剛認識阿姐的時候,她不停跟我說:希望我能夠幫<br />
助她早一點離開學校,到底她案子什麼時候到期,可以離開學校,成為我和她之<br />
間最常討論的對話。後來,我又漸漸知道阿姐的生世,原來我一直對外聯繫的家<br />
長,其實是阿姐的養母,也是姑姑(阿姐生父的姊姊),而媒介阿姐性交易案的<br />
「父親」,則是生父。因為國中叛逆,才從媽媽(養母)身邊離家北上找到生父<br />
和兩個妹妹一起生活。阿姐告訴我:「當我大概是幼稚園的時候吧!聽見阿媽喝<br />
酒醉的時候告訴我:其實我是被姑姑領養的,我的媽媽是我的姑姑,我的叔叔是<br />
我爸爸,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心理充滿恨,想要報復,心想『有一天,你們死定<br />
了。』」阿姐對我說起這些話的時候,已經沒有那麼多的恨了,帶著淺淺的微笑<br />
又說:「不過,現在還好啦!因為我來到這邊(中途學校)都是媽媽(養母)那<br />
邊在關心。」阿姐這樣的身世和境遇,讓她處在在兩個家庭之中成為夾心餅乾。<br />
打從好幾年前,媽媽(養母)和生父因為金錢糾紛鬧的不愉快,也鮮少往來了,<br />
7
但是她對兩邊的情感擁有同樣的矛盾:一樣是無法割捨的血肉之親,一樣是無法<br />
找到歸屬的空虛,直到她知道自己原來擁有兩個妹妹,終於歡天喜地的感覺到家<br />
的所在,是因為兩個妹妹,兩個妹妹在的地方,就是她的家。生父母從小對阿姐<br />
不聞不問,只管跟養父母要錢;而養父母面對阿姐叛逆行徑時邊打邊罵說:「有<br />
什麼樣的父母親,就有這樣的女兒!」,面對養父母和生父母,她感覺處處都不<br />
是的家。<br />
在一次家庭訪問的時,阿姐媽媽對我們說起她離開家的前一天晚上,鄰居說<br />
看到阿姐和男生在廟前摟摟抱抱,回到家裡,爸爸知道了之後氣到拿著棍子打阿<br />
姐,阿姐連唉一聲都不唉,站直直給爸爸打,但是眼底不服氣的都是恨,這便是<br />
這孩子的脾氣。「這小孩的『性』」她最清楚了,要給她硬的,她偏會更硬的反抗」<br />
媽媽說,後來她就離開家,跑到桃園找妹妹們。<br />
妹妹那時候還跟生父住,那時候生父正被通緝自顧不暇,生父當時候的女朋<br />
友在做酒店工作,問了阿姐願不願意去做 S(性交易),可以有錢賺,她似乎沒<br />
多想什麼就說好,我不解的問她:「爸爸只有叫你去,而沒有叫妹妹嘛?」她回<br />
答說:「爸爸說:『我是姊姊,所以應該我去。』」後來她噙著眼淚說:「我想爸爸<br />
是比較疼妹妹的吧!」而我也忍不住的掉下淚來,這是她第一次性交易,當時,<br />
這件事對她來說就是做一個姊姊做的事。<br />
(二)阿美<br />
阿美小巧的五官總是掛著甜甜的笑容,搭配著輕輕柔柔的聲音,發散著令人<br />
無法抵擋的女性特質。第一次見面,她就告訴我「我叫三八」,常常有事沒事黏<br />
了過來,主動說起她現在的故事。阿美同時也有著努力不懈的打拼精神,社工告<br />
訴我,她從國中就開始在美髮店工作,高中的時候則獨自一人北上新竹投靠姑<br />
姑,就讀輪調班(三個月工作,三個月讀書皆由學校安排),也許是從小工作的<br />
歷練,阿美做起事來勤快又俐落。<br />
阿美從小父母便離異,對親生母親毫無印象,曾在國中的時候,因為好奇,<br />
要求姑姑帶她去見媽媽一面,從此以後,阿美的世界便和生母毫無關連,僅有爸<br />
爸,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爸爸在她國小三年級的時候娶了現在媽媽,後媽說<br />
話刻薄、性情又急躁,阿美總跟我說:「她(後媽)現在改很多了,以前她是怎<br />
麼對我、怎麼打我的阿…」這些被打的傷痕,阿美一直暗暗忍耐,同時也磨練了<br />
阿美面對自己堅強的意志,當她說「不要」時,沒人可以勉強她做任何事的。上<br />
了國中,在一次和後媽的衝突中,阿美把後媽打到住院,爸爸這才發現兩個女人<br />
存在的衝突,似乎無法再忽視,便把阿美送到新竹姑姑家讀書,阿美的生命一下<br />
自由了,她就讀輪調班,三個月工作、三個月讀書,自己賺錢自己花,同時爸爸<br />
一個月也給她幾千塊錢花費。在新竹的日子一年過去了,學校那邊開始出現曠課<br />
紀錄的通知,爸爸發現不對了,想把阿美帶回高雄讀書,她開始「跑給爸爸追」。<br />
因為不想跟爸爸回高雄,也不能再跟爸爸拿錢,必須躲著家人靠自己賺學費,於<br />
是在寒假的時候,她經由美髮店裡的客人介紹,進入「傳播業」,上班的第三天<br />
被抓了,然後來到中途學校。<br />
8
阿美告訴我她在這邊(中途學校)讀書的事,只有爸媽知道,整個家族包括<br />
之前很照顧她的設計師都沒有人知道,因為這種事情總是不好跟別人說。問她是<br />
否後悔,她說:「人生要往前看,後悔也沒有用」,但是每每說到在學校不自由的<br />
日子,她仍會淡淡的說「當初不要跑給爸爸追就好了,只做了三天就被抓了,真<br />
倒楣。」<br />
(三)奶茶<br />
她是我第一個擔任導師時所接的學生。最有意思的是,社工拿她裁案法官的<br />
判決書上寫著「她在陪酒時因為歌唱的不好,被客人趕出來。」這個法官真奇怪,<br />
判決文竟然會出現這種東西。但這也告訴了我兩件事:奶茶歌唱的不好;第二件<br />
是在酒店混下去,歌要唱的好,所以奶茶在酒店可見一定混的不好。另一件社工<br />
告訴我的是:她小時候有過動症,曾經去醫院服藥。而從測驗中也發現他的非語<br />
言智商很低幾乎是臨界輕度智能障礙。奶茶做什麼事總是大驚小怪、十分的用力<br />
(很驚天動力的那種)。同學常跑來跟我抱怨、如果套句對過動症的描述就是:<br />
衝動控制不足,話都直直的出來沒經過修飾,而且時機、場合也都不對。但她是<br />
個情感細膩的孩子,擁有這個學生,常感覺到言談之中的體貼與溫暖。<br />
奶茶的家庭很傳統,嚴父慈母型的,父親不善於言詞,嘴裡總說不上好聽的<br />
話;而母親比較謙卑,面對老師的時候,總是屈著身的姿態說:「老師,你說的<br />
她比較會聽,幫我跟她說這樣不好…」並且重複不斷的叮嚀來照顧孩子,聽在孩<br />
子身上是綿綿不決的叨念。奶茶的家庭是學校很少數父母沒有離異,且依靠勞力<br />
辛勤工作。但是她和父母相處總是充滿了問題,她想抗拒父親為她築起保護傘,<br />
兩人硬碰硬下場總是不好。剛進學校時,她想起父母親之前為了她的離家傷透了<br />
心十分自責,常常發誓要好好孝順父母,而且和朋友間的分分合合也讓她看清楚<br />
唯有父母才不會背叛自己。奶茶總跟我說:不後悔在外面的生活,和父母賭氣的<br />
時候,甚至會說,外面的生活讓她知道很多東西,父母根本都不懂的,也覺得曾<br />
經走過外面的世界,看見社會的現實讓她比父母還有見識。<br />
一次晤談時,她跟我說了那時候離家的原因:「國中的時候沒有什麼朋友,<br />
也許因為當時候自己衛生習慣不好,身邊的同學都會欺負我,書包常常會不見;<br />
桌椅也常被弄壞,或是放垃圾到她抽屜裡。」記得那時候我聽的好心疼,怎麼這<br />
些殘忍的過程都一個人默默忍受不作聲?她說這些過程都不敢告訴父母,也許是<br />
愛面子,她不知道怎麼跟父母說。一次,在學校社團活動中,她認識了慈音,兩<br />
個人擁有一樣的決心,都想要離開學校、離開家,那一天她們看了報紙找到一個<br />
經紀人,那個經紀人知道她們未成年後不想負這個責任,但兩人離開家需要錢生<br />
活,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拼命拜託他。後來當天晚上經紀人就帶進一間酒店的包<br />
襄理去給經理瞧,奶茶略微激動的說:「那一天很誇張喔!他叫我們現場換衣服<br />
給她看,不然就不要做。」然後又笑笑補充:「那個經理很帥!」當天換上酒店<br />
的制服之後,就直接上工去。奶茶說自己都笨笨的,以為就是喝酒而已,其實工<br />
作場合,常感覺到很猥褻,有時候客人要親、要摸,就要推說自己 mc 來了,還<br />
信誓旦旦跟客人說:「不相信我用給你看」,奶茶說上班的壓力其實很大,和客人<br />
9
唱歌,還被客人「打槍」、被客人嫌,而且有時候儘管自己似乎沒有真正和客人<br />
性接觸,卻覺得自己很髒。後來我問奶茶:「如果沒有被警察抓到,你現在還在<br />
那裡上班嘛?!」奶茶似乎沒有多想什麼說:「會吧!因為要生活阿!其它的工<br />
作,就憑我國中,也找不到什麼」。<br />
奶茶來到瑞平,是她從沒想過的人生,當時被警察抓到送到短期安置中心,<br />
她認為「自己又不是去偷去搶,沒有做出違反良心的事情,只是在酒店喝酒而已,<br />
又沒幹嘛」,而且父母親未離異也都有正當的職業和功能,總認為自己被抓到也<br />
是回家而已,沒想到就被法官判來瑞平。奶茶喜歡學校生活,總覺得可以得到許<br />
多人的關心和照顧,出了事,也有很多老師可以討論,但是和同儕之間的互動,<br />
仍是她很大的難題,常覺得孤單沒有朋友。<br />
四、分析與討論<br />
在外面的生活<br />
在裡面的生活—扮演好學生<br />
10
吉拉米代部落阿美族人對於「Late’」的經驗與想像<br />
曾文廣<br />
Late’是阿美族語,它是阿美族人的感知經驗中,以超自然因素導致的身體<br />
痛苦反應。本研究將透過阿美族人述說自己的「late’」 經驗情形及內容探討阿<br />
美族人對於「late’」的主體經驗和主體詮釋,研究者藉由瞭解阿美族人如何詮釋<br />
該經驗,進而提出身體表現自我和社會期待的關係。<br />
「late’」是一種身體感到痛苦的現象,阿美族人認為獵人身上都會有某種超<br />
自然的能力,此「力」會使那些觸碰獵人器物或靠近獵人身體的人產生反應,受<br />
力的某人之身體將會有痛苦的感受,例如,下(腹)瀉不止、起疹子、冷顫、歪<br />
嘴等。阿美族人知道這種「莫名的」身體反應無法在一般醫療體系中得到治療,<br />
需由傳遞超自然力量的獵人進行儀式才得以康復。筆者分析吉拉米代部落的一位<br />
婦女和一位老獵人對於 lati’的經驗,從他們如何經驗和理解 lati’方式,提出可能<br />
的探討方式,並以身體研究視為重心,注重身體經驗中體現社會期待和表現自我<br />
的方式。<br />
本研究透過幾位感受過此經驗的阿美族人描述自己痛苦的經驗,瞭解他們對<br />
於該經驗的歸因、知覺和處理方式,分析其中的內容和理解方式。人對於痛苦經<br />
驗的詮釋往往來自於自身的文化脈絡,不在文化定義內的痛苦經驗就什麼也不<br />
是,必須從原有的概念中理解經驗本身。但是,痛苦經驗本身卻是只有當事人能<br />
夠經驗,以致於研究者在探討痛苦經驗與文化的同時,不能不去正視個人的本身<br />
生理經驗,當然這種生理經驗也不只是包含生理學的概念,也包含心理、文化象<br />
徵的意義。個人的「身體」在經驗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它能夠將文化的<br />
概念融入於身體之中,使之在非意識的狀況下從「感覺」和「想像」中展現出來,<br />
而且是毫不費力。它是一種自我的表現能夠在經驗中定義或理解內部和外部的社<br />
會,讓個人在此社會中有合理的行為和思維。<br />
因此,本研究以人對於痛苦的詮釋和痛苦的經驗,分析文化形塑和個人經驗<br />
的交互辯證關係。文化、個人和身體在當事人的經驗和詮釋間,表現出一種相互<br />
交融的體現形式。另外,研究中也進行「文化」概念的探討,文化是人所建構而<br />
成,個體相異的自我理解和身體自主表現個體實踐將是解構文化的可能性,所以<br />
從個體經驗看來文化並非一個先驗的結構。而且從經驗研究中更能夠發現「文化」<br />
是混淆的發生在人的實踐中,透過身體將各種相異文化交融於經驗中,卻不感到<br />
矛盾,是一種自然交融的現象,已經很難從經驗中抽取哪些是該族群的文化、哪<br />
些是受到影響的改變。<br />
一、身體研究<br />
日常生活中,人類的「身體」無所不在,所有的行為、情緒、感知以及表達,<br />
都必須透過身體,人類也透過身體的模仿、訓練、學習、陶冶而獲得知識或訊息。<br />
11
然而,身體議題卻在文化和知識的討論中缺席。過去人類學者都將身體以「生理<br />
肉體」來看待,認為身體是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這類文獻將身體定義為文化對<br />
於個體影響的結果,卻未正視「身體」存在的意義。<br />
Mauss(1979;見余碧平譯 2003)表示身體是人類與外界最首要和直接的<br />
接觸媒介,人使用身體的方式具有文化或地方性的差異,此差異即「身體技術」<br />
(body techniques);研究者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身體只是一種「工具」,應從「身<br />
體技術」來看待文化,去探究各種不同的身體技術,以發現個體行為的多樣性。<br />
Mauss 的提醒向我們顯示,身體的存在並不總是處於相同的情況,至於依身體使<br />
用方式來看待個體行為此一研究視角,乃屬於身體技術的討論層次,應置於社會<br />
學和心理學的範圍。<br />
Douglas 在 Purity and Danger(1966)中,討論聖經裡以色列人飲食上的規<br />
則,認為文化分類系統能夠引起社會和生理(身體)經驗間的共鳴。其後,她又<br />
在 Natural symbols(1973)中提到,在不同社會裡,身體狂喜的狀態(state of<br />
trance),呼應了該社會組織關於文化分類的格(grid)和自我控制的群(group)<br />
之位置。她的洞見,建立了文化人類學的「社會身體」(social body)典範,刺激<br />
更多學者在文化研究覺察「身體」存在的意義。<br />
除了 Douglas 重視文化象徵與身體的關係,Foucault 也關切「身體」的意義,<br />
他主要從「權力」的面向切入。他認為身體會受到知識系統的植入後,它便會主<br />
動在混亂中達到某種自然次序,修正至所謂「標準」的樣貌。但在知識權力下,<br />
個人身體將驅使自己修正成某種標準,知識隨歷史轉變時,個人的身體也繼續修<br />
正(Foucault 1981;見尚衡譯 1990)。Foucault(1988)提出「自我技藝」(technologies<br />
of the self)的概念,身體是文化權力下的產物,但因為不同的人、事、時、地、<br />
物及相異的技術(寫日記、告解、懺悔),造成不同的「自我技藝」過程,也形<br />
成不同的自我效應。在他的觀點身體絕對是權力下的產物,經由個體皆不同的「自<br />
我技藝」形成不同的結果,身體的表現並非一種先驗或同質的結果,而是在限制<br />
內多樣的自我表現。若干學者並不全然同意 Foucault 的身體觀點,以及他將「權<br />
力」和「知識」結合的解釋模式,例如 Bourdieu(1983;見蔣梓驊譯 2003)。<br />
Bourdieu(1983;見蔣梓驊譯 2003)提出「實踐理論」(a theory of practice),<br />
認為知識必須存在於身體實踐中,知識會在實踐過程中形成身體的習癖<br />
(habitus),透過習癖將知識銘記於個人的身上;此習癖將會回來反應於個人對<br />
於事物的理解和決策。他認為「身體」的重要性在於息癖的形成以及實踐的主體,<br />
若除去了息癖和實踐的課題,就沒有討論「文化」的必要了。習癖必定是儲存人<br />
的身體中,它一方面具有個人性,一方面具有文化⁄社會⁄結構性,既是身體實踐<br />
的原因也是結果,所以它是趨向於生成各種「合理的」、「符合常識」的實踐行為。<br />
Bourdieu 不同於 Foucault 認為身體是權力的產物,他傾向身體是實踐過程中的各<br />
處境「主動地」形成習癖,身體的行動及反應又會因為習癖所影響,在身體裡反<br />
覆建構及解構習癖。<br />
此外, Lock 和 Scheper-Hughes(1996) 反省了醫學人類學的新觀點,這門學<br />
12
科發現身體不全然是被動的,因此在「社會身體」(social body)以及「身體政治」<br />
(body politic)之外,提出了一詞,強調身體的自主性,認為身體的感知是發生<br />
在文化分類之前,我們應探究身體感知與文化分類相互碰撞所產生的現象。除了<br />
體現文化象徵的「社會身體」,或者受集體規則所控制的「身體政治」,也包含表<br />
現自我的「個人身體」,個體的身體都有主體的經驗方式,注意感官知覺與生活<br />
經驗。<br />
「身體」僅僅被視為「肉體」來看待,此乃知識建構迄今的結果;事實上,<br />
身體知覺具有主動性,身體本身也自主地融入社會秩序、分類和記憶。醫學不該<br />
只是將身體視為獨立於病人之外,筆者認為此區隔將病人的身體視為無生命的機<br />
器,身體被視為病人所擁有的實體,並不視為病人本身。因此本研究將以「身體」<br />
作為一個重要的課題,從阿美族 lati’經驗,討論「身體」存在之重要性,探討 lat’<br />
身體經驗與地方文化間對話的可能性,並將經驗者視為主體,進而發現身體如何<br />
實現文化象徵與身體主體。<br />
二、吉拉米代部落<br />
此部分介紹吉拉米代部落及其狩獵情形,以協助讀者對於本研究探討吉拉米<br />
代阿美族 lati’經驗的理解。<br />
吉拉米代部落為花蓮縣最南的阿美族部落,位於海岸山脈麻荖漏山西側鱉溪<br />
流域。麻荖漏山又名新港山,是海岸山脈最高峰,東側為台東縣成功鎮、西側為<br />
花蓮縣富里鄉,為兩行政區域的自然交界點,部落居民稱此山域為 ciutucay(三<br />
角點標高之意)。鱉溪是秀姑巒溪的上游,因經常有鱉群出沒而得名,鱉溪流域<br />
有三個主要支流,各支流如樹枝般向麻老漏山延伸,形成高山、溪谷縱錯的特殊<br />
地形,部落即位於峽谷地形中;唯支流匯集之處,形成山谷較為平坦和寬闊的地<br />
形。<br />
此地山勢高聳,生態複雜,大型樹木琳瑯滿目,牛樟樹及紅櫸是高山地區豐<br />
富的林相,保留完整的生態面貌;有山羊、山羌、山豬彌猴、松鼠、鼯鼠,過去<br />
還有熊和梅花鹿等大型動物。<br />
吉拉米代部落在百餘年前沒有人居住,通常也只是成功阿美族和卓溪布農族<br />
的獵區,傳說富源的 Saomah、Lameru、Cipoh 三兄弟是第一批在此定居之族人。<br />
他們因為被族人驅逐,便離開了部落,沿著秀姑巒溪而上,來到了富里這個平原,<br />
又溯著秀姑巒溪上游的鱉溪來到現在的吉拉米代。他們在這裡看見大樹根佈滿,<br />
當時樹根的長度足以橫跨鱉溪的兩岸,他們攀爬樹根以越過溪流,因此用大樹的<br />
根而命名 Cilamitay(多樹根之意思)。接著,部落族人的聚集從幾個地方遷徙而<br />
來,順序分別是台東海岸的都歷、東河、泰源部落,最後一次是縱谷德高部落遷<br />
移至此<br />
如今,部落居民居住於鱉溪各支流之谷地或平坦之山坡地。台東縣都歷部落<br />
的居民翻過麻老漏山從東側遷移到西側,居住的地方則是在鱉溪中上游地帶,東<br />
河和泰源的族人則開闢另一條較南邊的古徑來到吉拉米代部落;從不同地方遷移<br />
13
的居民皆分散地選擇土地定居,形成顯著的分界。<br />
部落人口數約一千多人,平時留在部落的居民約三百人,以阿美族人居多,<br />
佔總人口數百分之七十,其餘為外省、客家、閩南之漢人。阿美族散居於鱉溪各<br />
支流域,漢人較為集中居住,主要在各支流匯集處。與大多原住民部落相同,留<br />
在部落的居民六十歲以上老人較多,約占百分之八十,是處於老年化的部落型<br />
態,其餘為青壯年和兒童。<br />
部落族人一直都以農業為主,早期因地形開闢梯田種植水稻、玉米、地瓜、<br />
生薑等多樣作物為生,偶爾擔任林班挑夫和採金線蓮的零工。而後,富里米和富<br />
麗米的賣相不錯,米廠和農會收購的價格也比較高,所以部落族人將其他作物轉<br />
為種植稻米為主,偶有族人種植高接梨和柿子 1 。<br />
部落族人現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基督教和真耶穌教,外來宗教皆是 1950 到<br />
1960 年代傳入部落,在此之前部落居民信奉祖先和相信萬物皆有靈的信仰,有<br />
靈媒(cikawasay)能夠治病、問卜、祈雨等能力。部落也有矮黑人和巨人的傳<br />
說,矮黑人常是群眾的方式活動,會在山林中出現,他們會試圖在你身旁搗蛋和<br />
吵鬧,據耆老口述他們會趁著人在睡覺的時候,把人搬動,甚至搬移至峭壁,以<br />
此威脅族人給他們食物。巨人是單獨在山林穿梭,最喜歡抓小朋友,將之藏匿於<br />
樹幹之中,甚至藏在細細竹子裡或花瓣的背面,使人找不到。現在由於基督信仰,<br />
居民認為矮黑人和巨人被耶穌所趕走。<br />
在過去的吉拉米代部落,狩獵是每個男人都要會的技藝,男人若沒有打獵,<br />
將會被取笑,被視為沒有能力也不努力的人。現在雖然沒有這樣的壓力,但男人<br />
的狩獵依舊受到部落族人注意。在部落男人之間不時會討論放陷阱的位置和方<br />
式,或敘述自己在山林的故事;部落居民也會注意獵人上山的動向,或是詢問狩<br />
獵的情形。如果有一個獵人抓到一百多斤的山豬,一定會成為部落居民的話題,<br />
閒話家常至很久一段時間。<br />
據部落獵人口述他們狩獵時的情形。狩獵的方式有陷阱獵和追捕獵,直到近<br />
二十年才漸漸有族人自制獵槍進行狩獵。陷阱獵是阿美族最普遍的狩獵方式,獵<br />
人需要判斷獵物的路徑及分辨何種獵物,而設置不同的獵陷 2 。獵人會在一個星<br />
期或三四天後上山探視是否有獵物。而追捕獵為數較少,每次帶四隻狗上山,主<br />
要追捕水鹿。水鹿深按水性,既使被獵狗追捕滿山跑,只要一喝到水,碼少能恢<br />
復體力,渡溪擺脫獵狗。獵人便善用水鹿的特性,當獵狗追著水鹿跑時,在往溪<br />
流的途中攔截水鹿。獵槍的狩獵方式會在夜晚進行,因為獵物的眼睛受到燈光的<br />
照射反光,獵人因此容易分辨獵物的位置和種類。現在甚少看見獵人進行追捕<br />
獵,常以放置陷阱和攜槍狩獵為主。<br />
過去無論是陷阱獵或是追捕獵都有獵區的分別,獵人們不會進入別人的獵<br />
區,而獵區的決定都是先在此地狩獵的人所擁有,獵區擁有者終年都在這個區域<br />
狩獵。現在的陷阱獵雖然沒有像過去嚴格的區分獵區,任何人先在這個區域放置<br />
1 族人種植高接梨和柿子的技術,取於梨山種植水果的工作經驗。<br />
2 獵人用傳統的技術所製作的陷阱,主要是用鋼線將獵物的腳或頭部捆住。<br />
14
陷阱,別人既使路經此區也不會設陷阱;不過每個人放置陷阱都有自己習慣的位<br />
置,也保持了固定獵區的樣貌。只要抓到獵物,獵人們會知道這是誰的獵陷,便<br />
立即通報放置獵陷的人。獵槍的狩獵方式不以個人劃分獵區,而是以部落為主要<br />
區分方式,部落裡所有獵人都會在同一個區域進行狩獵,不進入其他部落的獵<br />
區。獵人會以今天上山的先後決定狩獵區域,後來的獵人會避開;有時結伴同行<br />
至山上的工寮 3 ,再從工寮分頭狩獵。<br />
對於獵人而言,占卜是上山重要的依據,尤其是陷阱獵。透過占卜可以知道<br />
此次行動會不會有獵物。吉拉米代部落的占卜方式,分別為竹占、鳥占和夢占。<br />
竹占是挑選竹子,削成半個指甲寬和一個手臂長的竹片,在自家大門口進行問<br />
卜。鳥占是在獵人想要上山的清早進行占卜,當獵人在自家門口看見樹梢的鳥正<br />
對著自己,就表示今日上山將有所獲;如果鳥是背對著自己,就表示此行將一無<br />
所獲,甚至發生意外。夢占是最普遍的占卜方式,透過隔夜的夢來判斷是否有獵<br />
物;夢見和女生友好或是夢到與女生發生性關係,表示自己獵到了山羌或山羊,<br />
若夢見殺人的情節則是獵到山豬,如果夢到火燒山表示所有獵陷都有獵物,而且<br />
獵物都已經死了,清晨必須立刻上山取獵物。目前除了老獵人會使用竹占和鳥<br />
占,青壯年獵人都傾向夢占,而鳥占則偶爾使用。<br />
上山前的撒酒儀式,也會決定今天狩獵行動會不會成功,上山前獵人會背對<br />
自家門口或望向山林,將未開過的米酒撒在地上,口中用母語唸著「祖先,這次<br />
上山狩獵,打擾了,路途遙遠將不會有任何問題,我們拿走該得到的,這些酒你<br />
就先喝了吧。」 4 獵人們相信如果忘記這項動作,什麼獵物也抓不到,甚至自己<br />
在山林的行動會相當不順。<br />
獵人通常是進行部落內的買賣,很少買給外地人,據了解是害怕被人家告。<br />
不同的獵物有不同的價錢,重量並不講究,除非是太大或太小價格多少會有些不<br />
同。因為狩獵隔天的宴客,族人知道那位獵人有所獲,便會跟打電話或到獵人家<br />
跟他購買。如果族人直接到獵人家作客,獵人的妻子將會從冰箱拿出獵物,烹煮<br />
後宴客;所以如果想要吃他的獵物,不一定要買,只要到他家聊天,並表示自己<br />
想要吃獵人所獲之獵物,有時甚至不用表明,他們也會拿出來烹煮。<br />
三、阿美族的 Late’ 經驗<br />
阿美族人認為有些獵人身上會有某種超自然的能力,此「力」會使那些觸碰<br />
獵人器物或靠近獵人身體的人產生反應,受力的那個人將會產生身體的某些症<br />
狀,例如下(腹)瀉不止、皮膚紅腫、冷顫、歪嘴等。阿美族人知道這種「莫名<br />
的」身體反應無法在一般醫療體系中得到治療,需由傳遞超自然力量的獵人進行<br />
儀式才得以康復。阿美族人就將此「力」稱之為「lati’」。<br />
目前為止,探討到「lati’」的文獻並不多,少數如黃貴潮(1989:130)認為「lati’」<br />
是草木精靈的法力、阮昌瑞(1994)將「lati’」視為黑巫術。他們兩個人都發現阿<br />
3<br />
工寮是農民為了將農具放置於農田附近而搭建,獵人常會在此過夜。<br />
4<br />
經筆者翻譯。<br />
15
美族人會使用「lati’」的能力來保護自己的財產,向自己的財產唸咒後,就能夠<br />
不讓其他人來觸碰,若是碰到了就會產生身體的不舒服反應,必須由施咒的人來<br />
「治療」才能痊癒。筆者發現這種超自然的「力」並不只有標幟財產的功能,它<br />
也具有其他功能,而且部落的居民相信這樣的力量依然存在,此力量只有獵人才<br />
會擁有。<br />
筆者將「lati’」分為三種。第一種是黃氏和阮氏所說的,具有標示財產的能<br />
力,獵人的身體、器具和獵物都具有某種能力附著,當其他人碰到獵人身體或器<br />
具時就會有痛苦的感覺,如果偷取獵物或器具,甚至會讓人死亡。第二種是獵人<br />
讓狩獵對象 malati’,他在設完獵陷的時候會對獵陷「說話」,希望它能夠蒙蔽獵<br />
物的眼睛而踏進獵陷之中;或者是讓動物看到獵陷,而後感到無力並且停留在獵<br />
陷附近不會離開。部落較老的獵人都還有這種能力,因此放置陷阱幾乎都會有所<br />
獲。第三種是獵人所擁有的獵具本身具有 lati’能力,它會讓獵人在數天沒有上山<br />
的時候,產生不舒服的感覺,越多天沒有上山,那種身體痛苦的感覺就越強烈,<br />
甚至會吐血。<br />
以下將以一位阿美族婦女和阿美族老獵人的親身經驗,來介紹 lati’經驗。<br />
Nikar 是一位 41 歲的阿美族婦女,她曾經有受到 lati’的經驗,並且請獵人進<br />
行儀式而得到療癒。在此經驗之前她並不相信有 lati’的存在,認為這是老人家所<br />
說的傳說故事,並不當真。她說道:<br />
我知道以前有malati'的事情,古時候是有聽說的,不過我是沒有相信,<br />
想說那是老人家說說的;沒想到碰到的時候才知道,原來阿美族的這個<br />
(lati’)也是很強的,之前都想說有這麼一回事嗎?就碰到的時候才知<br />
道有這樣的。<br />
從 Nikar 的言語中,可發現她並沒有對於這種 lati’產生信仰,只是將之視為<br />
無稽之談,但是自己的身體卻又經驗了這樣的感受。此例子可以提供一些討論,<br />
筆者相信「文化」建構身體的感覺,個人在自身「文化」浸濡下特別重視某種知<br />
覺,相對的也會忽略了某些感覺;可是 Nikar 並不是在這樣的文化裡成長,自己<br />
也沒有看過人家有 lati’的經驗,可是她卻能夠清楚的感受到該身體經驗,所以身<br />
體最原始的感覺是存在的,而文化所給予的是認識這等感覺的方式和框架。自己<br />
親身經驗的過程,也成為她認識此「文化」的方式,表現了個體經驗的價值,研<br />
究者不應將文化對於個體的影響視為理所當然,必須透過「經驗」與自我理解的<br />
過程,文化結構方能影響文化內的個體。這一種自我理解的過程,就如同 Foucault<br />
所談「自我技藝」(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經驗主體透過一種自我的省思與討<br />
論,因地、事、時、地、物產生出差異的自我理解,這種理解不是文化結構(文<br />
化權力)下的先驗結果。<br />
Nikar 經過此經驗選擇「相信」lati’的存在,改變了她對於阿美族傳統信仰<br />
的看法,從懷疑轉而相信;她的「相信」是依循著文化框架的影響,在她的知識<br />
16
系統裡,必須能夠解讀此經驗,才能夠在經驗這件事情後產生自我理解。<br />
以下是筆者和 Nikar 的對話,描述她實際的 lati’經驗。<br />
Nikar:喔,我malati'的時候喔,我只有一次而已,皮膚發燙又癢癢的,<br />
只有那個重要的東西(陰部)不會養。<br />
筆 者:其他地方都會癢。<br />
Nikar:嘿呀!耳朵拉,還有眼睛都腫起來,眼皮腫起來都不能張開眼<br />
睛了。身體紅紅的,就一直那個發燙,那個癢是不一樣的,是<br />
很裡面的那種,不是一般皮膚癢的那種可以抓到的癢。<br />
筆 者:就是怎麼抓都抓不到的感覺<br />
Nikar:嘿,抓不到,而且身體會感覺發熱,那個癢就是刺刺的,我那<br />
時候就在想我是怎麼了。<br />
筆 者:有去看(醫生)嗎?<br />
Nikar:就那個郵局前面,那個仁德診所,醫生說我是皮膚病阿,打個<br />
針又給我藥擦,也沒有好啊。<br />
筆 者:有長一粒一粒的疹子嗎?<br />
Nikar:可是啊,不是像起疹子那種一粒一粒,不是,就像那個(停頓),<br />
不會像被蟲咬,和皮膚病的不一樣。<br />
Nikar在對話中感受到和生理醫學不同的症狀,雖然醫生已經判定是皮膚<br />
病,她還是不太相信,強調其感受的差異性。皮膚有紅腫和發癢的現象,就一般<br />
觀念將會認定這是皮膚病;可是Nikar形容那是一種皮膚深處發癢的感覺,怎麼<br />
抓都無法止癢,身體感覺到刺刺熱熱的,也沒有起疹子。她強調這和你(指筆者)<br />
所想像的皮膚病不一樣。因為這樣的痛苦讓她三、四天無法入眠,醫生的診斷及<br />
治療也沒有讓她有所改善,她也就覺得很不太對勁。<br />
她能夠感受不同的身體經驗,也能夠清楚分辨感覺的差異。從生理學的概念<br />
來看,「癢」的生理反應是皮膚表皮的刺激,再傳導到大腦意識到「癢」。她形容<br />
這是皮膚深處,無法抓到以止癢,顯然是和生理學的概念有所差異,這樣就不太<br />
能夠用生理概念定義這種「癢」是什麼?對於Nikar而言,她已經定義了這種「癢」<br />
的感覺。<br />
她詢問附近的耆老這樣的狀況該怎麼辦,耆老馬上問他是不是有去過Do’eng<br />
的家。Nikar並沒有和Do’eng有說到話,只是她和Do’eng的女兒很要好,所以經<br />
常去他的家聊天。Nikar依照耆老的意見,拿一瓶酒到Do’eng家,告訴他自己身<br />
體的狀況。Do’eng也知道是什麼狀況,願意作儀式來為Nikar治療。她述說儀式<br />
的過程:<br />
那個阿嬤就說我應該是得到了他(Do’eng)的lati’,我還問說現在還有這<br />
種malati'的喔?阿嬤就說現在就只有他比較會讓人家malati'了,要我帶<br />
17
一瓶酒過去。我回去問我家的別人(她老公),他就叫我試看看,我才<br />
敢去的。阿公(Do’eng)的女兒是我的朋友,就有跟他說,阿公就說可以<br />
幫我用。他就給我坐在她前面,他就拿去我手中酒,倒進嘴巴裡,然後<br />
就pus~(嘴裡噴出酒的聲音)這樣噴我,就是像電視裡面的巫師ㄧ樣,<br />
可是他沒有拿什麼東西,就只有那一瓶酒而已。然後他用手摩擦 5 我的<br />
身體,用酒來洗,有聽到她唸說「不留在孩子的身體裡了,讓她身體不<br />
要痛苦」 6 ,其他的話我就聽不到,他的嘴巴一直動,也沒有講出來,<br />
然後叫我喝剩下來的酒。那個時候malati',真的,他弄好之後就可以好<br />
好睡了,我那時候已經好幾天沒有睡好了。早上他(Do’eng)還有過去問<br />
我說怎麼樣了,我就說好多了,他就說好了就好了,他也沒有說碰到什<br />
麼他的東西怎麼樣的。我想這個還是要看八字,輕的人就會得到,否則<br />
其他人怎麼都沒有呢?不過一次malati'之後就不會有第二次了,碰到他<br />
的東西就不會怎樣了,大概是外人不能亂摸他的東西,不能亂碰還是怎<br />
麼樣。<br />
Nikar 原本懷疑這種傳統的「治療」方式,但是人在處於一種失望的處境時,<br />
會盡可能的嘗試還未使用過的方式,她試圖透過詢問另一個人,也就是她老公的<br />
意見後才肯嘗試。<br />
這她的經驗中,我們也發現一些宗教的混雜。她用「洗」的概念來說明把身<br />
上的東西去除掉,這種洗的概念在阿美族時常見得,可能是用雙手將水撥到身上<br />
的動作,或是擦拭身體的動作,都有表現乾淨之動作(巴奈‧母路 2004)。此<br />
身體觀是認為病痛是附著在人的身上,必須透過一個超自然的潔淨方式,才能夠<br />
將病痛「洗」掉。從獵人嘴巴噴出的水,雖然混著口水但是絕對不會是髒的水,。<br />
這種洗身體的概念,與基督宗教有產生某種相似之處,基督宗教也將人的身體定<br />
義為有罪的身體,需要透過聖血來洗淨;基督宗教再阿美族社會也推行了四、五<br />
十年,這不免讓人懷疑有所關聯。<br />
Nikar 則用「八字」的概念,這詞彙又與漢人的傳統信仰有關,筆者提出兩<br />
個可能的解釋,第一,阿美族的身體觀中有類似於八卦輕和重,從這個概念延伸<br />
而借用此詞彙來表示;第二種可能性,就是阿美族現在的身體觀已受到漢人傳統<br />
信仰影響。吉拉米代部落有類似這種八字輕的概念,他們稱之為 pasafa,在部落<br />
族人認為人的兩個肩膀各有一個類似於「靈」,這個靈的強弱將會影響這個人是<br />
不是容易 adada,在過去族人們理解身體有任何症狀是因為自己 sala-afan 被人家<br />
的靈比下去(pasafa),所以不準小孩接近死人或是獵人,因為小孩的 sala-afan 並<br />
沒有生長成熟,容易被比下去(pasafa),也就容易得病。<br />
現在族人也將這種比下去(pasafa)理解成是傳染,認為過去被禁止接近死<br />
人、病人時,就是害怕他們的疾病會傳染給小孩。這樣理解的過程中,就沒有將<br />
5 報導人是用 suli 這個動詞,掌心壓在皮膚上,如搓揉麵團的方式摩擦皮膚。<br />
6 此句為「haman to tini tatilengan no wawa a dahen to cinga」的翻譯。<br />
18
「獵人」考慮進去,這也反應了某些矛盾,既然過去比下去(pasafa)的概念將能<br />
夠處理所有人的「傳染」問題,可是用生理醫學的「傳染」概念就無法理解為何<br />
不能夠接近獵人。所以部落族人還是用這種雙重的、混淆的概念在看待、理解。<br />
作為一個研究者也許會感到這種不一致的理解方式充滿了矛盾,對於部落居民而<br />
言,這種切割開來不一致的理解方式卻是不矛盾的、自然而然地。<br />
此現象也說明了「文化」或「宗教信仰」的複雜性,我們在其中已經無法清<br />
晰的找到阿美族文化或傳統信仰是什麼?因為它已經是各種元素的混淆狀況,這<br />
種混淆卻沒有混沌的感受,因為所有元素很合理的融合在一起,表現的是一種混<br />
淆的自然狀態。這種文化元素在非意識的狀態下達成平衡,這也強調身體主體的<br />
概念,身體能夠自主的吸收或排斥各種元素,產生一個新的樣貌,就像各種顏色<br />
的顏料混在一起完全分辨不出原來的元素在那?身體能夠在最省力最不產生突<br />
兀的情況下行程融合作用,看不見卻又實際發生。<br />
身體所產生出來的新元素,將會成為他理解文化或認知事物的方式,Nikar<br />
用這些元素理解自己的身體經驗和過程,在這樣的狀態下隨時解構文化,因為每<br />
一次的經驗或不同文化的融合中產生新的產物,此產物又能夠反映於經驗者的文<br />
化之中。這些的身體自主的活動,也強調了身體在研究中的重要課題。<br />
除了 Nikar,部落許多人都有經驗過 lati’,症狀大多身體癢到受不了,或是<br />
下瀉。<br />
Kacaw 的 lati’經驗,是一個年紀比他小的人 Caki 讓他受到的,他們一起在<br />
蔗田工作,下午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Kacaw 全身感到很癢,怎麼抓到還是很癢,<br />
Caki 的老婆就跟 Caki 說你現去幫他弄一下。Caki 就叫 Kacaw 休息一下,說要請<br />
他喝兩杯,兩人到雜貨店喝酒, Caki 就將米酒倒入嘴巴後,噴灑在自己的手上,<br />
然後拍一拍 Kacaw 的背部,並買一個皮蛋給他吃。Kacaw 被他拍得莫名其妙,<br />
但也沒有抵抗,吃下去之後立即感受到身體內的一種暖意,那種暖意是很輕鬆<br />
的、飄飄的感覺,原本全身都在癢,就在那個之後就沒有了,從拍打到整個身體<br />
好起來,不過五分鐘的時間。<br />
另一個身體經驗的報導人 Fulaw 是一位 75 歲的老獵人,他是部落目前唯一<br />
有靈性體質的獵人,他五年前丟掉製作陷阱的鋼線和部分獵具,因為他的某種體<br />
質必須讓他將這些東西丟棄,否則會讓自己身體有不舒服的感覺,丟棄的動作也<br />
宣告不再上山了。他並非一出生之後就有靈性體質,他是在 45 歲的時候發現自<br />
己有這種體質,以下是他和筆者的對話訴說自己得知靈性體質的過程。<br />
Fulaw:我的二兒子 E-mah,歪嘴,差不多三個月還是四個月看病沒有<br />
好。我們不知道麻,我們帶去漢人的祭司(乩童),後來我的阿<br />
姨就說要去布農族的巫師試看看。帶了一斗糯米、一隻雞,肉<br />
五斤,香菸一條,還有檳榔。帶去布農族的祭司,他不會我們<br />
的族語,一定要用他們的語言,我自己會講布農族的話,。他<br />
拿香蕉的葉子墊在最底下,拿一個碗裝滿水,旁邊放一瓶米酒,<br />
19
接著他就對碗唸著,dududa~dududa~dududa,那個訊息就會出<br />
現在碗裡頭,我們是看不懂。他就說等一下回去,要拍一拍自<br />
己的孩子,後來隔一天早上五點,我就拍一拍兒子的背後,然<br />
後出門工作,小孩也要去上學麻,(早上)八點我工作回來,小<br />
孩九點回來的時候,就沒有了(就好了)。<br />
筆 者:就從那個時候你才知道你有這個能力喔。<br />
Fulaw:我就是那時候知道,危險勒,我的lati'。只要有人malati'就直接<br />
會過來我這裡。<br />
筆 者:如果不是你的(lati')呢?也可以嗎?<br />
Fulaw:還是可以分辨的,每個人的lati’都不一樣,如果身體很冷的話<br />
就是我的(lati’),如果很熱就不是我的,歪嘴還有身體很癢的都<br />
是我的。<br />
在 Fulaw 的經驗裡,使人 lati’的能力(靈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一次偶<br />
然的情況下發生的,而且第一個被他的能力弄到 lati’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他求助<br />
於醫生和漢人的乩童皆沒有改變,轉而回來詢問原住民的巫師,而且是布農族<br />
的。布農族的巫師並沒有講明這個孩子發生什麼事情,而是告訴 Fulaw 應該要怎<br />
麼做,Fulaw 卻在第一個時間知道自己有這種讓人家 lati’的能力,他表示他原本<br />
就知道部落的獵人會有這樣的能力,可是卻發生在自己身上,也感到不可思議。<br />
只是他並不知道這樣的力量是如何產生的,也不能夠明確的說出這樣的力量到底<br />
是什麼,可是他確知道這是他身上所擁有,而且當有人接近他或處碰到他的東西<br />
時,會讓人產生不舒服的感覺,他就必須用某些儀式來醫治。<br />
擁有靈性體質的人,卻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從何而來,也不知道這股力量是<br />
什麼?這些能力已經離開了能夠意識或者能夠理解的層次,這是身體自我的一種<br />
表現,那些能力或感受都會這樣發生。Fulaw 他也知道有什麼樣的行為會讓這種<br />
能力增強,這一切都是一種信仰,相信這些就會發生,而不需要理解,當然不理<br />
解的同時這種力量也會讓自己受苦。他說:<br />
如果你有打到水鹿或兩、三百斤以上的山猪,那個lati'很強。我的lati'<br />
什麼都有(表示有比較多的症狀),做全身檢查,找不到什麼毛病,醫<br />
生不知道原住民的lati'。我沒有放陷阱,就是沒有放一段時間,那個lati’<br />
就會很壞,它(具有lati’能力的獵具)就會讓我不舒服(adada),如果有放<br />
就會沒有問題。所以要一直放才可以,身體也不知道怎麼樣的不舒服,<br />
頭痛也不一樣,可是我知道是它讓我這樣的,嚴重的時候還會吐血。<br />
獵到水鹿和三百多斤以上的山豬,是獵人能力的一個指標,這兩種動物是比<br />
較大型的動物,而且不太容易被陷阱制伏,諸多老獵人常述說自己追捕水鹿或刺<br />
殺大山豬的情境,可以見得對於獵人來說這不是一件普通的經驗。lati’的強弱也<br />
20
和這指標不謀而合,部落居民提到這些具有靈力的獵人,除了會感到害怕之外,<br />
也感到敬畏,因為族人知道擁有這樣能力的人,也表示他是一個優秀的狩獵者。<br />
Fulaw 知道當自己獵到這些較困難的動物時,lati’的能力就會跟著增強,也更會<br />
讓其他人受到痛苦。有時候是自己的親戚、朋友,據他表示他也不太希望讓人家<br />
得到 lati’可是這又非常的無奈,自己本身就是擁有這樣的能力。他自己也常到醫<br />
院幫朋友「治療」,因為族人經過幾個醫院診斷都無發的到治癒時,就會想到<br />
Fulaw,便請他到醫院來為他們「治療」。<br />
但是這種力量不只是讓人家受苦,這樣的力量卻也會因為自己沒有上山,獵<br />
具讓自己感到不舒服,獵人會有頭痛、顫抖的症狀,最嚴重的還會吐血,所以他<br />
並沒有因為這種裡力量得到太多好處,因為反應自己的卻是另一種痛苦的感受。<br />
這也使得 Fulaw 必須時常的要進入山林狩獵。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Fulaw<br />
表示很多人都不知道這種會讓人家 lati’的人,其實也因為沒有上山狩獵而自己就<br />
會 lati’。<br />
四、體現的文化與自我的身體<br />
在此研究中,Nikar對於身體發癢始終無法一致的經驗,有這一套理解的方<br />
式,或是認知的方式,他能夠分辨那次經驗的「癢」和皮膚病、過敏經驗的「癢」<br />
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他能夠理解這樣知覺的產生,事實上來自於文化對於身體的<br />
感知方式,那種差別只有在相同文化脈絡下才能夠解讀。Fulaw能夠感受到獵具<br />
對於他的身體影響,自己的在獵具上的靈力反置於自己,也不是一種能夠理解的<br />
感受,卻需要從某種特定文化脈絡才能夠瞭解。<br />
他們在這些獨特的身體經驗中的知覺和理解,實現自身文化的某些元素,當<br />
然他們的文化是很多樣的,無法定義的。這也呼應余舜德的觀點,他認為「每個<br />
文化以不同之方式感知內在與外在的世界,各自獨特的文化方式包含以不同的角<br />
度組合感官知覺,或發展出具文化獨特意義之感知的項目」(余舜德<br />
2003:108)。所謂感官知覺就是痛覺,是身體實際的刺激,而感知的項目是這些<br />
知覺延伸出個人的痛苦感或是不舒服感。從Nikar和Fulaw對於lati’的身體經驗<br />
中,體現了自己的文化。在此研究中還未能夠提出較明確的文化探討,比較明確<br />
的是提供一個文化的方式。<br />
在此經驗研究中筆者以「身體主體」解釋經驗中「非意識」實踐與感知。<br />
Nikar無法用科學理性理解這種反應只有獵人用米酒來洗身體之後才能痊癒的現<br />
象,她面對的是一個無解或是無法證實的「真實」,這種身體經驗的確是「真實」<br />
的感受,身體經驗就和一般皮膚病和過敏的感受區隔開來,這種區隔如果是在非<br />
意識狀態下的反應,從一個「身體主體」能夠理解,因為身體主動的定義和區隔<br />
經驗本身。Fulaw靈性體質是能夠知覺其特殊的感受,並且「使用」此體質,他<br />
的身體也表現出一個他無法意識到的感知,他能夠理解感知的存在,卻無法言明<br />
感知的力量是如何進來、如何刺激,他的身體已經主動的接收此感知,也主動的<br />
理解。<br />
21
這種身體區隔的感受,表現的是一種自我的身體,身體在不言明的情況下,<br />
身體自己卻做出了定義和決定,不需要進行思考或意識理解,身體已經在過程中<br />
主動理解,也就是身體主體此經驗中定義了此非理解的知覺,表現自我的身體。<br />
另一部份,在此研究中身體表現自我的例子,相異文化在身體主體的情況下<br />
進行自然的交溶,研究者雖然在過程中發現不同文化的交錯理解及使用,似乎呈<br />
現一種矛盾的情境,可是對於在地居民而言,在這種文化混淆的狀況下並不會感<br />
到矛盾,而且實踐的非常自然,筆者認為這種文化交融的狀況,也是身體在非意<br />
識的狀態下進行的主體展現,個人的身體能夠將不自然、混沌的接觸,主體的融<br />
合在個人的經驗和實踐中,實現自我的身體。<br />
不同文化會陶冶出不同的行為、動作和姿勢,既使是簡單的走路,我們還是<br />
可以從身體的觀察發現差異。這些行為、動作和姿勢皆是身體的技術,不是與生<br />
俱來,而需經由身體反覆的學習和試誤,才有所成就;文化知識提供身體技術的<br />
目標,每個人各憑本事修練自己的身體。身體本身具有自主性,身體感知是與生<br />
俱來,透過文化概念的經驗後形成,而身體感知也有能力選擇需要怎樣的一種文<br />
化(Lock Scheper-Hughes 1996)。身體有雙重的向度,一個是文化概念提供給身體<br />
的認知方式與技術,另一個向度,是身體的經驗、感知能夠向外影響社會或文化。<br />
本研究從「lati’」的經驗和想像中,發現身體是文化的接收者亦是文化的體<br />
現者,身體的經驗方式會受到限制亦會促成文化的建構和解構。每個人在習得與<br />
實現文化象徵的過程中,無法抽離自己的身體,唯有從身體作為各種元素的處理<br />
場所,才能夠理解客觀外部知識與自身內在知識的交融過程。文化概念影響個人<br />
的思想與行為,是我們所理解的事實,但個人轉而影響文化卻沒有較多的討論,<br />
筆者從「lati’」經驗中身體與文化的理解上,認為文化與個人的相互影響,是往<br />
後可努力的研究方向,也是身體作為知識研究的價值所在。<br />
五、結論<br />
「lati’」是狩獵「文化」裡一個重要且普遍的經驗,也是從理性科學概念裡<br />
無法理解的現象,在經驗中包含了文化所框架出來的概念,就像此研究的報導<br />
人,雖然無法理解這是什麼現象,但是文化卻給予他理解和定義的方式,而且這<br />
樣的定義過程卻是從身體出發的,身體主動從知覺中的進行定義及分辨,這種能<br />
力必須來自於文化既有的理解和思維。<br />
另一部份,「lati’」經驗本身是一個最直接的身體經驗,容許筆者從身體經<br />
驗的課題來研究文化內涵。雖然研究內容並不充足,卻能夠提醒身體研究的可能<br />
性,以及可能的方向,表達身體經驗使文化和自我發生在個體,也提供個體影響<br />
文化的思考方向。<br />
第三個部分「lati’」經驗中也可看見或預知個體差異的可能性,因為每個人<br />
的遭遇皆有所不同,可以從這一發現每個人因為經驗來理解內部(身體感受)和<br />
外部的世界,當有不同的經驗發生,就會有不同的自我理解,者也說明經驗和實<br />
踐中個體的重要性,因為皆有所差異的反應。<br />
22
通常人類學討論這種超自然力量的研究,探討的是族群信仰和價值、社會功<br />
能或是所傳達的文化象徵,經驗者本身和經驗的現場卻不被意識,在此研究中著<br />
重個人的經驗和他對於此經驗的理解,從中討論「身體」課題作為文化探究的方<br />
式。從此研究的經驗討探中,開啟探討文化的討論,我們時常使用「文化」的概<br />
念框架一個族群或人群,就如同阿美族是個母系社會、阿美族的傳統價值及信<br />
仰,但是這也造成了個體具有先驗的經驗結果,但是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br />
經驗者是人,我們沒有必要將一個複雜且多樣的結果,單一化或簡單化,我們試<br />
圖提供的是一個文化現象的可能因素或者相關性,而不是在諸多個體實踐中尋早<br />
某種定則或公式。<br />
人類學時常要去界定這是誰的文化,發現這一群人對於事物獨得的理解或認<br />
知系統。筆者從經驗研究裡發現,如何能夠辦到這種發現對於異己文化的發現屬<br />
於原來族群的因子,所有事件所有理解方式皆是混淆在實踐過程中或是經驗過程<br />
中,我們在經驗過程中發現了許多矛盾、混沌,但是對於實踐者或經驗者而言,<br />
卻是理所當然且自然的,這些所謂的「文化」已經很自然的混淆,卻不矛盾。人<br />
類學者試圖在這些理所當然中找尋矛盾、混沌,提供一種「想像」的空間,試圖<br />
在其中發現各種相關性。這也提醒研究者,文化並非組合而成,我們很難向拼圖<br />
一樣找到一片一片的拼圖,拼成一幅叫做「文化」的圖形,卻是在一個大染缸裡<br />
找到一些可能顏色元素,這些元素在這缸文化的流體中,幾乎很難的單一發現。<br />
從經驗研究中發現筆者對於身體課題的重要性,這種混淆的融合,必須透過身體<br />
實踐和身體經驗才能夠實現,身體的概念,也發揮這種非意識層次的自然交融。<br />
23
參考書目<br />
巴奈.母路<br />
余舜德<br />
2004 靈路上的音樂:阿美族里漏社祭師歲時祭儀。花蓮縣吉安鄉:原音基<br />
金會。<br />
2003 文化感知身體的方式:人類學冷熱醫學研究的重新思考。刊於臺灣人<br />
Douglas, Mary<br />
類學刊 1(1):105-146。<br />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br />
New York: Pantheon Books.<br />
1973 Natural symbols : 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 New York : Vintage Books<br />
Foucault, Michel.<br />
1988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uther H.<br />
Martin, Huck Gutman and Patrick H. Hutton, eds. The University of<br />
Massachusetts Press,.<br />
1990[1981] 性意識史‧第一卷:導論,尚衡譯。台北:桂冠。<br />
Lock, Margaret and Nancy Scheper-Hughes<br />
1996 A Critical-Interpretive Approach in Medical Anthropology: Rituals and<br />
Routines of Discipline and Dissent. In Handbook of Medical<br />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Method. Carolyn Sargent and<br />
Thomas Johnson, et al. Pp. 41-70.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br />
24
下車:重返水底寮<br />
蔡欣齡<br />
這些曾經發生的事情如果沒有寫下來,過去就這樣過去了,留下來的只有書<br />
本上看得到的東西,而真正呼吸過的生命卻留不住。當然我也不是認為文字可以<br />
完全留住生命,但至少我想盡力留下一點點。常常覺得我現在可以用文字表達思<br />
想,這不是一件偶然又容易的事,到目前為止的生命過程中,只要有任何一處不<br />
是按照那樣走,或許我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如果現在我有一點文字表達能力,<br />
那一定有什麼事等著我去完成。<br />
經濟生活影響一個人應該是很深的,一個人會去關心什麼問題,這跟一個人<br />
的背景有很大的關係;或者說,一個人不會去關心什麼問題,這跟他/她的背景<br />
有很大的關係。最近看到一篇學術論文,文中描述某位西方學者在經濟不景氣時<br />
「一度淪為計程車司機」,看到作者使用「淪」這個字,我感到非常沮喪,這個<br />
字通常用於「沈淪」或「淪陷」等負面詞意;我不由得想到,如果這位作者生命<br />
中至愛的親人以計程車維生,甚至父親或母親正是拿開計程車的錢來供養其就<br />
學,那麼,這位作者在用詞上會不會客氣一點?<br />
我所關心的原漢物資交換關係,在既有的文獻記載中,通常以客觀的敘述句<br />
呈現。例如:「各社生番持(山產)與熟番交易珠布鹽鐵,熟番出<br />
與通事交易。」(黃椒敬 1957:153)又如《鳳山縣志》:「毛布:番婦以獸毛和苧<br />
織成。漢人買以代氈,或為包裹之用。」(陳文達 1993)以上為文言文的例子,<br />
白話文的例子如《浸水營古道人文史蹟調查報告》:「早在荷蘭時代,位在三條崙<br />
道中途站的力里社排灣族,已經攜山產下山來交換日用品。」「嘉慶年代(西元<br />
1796-1820)水底寮已設民、番交易所,當時稱為『換番所』」(楊南郡 2003:55,93)。<br />
從上述記載中可歸納幾個要點:第一,原住民與漢人的物資交換由來已久;<br />
第二,原住民方面的交換物資為山產、漢人方面的交換物資為日用品;第三,固<br />
定的交易地點史上稱為換番所或漢番交易所。目前台灣史的研究中,當討論到「番<br />
界」、「生番(高山族群)、熟番(平埔族群),與漢人之間的關係」等主題時,內<br />
容必探討到不同族群交換民生物資的史實(詹素娟 1986,2004;王慧芬 2000;<br />
翁佳音 2000;柯志明 2001;鄭維中 2004)。然而我所關心的並不是考證有哪些<br />
物資被交換、何時成立交換所,也不是執政者對於交換現象的決策動向,我所關<br />
心的是交換的過程中,那當時真實呼吸的人們究竟如何互動?當彼此的穿著不一<br />
樣、說不同的語言、生活在不一樣的地方,面對面接觸的時候,當事者心裡在想<br />
什麼?感受是什麼?說些什麼話?做了什麼動作?<br />
我的報導人出生於 1951 年,她成長於屏東水底寮的務農家庭,在家庭中的<br />
角色為次女(三個姊姊、兩個哥哥、一個弟弟),讀過小學但沒有畢業,童年時<br />
曾經目睹排灣族人身著黑色衣衫,攜帶木柴、芋頭等山產,來到水底寮家中交換<br />
衣服、米等物資的情景。同樣講述交換的史實,從報導人的口述中,我看到了與<br />
25
上述種種文獻記載完全不同的內容與表達方式:<br />
伊歸身軀攏酒味,穿著跟咱無共。我彼陣實在是真生氣,我的衫找<br />
攏無,攏恁阿嬤拿去換了。我想,囡仔若哭,大人會緊帶走,所以<br />
我才會把他捏落去(笑)。大家攏真艱苦啦,即馬想想咧,他們行跡<br />
呢遠的路,換的是一點仔簡單的東西爾,大家攏真艱苦啦。<br />
報導人使用的是她慣習的閩南語,這段話譯成中文的意思大約是說<br />
他們全身都是酒味,穿得又很不一樣。我那時候很生氣,常常找不到我<br />
的衣服,找了很久才知道是妳外婆拿去交換。我想,如果小孩子哭,大<br />
人就會趕快帶小孩離開,所以我才會偷捏他們的小孩子。現在想想,他<br />
們走那麼遠的山路,只是為了跟我們交換那一點點東西,只是為了吃<br />
飽、穿暖,大家都很辛苦。<br />
這段報導人的記憶所代表的是「女性、孩童、閩南語」的話語呈現,這跟我<br />
目前所見的文獻所呈現的客觀敘述句有很大的差異。Mary Louise Pratt 通過「話<br />
語 discoruse」檢視民族誌寫作所涉及的問題,提出民族誌有所謂的「話語傳統」,<br />
亦即在民族誌寫作中,研究者如何看待或書寫研究對象,將可能受到研究者當時<br />
的背景、研究對象在歷來民族誌中的形象變化等因素所影響。在我的田野資料<br />
中,「女性、孩童、閩南語」的話語呈現並沒有可溯及的文獻對象,這也可以說,<br />
在過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女性、孩童、閩南語」是較為受到歷史論述所忽<br />
略的。既然我所要呈現的內容在歷史中沒有話語傳統,我便認為,在寫作上更必<br />
須選擇合適的方式,才能夠傳達研究主題以及田野資料的特質。<br />
我預計以第一人稱的敘說方式,朝三個向方進行寫作。第一個部份是將小學<br />
以前完全沒有接觸過原住民的情況舖敘出來,新莊的原生家庭以及水底寮的外婆<br />
家都是閩南文化氛圍,映照接下來身份辨識的主題。第二個部份是我國中、高中、<br />
大學、研究所等每個階段,都遇到外界關於原住民的身份指認,「妳是山地人嗎?」<br />
「妳是原住民嗎?」「妳也是原住民嗎?」「妳是哪一族?」這些指認的話語在不<br />
同的時空中跟我對自己的認知產生對話,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因此是一直在變動<br />
的,此為第二部份的寫作重心。第三個部份是透過報導人的回憶口述,返回五O<br />
年代的水底寮,將報導人所回憶的內容以「場景」的方式描寫出來,如農忙的場<br />
景、與排灣族接觸的場景等。<br />
本研究成果即第一部份「小學以前的生活」之最開始,內容是回憶童年的家<br />
庭處境以及每年春節與母親搭車返回水底寮的過程。以「下車」為題,比喻書寫<br />
水底寮的動作,如同童年時跟著父母搭乘客運至水底寮下車的經驗,只不過現在<br />
是自己前往、自己下車,透過回憶敘說以觀照自身生命。<br />
26
●<br />
菜市場街路在中午過後安靜許多。那天,大部份攤位都收了,只有文具店前<br />
面的水果攤還擺著,文具店老闆娘、水果攤老闆等幾個大人坐在一起,媽媽把紅<br />
色鈴木五十停在水果攤前,我坐在後座,雙手環抱媽媽的身體、耳朵貼緊背部,<br />
一邊聽到模糊的砰然節奏,一邊聽到清楚的講話聲音,媽媽說:阿嬤疼姊姊,接<br />
下來想抱個男孫,這個孩子是第二個女的,阿嬤不疼她……<br />
媽媽外出工作,傍晚時分,紅色鈴木五十的引擎聲從巷子口傳來,我一整天<br />
的重擔才卸下來。跟著到二樓,迫不及待訴說阿嬤有多麼不喜歡我,「今天阿嬤<br />
有打我們,阿嬤打大姊比較多下,可是都很輕,阿嬤打我比較少下,可是都很用<br />
力。」媽媽不會附和我,說我太多心,可是很奇怪,我又經常聽見她跟別人說阿<br />
嬤對我不好,這真的是我一再感到不明白的地方。<br />
月底那幾天沒錢,跟媽媽去泰山的乾洗店找一位童年玩伴。進到乾洗店,一<br />
下子無法與那假得像塑膠的味道和平相處,儘管沒有任何束縛,壓迫感卻無所不<br />
在,我不動聲色地一再吸氣、吐氣,直至感覺不到為止。媽媽買掬水軒營養口糧<br />
給我,滿足又忍耐地混著乾洗店的味道吃。等她們講完話,媽媽順道在泰山幫紅<br />
色鈴木五十加油,然後回到新莊家裡。<br />
在一樓通舖房間被阿嬤捏得很痛很痛,並不是先被捏痛才哭的,而是撕喊著<br />
想到二樓,無論如何表達心願,情況不允許就是不允許。抽抽噎噎躺回床上,阿<br />
嬤捏我大腿,「掐」下去時預備承受,「轉」最是痛到極點,強忍住,在痛與忍<br />
之間產生一種抵抗的快意;如果再哭,又會被捏,重複痛的感覺。這全是因為剛<br />
出生的弟弟需要照顧,四歲的我不能留在爸媽二樓房間。<br />
從這時候起,睡在我右邊的是阿公,他一隻耳朵聽不見,阿嬤跟他講話很大<br />
聲,有時會念他「臭耳聾」。阿公的耳朵是日本時代在嘉義機場修飛機時,被飛<br />
機的聲音弄壞的。阿公的頭髮終日抺上黏稠的髮油,枕頭上有一層油垢,另隻耳<br />
朵貼近一台小收音機,擴音的黑色網點也卡著油垢。收音機裡的講話跟我愛聽的<br />
流行歌不一樣,聽吳樂天講「日本時代義賊-廖添丁」的故事好似在看電影,有<br />
個壞人的偷襲行動被人預料,就在壞人往上推開木板的剎那,早已準備好的麥芽<br />
膏從上面倒入壞人的眼睛。剛好我眼睛受傷、出院回家休養,一直想,若真的被<br />
麥芽膏沾到,眼睛還有救嗎?感覺好像很難過、很恐怖。還有,那個麥芽糖很好<br />
吃,菜市場偶爾有人來賣,只要跟那個人講我們想要什麼圖案,他就會做成一片<br />
棒棒糖,有很多大人小孩圍著看,我常擔心他做不出別人要的圖案,可是從來沒<br />
有發生,如果有人說要「牛」,他用棒子在鐵盤上勾畫一下麥芽膏,就有一隻牛<br />
了!我還看過鬍鬚很長的龍。所以說,怎麼會去把麥芽膏拿來倒在人的眼睛上<br />
呢?<br />
睡在我左邊的是姊姊,姊姊的左邊是阿嬤,這是每天睡覺固定的位置。夏天<br />
的時候,阿嬤側身向著我們,手上的扇子在她睡著時停住,一會兒醒來又繼續搧,<br />
阿嬤腳邊還有一台小電風扇轉來轉去,我有時吹得到風,有時吹不到,就這樣搧<br />
27
搧停停直到睡著,醒來又是另一天。有一天我跟姊姊擁有了自己的扇子,阿嬤不<br />
在時我們就互相搧風,我手痠換姊姊搧,姊姊手痠就換我,我會搧到真的忍不住<br />
痠了才停止,我常覺得姊姊的手很容易痠。我的扇子是藍色塑膠材質,上面有小<br />
天使、雲和彩虹圖案,小天使長得圓嘟嘟,身體飄行在兩朵白雲和彩虹之間,彩<br />
色木馬也在這片天空優遊,兒童樂園的旋轉木馬是好玩的地方,扇子裡的世界是<br />
可以飛翔的快樂天堂,我還另外貼了一些喜歡的糖果、餅乾、草莓貼紙上去。姊<br />
姊的是粉紅色小白兔圖案,不知是不是她屬兔的關係才挑這圖案的。我屬蛇,阿<br />
嬤很怕蛇,電視上如果出現蛇,就要趕快轉到別台去。<br />
當我可以靜靜閉上眼睛,想像回到外婆家的感覺,那應該是不再哭的時候了。<br />
小時候過年就是做一些相同的事。從除夕晚上吃火鍋開始,隔天睡醒是初<br />
一,那條平日上午有很多攤位的菜市場街路一片寂靜,相銜的中正路幾乎沒有車<br />
子往來,跟平時差很多。初一白天,大人都會帶我們去逛新莊街,媽媽則是忙著<br />
準備很多事情,接近晚上十二點,拖著行李穿越菜市場街路,我可以認出平常哪<br />
個攤位是賣菜的、賣豆花的、賣衣服的、賣肉鬆的,肉鬆店老闆有時在門口烤一<br />
種四方型片狀的紅色肉乾,這是姊姊愛吃的,老闆有時在門口炒肉鬆,攪拌機器<br />
散發出誘人的香味,聞到的感覺很像在夢裡吃到餅乾,醒來卻失落了咀嚼的真實<br />
感。肉鬆店斜對面,雞從狹小的籠子哎哎地被抓出來,脖子劃一刀、丟進攪拌筒,<br />
平常要不動聲色地憋氣走過去,雞糞的味道很像是腳底踏在陰天的黑色砂岸,上<br />
岸時沾黏許多細小砂石,無法完全撥乾淨的感覺。行過西藥房、麵包店、豆漿店、<br />
幼稚園,抵達中正路。在這冷清大街,周遭的空寂讓我驚訝,不知道人都哪去了?<br />
爸爸攔一台計程車載我們去台汽西站,排隊等待台北到高雄的國光號補位。<br />
坐上國光號,車子開始移動,就有一種出遠門的興奮,好像接下來要去一個<br />
跟平常不一樣的地方。從台北到三重這一段路,看著窗外街道、車子、招牌閃爍,<br />
一直到了高速公路,窗外閃爍的燈光離我遠去,才不再盯著外面看。車行愈久,<br />
想做一點事情來推移時間,眼睛貼近玻璃窗探望車窗外的風景,所見仍然是潻黑<br />
的夜晚,偶爾遠方出現點點亮光,想不透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家住在這樣遠僻的地<br />
方?往前看,潻黑的夜晚被長長的紅色車燈妝點,車燈蜿蜒著道路的曲向,而對<br />
向的北上車道偶有金色車燈閃過,為什麼我們不是在那條比較好走的路上呢?每<br />
年都這樣,國光號小姐沿走道一手拉桿子一手捧盤子、端水給乘客,司機在我們<br />
睡得很累時仍然耐心地推進。<br />
我和姊姊、弟弟在車子上吃除夕拜拜過的旺旺仙貝、媽媽準備的飯團、切好<br />
的水果等零食。當弟弟還是嬰兒的時候,我跟姊姊一人坐一個位子,後來弟弟愈<br />
長愈大,變成三個人擠兩個位置。有次弟弟在唱「明天會更好」,我擔心太大聲<br />
吵到別人,叫他唱小聲一點。媽媽常叫我要愛護弟弟,我和姊姊回娘家都是要靠<br />
弟弟,將來是弟弟當家的。弟弟小時候大完便還不會自己擦屁股,媽媽在客廳忙<br />
著車衣服,叫我幫弟弟擦,弟弟每次大完便,總是走到廁所門口,叫:「二姊。」<br />
然後把屁股抬高,我就去馬桶那邊拿衛生紙出來幫他擦,若遇到水水的黃色大<br />
便,那種就要用比較多張衛生紙,才能把旁邊皮膚的大便擦掉。<br />
28
車子走走停停而我睡了又醒的途中,吃過零食的嘴巴逐漸發酸,剛開始興奮<br />
的心情都消磨盡了,只希望趕快到達高雄。到高雄天已經亮了,這就是正正當當<br />
的初二,媽媽說女兒可以回娘家的日子。一下車,跟台北不一樣口音的閩南語迎<br />
面而來,計程車司機過來招攬正在拖行李的人,「屏東!屏東!」「潮洲!」「東<br />
港!」「枋寮哦!」「恆春哦,恆春!」我不敢看他們,因為我知道坐計程車很貴。<br />
往水底寮的客運站在高雄台汽站的旁邊。搭客運的人很多、沒有位子坐,我<br />
們硬擠上車,我在門口只有一隻腳站立的空間,每當有人下車,門一摺開,腳就<br />
受到壓迫。晃著晃著,窗外景色從高樓大廈漸漸變成舒展的綠地以及拍打著幫浦<br />
的池子,水底寮彷彿就快到了,然而每次都是爸媽提醒,我才知道該下車了。我<br />
想,要是我自己一個人來,我會知道在哪裡下車嗎?下車之後,媽媽經常一時找<br />
不到路,這時爸爸就笑她,自己家還會找不到路,媽媽也自己笑自己,她說房子<br />
愈蓋愈多,差點快不認得了。終究我們還是會找到路,拖著行李走在水底寮的街<br />
道,呼吸著燒柴火混著雞大便或豬大便的味道,爸爸說:「就是這個味道!」姊<br />
姊和我也這樣覺得,水底寮才有這種味道。有時候路上有人認出媽媽是「慶嬸的<br />
女兒」,媽媽一路上都在笑,感覺這就是她的地方。<br />
29
參考書目<br />
王慧芬<br />
翁佳音<br />
2000 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台北: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2000 地方會議‧瞨社與王田─臺灣近代初期史研究筆記(一)。刊於台灣<br />
文獻 51(3):263-281。<br />
陳文達<br />
1993 鳳山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br />
黃叔璥<br />
1999 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br />
楊南郡<br />
2003 浸水營古道人文史蹟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農會林務局。<br />
詹素娟<br />
1986 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關係之探討。刊於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br />
詹素娟<br />
2004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的「熟番」政策─以宜蘭平埔族為例。刊於台灣<br />
史研究 11(1):43-78。<br />
詹母斯‧克利福德、喬治‧馬庫斯編<br />
2006 寫文化,高丙中、吳曉黎、李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br />
30
愛情,需要翻譯:戀人絮語的言談分析<br />
謝佳玲<br />
最初是想瞭解人與人之間的「同在」是怎麼一回事。「同在」簡單說就是一<br />
種「我跟你在一起」的感受,一種幾近自我消融的聯結經驗。戀人間有時出現強<br />
烈的同在感,像回到母親溫暖的子宮般讓人重新感受到安全、完整,但這經驗卻<br />
如閃現的靈光,存在於用語言辨識前的瞬間,在辨識當下就遠離了它。經驗中也<br />
發現越刻意要達到「同在」越只突顯雙方的差異與距離,可是在某些自自然然的<br />
時刻,「同在」又如神的恩賜般悄悄冒出,讓彼此珍惜而享受相互的陪伴。<br />
如果「同在」是一種人與人之間親暱的靠近,那我感到困惑與好奇的是:他<br />
人其實是我無法完全瞭解的他者,這種同在難道是一種幻覺?又兩個人都感到同<br />
在才是同在嗎?關係裡我們總說要溝通,但更常是發現越溝越不通,又或者同在<br />
需要的不是語言與理解,而是別的?而且,感到同在的是哪個部分的自己?是「自<br />
我」還是更深層的「存在主體」?<br />
戀人想瞭解彼此,透過言語行動試探對方真正的心意,在戀人的對話中特別<br />
能展現這種試圖抵達同在的欲望。然而戀人常常也是最受挫的,在試探的同時,<br />
可能發現對方是自己永遠抵達不了的他者;或者在某些時刻以為瞭解了彼此,以<br />
為同在了,但之後又發現其實並沒有。一般觀點認為要理解不同的語言、文化需<br />
要透過翻譯,但其實即使是同種族同語言的戀人也未必能真正瞭解彼此。這不是<br />
在說明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這種對性別差異的通俗說法,而是想呈現語<br />
言本身的問題。<br />
詮釋學討論語言與理解之間的關係,認為人類理解事物是以語言作為符號來<br />
替代真實的對象物,然而符號與真實對象物之間的對應性並非如此絕對,符號有<br />
其任意性,真實對象物亦有其不可符號化的部分。以此觀點我們可以說符號與真<br />
實對象物之間有一道很難跨越的鴻溝,語言符號是一種對真實對象物的「修辭」,<br />
兩者不能等同視之。<br />
那麼,直接以語言追尋「同在」就像立即要以符號抵達真實對象物一樣,會<br />
陷入追尋海市蜃樓的虛妄,不斷自我反覆而找不到出口。「同在」與「理解同在」<br />
其實不等同,但是戀人總是很依賴語言去抵達同在,可能失敗 N 遍後才會慢慢<br />
看出某種徒勞,感覺到那道阻隔的透明之牆。所以,我試圖尋找其他出路,看有<br />
無可能建立一種經驗(身體)的知識,放棄用語言去抵達「同在」,而接受這路<br />
途的迂迴與掙扎的徒勞,發展出如關係修練般更切合真實情況的描述?<br />
關係修練將企圖抵達同在的經驗與理解視為不斷地以動態方式交錯的向<br />
度。就像旅行一樣,讀大堆旅行書無法替代真正在當地的經驗,上路前每個旅行<br />
者對旅途都有一套自己的想像與期待,可是實際一定不一樣。旅行就是在想像理<br />
解與實際情況間交錯的動態過程,而且每個旅行者都各自有無法複製的獨特性,<br />
我們只能參考其他人的經驗,然後決定自己要怎樣才能玩得「爽」。<br />
31
追尋同在大概也是一樣的,關係修練重視的是那種過程的「爽」。如果同在<br />
不能直接追求,是一種虛妄的幻見,那麼在關係裡我們為了達到「同在」,不可<br />
自拔地不停使用語言,語言又作為一種「修辭」,這種「修辭」的價值該是在其<br />
過程而非結果。換句話說,關係修練是作為一種自我技藝或生存美學,而非真的<br />
要抵達某種理想樣態。如果我們只能不停地「修辭」,那麼把關係裡的「修辭」<br />
當作自我技藝,觀察它怎麼形塑主體,可能比苦苦追求「同在」更有建設性。<br />
一、問題意識與研究取向<br />
過去對愛情的研究大致有幾個方向,心理學多在分析當事人對愛情的敘說來<br />
建構愛情的意義、發展歷程與其對個人帶來的轉化。人類學可能探討文化差異如<br />
何對愛情帶來不同的想像與實踐。而社會學則較從性別政治或歷史的角度來看待<br />
愛情的系譜學。<br />
此研究較採心理學取向,著重戀人絮語如何作為「修辭」而轉出成長的可能<br />
性。與一般心理學研究不同是採納符號學與詮釋學的觀點,不將戀人的敘說內容<br />
當作真實,也不將其視為特定的個人經驗,而是將戀人的對白當作文本。文本是<br />
一系列修辭的符號,這些符號的給出不歸因為個人的性格特質,而歸因於處境。<br />
如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 書中所強調的「不是人在談戀愛,是戀愛在談人。」<br />
不應將戀人僅僅歸結為單純的帶有某種特殊症狀的主體,而是戀愛作為一種人與<br />
人互動處境將人帶入戀愛的語言裡。<br />
這觀點預設了語言是先於主體而存在的客觀條件,人是語言符號作用過程的<br />
產物,而非這個過程的成因或起源。基於此,這裡將戀人間的絮語視作一種修辭<br />
的符號來探討追尋同在的歷程,繼續探問下去的便是,這些符號與指涉的真實對<br />
象物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說出這些符號背後的欲望動力是如何運作?而這些符<br />
號又怎麼回過頭去塑造戀人對自己與對關係的理解?<br />
研究者先以言談分析的方法來檢視戀人的對話資料,區分出話語的行動意<br />
圖,與話語中呈現的主體層次。未來將試圖詮釋戀愛作為一種處境,追尋同在作<br />
為一種欲望下,雙方如何使用語言、如何理解彼此,語言又如何磨塑主體的歷程。<br />
研究的最終是期盼能發現具有時代意義的自我技藝策略,發展出關係修練作為修<br />
行法門的可能性。<br />
二、言談試分析<br />
言談分析視交談不只是 saying something,也是 doing something。交談是一系列<br />
的社會行動,語句作為談話中的動作,交談者不僅試圖理解話語的內涵,同時也在<br />
詮釋對方話語作為動作的意圖。<br />
言談分析會檢視話語的三種意涵類別,(1)行動序列:一系列溝通行動中所呈<br />
現的次序。如一方問問題,另一方就被要求回答,這是鄰對,是兩個溝通行動所組<br />
成的次序。(2)談話行動:語句作為對話過程中的行動。如「Oh」是對對方話語表<br />
示新奇或疑惑,其目的在試圖保持對話順暢進行。(3)延展結構:構成某種特定敘<br />
32
述形式的一系列語句,包括論說與敘事。論說涉及互不同意的擴張性談話,而敘事<br />
是描述故事的一系列語句 1 。<br />
試分析一(S與A是一對剛分手的戀人)<br />
行動序列/行動 語句內容 備註<br />
伏起<br />
A: 唉<br />
S 接引<br />
S: 為什麼要唉阿 ?<br />
論說/宣稱 A: 我真的搞不懂你啊<br />
S 論說/基礎(反) S: 我其實很努力要你懂的<br />
論說/強度 A: 可我真的不大懂你<br />
S 接引/共同完成 S: 你以為我是這樣了,可是又是那樣,是嗎<br />
論說/理由 A: 是啊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真的要我<br />
基礎<br />
我覺得你在告訴我,你沒有我也可以很好,甚至更好<br />
你今天下午說,其實愛,就是許多的慾望吧<br />
我覺得也有道理<br />
S 論說/基礎(反) S: 要,又怎麼樣呢? 我要的,你又不想給。<br />
論說/理由(反) A: 可能我也害怕吧 感覺你隨時可以放棄我、離開我<br />
A:唉<br />
伏起,由之前對話所引發。<br />
S:為什麼要唉阿?<br />
接引,保持對話順暢進行。<br />
A:我真的搞不懂你阿<br />
論說/宣稱,請對方同意。由先前討論的主題延伸出來,話語的情緒可能中<br />
性,也可能隱含埋怨。這話作為一個符號,符號與承接符號的平台還處於一種模<br />
糊不清的狀態。對 A 而言 S 這個對體是模模糊糊的,難以定論。<br />
S:我其實很努力要你懂的<br />
論說/基礎(反)。基本上認可對方話語的宣稱,但詮釋對方的行動有指責埋<br />
怨意味,因此在辯解「對方宣稱的基礎」。「其實」意味著「事實上」,那至少就<br />
分出了兩層:事實與非事實,「你說不懂我,隱含了你怪我的意思,這是非事實。<br />
事實上你不能怪我,我有努力要你懂。」。<br />
如果 A 上一句呈現的符號平台處於模糊的狀態,A 想要釐清那是什麼,則 S<br />
這句話並沒有回應在那個平台上。<br />
A:可我真的是不大懂你<br />
論說/強度。「真的」表達論說的強度。「可」意味著「即使」,「即使你有努<br />
1<br />
李維倫 2004 以置身所在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目標現象及其相關之方法論。刊於應用心理研究<br />
22:157-200。<br />
33
力,不過我還是不懂你。」A 的話語再次呈現了基底那個模糊的符號平台。<br />
S:你以為我是這樣了,可是又是那樣,是嗎?<br />
接引/共同完成,猜測對方話語所指的意涵,保持對話順暢。話語中「這樣」、<br />
「那樣」並無實質所指,僅表達一種差異,是不會犯錯的空洞指涉。<br />
A:是啊,我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真的要我。我覺得你在告訴我,你沒有我也可<br />
以很好,甚至更好。你今天下午說,其實愛,就是許多欲望吧。我覺得也有道理。<br />
論說/宣稱、理由、強度。<br />
開啟一組新談話,「唉」、「不懂」已經跟先前另一話題無關了,擴展到更全<br />
面、更底層的嘆息「我不懂你阿」。「到底」,意味著「究竟」、「從開始到末了」,<br />
具有強度。「真的」,也是表達強度。那個原本模糊不清的符號與符號平台慢慢露<br />
出一些具象的影子,在「你要不要我?」這個疑問中呈現。「你要不要我?」這<br />
個疑惑在心中已經累積一段時間,先前的互動中不斷暗暗試探,想要猜,看起來<br />
像有,可是又好像沒有,猜了很久,忍不住問了。這是把心上困惑很久,不敢碰<br />
的陰影浮上兩人互動的檯面。<br />
前半段翻譯就是「你說你是要(愛)我的,可是我覺得沒有。」顯然 S 曾經<br />
表態「要」,而 A 感受到的是 S「不要」,所以對矛盾的訊息感到困惑。想要知道<br />
S 真正的想法,以隱隱預設的答案「你大概就是不要(不愛、不夠愛)我吧」來<br />
試探。<br />
後半段「你今天下午說,其實愛,就是許多欲望吧。我覺得也有道理。」因<br />
為已經預設「對方可能不要」,所以 A 也開始有點撤退,先採取保護自己的姿態。<br />
「我覺得也有道理」,可能是「我對你也只是欲望吧。」<br />
弔詭的是,戀人已經表態過了,可是又好像不能完全相信對方所說,然而,<br />
還是要依賴語言跟對方確認。想要抵達對方的欲望,像一條無限趨近零但永遠達<br />
不到零的曲線,也像有名的數學悖論「我抵達不了目的地,如果永遠只走相距距<br />
離的二分之一。」這也是語言的極限,語言(能指)抵達不了所欲瞭解的他者(所<br />
指)。<br />
我拿我所知道的「你愛」或「你不愛」這兩者來套在你身上,要不「你愛」,<br />
要不「你不愛」,這些都是試探,而你是哪個?<br />
接下來想探討的就是主體與欲望的問題。在理論上,語言能指與所指中間的<br />
裂隙即是主體浮現之處。戀人是說話主體,說話主體是分裂的主體,擺盪在社會<br />
結構制約與無意識欲力的兩軸之間。幻想透過說話主體的符號動力而滲透入象徵<br />
界。<br />
S:要,又怎麼樣呢?我要的,你又不想給。<br />
論說/基礎(反)。不直接回答對方的疑惑,也無法直接回答(所指太複雜了,<br />
話語無法抵達)。解釋自己對要不要的看法。「我要你」,這個「要」是設限的,<br />
34
要的「你」也是設限的。假設「要的對象」是一塊大圓,(無法確定要的是什麼,<br />
是 A?是欲望的 A’?還是純粹只是欲望?)想要完整的大圓,可是得排除其中<br />
一塊「污穢」(你不給的東西)。<br />
翻譯「我要。可是要的不只是你,還包括一份完整的感情。你又不想給。」<br />
含有指控。這是戀人對彼此欲望進行協商談判,要區分[真實的 A]、[S 欲望的 A’]、<br />
[真實的 S]、[A 欲望的 S’]<br />
A:可能我也害怕吧。感覺你隨時可以放棄我、離開我。<br />
論說/理由(反)。基本上承認,但以反指控的方式回應對方。<br />
35
知識生產的地方情境:蘭嶼的例子 1<br />
戴惠莉<br />
摘要<br />
回應民族誌上關於蘭嶼人將知識視為「財產」的傾向,這些含括祖先起源、家<br />
族史、財產故事等概稱傳統知識、在民族誌上常以「知識」一詞所含括的口述故事,<br />
其傳遞所憑藉的動力及所欲達到的作用為何?在討論蘭嶼人如何使用及看待「知<br />
識」,要討論「知識」的屬性終究要回到當地人如何看待「財產」的概念。而財產對<br />
蘭嶼人而言,意謂著什麼?本文即藉由討論蘭嶼人對於財產的概念,關照蘭嶼人的「知<br />
識」生產。<br />
經由對養子與招婿、婚姻與喪禮以及家族與部落等討論當地人對財產的概念得<br />
知,蘭嶼人經而勞動生產知識,也透過知識傳遞財產與祖先及親屬關係的社會關係,<br />
而養子或招婿的作用乃透過生產關係,並以同居、共食等物質分享轉化成親屬關係的<br />
過程;而透過婚姻則是以財產交換及共同生產的形式使無血緣關係的(男女)雙方建<br />
立親屬關係,而喪禮的財產交換不僅實現互報原則,也是藉以界定彼此之間的社會關<br />
係。藉由討論這些家族、部落、zipos 的社會運作範疇其實是反映當地人的知識生產<br />
方式,必須以居住、共勞及共食等物質分享為條件。知識的屬性與承接對象依社會範<br />
疇運作著,兩者互相界定的關係除了彼此的親屬關係外,還有藉由勞動生產所建立的<br />
社會關係。<br />
關鍵字:蘭嶼,知識,生產條件,財產<br />
蘭嶼人的語言中並沒有與中文「知識」一詞同義的詞彙。過去研究者,有將<br />
世系故事(祖先起源)視為後代引以為榮的知識者(de Beauclair 1959a),有將<br />
稱父傳子母傳女的知識稱為「生活知識」者(夏曼‧藍波安 2003)或「文化知<br />
識」(劉欣怡 2004),有認為「故事」與歌謠便是知識傳遞形式者(黃郁茜<br />
2005:24),我的報導人對我以國語「知識」兩字詢問的反應是陌生的,他們常以<br />
「我們的文化…」來回應我的問題,而不同的報導人對知識有不一樣的解釋,包<br />
括泛指「有技術」、「有能力」、「有智慧」、「知道很多的人」等不同定義。雖然這<br />
些定義都是可以理解也被一般人接受的範圍內,但如 Crick 所言,人類學不僅是<br />
1 本文摘自個人碩士論文「知識的生產與傳遞界限:以蘭嶼為例」中第四章。謝謝指導教授趙綺<br />
芳在書寫過程中細心審閱及寬容、鼓勵的指導方式,以及口試委員蔣斌及郭佩宜兩位老師在口試<br />
過程中給予學生許多精闢及有趣的見解,使我得以修正論文不足之處,並感謝中研院惠予田野經<br />
費補助。我的碩士論文田野駐紮地點為蘭嶼野銀部落,但訪談對象則不在此限,田野進入日期分<br />
別為 2005 年 2 月 15 日到 3 月 5 日、3 月 22 日到 4 月 16 日及 2006 年 2 月 7 日到 17 日、8 月 13<br />
日到 25 日、11 月 13 日到 21 日。<br />
36
「他者(others)」的知識,它也是生產於互相定義的自我與他者的基本對話的知<br />
識,可知,人類學亦仰賴「自我知識(self-knowledge)」(Crick 1982:308),Crick<br />
更斷言人類學若缺乏反身性(reflexivity),則其知識生產方式也會造成許多文化<br />
被埋葬在人類學知識中(ibid.:302)。儘管如此,Crick 對 self-knowledge 並未下<br />
定義。Geertz 則提到,人類學家觀察不同部落社會的重點,不是在他們顯而易見<br />
的差異,而是他們在人類學產生的連結。要將不同部落社會的案例一起思考、翻<br />
譯,依某一觀點互相評論並連結各自差異,事實上是驅使我們思考缺席者的在場<br />
(the presence of the absent term)(Geertz 1996[1995]:47-8)。因此要討論蘭嶼人的<br />
「知識」,試圖從當地人的觀點看待事物(Geertz 2002[1983]),還是先須由「當<br />
地人」的脈絡中理解。<br />
蘭嶼男人往返海上漁獵、山上採集林木,女人於水田耕作,在尚未有水、電、<br />
公路的年代,清早起床趕緊吃飯後上山工作或海邊抓魚釣魚是每日行事<br />
(everyday work),至今這些每日行事仍是象徵「活著」、「像個人」的重要寫照。<br />
這些勞動聚集了人力及知識的再生產。蘭嶼人篤信語言具有靈性(陳慧敏 1978;<br />
郭舒梅 2000),過份的言詞會招來不滿(劉斌雄 1959;董瑪女 1995),勞動不<br />
需透過日常交談,而是透過行事表露出來。靠著曬魚杆上的漁獲,同村的人走過<br />
就知道你今日勞動的成果,而落成禮的財富展現更必須透過夫妻生產及勞動才能<br />
實現;展現在日常生活上的「言」與「行」,更是說的少、做得多才能贏得他人<br />
的敬重;而透過落成禮才得以吟唱的歌謠正是展現勞動的成果,歌詞則要自我抑<br />
制不能炫耀。所以,透過勞動及歌謠是下一代連結上一代的知識傳遞的方式,也<br />
是知識的再生產(reproduction)。<br />
在傳統上,蘭嶼人不同的月份有不同的「該作的事」(陳玉美 1994;夏曼‧<br />
藍波安 2003:87),傳統的文化知識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這些知識來自父母、<br />
老人家的調教以及勞動、祭儀中累積、學習、模仿而來的經驗,這些文化知識或<br />
經驗亦即民族誌上所說的「文化知識」(劉欣怡 2004)、「生活知識」(夏曼・藍<br />
波安 2003),也就是我於本論文中所要談論的「知識」,而知識是靠一代又一代<br />
講述、傳承下來。研究者(陳玉美 1994;夏曼•藍波安 2003;劉欣怡 2004;黃<br />
郁茜 2005)都指出蘭嶼的知識傳承,主要由父傳子、母傳女的方式襲得,在財<br />
物上,透過父系繼承的與造船、建屋有關的知識外,尚有家屋、宅地、田地、水<br />
田、黃金、銀帽等;透過母系繼承的則有薯芋的耕作知識、織布機、珠寶及家務<br />
等。而田野的報導人回答我所詢問「什麼是財產」時,多以 katatabilan do karawan<br />
或 amoamolo karawan 回答,katatabilan do karawan 是一代傳一代下來的意思,後<br />
者的 amoamolo 較有財物的意思,在當地人認知中,財產就是一代又一代傳下來<br />
的。蘭嶼人自小子從父、女從母依兩性分工,由漁獵、農作等勞動中學習的傳統<br />
文化、生活常識外,知識的很重要功能是用來使子嗣明瞭祖先傳下的財產,可以<br />
說,知識的傳遞與財產息息相關。<br />
如de Beauclair(1959a:106)所指出的,蘭嶼人將「故事」、「傳說」視為知<br />
識傳遞的一種,並有「財產」的傾向。而關於知識要如何傳遞,多位研究者(陳<br />
37
玉美 1994;劉欣怡 2004;董森永 2004;鄭漢文、王桂清 2004)均指出蘭嶼人<br />
主要學習管道為自生活經驗中學習、長輩傳授等方式,知識就像財產一樣,由父<br />
母傳給子女,但對於知識與財產的關係並未有進一步討論。 2 就蘭嶼人財產的研<br />
究,衛惠林與劉斌雄曾指出,雅美族的私有財產發達,衡量家族、個人的社會地<br />
位標準是財富。家屋落成禮及新船下水禮是用來聚讌、餽贈及展示財富的儀禮場<br />
合之外,喪禮也是展現財富的時刻。誇示財富是提高個人與家族地位的主要方<br />
法,年長而富有才是成為部落長老的條件(衛惠林、劉斌雄 1962:155)。de<br />
Beauclair亦認為蘭嶼人的個人地位由成就得來,而儀禮性的分配與交換為獲得個<br />
人地位的主要手段之一(de Beauclair 1959b:185-207),其他多位研究者多將蘭嶼<br />
人的財產交換,多聚焦於落成禮(鄭惠英等 1984),或是蘭嶼社會的交換特性(余<br />
光弘 1992;楊政賢 1998;黃郁茜 2005),以及討論交換關係所建立的權力機制<br />
及流動關係(郭舒梅 2000),而蔣斌(1986)提出「互報」作為繼承財產的原則,<br />
劉欣怡(2004)則繼而以互報原則討論蘭嶼人的照護界限。這些研究都告訴我們,<br />
財富的交換不但說明蘭嶼社會的特質,也維繫著社會制度及階序的運作;財富交<br />
換機制促使個人努力達成社會期望以便延續(家族)下一代的財富,也使得當地<br />
人在傳遞知識時,一直環繞著「財產」這個主題進行著。<br />
Crick 指出討論「知識」的人類學的書籍不多,相對地以認知(cognitive)、<br />
範疇、分類、宇宙性(universals)、意識型態、象徵等用來指稱「知識」的討論<br />
較為多(Crick 1982:287),而人類學透過田野工作多以「文化(cultures)」的概<br />
念作為記載人類生活的面貌(Geertz 1996[1995]),少數如 Barth 指出知識應包含<br />
三種面向。首先,傳統知識包含任何實質性的主張和世界樣貌的理想,其次,它<br />
作為一系列由名詞再現之部分或具體符號、姿勢(point gestures)、行動,必須能<br />
被一個或幾個媒體溝通的,第三,它將被分發、傳遞、賦予、轉發了一系列建制<br />
的社會關係。而這三個知識面向是互相連結的(Barth 2002:3)。對蘭嶼人而言,<br />
「知識」意謂著什麼?什麼使得「知識」發揮作用,又透過「知識」能再生產什<br />
麼樣的社會關係?就知識的社會功能及屬性而言,蘭嶼人對於知識傳遞有套社會<br />
秩序維繫著(鄭漢文 2005),亦有將知識視為有「財產」的傾向(de Beauclair<br />
1959a:106),因此在討論蘭嶼人如何使用及看待「知識」,要討論「知識」的屬<br />
性終究要回到當地人如何看待「財產」的概念。而財產對蘭嶼人而言,意謂著什<br />
麼?本章即要藉由討論蘭嶼人對於財產的概念,關照蘭嶼人的「知識」生產。<br />
一、財產的轉移與交換<br />
蘭嶼人分財產時,就是當父母親把舅舅或叔叔及小孩子叫來都坐在一起,此<br />
時,爸爸會說以後財產怎麼分,好讓大家都聽到、知道這回事,因為沒有聽到就<br />
不能算數。如果父親突然過世的話,母親因事前私下有聽父親講過而知道,因此<br />
母親成為宣佈財產分配的人。如果母親先於父親過世,財產尚不會分配,一旦父<br />
2 由「知識如何傳遞則」可以看出蘭嶼人如何將知識更具體化地視為「財產」,這部分討論則在<br />
我碩論的第五章。<br />
38
親過世而母親尚在,就由母親管理財產,不致於馬上分家;若母親也過世,約一<br />
個月後,小孩就開始分配財產。很多關於財產的爭議,一來是因為當事人沒有聽<br />
到財產如何分配而引起爭議,二來是因為父親很早過世,孩子成為孤兒,財產被<br />
親戚所奪。這些因素都會導致兄弟或親戚之間有財產紛爭,因財產分配不當或不<br />
均而導致兄弟成仇的事情在當地來說很常見。過去遇有這些糾紛,當地人會找長<br />
輩做協調,近來則常以協調委員會為協調此類爭議的機制。<br />
就財產分配而言,當地人常以孩子是否孝順、聽話,或女婿、女兒是否養他,<br />
來決定財產分配給那個孩子。沒有孩子的老人家會認養乾兒子(alamen),乾兒<br />
子養老人家才由他繼承財產,沒有生育男孩子的老人家會以招婿(manlam)的<br />
方式延續家族的財產。另一方面,喪葬及婚姻的關係也決定財產轉移或交換的強<br />
烈因素,葬團成員可以取得喪家的部分財產;再者,男女雙方的財產因婚姻而結<br />
合或交換也是財產的交換機制。<br />
財產是什麼?Syapan K(男)說,是土地、房子、黃金、太太,及「養別人」。<br />
為什麼是「養別人」而不是一定要有孩子才算富有。因為蘭嶼人認為沒有小孩的<br />
可以將勤勞的年輕人或兄妹的小孩做為養子(alamen,乾兒子),所以跟沒有小<br />
孩相較之下,沒有老婆才會被人看不起。沒有財產的人就是因為太懶惰的人而無<br />
法勞動生財,以致於沒有財產而娶不到老婆;反之,沒有老婆就沒有人幫忙去田<br />
裡挖地瓜、種芋頭,無法生產食物及累積財產;男女兩性結合成為夫妻,有配偶<br />
才能形成一個生產單位,因此配偶早逝的人通常都會再婚,有人找飯有人找菜,<br />
夫妻透過一次又一次地舉行祭儀,表示很勤勞,「別人追趕不上」,藉以完成圓滿<br />
的生命禮儀。<br />
下面透過我與 Syapan L 夫妻的對話,可以呈現蘭嶼人如何看待財產,包括<br />
黃金、芋頭、歌謠及家族的關係,在我與其他報導人的對話中,有的人說財產尚<br />
且說包括釣鬼頭刀、或織布技術、祖先的歌,不同的報導人之間有些出入,但大<br />
同小異,多半包括基本的家屋、黃金、瑪瑙、水田、銀帽、羊。<br />
我:你們認為的財產包括那些?<br />
Syapan L(女):黃金、瑪瑙、銀帽、水田的田地,然後如果很多羊隻,<br />
也包括羊。<br />
我:猪呢?<br />
Syapan L(女):猪是拿來餵的,沒有包括,只有羊。<br />
我:歌謠算嗎?<br />
Syapan L(女):歌,不算,只是如果你祖先很廣[按:報導人補述就是<br />
台語的「紅」]的話,他的歌比較有名,可是不算是財產,因為他的財<br />
產,他的財產是以他的財富而變歌的,因為他的歌很好很高,因為沒有<br />
人比得上他的財富,可是這個歌沒有包括[在財富中]。<br />
我:很高的歌怎麼會有人知道呢?不是不能給人家聽到嗎?<br />
Syapan L(女):可以聽啊!只是不要給,只有一家人或親戚知道,外<br />
39
面人不能聽到。<br />
我:那個歌為什麼會留下來?<br />
Syapan L(女):那個要留到,要一代一代傳下來啊!這個歌,妳的祖<br />
先的歌那個歌,是怎樣的,為什麼我們的祖先紅,是紅在什麼地方,我<br />
們蘭嶼人從祖先傳下來的話,如果你的祖先很有財富,比如說這一年有<br />
飢荒,我們野銀村就沒有得吃,我是比喻,如果我的祖先有很多芋頭的<br />
話,家裡比較窮的會向我的祖先說,我能不能向你買芋頭,然後我要換<br />
黃金,多少黃金給你,他就會差不多是這樣的(比出大拇指頭的一小節<br />
指甲)、會差不多是這樣的(比出大拇指頭的一小節指甲再多一點點),<br />
或是他們都這樣的,比如說你一家有七個人或八個人,那個黃金是這樣<br />
子或那樣子(比出比之前比得再多一點)<br />
我:是薄薄的那種黃金嗎?<br />
Syapan L(女):就是蘭嶼人的黃金啊!這個就是你的財富,因為人家<br />
向你以黃金買芋頭的話,因為人家沒有得吃啊,如果你有羊你自己沒有<br />
飯吃,就把羊給妳,人家向你買芋頭的話,[問說]有兩人份嗎?三人份<br />
嗎?這樣子飢荒的時候沒有得吃還有[可以]向人家買。<br />
(此時,Syapan L(女)的先生 Syapan L(男)插話進來)<br />
Syapan L(男):意思就像作生意的,做生意不是我有東西你有錢不是<br />
[嗎],錢給我、東西給妳,我會收很多財產,你有錢別人沒錢啊!你有<br />
工作[賺錢],我這裡有東西你有錢,我的東西永遠在這裡。<br />
Syapan L(男):一樣!<br />
Syapan L(女):怎麼會一樣?財產跟生意怎麼會一樣。如果你的祖先,<br />
比如說我這一年收一個項鍊的黃金,然後像明年還有繼續飢荒的話,我<br />
有時候兩個黃金,如果繼續三四五六年的話,我這一年不管是外村或我<br />
們村莊,我收到有三個兩個黃金,像明年有五個黃金,知道那個飢荒如<br />
果好的時候,有的吃了,他就不買了,可是那階段妳的收入有多少,比<br />
如她的祖先有一個,那個祖先有兩個黃金,那個祖先有十個,那個就是<br />
野銀的那個(比出大拇指),雖然你祖先只有收一個黃金也不代表你有<br />
財富啊!人家有兩個三個,這一年的收入就是飢荒時候的收入你有多少<br />
就是你的財產,你的祖先,最紅的就是他,那個就是我們這邊的財富,<br />
而是算你有多少黃金,然後你有多少地只有這兩個。<br />
我:黃金重要還是芋頭田重要?<br />
Syapan L(女):兩個都一樣重要,你有黃金你可以買東西吃,你有芋<br />
頭,你可以向人家買到黃金,可以換黃金。因為我們全鄉最注重的飲食<br />
就是芋頭,你有芋頭天天吃地瓜不算是你家裡富有,你有芋頭吃那你就<br />
很富有,那如果你有芋頭吃,常常吃芋頭那就很好,偶爾吃芋頭就算妳<br />
很多財富、很多芋頭。<br />
我:芋頭比較難種嗎?<br />
40
Syapan L(女):不是比較難種,啊你的芋頭有很多妳就常常吃啊!沒<br />
有多少你不會常常吃阿,你只有拜拜時候才會拿芋頭。<br />
我:常常吃地瓜不好嗎?<br />
Syapan L(女):常常吃地瓜也是算你的[財富],地瓜是有你的勞力,你<br />
有時候就種地瓜,那是可以不是不可以,可是飢荒的時候只有芋頭沒有<br />
地瓜呢。它[飢荒時]只有長芋頭啊!為什麼芋頭跟地瓜差的地方就在這<br />
裡,飢荒的時候有長芋頭,地瓜不會長果實。<br />
沒有羊的人會以金、銀、珠寶來換,增加了祖先繼承的財寶,使有羊的人成<br />
為富裕人家;而不管是羊、豬、或水田的芋頭都是為了在落成禮的祭儀上使用(周<br />
宗經 1996:221-2),好吃懶做的人,沒有足夠食物可吃,會把黃金、銀子、水田<br />
等財產變賣換食物吃,以致造成他們的貧窮,而勤勞節儉的人夠更富裕。而地瓜<br />
通常用來補充芋頭生產的不足,貧窮人家因此常吃地瓜(周宗經<br />
1994[1995]:73)。事實上,野銀的芋頭近兩年來「一直種失敗」, 3 芋頭的產量銳<br />
減,但即使這樣,所有的Kaminan仍然每日起早去山上清理雜草種芋頭。我與<br />
Kaminan去水(芋頭)田時,她抱怨芋頭一直種失敗。但一直失敗為何還是要來<br />
清雜草種芋頭?因為若沒來清理的話,田裡的雜草變得很多,「看起來就好像人<br />
死掉一樣」。那些荒蕪的田也暗示這個田的女主人很懶,女人之間暗自以草的長<br />
度、整理與否誰較勤快或懶惰。如周宗經所言,芋頭不僅是主食更是祭儀式的飲<br />
食(周宗經 1994[1995]:136-142)。儀式所需要的飲食是芋頭不是地瓜,芋頭能<br />
豐收才有能力舉行儀式,芋頭本身即表彰女性的勞動生產。芋頭因欠收,成為部<br />
落裡的人討論能否有足夠的芋頭舉行大船落成禮的因素之一; 4 欠收的芋頭田,<br />
也使得部落裡的人感嘆,今日的蘭嶼人不若以往重視「水田」的財產分配,因為<br />
有田也種不出芋頭來。<br />
芋頭之所以重要,因為「吃飯」很重要。當地人常問「妳在誰家吃飯」,報<br />
導人談到入贅時,常用的語言是「上去吃飯」,表示入贅的女婿要住到岳父家與<br />
岳父母及妻子共食,「要養岳父」才能與妻子共有岳父家的財產。芋頭是主食<br />
(kanen),在沒有貨幣的年代,有辛勤的勞動就不會餓死,在飢荒時,也可以以<br />
黃金交換芋頭, 5 黃金代表的是一個家族的財富及救命、解危用的靈器。Syapan L<br />
(女)堅持財產不像作生意。因為有勞動就會有財產,不像作生意的貨品可以以<br />
3 「一直種失敗」的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野銀比其他部落缺乏山泉水,有人認為是因為從<br />
不休耕導致土地沒有養分,有人認為是芋頭根部腐爛、生病了,但芋頭產量銳減不是單一部落,<br />
而是全島皆如此。<br />
4 野銀部落最後決定要在 2007 年作大船,同年也會舉行落成禮了。當初所考慮的芋頭產量問題,<br />
因為發現其他部落也以不足夠的蘭嶼芋頭及臺灣買回來的芋頭混雜在一起舉行落成禮,所以野銀<br />
部落也覺得這樣的變通方式是可行的,加上是部落的人一起建造大船,所有人分配芋頭份量,解<br />
決了各家芋頭產量不多的問題。<br />
5 若是拿黃金珠寶換芋頭會造成貧窮,這是很不好的事情。周宗經(1996:220)記載的歌謠經其<br />
釋義:「芋頭要長得好,因為萬一遇到荒年,哪有芋頭可吃,家的黃金與珠寶絕不可能賣調來換<br />
食物,(要不)豈不造成貧窮嗎?」<br />
41
金錢購得,再以金錢交換。在周宗經記載的幾首歌謠裡有載,連年的飢荒通常使<br />
得貧富差距加大,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有錢人的財產通常在飢荒時加速累積,<br />
經得起飢荒的財產才能一代傳一代。而歌謠中以常以女子指涉鐵器(鐵條或棍),<br />
是用來開拓水源的,決不能讓她嫁給外村的人,只能讓她嫁給有財富的人,如此<br />
才有代價(周宗經 1996:223-5),甚至祝賀荒年的到來,因為那使富者得到更多<br />
財產,而無能為力者便破財無飯吃,富者因此成為部落理有財勢的家族<br />
(ibid.:258)。財富是累世而來的,財富能與財富交換,而財富的轉移通常是要有<br />
相對的代價。而沒有勞動不會生產財物(芋頭、漁獲),有足夠的勞動經驗及能<br />
力才能創造出歌詠出釣魚、山林經驗的歌詞來,由祖先一代又一代地傳下來給子<br />
子孫孫聽,成為祖先的歌謠;而有財富的家族後代也常以祖先的名字命名,也可<br />
以將子孫的名字取得「很高」,因為家族具有財富,地位不一樣。<br />
而蘭嶼人除了透過勞動產生的財產外,透過婚姻不但使得自家財產不外流,<br />
也使得家族一分再分的財產,因透過婚配關係而再次聚集。此外,喪葬制度及養<br />
子、招婿的財產繼承,則是在血親關係之外的財產轉移,透過這些因互報原則而<br />
使財產進行交換的機制,也反映著蘭嶼人如何看待「財產」。<br />
二、養子與招婿<br />
祖先沒有多少財產留下來且父母早逝的人可以養其他老人家,叫做 alamen,<br />
老人家如果沒有生育孩子,可以由兄弟姊妹的孩子(姪子)來奉養他,也可以指<br />
定一個勤勞或很會抓魚的年輕人來養他;老人家過世後,若沒有兄弟姊妹的孩子<br />
來繼承他的財產,就會由年輕人來繼承老人家的財產;若是由姪子奉養他,則一<br />
定由姪子繼承其財產;總之,誰奉養老人,誰就繼承他的財產。萬一老人家不滿<br />
意養子的話,就給他一塊地後,再去找另一個年輕人。alamen 指的就是非親生<br />
子女的奉養,不管是認養的乾兒子、或是自己兄弟姊妹的孩子(姪子),都叫<br />
alamen。部落的人只要看到年輕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拿(抓)魚給老人吃,大家<br />
就知道他與老人家是 alamen 的關係。<br />
Syapan Y(野銀人)在二十七歲時,有個老人家因結婚後沒有小孩,看Syapan<br />
Y常常往山上跑、很勤勞,老人家知道他的父母早逝,於是要Syapan Y養他,Syapan<br />
Y一共養他二十九年,直到老人家八十七歲過世。老人家原本因為討厭他自己的<br />
親弟弟,就自己指定一個養子(乾兒子,即Syapan Y),沒想到後來有姪子出生,<br />
姪子慢慢長大到五六歲左右(確定能活下來了),老人家就開始對Syapan Y比較<br />
冷淡,另一方面,也因為Syapan Y沒聽老人的話,老人家因此Syapan Y有些不滿<br />
意,加上老人家的弟弟後來生了小孩,因此老人把他的財產一大部分給自己的姪<br />
子,而Syapan Y只分得一點芋頭田、一點黃金和一點點銀帽。村人強調是Syapan<br />
Y不聽話,加上老人家後來有了姪子,姪子的繼承權常是優先於沒有血親關係的<br />
養子,但因為Syapan Y養老人多年,老人家自然會將財產分給他,於是,Syapan<br />
Y的財產比他自己的親生哥哥多得多,因為Syapan Y有奉養老人的alamen關係 6 。<br />
6 我詢問 Syapan Y,老人家是否有將祖先的歌謠傳給他,他說老人的爸爸不好會打人,所以不喜<br />
42
而沒有生育男孩的家庭會以入贅的方式招婿,稱為manlam。magai mamlam<br />
指住進另外一個家,奉養這一家之意(劉欣怡 2004:89),報導人直接以國語「入<br />
贅」說明此類婚姻。兄弟多的男性娶沒有兄弟的女性是當地人稱為「招贅manlam」<br />
的婚姻關係,不管此男性是否貧窮,在當地人的主觀認知上,凡是兄弟多,財產<br />
分一分就沒了,因此入贅為必要的。而雙方結婚後,入贅的女婿會開始管理妻家<br />
的財產, 7 彼此的兄弟姊妹成為zipos,男方的兄弟可以保護女方的財產。而入贅<br />
的男性依然保有繼承原生家庭財產的權力,因此,他有自己繼承的財產。同樣地,<br />
妻子若沒有兄弟則繼承其父親的財產,當男女雙方結為夫妻後,是夫妻共享女方<br />
家及雙方的財產,而非女婿,因女方父親傳下來的財產仍是由女方繼承,並非由<br />
入贅的女婿繼承。 8 女婿如果很孝順的話,岳父會分一塊地給他。但在當地人的<br />
認知裡,岳父的財產仍屬於女兒(妻方)所繼承,只是因為夫妻結合起來的財產,<br />
將來依然由其生育的孩子繼承,故這些由各自家庭繼承而來的財產,經過婚姻結<br />
合成為一個新的家庭時,就成為彼此共享的財產。<br />
我自初入田野即認識Syapan Lu(女),曾多次聽 她提過,原本該由她與唯一<br />
的親生姊姊平分繼承父母親遺留的財產,但因為姊姊與姊夫佔去了她的土地,雙<br />
方遂有財產糾紛,但從未聽她說過她們姊妹有贅婚。一直到我問她是否為入贅婚<br />
時,她說:「不算,因為我先生是獨子」。但她的姊夫因為不是獨子,就算是入贅。<br />
而村人所講述的重點也是因為她先生是獨子,所以她不算是入贅婚,<br />
力分配,如何分配非旁人及孩子能置<br />
9 而非以「她<br />
是否招婿」作為敘述的觀點。報導人主觀上認為,獨子需繼承父母的財產,也因<br />
是一人繼承沒有分家的顧慮,故不可能是入贅於女方,而當地人重視的是財產的<br />
繼承與保全,入贅則是用以保全父母遺留下來的財產的一種方式,跟是否需要男<br />
性繼承沒有絕對關係,而是家中一定要有人繼承父母的財產。沒有男孩的家庭,<br />
若有女孩,則以招婿的方式,保全父母留下的財產,雖財產為夫妻雙方共有,但<br />
夫與妻各自繼承的財產仍分得很清楚。<br />
父親、母親各有各的財產並各自有權<br />
喙,這類的繼嗣法則是當地人所強調的,如 Syapan L(女)所說的:<br />
我 有兩個姊姊,我爸爸叫她[們]不要嫁給外村的,因為我[爸爸]沒兒子,<br />
妳(姊姊)先生入贅,[妳先生]不要[入贅]就算了,是你的意思,不是我<br />
的意思,二姐又是這樣,結果她的先生不要[入贅]。我結婚就是[年紀]<br />
歡他們留下的歌。而村人私下議論的是 Syapan Y 侵佔了老人家要傳給姪子的地,大家都知道,<br />
因為關於那些土地的歌謠如此傳唱。Syapan Y 對於老人是否教他歌謠則說,他自己會做詞,所<br />
以不希罕老人家的歌詞。一般來說,如果養子很聽話又孝順,老人家就會將這類歌詞傳授給他。<br />
7 如加入女方之水源整修、小米田等工作(周宗經 2004:146)。<br />
8 關於入贅,劉欣怡認為,形式上父母親的財產全由女兒繼承,然而男性的財產仍屬於男性使用,<br />
實質是從妻居的女婿在繼承岳父的財產(劉欣怡 2004:89)。但野銀的報導人強調的是女方繼承<br />
其父親的財產,女婿頂多只能算是管理財產而已,並不算是由女婿繼承或享有;因為這些繼承的<br />
財產日後仍由其婚後所生的孩子繼承,所以女方繼承自父母的財產,但婚後財產是夫妻共享的。<br />
9 入贅的男子是否從妻性而改姓呢?報導人說紅頭的會改姓,而野銀的則沒有改姓的習慣。部落<br />
的人對於是否需要改姓,顯得很不在意,大都以「看個人啦」回答。我認為這可能也跟蘭嶼人有<br />
自己傳統的命名方式,所以改不改姓並非他們意識裡的重要事情。<br />
43
最小[的女孩],要不然是誰在養我爸爸,結果我爸爸財產就留給我,他<br />
們不要,該死,權力是我爸爸的,不是你的,財產的權力是父親啊,媽<br />
媽沒辦法講啊,媽媽的是媽媽的財產,她要給誰就給誰。<br />
Syp an L(女)則是家中有三女,但兩個姊姊都嫁給外村,因為 沒有聽父親<br />
的 話嫁給本村的人,也沒有照顧父親,所以財產都由 Sypan L(女)繼承。Sypan<br />
L(女)與媽媽好友的兒子自幼婚配,也因為 Sypan L(男)家有三子,其中兩<br />
個兄弟均為入贅,因此,Sypan L(女)繼承父親所留下的傳統屋,而 Sypan L<br />
(男)也繼承父親要留給他與三弟共有的的主屋,他們很清楚地敘述各自有各自<br />
的財產,但婚後夫妻成為一體,這些財產都會留給他們的小孩,到了小孩那一代<br />
則又回復父親的財產留給兒子,母親的財產留給女兒,父傳子、母傳女,如此類<br />
推。<br />
入贅的男性有沒有地位呢?我得到截然不同的兩種答案,我發現跟我詢問的<br />
對象是 否為入贅婚有關。非入贅婚的報導人會說,在蘭嶼,入贅地位「很低很低」,<br />
一輩子要聽老婆的話。但是,入贅婚的報導人則以大拇指表示,在蘭嶼入贅是最<br />
有地位的,因為男方有自己的財產加上老婆的財產,是「好嘢人」。入贅婚的關<br />
係中,若是夫妻日後吵架時,女方常會說「沒有我,你的財產哪裡來」,而報導<br />
人也說「若是他孝順他岳父,那麼我尊敬他,大家尊敬他,他就很有地位了。」<br />
這兩種說法都呼應了蘭嶼人對社會地位的看法,雖然地位的高低取決於財產的多<br />
寡,但受人尊敬也能抬高其社會地位,而入贅婚的女婿與親生兒子的孝順與否,<br />
標準並無二致,聽話、孝順與奉養都使後代享有繼承財產的權力。以男子入贅的<br />
形式進而保全父母親遺留下來的財產,是入贅婚的主要原因,而不是以需要男性<br />
延續家族命脈為理由,因為女孩子一樣可以延續家族命脈。<br />
當地人對於招婿及養子能否繼承財產,強調的是「要看他孝不孝順啊!」、「聽<br />
不聽話」來決定。財產的傳與不傳除了親屬關係之外,以「互 報」決定繼承仍是<br />
親屬及非親屬關係的主要因素。家屋的繼承除了互報的關係決定外,父母也會考<br />
慮使每個小孩都有房子或地可以繼承。但有些父母為沒能力蓋房子的孩子著想,<br />
因為在傳統上,蓋房子與婚姻的關係是緊密結合的,男子結婚後蓋房子才算完成<br />
人生的階段任務 10 (cf. 陳玉美 1995),因此,房子將要留給哪一個孩子,除了<br />
互報機制外,有些父母親會考量到孩子的個別經濟狀況。<br />
Syapan A(男,八十歲)的房子會給兩個沒有結婚 的兒子,因為沒有用<br />
也結不了婚,沒有本事蓋房子。不給 X[Syapan A 的四子]是因為他已經<br />
佔了一塊[地]了啊,反正以後財產還不是會流向 X 嘛!因為哥哥[Syapan<br />
A 的二子]沒有小孩,就會由他繼承。但老大的兒子長大了搞不好 Syapan<br />
10 我曾認為當地人財產繼承的觀念中,似乎隱含著「自動調適」的功能,沒有能力沒有房子(特<br />
別是連水泥屋都沒有)的小孩會使父母將房子優先保留給他,這點跟後面要討論的婚姻關係中,<br />
男女雙方以財產(有形物產及無形的人力產)的交換為動機似有相近之處,但仍待進一步討論。<br />
44
A 會分給他的孫子,如果分了之後[哥哥]才結婚有小孩,就算他[哥哥]<br />
的了。(Syapan Lu)<br />
這段 話意在說明即使 X 的 哥哥繼承了父親的傳統屋,但因為他沒有結婚生<br />
子 ,若死後,遺留的財產仍會由他的兄弟 X 繼承,仍然為由同手足繼承,除非<br />
他將來會結婚生子,或者是父親將財產留給孫子(過世大哥的兒子)。這種情形<br />
雖然常有,但並不是必然的慣例。<br />
蔣斌研究野銀的家屋繼承與轉移,指出沒有子嗣的老人家常以兄弟之子(即<br />
姪子)為養子,導致宅地在「世系群 」間轉移的現象,或是因男嗣要奉養父母而<br />
造成父子兄弟集居的現象,即因「父系直系」及「父系旁系」繼承而造成的宅地<br />
轉移(蔣斌 1986:108);無子嗣的人則可以以養子或喪葬團體共管,他人如欲使<br />
用,需要向他們提供補償(ibid.:103),但這類子女夭折或年老無嗣者所遺留的宅<br />
地,也常被視為不祥地(ibid.:96),而任其凋零成為空屋、荒地。蔣斌認為,以<br />
「贅婿為養子」的情形,造成「岳婿繼承」,及宅地在世系間的轉移,實乃依互<br />
報關係的實現,而非衛惠林所說的「父系群宅地」觀念所致(ibid.:108)。他認為<br />
會造成這種誤解,「固然類似世系群的雛形,但在主觀上所依循的規則乃是『奉<br />
養』與『繼嗣』的權利義務互報關係」(ibid.:108-111),事實上,如同蔣斌說的,<br />
繼承財產關係乃是主觀上所依循的規則,是「奉養」與「繼嗣」的權利義務互報<br />
關係,而非世系群的雛形,但我認為會造成這種印象,也是因為未將養子 alamen<br />
及招婿 manlam 分開來看的關係,而將 manlam 與 alamen 兩者認為具有類似的意<br />
涵(即「奉養」),也足以證明當地人最重視的仍是「奉養」的履行。<br />
蔣斌(1986:93)對養子及招婿皆以 manlam 一詞表示,但野銀的報導人多以<br />
manlam 表示入贅,以 alamen 表示養子,雖也有一、兩位報導人說這兩 個詞意思<br />
「差不多」,manlam 與 alamen 都是指非親生關係的養育,alamen 指被養育者,<br />
即養子,manlam 指養育、養別人,前者為名詞,後者為動詞。但對村人而言,<br />
這兩個詞彙仍有使用對象的區別。manlam 與 alamen 讓人覺得意思差不多,也是<br />
因為村人如果看到年輕人常常送魚給老人家吃,就認為他們是 alamen 的關係,<br />
然而不管是照顧岳父的贅婿或養子(或姪子)都一樣要常送魚給老人家吃,因此,<br />
實際的「奉養(照顧)」關係高於任何親屬關係,加上一般人常以姪子為 alamen<br />
為優先選擇,只有與兄弟不合、兄弟無子或是不喜歡姪子的人才會另外指定年輕<br />
人作為養子,因此以姪子作為 alamen(養子)不僅符合家族財產不外流的顧慮,<br />
也有奉養的實質效果。<br />
我幾次聽過不同報導人說,哪戶老人家的姪子常送魚給他吃,老人家就跟姪<br />
子說,你不要來了,要不 然人家以為我沒有兒子。蘭嶼話 macya mo do kanganegy<br />
是指,父母的財產要由孩子繼承。以此看來,財產的繼承是有排他性(劉欣怡<br />
2004:86)。但非血親關係的贅婿或養子仍可繼承財產。劉欣怡認為蘭嶼人設計一<br />
種填充機制,使無嗣者正當地引入非親生子嗣,但其底層意義仍來自照護與繼承<br />
的互惠(ibid.:94),劉欣怡所謂的「照護與繼承的互惠」就是蔣斌所說的「奉養<br />
45
與繼嗣的互報」。蘭嶼話 maka kabob so kanensospa 意指,不要忽略你有自己的孩<br />
子,則表示照護父母的責任需限制在親人之間,外人若隨意介入則是詛咒孩子死<br />
亡(ibid.:121)。沒有子嗣的老人會由兄弟或兄弟之子(姪子)送葬,若是沒有其<br />
他兄弟,財產也會由姊妹繼承,或者就是老人會指定養子,由養子送葬也由養子<br />
繼承財產,但若有姪子又有養子的話,財產通常不會全由姪子或養子單一個繼<br />
承,除非養子不孝順,才會全由姪子繼承。<br />
養子與贅婿為蘭嶼非親屬關係繼承的主要對象,其繼承原則就是透過奉養的<br />
互報。老人家透過養子或招婿,可以有人協助取得食物(尤其是魚類),而奉養<br />
者也因此繼承老人家的財產。蘭嶼人以「贅婿為養子」的現象說明了,蘭嶼人觀<br />
念上對奉養的重視,奉養長輩且又孝順聽話的養子或贅婿也可以贏得部落裡他人<br />
的尊重及社會地位。這類由非血親關係的繼承是當地人財產轉移的重要機制,也<br />
不會違背當地人所說的 maka kabob so kanensospa,相反地,若是還有孩子的老<br />
人卻被外人奉養,也會嚴重損害老人的面子(社會地位)。<br />
三、婚姻與喪葬<br />
夫妻兩方結合一體時,雙方的兄弟姊妹成為 zipos,姻親被稱為 icyarwa,是<br />
ikararwa(另一個)的意思,親家則是 micarowa so vahey,是指本家的另一個家<br />
(謝永泉 2004:5),由字義上可見親家之間的密切關係。傳統的蘭嶼婚禮並沒有<br />
盛大的結婚儀式,親家以瑪瑙或黃金贈與未過門的媳婦,或是加上殺豬,然後媳<br />
婦開始至先生家幫忙勞動,提水、餵豬、種芋頭等等勞動,等到男女(夫妻)雙<br />
方均能接受(若有一方後來婉拒了這項婚姻,就會退回聘禮)、或是女方懷孕了,<br />
部落的人自然就會知道他們結婚了,因此男女雙方直到生了孩子才能進一步確立<br />
婚姻關係。重視婚姻是因為重視子嗣的繼承,有了孩子繼承家族財產,才不致於<br />
讓家族的財產外流(董森永 2004)。重視婚配對象的經濟條件也可以由蘭嶼人對<br />
孩子的命名看出。父母為孩子找一個富有家庭的婚配對象,並且期許生育眾多孩<br />
子、受人敬重(董森永 2003)。婚姻是蘭嶼人進一步發展社會位階的關鍵,親家<br />
成了擴展的親屬關係及互相結盟的對象。也因為本家與親家的密切關係,因此當<br />
地人在擇偶上經常以財產為考慮的條件之一,甚至是主要條件。<br />
Sypan Lu(女):Syapan Ci(男)有五個兄弟,一個兄弟 [老四]也是入<br />
贅,因為家裡兄弟多,[財產]分一分就沒有了。兄弟多的人就會找兄弟<br />
少的人結婚。<br />
我:為什麼財產那麼重要?<br />
Sypan Lu(女):因為沒有財產不像個人阿!<br />
我:[蘭嶼話]怎麼說?<br />
Sypan Lu(女):不像一個人叫 pakananaken,不像一個人 、沒有財產的<br />
意思。amowamolon 財產 的意思,我爸爸的地繼承給我,我爸爸的地交<br />
給我,繼承來的東西都叫 amowamolon。<br />
46
我:如果不是繼承的,是自己賺來的呢?<br />
Sypan Lu(女):我們蘭嶼哪有自己賺來的,我們都是繼承的。我們[的<br />
財產]又不是錢了,我們以前都是繼承財產。<br />
為什 u(女)時,她馬上接著<br />
,因為沒有財產不是人啊!沒有財產會被稱為不是人 pakananaken,不像一個<br />
,<br />
嶼人強調結婚對象的門當戶對, 11 麼結婚要那麼重視財產?當我這樣問 Syapan L<br />
說<br />
人 pakananaken 也泛指沒有錢、沒有土地、窮人,另位報導人曾比出「小(尾)<br />
指」指稱這個字彙。財產很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以致於沒有財產不足以像個<br />
人。在尚未有貨幣進入的年代,有女人耕種水田、餵養豬隻等財產等於有主食吃,<br />
有男人才可以出海抓魚補充副食,主食、副食都有了才是完整的一餐。所以夫妻<br />
的結合往往先考慮到男女雙方的「財產」;其次,是親家是否有足夠的人口可以<br />
保護財產。<br />
Sypan L(女)說「財富跟財富結婚,窮人跟窮人結婚,普通生活跟普通生<br />
活結婚。」蘭<br />
如紅頭部落的周宗經也指出,早<br />
期雅美族社會非常注重婚配對象的條件,所以產生三等級的家族(有德望的貴<br />
族、中庸家族及卑微家族),內婚制通常是富有且有名望的家族所舉行,外婚制<br />
尋找對象較自由,但以同一階級的家族為主。夫妻之間的身份是很重要的,因此<br />
只有同等身份的男女,才可以結成夫妻、成立家庭;不同身份的夫妻組成家庭,<br />
則常常爭吵不休(夏本奇伯愛雅 2004:141-152)。但若是窮人如果兄弟多就會入<br />
贅女方家裡,多位報導人如Sypan Lu(女)即常說,「嫁給兄弟多的最有福氣,<br />
要不然沒有親家保護你。」夫妻如生育很多男嗣,財產要分配給眾男嗣,而導致<br />
平均下來每個男嗣所能分配的財產不多,所以家裡男嗣眾多的男孩子會入贅沒有<br />
男嗣的女方家,岳父會對女婿說:「你娶我女兒就要養我一輩子」,這樣一來,男<br />
方因女方所繼承的財產而增加他們共同的財產,而女方則增加人力可以保護自己<br />
財產。<br />
因為以前女生沒有哥哥弟弟的話,財產通通給你[按:指別人]搶走,所<br />
以爸爸還沒死以前,可以嫁給很多親戚的人,爸爸死了之後,女孩子的<br />
財產他們就不會[被]搶,因為親家公那邊的人會講說不要去拿她的財<br />
產,我們要保護她的財產,讓外面的人不拿,雖然[他]家裡很窮,妳嫁<br />
給他不是窮的問題,而是因為妳自己本人有財富嘛,他窮沒關係,老婆<br />
有財富的話就還可以,只要老婆這邊的地[財富]保管起來就好了,不要<br />
讓人家去偷拿你的財產的話,兩夫妻就不會怎樣。(Sypan L(女))<br />
11 周宗經認為,蘭嶼人採取同一家族世系內的通婚制的,稱為 olinzipoziposan。婚姻乃是關係著<br />
個人、家族與社會的連結,以前擇偶的不自由,因為族人有強烈的階級觀念,不同家族有其功能、<br />
勢力與理念,因此早期擇偶多傾向家族內成員。周宗經也認為,蘭嶼人婚姻有內外婚制,內婚制<br />
通常是由富貴有名望的家族所盛行,不讓自己家族成員的繁衍、素質及優美形象、道德價值等等,<br />
任意被他人破壞,而外婚制選擇對象較自由,但尋找配偶的範圍僅在中庸家族 todapiyatao,其他<br />
則排除在婚姻之外,除非有其他個人因素(周宗經 2004:142-144)。<br />
47
當地 人常談論嫁娶對象的財產關係,Syapn Lu(女)即對我說,這裡的父母<br />
若是家裡有男孩子,則父母親不會幫女兒介紹男朋友,因為女兒是嫁出去的,祖<br />
先不會延續;家裡沒有男孩子的,才會幫女兒介紹男孩子。父母為女兒介紹男孩<br />
子,因為要有男孩子「嫁進來」,與女兒結婚而延續家族的命脈及財產。<br />
大致說來,父親早逝的話,母親一般都會改嫁,父親的財產仍由小孩繼承,<br />
母親的則會帶著瑪瑙改嫁。母親改嫁後,繼父的財產則由繼父與母親的生的 孩子<br />
繼 承 ,除非新生的孩子不孝順,才會由同母異父的孩子繼承,財產一定要等父母<br />
死後才會分。<br />
數,有沒有足夠的親家可以幫忙守住財產,是很重要的因<br />
。<br />
是財產分配。劉斌雄以野銀的情<br />
12 父母親與小孩之間的財產繼承關係,乃是繼承自「親生」的父母,<br />
否則,就以誰「奉養」他、就由誰繼承。反之,若是母親早逝,父親再娶,依循<br />
的也是一樣的標準。不管如何,有多少小孩就要找多少食物,孩子多並不是很好<br />
的事情,但另一方面,孩子多,也是一種無形的資產,因為表示將來能一起從事<br />
勞動的人口增加了。<br />
因此在婚姻關係中,男女雙方考量的是對方的財產或是人力,財產若是不<br />
足,就會考慮親家的人<br />
素 13 而因夫妻雙方而結合的親家,則會互相參與對方的社會儀式,其中又以喪<br />
團禮儀與財產分配有密切關係。由喪葬的財產繼承與交換,可以得知,「互報」<br />
主宰喪團成員的組成,另一方面,親家是否為同一祖先(asa so itetngehan)的因<br />
素,也會決定其能否參加喪葬團體,乃因為不同家族的親家不會與喪家有直接的<br />
財產繼承紛爭,故成為喪團的成員,而往往同一家族(又不可能是asa so inawan)<br />
的成員原則無此顧慮,因此也是喪團的成員。<br />
蘭嶼的喪禮參與的成員有父系成員(malama)、親戚(zipos)及姻親<br />
(icyarwa)。死者埋喪後,經過一些儀式,最後<br />
況為例說明,因為喪家必須對參加者贈與金、珠寶或水田等珠寶財物,故有限制<br />
的必要。因此,同樣是抬喪的人也會因是否與喪家有親屬關係,及喪家是否因付<br />
不起要分送的財物而要求抬喪者不再參加葬團(劉斌雄 1959:167-169)。婚姻的<br />
考量相當於對財產的支配與安排,傳統上由父母決定婚配對象的不在少數 14 ,另<br />
一方面,也由於送喪團多由親戚組成,而喪團成員會取得喪家的財產,因此,父<br />
母親在安排子女婚姻時,也會考慮到彼此雙方是否有asa so itetngehan的關係,因<br />
為這樣的婚姻能將家族財產再度結合,而親家(zipos)若為喪團成員,則財產<br />
會再度結合,甚至形成同一家族中財產的再度交換,而不致外流。但現代婚姻的<br />
結合幾乎都趨向自由戀愛,因此,若是參加送喪卻無法取得財產以致形成糾紛,<br />
或是因顧慮財產會外流而限制由誰來送喪的情形則一直都有。<br />
12 2006 年 11 月 18 日,Syapan Lu(女),田野訪談。<br />
13 這現象持續至今日的選舉中依然可以可見,往往親家與親家合作配票,村人議論到選舉現象<br />
總是認為選舉都是靠親戚,而選舉候選人若有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也會被認為勝選的<br />
機會比較多,因為親戚多。<br />
14 如周宗經(2004:143)也提到,早期族人擇偶,一來由祖父母選定嬰兒作為本家成員之偶,二<br />
是父母在家族內選對象,所以年輕人都要聽從家族長輩的安排,很少是自己選擇的對象。<br />
48
Sypan Lu(女):有的是不會貪心也不會拿[你的財產]。因為我沒兄弟,<br />
我跟我姊姊只有兩個,我爸爸死掉沒有男的可以送葬啊!我爸爸那時老<br />
了有病了,每次我爸爸都會就交代我說快要死了,趁我現在還活著,帶<br />
我去墓場那裡,你的財產才不會有人拿走,我爸爸都會交代我不要人家<br />
給我送葬,要不然親戚會把財產拿去。[按:Sypan Lu(女)為紅頭人,<br />
嫁至野銀。]<br />
我:可是你爸爸還是要人家抬去墓地阿?<br />
Sypan Lu(女 ):那時候他的堂哥是 C(女)的爸爸,D(女)的爸爸,<br />
還有紅頭的堂弟。他說紅頭的堂弟,不要讓 他們來看我。他生病的時候<br />
不要他們來看我,但野銀的堂弟[按指:D(女)的爸爸]可以來看我,C<br />
(女)的爸爸[也]可以來看我<br />
我:因為他們比較不貪心?<br />
Sypan Lu(女):不是。因為他 們住在野銀,不會要[紅頭的]地啦!我的<br />
芋頭阿!在紅頭會講阿,只有 C(女)和 D(女)[的爸爸]能來看我,<br />
不貪心的人可以來看我沒有關係。…像我爸爸死掉,他爸爸[按指:Sypan<br />
Lu 的公公]也送葬,我姊夫的爸爸也送葬,啊我親家[按指:姊夫的爸爸]<br />
有參加送葬,向我媽媽拿地,他[按指:姊夫的爸爸]爸爸沒有拿,他不<br />
要啊!差那麼多~我媽媽說,如果他[按指:姊夫]要的話,我野銀的親<br />
家也要[給],這樣才公平,她拿一塊給他爸爸。我姊夫的爸爸還拿一塊<br />
地,我一直想繼承的不是他的兒子嗎?為什麼他還要拿一塊地。<br />
喪團 的成員,因為要獲得財寶或水田,以便保護喪團成員的靈魂,去除晦 氣,<br />
若 沒有分得財物,則不敢入家門,因此當地人嚴守這項送喪者必須取得喪家財產<br />
的法則。謝永泉認為,一般人一定會參加親家的喪禮,但親兄弟不見得參加,因<br />
為兄弟間可能因sawalan(水源)、ahakawan(田地)等因素反目成仇,然而親家<br />
則沒有所謂的水源、田地之爭,因此在參葬隊伍中,親家是經常出席的成員(謝<br />
永泉 2004:5)。劉斌雄認為是否參加喪團取決於喪家是否有能力致贈送喪者珠<br />
寶,但喪家若沒有財寶可分,也可能要求抬喪者退出 15 (劉斌雄 1959:169),互<br />
報關係主宰喪團成員的組成。兄弟因為是asa so inawan的關係,往往最容易因為<br />
分產造成嫌隙,或是反目成仇,也就不會出席互相之間的喪禮,但親家若是同一<br />
世系家族(asa so itetngehan)的成員,則因為非同一祖先(malama,父系)不致<br />
於有密切的財產之分,若為不同家族的親家更因為沒有這些紛爭,反而是葬團的<br />
既定成員。Sypan Lu(女)的父親所顧慮的,就是他不願意同村的親戚送喪,而<br />
願意讓外村的親戚送喪,因為外村的親戚不可能會要別村的土地, 16 據報導人<br />
15 另外一個可能則為,抬喪者因為自己的家人不願意他參加而要求他退出喪團,如劉斌雄所舉<br />
的例子(劉斌雄 1959:169)。<br />
16 這是屬於不同村落之間的層次,衛惠林劉斌雄指出,若有家族遷往他村,則他們必須放棄一<br />
切土地財產權力(衛惠林、劉斌 雄 1962:50)。<br />
49
說,最實際的原因是,「不可能每天去外村的田裡工作吧!」。<br />
藉由男女雙方(親家)是否為同一家族的成員,可以進一步看出同一家族間<br />
財產繼承的交換關係,而雙方若為不同家族也可以看出財產轉移的競爭關係。而<br />
同一父系家族中的財產關係,以喪禮為例,可以發現當地人所謂第三代以後(asa<br />
so itetngehan)的通婚關係是最好的(陳玉美 1994),因為這時候有點親戚關係,<br />
但不是很親,比較不會有財產紛爭,如果雙方通婚的話,就是「又讓我們的財產<br />
聚集在一起」。以喪禮為例,不同家族的成員是否加入喪團,也是以喪家能否有<br />
能力送給喪團成員珠寶,能否「互報」為決定彼此關係的根基。<br />
因此,婚姻及喪葬為蘭嶼人達成財產交換的重要機制。以婚 姻作為財產交<br />
換 , 其重要性在於,藉著婚姻,交換的對象是個人,但又是家族財產的延續,甚<br />
至透過 asa so itetngehan 的婚配,可以將家族分散出去的財產再度聚集;而透過<br />
喪葬,交換的單位則是家族,因為親戚 zipos(因婚姻而成親家的關係)參與喪<br />
葬,喪禮過後的財產仍會轉移給親戚,若是親戚為 asa so itetngehan 的親家,則<br />
形成家族財產再次交換,若不是的話,也會因為雙方(喪家與送喪者)是 asa so<br />
inawan 親屬關係而形成不同家族的財產交換;當然,若送喪成員非為血親或親<br />
戚,則財產等同於轉移給外人(非親屬),所以,當地人才會顧慮送喪者的身份,<br />
重點就是不要使得財產外流。<br />
四、家族與部落<br />
在我詢問報導人關於財產的資料時,家族與部落的關係總是隱隱約約地浮<br />
現。財產猶如芋頭、黃金、水田、豬羊等,財產是指katatabilan do karawan,一<br />
代一代地傳下來人世間的,才叫「財產」。儘管就現代來說,黃金與瑪瑙都是可<br />
以由臺灣買入,<br />
」,<br />
不會。<br />
17 但當地人普遍認為,買的不算,只有繼承的才算是財產。<br />
傳承下來的象徵財產,如Sypan L(女)所說的:「以他的財富而變歌的<br />
董瑪女所收錄的一首歌即唱出擁有財富的家族會流傳於後代, 18 家族的財富以歌<br />
謠作為管道傳承下來,有財富的家族地位也較高;富有的家族可以取很高的名<br />
字、結婚要門當戶對,但一般認為平權社會如蘭嶼,乃靠後天努力獲致地位(de<br />
Beauclair 1959b:185-207),一個人透過日常生活的種種競爭可獲致卓越的交換能<br />
力,而成為一個完滿的Tao(黃郁茜 2005),似乎後天努力得來的財產相當地肯<br />
定個人的社會地位。但報導人的話裡仍時常出現,像是婚姻要富有家族與富有家<br />
族的結合,而且村人的閒聊之中、以及有意無意在言談中,暗示對無父孤兒的輕<br />
蔑,似乎後天努力而獲致的地位並不足以肯定個人一切。當我問及不同報導人,<br />
若是父母早逝,而他很努力工作得到財富,會不會變得有地位?報導人均答以:<br />
17 有年輕人為了慶祝父母親壽誕,會由台灣買了象徵性的黃金為了使父母高興。<br />
18 這首歌意譯為:雖然我不是很有名望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有關於 Si Rayoyo 和 Si Gazimot<br />
這兩位名人很多事。以前,本島飢荒的時候,很多人都把自家代代相傳的寶物拿出來跟他門換取<br />
食物,使得他們更加富有了(董瑪女 1995:166)。<br />
50
我:那像蘭嶼人覺得有地位的人要有什麼?<br />
Sypan L(女):黃金、財產,也包括很會抓魚的話,也包括在內。<br />
我:沒有財產,但很努力開田拜拜作船會不會變得有地位?<br />
Sypan L(女):沒有,算是窮人。<br />
我:窮人不能翻身?<br />
Sypan L(女):但只要人有努力不會餓死就沒關係,因為我們是 看祖先,<br />
要祖先留下來的。<br />
「財 產」這一概念,對蘭嶼人而言,不僅代表一個人的努力程度,更是他依<br />
襲的先天 地位,社會與財產需 成相輔相成的搭配。如蔣斌曾提過,某戶無子嗣的<br />
老 人家依然居住四門房,蓋因其為部落首富,論地位不可能住小房子(蔣斌<br />
1986:87)。又如從擁有的水源也可看出一二。越是被分配在水源末端的擁有者,<br />
表示其主人越貧窮,因為越靠近水源、出水越大、維修方便,而那些末端、甚至<br />
是自己開挖的水源,乃是沒有父母的庇蔭,導致必須自己挖掘水源,越是彎彎曲<br />
曲、出水口又在偏遠山區的水源,也暗示這人沒有長壽或富有的父母親。 19 先天<br />
的財產繼承自父母及家族,甚至是象徵式的天賦地位,例如報導人所敘述的,以<br />
前的野銀,每個家族有固定的擺放拼版舟的位置,墓地裡不同家族也有不同的位<br />
置,家族與家族之間有清楚的界線。但關於家族的資料,現今五、六十歲左右的<br />
中年人多已不能清楚描繪,如Syapan L(女)所說的,「越來越沒用。常會因為<br />
財產吵架,因為aso so inawan是同一個水源,妳接我這裡,又彎去哪裡。」同一<br />
家族的關係是最親的,但也是最容易因財產引起糾紛的,引述黃郁茜碩論中一段<br />
民族誌資料:<br />
以前是家族、親戚交往最密切,朋友則次之;現在是朋友第一個,親戚<br />
擺在後面 。朋友沒有「利」,可是親戚有利。有時候你注意到有的地方<br />
的田地分的好小很小,這個就是家族在分土地。水源也是,水源是我們<br />
的祖先,我們父母親開的,當我們有孫子的時候,就開始搶這個水了,<br />
你的水比較多,就開始糾紛了。可是朋友不會跟你要水啊,因為水是引<br />
到你們這個家族,朋友利益關係,親戚就有差了(引自 黃郁茜<br />
2005:52)。<br />
因為 財產的再分配總是涉及利益,越是親戚關係越是容易有糾紛,以致於後<br />
來「家族 」這個範疇已 經逐漸弱化,在實際生活的互動上,重要性已經讓位給朋<br />
友 (黃郁茜 2005:52)。然而各部落間一直存在的競爭意識,也反映出蘭嶼人以<br />
「聚落」作為完整生活及行動單位(ibid.:27),尤其在政治行為與共作關係上,<br />
部落是較明確的單位(蔣斌 1986:111)。郭舒梅研究朗島的權力機制指出,達悟<br />
19 周宗經(1996:253-4)指出會開闢水道引水灌溉芋田的原因有三:(一)家族男人多,分得芋<br />
田極少,不足維生,(二)他人輕視我們,沒有財產就沒得吃,(三)田園面積小,不足耕種。<br />
51
族的村莊基本上是獨立而半開放的,除了小船飛魚祭的領袖基本上是繼承的, 20<br />
承接自祖先的來源與神話的傳說,以及並非經常性行動團體的「家族」概念,而<br />
只對本村(朗島)有影響力之外,人莫不極力藉由其他的禮儀擴展其他村跟隨/<br />
被跟隨的關係,因此達悟無論村內村外均保持競爭交換的關係,而這些設計也凸<br />
顯出部落間在意識及實際層面上的分野,以及各自獨立的特質(郭舒梅<br />
2000:70-1)。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界限分明,也表現在落成禮歌會進行時,外村人<br />
只能在一旁觀禮而不能歌詠一事(呂鈺秀 2004),個人成就透過落成禮得邀請其<br />
他部落的親戚、朋友參與,將聲望傳達到其他部落。另一方面,蘭嶼人偏好在不<br />
同部落都有姻親關係(張慧端 2004:113),報導人Syapan Po即說:「當年我的二<br />
姐要結婚時,我爸爸挑選的對象是很會抓飛魚的東清人。」能抓飛魚且居在不同<br />
部落的姻親對象對當地人而言非常重要,透過姻親對象連結到不同部落的財產交<br />
換,由此,也可見當地人對財富擴展的重視。<br />
在過去,部落與部落之間會引起糾紛的原因,幾乎就是與部落界線有關,侵<br />
入隔壁部落的漁場是最大的因素(衛惠林、劉斌雄 1962:158),一旦發生糾紛,<br />
部落內的由雙方親戚或被敬重的老人出面協調,不同部落之間的話,則由另外其<br />
他部落的人協調,協調的重點是避免更大傷亡,即使是真的械鬥,也以不出人命<br />
為最大原則,避免被「以牙還牙」。蘭嶼人對於犯罪的代價,通常是以報復或賠<br />
償兩種方式解決(ibid.:159)。賠償與刑罰的觀念常是混淆不清的。金箔、琉璃珠、<br />
水田都可以作為賠償罪責,豬則是賠償儀式中的祭品。唯在和解成立以前,被害<br />
者之近親,尤其是直系親屬必定要先發動復仇,其時兇手之家屋常被焚燬<br />
(ibid.:160)。通姦、鬥毆、侵佔他人財產都會引發糾紛,但與其說蘭嶼人對賠償<br />
與刑罰分不清楚,不如說是因為「財產」本身被賦予帶有咒術的性質,財產本身<br />
即能造成刑罰的作用。 21 我多次聽當地人講述財產之爭時,一再強調詛咒的靈<br />
力,這種不需要特地學習就能靈驗的咒術,最常用來因被侵佔財產而發下咒語,<br />
誰先死誰就是說謊的人,Syapan L(女)形容為:「財產有種詛咒,不能拿別人<br />
的財產。」而沒有小孩的人最最令人害怕,因為他們沒有孩子不用怕詛咒,像這<br />
樣的人,一般人都不敢得罪。所以沒有孩子的老人雖然後繼無人,但沒有孩子也<br />
意味著,他不用因為擔心財產受損沒能留給後代繼承、就任由他人欺凌。 22 「年<br />
長而富有」才是成為部落長老的條件(衛惠林、劉斌雄 1962:155),夠年長的老<br />
人才能享有被子嗣(包括養子、贅婿)奉養的過程,也才能將財產(及知識)傳<br />
20 野銀的報導人 Syapan L(女)也表示,過去主持飛魚祭有固定的家族,但現在已經沒有了。<br />
也 由於家族與部落的民 族誌 資料有限,所以這一節談論的是當地人對財產的概念。<br />
21<br />
財產本身賦予的咒術 可以 保護,而墓地的沙子及、貝灰及被吐怨氣的石頭更是令人害怕的詛<br />
咒物,所以過去部落間發生戰爭時,有時候甚至只是互相丟石頭而已,如此可以不用 傷害到人命<br />
又可以象徵性地抒發怨氣達到喝阻作用。如鄭漢文、王桂清(2004)指出,蘭嶼人有將貝灰用來<br />
驅除惡靈的作法,通常是放在芋頭田、豬圈、墳場及無端遭受破壞的田野。當與人發生爭執時,<br />
挾怨報復時,會將貝灰灑在芋田,詛咒芋田的芋頭毀滅,甚至以 mopivalvalion、mokamed 等話<br />
詛咒仇家粉身碎骨的意思。<br />
22<br />
時空變化,現今的蘭嶼人有見血及財產的紛爭時,多以法院為解決途徑,以水田或黃金作為<br />
賠償物反而不是現代人想要的 。<br />
52
承給下一代;而財產以一種隱含著詛咒的制約,規訓著族人不可盜竊他人財物、<br />
以合乎禮義的法度維繫社會秩序,反之,沒有孩子的人就不受制於此,因此,一<br />
般人都不敢得罪他們。因此,年長及財富才能有社會地位、備受尊重,兩者缺一<br />
不可 23 。<br />
不同的部落間互相競爭是常態,昔時常因有人出言挑釁或是跨越村際界限及<br />
侵佔財產而引起的部落戰爭現今已不再;但部落間的競爭在平時被刻意地突顯出<br />
來,亦即部落間隱性的比較、競爭仍一直存在。每個部落都強調自己是強悍的、<br />
特別的以及團結的,部落戰爭不再,除了因為時空環境已經改變的因素外,更明<br />
顯可以從現今家族的弱化與部落間持續不變的競爭意識呈現反差。今年(2006)<br />
的鄉長及鄉代選舉完畢,野銀的報導人說:「那個紅頭的丟臉死了,推出四個卻<br />
選不上一個」;當野銀部落裡討論要不要作大船時,原本反對的老人家聽到中壯<br />
輩的以可以邀請東清的老人協助作船(擔任船主及舵手)來解決作大船的爭議<br />
時,老人家一聽不得了,「激不得」,因而就答應作大船。現今部落之間的關係漸<br />
漸以競爭取代戰爭,而 zipos 的實質功能取代被弱化的家族,在飛魚祭的儀式過<br />
程中也可以窺見。<br />
陳玉美指出從飛魚祭開始到結束,透過儀式、聚落空間,與主屋空間的男:<br />
女對立的象徵,其實是在敘述集體(聚落)與個人(家、夫妻)的對立關係。從<br />
飛魚祭開始到結束, 主屋內相關儀式及事物在空間的移動,每一階段都牽涉到由<br />
個人〉集體〉個人的轉化。個別性的強調,乃至進一步取代集體性,實與當地人<br />
強調競爭的精神相符;而在儀式過程中所顯現出家重於聚落的現象,好似以女性<br />
為表徵的家—夫妻單位(miyaven do vahay)的價值,始終是當地社會的基礎,<br />
且夫妻單位、核心家庭(asa ka vahay)為蘭嶼社會組織與結構最基本單位(陳<br />
玉美 1999:146-154)。儘管時代不一樣,但持續至今的蘭嶼人觀念中,仍強調要<br />
辛勤工作、造舟、開田、舉辦落成禮,但這些工作都需要夫妻雙方相輔相成才有<br />
能力舉行祭儀,沒有妻子的男人及沒有丈夫的女人都是不被社會認同的對象。工<br />
作與人的成長、社會身份、社會地位密不可分,彼此互相界定。而這些努力需要<br />
透過祭儀被展示出來,而除了家傳的寶物外,落成禮更是累積個人的社會資本<br />
(social capital)。人的聲望與地位,並非繼承而來,而是在成長過程中,透過個<br />
人(夫妻)的努力,累積個人(夫妻、家)的財富(家畜、田地)(ibid.:131-2)。<br />
在蘭嶼人形形色色的財產中,父/母系或世系傳承下來的財產,如自然財<br />
物、土地財產及家屋、衣服、禮器、財產標記(船外壁刻畫、伐木標記、山羊剪<br />
耳)、祖先歌謠等;而靠後天努力獲致的如芋頭、漁獲等食物,舉辦祭儀的次數、<br />
造 舟 、建家屋的能力等,蘭嶼人藉著各式財產的轉移及交換將先天繼承/後天努<br />
力的財產,成為一種由夫妻、zipos 往外擴散至其他部落的親屬團體的交換機制,<br />
如小船與家屋的落成禮是 zipos 舉行的落成禮,大船是 zipos 及世系等船組各家<br />
戶集體的儀式,而小米祭則是完成大部分落成禮後,舉行一種最高的交換形式(郭<br />
舒梅 2000),這些儀式交換財產對象可對應到衛惠林、劉斌雄所言的,財產的所<br />
23 承蒙蔣斌老師在口試時,提出這個觀點,在此再次謝謝蔣斌老師。<br />
53
有對象分為村落、父系世系群、家族與男女個人性別分別所有等四級單位(衛惠<br />
林、劉斌雄 1962:127-131)。就現代的蘭嶼而言,部落不再有戰爭、部落財產也<br />
就不再有因戰爭紛爭而引起的損失,而家族的弱化及 zipos 以實質功能取而代之<br />
也彰顯夫妻是蘭嶼社會財產交換的主要單位(余光弘 1992;陳玉美 1994;黃郁<br />
茜 2005)。因此,以部落與家族兩個範疇的財產性質而言,蘭嶼人雖重視的是先<br />
天財富優越的天賦條件,但後天的努力所得到的成就及權力才是決定社會地位的<br />
關鍵,如夏曼.藍波安亦指出,蘭嶼人雖承認每個人先天資賦條件不同,但大致<br />
上認為只要願意做就會有人協助(夏曼.藍波安 2003:87),又如很會抓鬼頭刀<br />
及很會作船的男人仍更是享有美譽,因此後天努力的重要性仍優於先天繼承的條<br />
件;儘管先天繼承的良好條件則凸顯出其家族的不同地位,但這類先天地位仍要<br />
靠後天努力舉行的祭儀所伴隨而來的交換、歌謠、建屋、造舟等等財產才得以維<br />
繫不墜、方可保留。<br />
另一方面,從罪罰的賠償物則可以看出先天繼承與後天努力的財產性質差<br />
異。如同 Earle(1994)所指出的—部落社會常見的儀式性禮物一般可分為兩種,<br />
一是食物(staple finance),一是財物(wealth finance),即非實用性但有價值的<br />
物品(引自 張慧端 2004:103)。賠償物為金箔、琉璃珠、水田等,而豬則是賠<br />
償儀式中的祭品;如前者是家傳寶物,後者是生財工具也是生活財產;前者是可<br />
以代代相傳,後者則是生命有限的。豬羊是儀式性的重要牲禮,也用來換取水田、<br />
黃金、珠寶等財物,及用來換命、消災解厄(夏本奇伯愛雅 2004:125),賠償物<br />
是可以轉移及交換財產的家族寶物,而祭品如豬羊(主要是豬)是用來交換的物;<br />
豬可以換來財物,但若拿財物換取豬、羊等家畜則會導致家族越來越貧窮。雖家<br />
傳寶物才有語言靈力所賦有的詛咒性,但卻需倚賴上一代傳承下來無法增生,而<br />
豬羊及芋頭飛魚卻是能因後天努力不停不斷增加的財產。最後,由家族與部落的<br />
關係,也可看出現今越來越不明顯的部落與越趨明顯的家族,所各別呈現的兩極<br />
化傾向。<br />
五、小結<br />
經由對養子與招婿、婚姻與喪禮以及家族與部落的討論來看蘭嶼人對財產的<br />
看法得知,在蘭嶼,由父/母傳給子/女的家傳財產要一直傳遞下去,靠的是夫<br />
妻二人成一 單位勞動不已,得以舉行祭儀、吟詠歌謠,將工作所得的芋頭、豬與<br />
他人分享, 也 將勞動經驗以歌謠記載下來傳頌後代,這些都是後天努力要獲致社<br />
會地位的目標 。因此,若沒有子嗣的老人家會以養子或招贅的方式引入非親生關<br />
係的 男子,養子或贅婿都可以經由奉養老人家的過程,轉化為「親屬」關係,如<br />
此一來,老人家也會將財產或關於家族的故事、生活文化等知識傳承給養子或贅<br />
婿,當地人強調養子或贅婿如果聽老人的話、養他,就可以繼承財產,其實是在<br />
親屬關係的範圍內進行財產轉移。蘭嶼人為了保全 asa ka vahay 的財產得以延<br />
續,在挑選婚配對象時要找的是財產或有能力的人;有財產的人可以藉著婚喪再<br />
一次交換財產,有能力的人則可以勞動換取及累積財產;而沒有兒子的老人以招<br />
54
婿的方式,引入非親生關係的贅婿與老人家的女兒結婚,為的就是要完成一個以<br />
夫妻二人為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才能在社會上晉級,而並非為了延續父系的命<br />
脈。因此,當地人對財產的看法,除了以奉養與繼嗣的互報機制作為延續家族財<br />
產之外,也顯露出對於追求「年長且富有」的價值認同,夠年長才能享有被奉養<br />
的過程,夠富有才能擴大交換範圍及能力,一步步晉級社會位階,成為一個完整<br />
的人。<br />
馬克斯主義者認為,人類透過勞動不僅意識到人的本質,也通過勞動中獲得<br />
知識(Ritzer 1989[1995])。60 年代末興起的結構馬克斯主義則認為,決定社會<br />
文化發展的因素存在於社會關係的結構或生產的政治組織之中,是生產方式決定<br />
社會關係結構,而不是被英國人類學稱為「社會結構」的社會關係。 24 結構馬克<br />
斯主義者認為實質性的社會分析概念是馬克斯主義的生產方式理論,它可以用來<br />
分析不同社會的組織方式,因而才是超越「土著觀念(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br />
的概念。Godlier(1977)則認為過去的部落社會因各有其不同的生存環境要適應,<br />
因此社會生活的再生產乃依活動需求(activities necessary)所產生,因此透過經<br />
濟生產而產生新的「社會關係」。而親屬關係的功能是作為生產關係,以及關係<br />
的支配。Godelier就針對部落社會的親屬與生產關係,認為親屬關係或宗教觀念<br />
成為生產的部分力量,也幾乎可以說,在決定社會生活的一特定範圍裡,是整體<br />
的技術經濟(total technoeconomic)情況藉著它所強加的限制,扮演支配的角色<br />
(Godlier 1978:762-71)。在蘭嶼,不管是養子或是贅婿,並非為了彌補父系繼承<br />
的空缺,而是為了勞動生產的關係能夠延續,養子或贅婿也以勞動關係與老人家<br />
形成新的社會關係,而這些都是為了要延續家族的「象徵」命脈—財產。<br />
就親屬關係而言,新的親屬研究趨勢著重從「過程」及行為實踐的過程理解<br />
「親屬」現象,如Carsten(1995,1997)提出,由”sharing of substance”、同住等<br />
實際的行為過程,建立了「親屬」關係,但基本上此關係是不固定(not fixity)<br />
而具有流動性質的,如婚姻是一種納入(incorporation)的過程,透過婚姻的過<br />
程將姻親慢慢轉化為血親。婚姻儀式開始此一過程,到了孩子出生後,這項 轉化<br />
過程 也隨之完成;透過孩子將父母親雙方的substance結合與混合,也象徵彼此的<br />
「異」已轉化為「同」了。因此,親屬身份基本上是具有流動的性質。而Feingberg<br />
(1981)在討論玻里尼西亞人的「親屬」關係時亦提出,由繼嗣與行為(指共享<br />
sharing,包括共享食物、土地、服務)同時是決定一個人「親屬」地位的運作法<br />
則(working principles)(引自 林曜同 2000:140-1)。由蘭嶼人透過養子及招婿<br />
的方式,藉由食物分享、共同居住等substance分享及行為實踐,將非血親關係轉<br />
化成為親屬關係,養子抓魚給老人家吃、贅婿照顧老人家並一同居住,不僅是履<br />
行奉養的勞動行為,也在這過程中轉化彼此的關係,因此,養子與贅婿繼承財產<br />
的身份仍是在親屬範圍內進行。 25 而養子及贅婿、甚至姻親都是zipos,具有承接<br />
24<br />
英國人類學家稱為「社會結構」的社會關係,如 lineage 與 clan 等社會的表層組織,它們在結<br />
構馬克斯主義看來是社會組織的「土著模式」,而非實質性的概念(王銘銘 2000:174)。<br />
25<br />
林曜同(2000)亦認為要解決蘭嶼人的親屬爭議,養子是一個重要線索,可惜林曜同並無進<br />
一步田野資料佐證。<br />
55
知識的身份,而居住、食物(共享或餵養)乃達成知識生產的條件,這些實際行<br />
為界定了彼此之間的「親屬」關係,也在這過程中將知識傳承下去。<br />
蘭嶼人經而勞動生產知識,也透過實際行為的履行轉化社會關係。養子或招<br />
婿的作用乃透過生產關係及食物、居住的分享行為成為親屬關係,藉以將無嗣者<br />
空缺的親屬關係填上位置;另一方面,透過婚姻則是以財產交換及共同生產的形<br />
式使無血緣關係的(男女)雙方建立社會關係,而喪禮的財產交換不僅實現互報<br />
原 則 ,也是藉以界定彼此之間的社會關係。養子、招婿或締結婚姻的對象原本都<br />
是非血親關係的他人,但透過當地社會認同的勞動價值,並藉由生產將社會關係<br />
更加連結後,其「親屬關係」甚至超過原生家庭的血緣關係。以結構馬克斯主義<br />
詮釋蘭嶼人知識生產的地方情境,可以看出,當地人以生產建立社會關係,也連<br />
結甚至產生新的親屬關係,而連結後所生產的財產,將再被新產生的親屬關係所<br />
支配,形成新的社會關係。這種透過夫妻努力所獲致的後天成就,也顯示蘭嶼人<br />
最重要的視夫妻為一單位的社會基本單位。在現今的部落不再有昔時的戰爭所導<br />
致的財物損失,儘管競爭仍在日常生活中實有所見,但就重視財富交換能力的蘭<br />
嶼人而言,家族不僅凌駕部落的重要性,也表現在蘭嶼人雖以部落為一獨立生活<br />
單位,但家族財產的延續才是當地人最重視的。由本文的討論可見蘭嶼人不僅重<br />
視財產,在討論財產時脫離不了個人、夫妻、家族、部落等範疇的運作,藉由這<br />
些運作過程,彼此界定關係,並將知識傳承給被認同的對象(下一代)。可以說,<br />
知識對蘭嶼人而言,其生產條件需在同居、共食之下才能轉化原本非血親的他人<br />
成為非血親關係的「親屬」,這樣的情境也使得當地人一方面視知識為財產的一<br />
種,也使知識在親屬關係傳遞的過程中,彼此界定互相的關係,進而再生產知識。<br />
56
參考書目<br />
王銘銘<br />
2000 社會人類學。台北:五南。<br />
余光弘<br />
1992 田野資料的運用與解釋──再論雅美族之父系世系群。中央研究院臺<br />
灣史田野研究通訊 24:48-75。<br />
呂鈺秀<br />
2004 達悟歌會中音樂行為探討。發表於「2004 蘭嶼研究群研討會」,中<br />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蘭嶼研究群主辦,東臺灣研究會協會,12<br />
月 20 日,台北:中研院。<br />
周宗經(夏本奇伯愛雅)<br />
1994[1995] 雅美族的社會與風俗。台北:臺原出版社。<br />
1996 雅美族的古謠與文化。台北:常民文化。<br />
2004 蘭嶼素人書。台北:遠流。<br />
林曜同<br />
2000 "Sharing of Substance"、過程與反省民族誌思潮--論蘭嶼雅美人「親屬」<br />
研究的一些新趨勢。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6 (12):130-157。<br />
夏曼‧藍波安<br />
2003 原初豐腴的島嶼:達悟民族的海洋知識與文化。新竹:清華大學人類<br />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郭舒梅<br />
2000 流動的權力—以朗島村為例探討達悟族權力機制的形成與延續。新<br />
竹: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陳玉美<br />
1994 論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從當地人的一組概念 Nisoswan(水<br />
渠水源)與 Ikauipong do soso(喝同母奶)談起。中研院歷史語言所<br />
集刊 65(4):1029-1052。<br />
1995 文化接觸與物質文化的變遷:以蘭嶼雅美族為例。歷史語言研究所<br />
集刊 67(1):133-166。<br />
1999 時間、工作與兩性意象:蘭嶼 Tao 的時間觀。黃應貴編,時間、歷史<br />
與記憶,頁 27-156。臺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br />
陳慧端<br />
2004 傳統社會領袖的構成:船組、財富與親屬的作用。考古人類學刊<br />
61:77-120。<br />
黃宣衛<br />
2005 語言、社會生活與田野工作:評介 Maurice Bloch 有關認知人類學的<br />
57
黃郁茜<br />
一些觀點。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62:122-135。<br />
2003 「交換」與「個人主義」:蘭嶼野銀聚落的例子。台北:臺灣大學人<br />
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楊政賢<br />
1998 蘭嶼東清部落「黃昏市場」現象之探討~貨幣、市場與社會文化<br />
變遷。花蓮: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董瑪女<br />
1995 芋頭的禮讚。台北:稻香。<br />
董森永<br />
2004 蘭嶼達悟族的傳統婚姻禮俗。發表於「2004 蘭嶼研究群研討會」,中<br />
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蘭嶼研究群主辦,東臺灣研究會協會,12<br />
月 20 日。台北:中研院。<br />
劉欣怡<br />
2004 達悟(雅美)族的老人照護關係與社會界線之建構:護理人類學的民<br />
族誌研究。花蓮:慈濟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劉斌雄<br />
1959 蘭嶼雅美族喪葬的一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143-183。<br />
蔣斌<br />
1986 蘭嶼雅美族家屋宅地的成長、遷徙與繼承。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br />
所集刊 58:83-117。<br />
衛惠林、劉斌雄<br />
1962 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甲種之一。<br />
鄭惠英、董瑪女、吳玲玲<br />
1984 野銀村的工作房落成禮。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58:119-151。<br />
鄭漢文<br />
2004 蘭嶼雅美大船文化的盤繞-大船文化的社會現象探究。國立東華大<br />
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謝永泉<br />
2004 達悟的傳統死亡觀初探。發表於「2003 蘭嶼研究群研討會」,中央研<br />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蘭嶼研究群主辦,東臺灣研究會協會,12 月 20<br />
日。台北:中研院。<br />
Barth, Fredrik<br />
2002 An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43,<br />
Number 1, February. Pp.1-18. 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br />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br />
De Beauclair, Inez<br />
1959a Display of Wealth, Gift Exchange and Food Distribution on Botel<br />
58
Tobago.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8:185-210。<br />
1959b Three Genealogical Stories from Botel Tobago: A Contribution to the<br />
Folklore of the Yami.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105-138。<br />
Crick, Malcolm R.<br />
1982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Ann. Rev. Anthropol 11:287-313.<br />
Geertz, Clifford<br />
2002[1983] 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台北:麥田。<br />
1996[1995] After the fa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r />
Godelier, Maurice<br />
1978 Infrastructures, Societies, and Histor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9, No.<br />
4, December. Krader,Lawrence. Pp. 763-771. The Wenner-Gren<br />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br />
Ritzer, George<br />
1989[1995] 社會學理論,馬康莊等譯。台北:巨流。<br />
59
依附之始至終:從同情到不歸路<br />
林憶珊<br />
Tom Regan 主張動物權利觀點,有別於《動物解放》的作者 Peter Singer 的<br />
效益路線,但二人口徑卻一致地抗拒女性的情感路線。Tom Regan(1983)<br />
提到:「所有關心動物利益的人都…熟悉像『非理性』、『濫情』、『情感<br />
豐富』或者其他更糟的指控。我們要證明這樣的指控是假的,只能藉由共同<br />
的努力,不要再放縱我們的情緒或炫耀我們的感情,而那樣作需要持續投入<br />
理性的研究」。(Donovan 2003:132)<br />
男性學者怕動物權運動和女性化情感牽扯在一起,會導致動物權運動遭到貶<br />
值。由此可知倫理學一直由象徵男性精神理性所主導,其另一個重要的面向「關<br />
懷」也在男性文化的扭曲下,被詮釋為貶值、盲目意味的愛欲。近來漸漸出現將<br />
性別結構納進動物權的思考當中,從女性的關懷倫理來看,事實上是必須的。女<br />
性的情感一直是重要的價值,與男性主導的理性研究文獻相較,女性動物權理論<br />
家的理論發展基礎,比較建立在和動物之間的情感上,所以出自女性的照顧和關<br />
心之愛的互動式的文化之中,產生女性主義式的動物倫理(Donovan 2003:137)。<br />
我們看到當代男性動物權運動者依循理性的辯論,試圖抺除女性的存在和情感面<br />
的重要關切,如此界定也無異反映父權體制的論述。以生態女性主義來看,我們<br />
必須打破二分法的優劣思維,加以肯定女性的情感價值 1 。從動物權論述來看,<br />
理性總是被揚舉在感性之上,不過,在台灣流浪動物的環境與國情脈絡,我將情<br />
感當成推翻理性的辯證。我發現狗媽媽的情感價值被視為「他者」將以貶值,根<br />
本是不正當的。她們的女性情感與利他能力,反倒促成一幕幕的照顧圖像,因此<br />
我將她們的救狗模式稱之為照顧圖像卻不是動物權運動,藉此釐清不同的路線。<br />
往昔我傾向著重分析外部性的社會處境與支持,但總覺得研究內容缺少重要<br />
的靈性,好似光有空殼沒有靈魂支撐。後來我才慢慢了解,歸根究底我根本沒有<br />
注意人狗之間的密實情感,難怪難以理解她們堅強有力,始終如一的照顧立場。<br />
倘若我以理性為主將研究變成與情感無關,情感貧乏的描述根本無法適切描繪女<br />
性照護者──台灣狗媽媽的動物倫理。尤其在研究期間,她們與流浪動物的愛欲<br />
與情感,提供相當豐富的田野資料和重要線索,她們不是徒有感情而沒有行動<br />
力,相反地情感因子促成一幕幕始終無悔的照顧圖像,本章將介紹狗媽媽照顧流<br />
浪動物的實踐邏輯與種種情事。<br />
1 父權思維反映理性為男性特質,感性多情為女性特質。理性需要非理性的存在,男性氣質等同<br />
理性,女性氣質等同不理性,女性無法作理性思考,男性有客觀性及純理性,女人無法超越其位<br />
置。這正好代表理性需要將感性視為「他者」,以便合法化其自身的表現。從生態女性主義來看,<br />
我們應當頌揚女性的陰性文化,女性的直覺、同情心與關愛倫理,重視網狀人與自然關係需要被<br />
肯定,並認為性別的差異,給予男女不同的權力憑藉(葉為欣 1998:12)。<br />
60
一、從給一口飯開始<br />
幾乎在我們察覺差異的那一瞬間,我們就想要確定權力,道德或經濟價值,<br />
以及美感偏好的價值,不管是不同的動物,文化或膚色,我們都要這樣做。<br />
(Gray 1981:19;引自 Fox 2005:135)<br />
無論是生態女性主義學者葛雷(Gray)的相對評價,或是辛格(Singer)所<br />
談的物種歧視 2 ,皆是源於階層式的優劣等級差異。社會對她們救狗的質疑論調<br />
之一為「有錢有閒怎麼不救孤兒,救什麼狗」、「人都救不完了,還救狗。」 3 我<br />
想會講這種話的人恐怕連「人」也沒救過?這種相較價值都是立基於「人類中心<br />
主義」的框架。在社會上有許多可以展現關懷的對象,有其它付出愛的方法,為<br />
何她們要投注精力在照顧動物身上呢?找出她們的動機並不難,黃黃說出她們的<br />
共同理由:「流浪犬生活在台灣真的很可憐,人類可以自行覓食或開口說話要食<br />
物,但牠們卻只能仰賴人類給食物。人類有人在救就好了,我看牠們卻都沒人要<br />
救,因此我想我來救好了。」<br />
我們並不是愛動物,我們所要的只是希望人類把動物視為獨立於人之外<br />
的有性生命看待,而不是將牠們當做人類的工具或手段。(Singer<br />
1996:18)<br />
我一直覺得狗媽媽與 Singer 的立場,並不是二條不能交會的平行線,狗媽<br />
媽不一定喜歡狗才救狗,有些媽媽甚至拒絶本質化的說詞,她們告訴我「也不是<br />
說多愛,只是覺得牠們真的很可憐才餵牠們。」愛狗理由並不能解釋一個現象,<br />
在台灣,許多將狗當寵物疼愛的愛狗人士,甚至很厭惡流浪犬。我很訝異發現狗<br />
媽媽不一定開始都愛狗,例如黑白從小家境不好,窮困到連狗肉都吃,阿丹以前<br />
看到狗還痛恨地驅趕牠們,小花花向我坦誠以前不喜歡狗,連碰牠們都不敢碰,<br />
金局過往曾遺棄一隻狗,內心因為很愧疚才開始救狗彌補罪過。<br />
她們對狗前後態度的丕變,很高的比例源於開始照顧孩子帶回家的狗。從來<br />
沒養過狗的沙皮與毛毛,她們坦言沒養過狗只養過貓,當初因為同情才開始餵<br />
養。為何觸發她們同情心?每一個的成長過程與背景都不同,背後都有一些成<br />
因,生命經驗是最大的因素。一位狗媽媽告訴我,她的父母都是在救流浪狗,因<br />
此自幼深受影響,她長大有能力後也開始投身照顧工作,她救助的規模甚至超越<br />
父母,後來因為救一隻狗認識她老公,夫婦二人一起從事餵食與收容。黑白憶起<br />
她過往的成長際遇,救狗因緣就是在於感同身受牠們的飢餓模樣。<br />
2<br />
物種歧視和過去的性別和種族歧視一樣,三種偏見擁有相同的結構。物種歧視—這個新詞是種<br />
偏見、一種偏頗態度,偏袒人類成員的利益,壓制其它物種的行為(Singer 1996:45)。<br />
3<br />
我自己就常遭到別人的質疑,我若告訴別人台灣的街頭有很多棄犬,別人會回我棄嬰更多,甚<br />
至棄婦也很多,怎都不來關心。<br />
61
這好像是命,是不是我前生欠這些狗。現在想想會走這條路的原因,跟<br />
我小時家裏的環境有關,我若走過一個地方,看到狗在翻垃圾,我手上<br />
有東西一定要餵牠。因為我從小很窮,米都去賒帳,生活過得很苦。過<br />
年過節都有人來討債,我爸都去躲起來,所以我知道那種沒有東西吃的<br />
可憐。小時這樣子,結婚後也如此,老公的工作不穩定,最可憐的一次,<br />
我印象深刻,家中沒米,同朋友借錢買米,那時只有腳踏車,米放後面<br />
結果騎車米掉在地上,還被人家撿去,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情景。所以看<br />
到那些流浪犬,我就會同情牠們,因為我窮過了,體會過沒飯吃的痛苦。<br />
但比起其它狗媽媽,我不算多喜歡狗,我小時連狗肉都有吃,小時家裏<br />
窮,什都會吃,兔子和老鼠肉都要吃,現在想想有點噁心。(黑白)<br />
我從小就很有同情心,很容易對可憐的東西動心,從小時就很嚴重了。<br />
看到可憐的就很難過,很容易煩惱,這樣真的很不好讓我的心情很累。<br />
我媽媽也覺得我很奇怪,我和其它小孩子都不同,好像看到可憐的東西<br />
就哭個半天,不止哭一天,甚至連續好幾天,這種我不會講真的很奇怪,<br />
因此嫁來台灣時,看到街頭的流浪犬真的很可憐,因此就開始照顧牠<br />
們。(沙皮)<br />
我發現一個現象,有些狗媽媽身為母親,她們的第一次接觸是孩子買狗或撿<br />
狗回家。孩子從開始新奇好玩到放手不管,最後變成媽媽負責照顧,此後開始喜<br />
歡狗。當她們出門看到家犬和流浪犬的差別待遇,觸發同理心開始餵養牠們。<br />
Chodorow(1974)等人堅持主張男女所接受的性別角色差異如此之大,與其說<br />
是因為遺傳與荷爾蒙的差異,不如說是因為男女在生命週期與生活情境中的差距<br />
所致。這項差別基於一項事實,即全世界的女性都是在家庭中扮演生養小孩的工<br />
作(引自keesing 1991:117)。長久以來,勞動的性別分工與養兒育女的文化實踐<br />
等既定工作,多半指派女性來擔任。不少已婚的狗媽媽在家庭扮演傳統女性照顧<br />
的角色,在家務上做家事帶小孩,因此在救狗的模式依然沿續母職一肩扛起照顧<br />
工作 4 。<br />
剛開始養第一隻狗,我女兒抱回來給我養,我女兒是真正的主因,其實<br />
喜歡狗是我女兒,流浪犬是我女兒國小時帶回家的。我當初會開始救<br />
狗,起因是因為家裏的狗很幸福,偶爾帶牠去散步,就看到外面的狗好<br />
可憐,根本沒得吃。然後,當時我看到一隻殘障狗受傷很可憐,於是我<br />
拿出手邊的食物餵食,其它附近的五、六隻就圍過來,我哪有可能只給<br />
4 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傳統婦女的餘量,本來傳統婦女的能量被封鎖在家庭空間。當這個社會開<br />
始專業化,家庭功能萎縮,家庭主婦的餘量可以轉為對社會有幫助,例如慈濟的女性(抄自 2005<br />
文化諮詢十五講發的上課講義)。我在某幾位狗媽媽身上也看到如此的影子,那些退休後將餘力<br />
拿來照顧狗的女性,以及我也看過一位有錢女性身兼慈濟媽媽與狗媽媽二種角色的人<br />
62
一隻,因此其它隻我也給牠們食物,於是就這樣子開始。(疏洪) 5<br />
狗媽媽敏於可憐起而餵養,食物本身被賦予豐富的象徵意義,這攸關動物的<br />
生存,餵食對狗媽媽而言充滿意義,給牠們東西吃都是深具情感的動作,那是一<br />
種女性的慈愛與養育之心。她們餵養後都會發展情感關係,因此基於責任與情<br />
感,只好不間斷持續地照顧牠們。疏洪告訴我:「時間一到,狗彷彿好像在等巴<br />
士一樣守侯,很奇妙的是牠們都很準時,知道我要去餵牠們的時間。」每日定點<br />
定時狗都在等待她們,她們若沒去餵養,心裏頭也會開始擔心牠們沒東西吃,她<br />
們都沒想到本來只是餵幾天,最後變成全年無休的工作。<br />
我救狗已經十五年,剛開始在學校附近,看到一隻賴皮狗很可憐沒東西<br />
吃,我就買一碗魯肉飯給牠吃,後來看到旁邊還有一隻狗,只好再買二<br />
碗飯,後來再出現第三隻狗,再買第三碗,心裏想著這樣子不行,沒那<br />
樣多錢,於是就去買人家煮熟的雞頭。記得那時四個雞頭十元,我先買<br />
十元,後來再買二十元,再來三十元,連五十元都不夠,本來只有幾隻<br />
結果越養越多,這樣子買還是不行,只好去菜市場買一大堆雞頭回來自<br />
己煮更便宜。(黃黃)<br />
在城市裏,定時定點餵食流浪犬貓,最艱難的,除了其他人族莫名其妙甚至<br />
殘忍地抵制、虐殺外,其實也最容易發生的就是與之發生情感(朱天心<br />
2005:194)。動物與人相逢一定會產生感情,狗媽媽為了讓一些對人類不信任的<br />
流浪狗慢慢願意接近人類 6 ,得要和牠們「培養感情」,每日的餵養就是一種情感<br />
培養的最佳方式。狗媽媽快樂的泉源就是幫流浪犬找到好歸宿,或是看到牠們吃<br />
飽後的滿足感,但和牠們產生感情就會開始有煩惱,她們常心疼牠們可憐的處<br />
境,因此,悲傷情緒總是淹沒了她們,得不時地面對情緒上的折磨。<br />
以前在橋下養狗時,只要颱風天雨量就會變高,為了牠們的安全,我只<br />
好將狗一隻隻抱到比較高的地方,那時我一個人很無力,因此我會叩我<br />
先生,他再叫他朋友來幫忙。有一年颱風淹大水,不知怎搞的,有一隻<br />
狗自己竟跑進去籠子裏,我身體站著水高到淹到我的脖子,我看水一直<br />
淹,牠在籠子裏卻出不來一直往下沉。我很心急,但當時真的沒辦法,<br />
很多流浪犬沒地方去,一直跳上正往下沉的籠子上面,籠子越沉越下<br />
5 這位狗媽媽曾告訴我一個故事,她取名的源由為:「有一次我在疏洪道撿到狼犬,結紮好將牠送<br />
某戶人家,他們沒有好好地善待牠,拿壞掉的肉給牠吃,結果我就跟他們說,那我每天拿肉來餵<br />
給牠吃。有一天疏洪異常地和我親親,我跟疏洪說,我知道你要走了,你的條件很好,要是有人<br />
對你好,你就跟他走沒有關係,我能幫就幫到這裏。我和疏洪是能溝通的,我懂牠的話語,我知<br />
道狗親我,就是要跟我相惜告別,果真隔天疏洪就離家出走了。」<br />
6 記得沙皮曾告訴我:「以前剛開始接觸流浪犬貓,看到台灣的流浪犬看到人害怕地跑走了,躲<br />
得遠遠的,東西擺著都不過來吃,我走了牠們才過來吃。有一隻狗餵了三年,才慢慢信任我,願<br />
意讓我摸。這在我們國家都不會如此,好奇怪,牠們是慘遭什樣的對待方式,讓牠們如此害怕。」<br />
63
去,我想要趕牠們下去都趕不了。我力氣有限根本無法用手抬起那籠<br />
子,結果當場我就哭了,我真的很想救那一隻在籠子的狗,我能救的就<br />
救了,但那一隻狗我真的沒辦法。(咪咪)<br />
我餵的流浪犬有死的很慘的,尤其是車禍的狗更可憐,我有一隻狗叫彎<br />
彎,就被壓的扁扁的,想替他收屍都不行,我只有蹲在斑馬線上一直哭。<br />
那天下大雨,我的淚和雨水就混在一起,從那一次以後,只要我遇到狗<br />
貓的屍體我一定收屍,因為實在太可憐了,生前沒人理牠們,死了更沒<br />
有人同情牠們。我知道有些人救狗覺得狗死了就算了,不過我怕牠們被<br />
車子壓或被丟垃圾車,主要是我希望我的狗貓在外遇到不測時,也會遇<br />
到有人幫忙收屍。(安安)<br />
三百年前若講動物有情感有愛能和人溝通,可能是被定罪的異端邪說。近日<br />
科學家並沒有把動物情感或情緒當作一個研究對象與範疇,反倒是一般大眾剛好<br />
相反,他們關心動物與我們心靈狀態互通遠甚於剝削牠們,尤其是同伴動物。但<br />
我們深信動物有感覺,這種沒有足夠的資訊能為我們解答一切(Knapp<br />
1999:114)。在科學世界裏,若有人探討動物內心世界會遭到打壓 7 ,反倒是一般<br />
大眾較能體會與動物之間互動感情。「有人說印度象會哭泣」──達爾文 8 ,這句<br />
話代表動物也是很有情感,牠們並不是笛卡兒所言沒有意識的動物 9 ,許多例子<br />
都描述了動物情感的展現,不只是適者生存的競爭驅使,牠們是可以表達傷心、<br />
快樂、憤怒、愛等情感的生命。對狗媽媽而言,她們從實際與流浪犬的接觸經驗<br />
來看,無不堅定地表示牠們是有情感的動物。<br />
以前大颱風天,有一隻流浪狗在工廠門口都不敢離開,颱風很大我們三<br />
個瘋女人(都是狗媽媽),我們就將牠抱著去遮雨棚躲雨。但那一隻狗<br />
還是很死忠地想要守衛工廠,可能也在等主人吧。但颱風工廠休息關<br />
門,根本不可能有人回來。我們一共抱了牠二次去躲雨,但牠都跑回去<br />
淋雨等主人,後來火大就讓牠去淋。(自生自滅)<br />
有一次回去時,我發現樓下的三隻流浪狗跑來找我,我快嚇死了,我住<br />
十幾樓,也不知道牠們是如何找上我家的。那三隻有二隻是老狗,有一<br />
隻二個眼睛還瞎掉,牠們很忠心,一直賴在我家門口不回去,那樣子好<br />
像哭著請求我給牠們一個家。記得那時還是冬天天氣很冷,我很想要拿<br />
7 我向其它研究海豚行為的學者提出海豚是否表達情感,他們都不願意揣測甚至拒絶說明,一名<br />
學者將這問題推給他的女研究生,暗示這個題目配不上他的崇高的學術(或男性尊顏嚴)(Masson<br />
&Mccarthy 2000:8)。<br />
8<br />
這一句話說明動物會哭泣,或者至少可以說,牠們會以聲音傳染痛苦煩惱(Masson &Mccarthy<br />
2000:2)。<br />
9<br />
十七世紀,哲學家笛卡兒是第一個主張動物沒有意識的哲學家(Knapp 1999:114)<br />
64
棉被給牠們,但我不能,因為這反而害了牠們,怕引起附近住戶反感。<br />
我後來怎樣子趕都趕不回去,最後還用踢的,但牠們還是一心要回來找<br />
我,我先生還拿棍子趕牠們,牠們下去後十秒鐘後又上樓。我看了很不<br />
捨很難過,看得出來牠們流浪很久,多渴望一個家庭,我都看在眼裏,<br />
心裏也很想給牠們一個家,但我很無奈因為我沒地方收留牠們,我沒能<br />
力給牠們一個家,我家才十坪多養了三隻貓,我先生也不答應養牠們。<br />
其中有一隻將我當主人,牠們看到陌生人來都會吠,牠們真的很傻,但<br />
問題總要解決,住戶都在說話了,說要叫捕犬的人直接進來大樓裏捉走<br />
牠,我餵了牠們七年了,其中有時被捕犬人捉走,我也有領回來,因此<br />
現在我也很捨不得讓人家捉走。我就求我先生,足足求了二天,請他給<br />
我錢,將牠們送到一個愛心媽媽的狗場,我先生後來答應給我一筆錢,<br />
大約六萬元,我送牠們去狗場生活,我真的沒辦法,想到這裏我就很難<br />
過。(沙皮)<br />
狗媽媽最常遇到流浪犬發生意外事故,因此,她們最清楚到底什麼是失落的<br />
意義。當她們的流浪狗被清潔隊捕捉、香肉店抓走、忽然不見失蹤、毒死或病死,<br />
她們可以馬上處理遺體和整理悲哀情緒,調適自己很快地恢復正常,才能接續照<br />
顧工作。她們在情緒的適應上不同於以往,從初期的痛哭流淚到後期只能想開,<br />
現在她們敍述這些事情時都以平穩的語氣敍述,一副好像沒事,反倒是我為了這<br />
些悲慘的故事,在旁邊動容哀戚不已。正如咪咪:「起初都會哭,後來看很多淒<br />
慘的,比較不會放那樣多感情了,因為感情麻痺了,真的看太多了。」<br />
有時生病是一大堆互相傳染,而不是只有幾隻得病,因此餵藥時我很小<br />
心,一隻狗就要換一雙手套塞藥給狗吃,食物也要分裝給牠們吃,而不<br />
是倒在一個地方一起吃,否則互相感染會更慘。以前想不開,狗生病時<br />
很笨就死命想要救回來,不行也硬要救回來,救得很辛苦。那時全部集<br />
體生病時,一天到晚都在跑醫院,一次帶二隻去看,去了打完針再回來,<br />
有時一天來來回回四、五趟,但救到最後想說沒有錢救了,後來一半就<br />
用自己的方式救,自己去藥局買成藥給生病的狗吃,也不要帶去醫院打<br />
針了,負擔不起了,不是我不救,而是沒辦法了。由於沒錢醫,因此眼<br />
睜睜看流浪狗沒醫而死,心情好痛苦,剛開始的五十隻都很難過,哭到<br />
不行,情緒的波動會好幾個星期,心疼到不行。疏洪每次看到我眼睛紅<br />
到不行,她會跟我說又是哪一隻狗死了。然後她教我一個方法,想說第<br />
五十一隻後的任何一隻流浪犬死掉,就想說牠們一路好走,這樣想就比<br />
較不會像之前哭地要死要活的,我只能如此,否則根本餵不下去。(毛<br />
毛)<br />
疏洪告訴我,她的個性可以控制自己的悲傷程度。<br />
65
有一次二隻小狗出來馬路玩,我本來要撿牠們回家養,但想說先餵完回<br />
頭再撿,結果回去發現二隻都被車撞到,被一台台車子開過去再被壓<br />
平,我不會難過,因為那是牠的命。我告訴你餵流浪犬,牠們再如何慘,<br />
怎樣哭都沒有用,若有能力幫牠們就幫,自己若難受,心情和身體不好,<br />
對狗也不好,我自己個性是可以控制的。<br />
動物和人類的情感回應不同,對狗媽媽而言,她們絶對可以理解那種情感形<br />
式。我也常會聽到狗媽媽在餵養時,她們會以憐惜的口吻,細數一大串流浪犬的<br />
故事,她們常一邊跟我介紹,你看那一隻是被某某人丟的狗,他們不要養了之類<br />
的,或是今天又有一隻新來的狗,哪裏被丟一窩狗等事。她們如數家珍般地訴說<br />
曾遇到的流浪狗,在說的同時就邊倒食物給牠吃。對狗媽媽而言,因為感情因素<br />
有時反而會自我苛責。<br />
想一想我感情可能太豐富了,或許有人真的比較理性吧,有感情了就很<br />
麻煩,擔心他們沒吃、受凍、沒水、太熱、被趕、為覓食遭車禍。有一<br />
隻毛毛(已往生),我餵完牠後,他一直跟我一直甩,牠又一直跟我,<br />
我一直甩,但甩成功了,我又不忍他的表情又很三八地去安撫他,一來<br />
一往折騰至少 1 小時,每次都要搬演著這樣的戲碼。後來牠被竊盜集團<br />
整得肚破腸流,因為他愛窩在情侶身邊。他很聰明,機警集團的人一靠<br />
近情侶,他會提醒情侶狂叫,壞他們的好事,因此最後被壞人刺死。以<br />
前常要甩牠,但當他真的死掉,那愧疚痛心的感覺,現在還很深刻,每<br />
次走到那段路心中就很陰影,到現在還忘不了牠。我真覺得很對不起很<br />
對不起牠,沒辦法給牠一個安穩的家,那竟然是十一年前的事了。洗澡<br />
時想到一些狗狗會突然哭泣,覺得對不起他們,但實在力不從心,我覺<br />
得好像玩弄了牠們的感情,痛澈心腑,真的!胸口一直往下陷揪在一<br />
起。(我與安安 msn)<br />
被拋棄的孩子,<br />
忽然醒來,<br />
他恐懼的眼光環顧四周一切<br />
只尋找他看不見的,<br />
迎上來的關愛眼神<br />
──喬治•艾略特(Hrdy 2004:362),一八七一年<br />
以上這首詩是在講嬰兒被拋棄的樣態,此種眼神對狗媽媽並不陌生,小孩和<br />
狗被丟的樣態,一開始都在找愛的眼神。她們告訴我狗被主人拋棄時,和小孩子<br />
的反應是沒太大差異的,牠們會到處找尋類似主人的衣著、身影甚至主人的車<br />
66
子,有些試圖不辭千里尋找回家的路。每個狗媽媽都很清楚牠們被拋棄的樣態,<br />
她們總是既擔心又同情地看著牠們,想說讓我來照顧你吧,不要再等那位不再回<br />
來的主人了!<br />
剛丟出來的狗,都會守在原地不會跑遠,看到類似主人的車子都會迎上<br />
去,想說主人會不會來帶走牠。牠們剛開始被丟,個性變得較沒有安全<br />
感,有些都很自閉地躲在一邊,但經過餵養與互動後,都會變地很活潑。<br />
(毛毛)<br />
我曾遇到一隻流浪犬剛被丟出來,從第一天開始,牠一直不斷地繞圈,<br />
不斷地在地上一直聞,牠一定是在找主人。結果到第三天,牠從第一天<br />
開始很恐慌地不斷地繞圈,到最後垂頭喪氣的樣子走路,讓人很心庝。<br />
我遇到有些剛丟出來的,甚至遇到對牠們示好的人,都會一直跟著走。<br />
(安安)<br />
動物不是他者而是互動的主體,人和狗的互視眼睛,形成一道無法跨越的深<br />
淵,但狗媽媽卻能以不是言說的方式,用另種肢體語言親近牠們,不少狗媽媽很<br />
害怕去公立收容所,她們最害怕見到牠們的無望眼神。沙皮自從去過公立收容所<br />
後,從此若餵養的狗被捉,她到處請托朋友甚至出錢請人幫忙,她絶對不要再踏<br />
進去了,她告訴我。<br />
我去公立收容所,那是在山頂上面,一般人根本很難找,去那邊回來好<br />
幾天,整個頭到腳一直麻麻的,回不了神。我不會講,那感覺很不舒服,<br />
尤其是看到一大堆眼睛看著我,牠們都在等死,希望我帶牠們回家,但<br />
我卻無法帶那樣多狗回家。另一個不舒服的原因,可能是體質的關係,<br />
那邊過去有多少小生命被殺了,很多靈魂會靠近我,牠們需要我唸經<br />
吧,我當時還不懂,現在才懂。(沙皮)<br />
安安餵養的狗只要不見時都會去收容所找,她為了將狗領出來,只好一再地<br />
進去公立收容所。<br />
每次我餵養的狗不見了,我都很緊張,心情很不好,我會一直想是不是<br />
我的狗被捉了,想到即將要去動物之家報到找狗,那是一種折磨,還要<br />
花一趙時間去動物之家。每次去動物之家,都在門口翻狗被捉記錄的本<br />
子,手一直抖,心臟一直在跳,我自己都聽的到心跳聲,那是害怕和焦<br />
慮。進去公立收容所後,我每次都整場繞一圈怕遺漏認識的狗。有些較<br />
乖的狗,我會摸牠,我會說不要怕試圖安慰牠們。其實也是在醫自己,<br />
告訴自己不要怕,我很清楚我救不了那樣多狗,心裏一再調適保持正<br />
67
常,腦筋保持清楚,很坦白面對自己。(安安)<br />
我發現很多狗媽媽遇到挫折時,她們會以東方的輪迴因果解釋,或是宿命論<br />
這種不可抗力的因素安慰自己。博士告訴我:「我覺得我是來完成使命的,但怎<br />
如此辛苦,只能說自己欠狗債。」有些狗媽媽則以宗教信仰的方式和神明對話,<br />
得到一絲寬慰後才能幫助她渡過難關。當我去阿桑的私人收容所時,看到幾個狗<br />
媽媽拿著水果和紙錢和隔壁的私人收容所聯合祭拜,對她們而言,超渡升天的牠<br />
們以及求神保佑平安是件要緊的事情。<br />
綺綺告訴我,對於救狗的事情,她都回去求佛祖不斷地上經,保佑這些<br />
流浪狗平平安安。我去幫忙綺綺捉狗時,我印象很深刻,那一隻狗被麻<br />
醉藥吹中時,由於藥性的作用不大,因此牠一直走路亂晃左右搖擺,路<br />
上車子來來往往,牠橫行馬路的樣子看起來很危險,綺綺在旁邊來回踏<br />
步,左右來回一直唸著阿彌陀佛,請佛祖保佑,我們是做好事,要幫助<br />
那一隻狗,你一定要保佑事情成功。綺綺對於死掉的狗儀式很注重,不<br />
但會用往生被也會唸經祝牠一路好走(田野日誌)<br />
我的三位受訪者告訴我,她們曾經看到虐待流浪犬的現世報。小可愛告訴<br />
我,有個壞人因為害狗得到相關的病症─口腔癌。<br />
那一天晚上我六點半時去餵,但很奇怪,我發現都沒有狗在原地等我。<br />
我沿著路去找,發現我平常餵食的盆子,裏面的食物都已經綠了,那顏<br />
色很奇怪,原來是昨天我放的食物被下毒,因此狗通通死掉了。這種毒<br />
死都會有因果關係的,那個下毒的人,聽說只要是進去竹林裏的流浪犬<br />
都要毒死。有一次我得知毒狗的人後來得了口腔癌,我高興死了,心想<br />
這是報應,太好了。(小可愛)<br />
動物在重要的,與道德相關的方面,諸如經驗快樂與痛苦的能力,以及保持<br />
康樂的慾望和我們極類似,這種使我們產生一種對非人動物之道德社群的需求<br />
感,這就是「物種間的親屬關係」(Fox 2005:143)。狗媽媽同理牠們的苦難發生<br />
情感後,產生親生命的「物種間的親屬關係」,她們將精神時間金錢全力投注關<br />
注,再加上平日的互動記憶,不知不覺產生依附作用,讓彼此緊緊包縛在一起。<br />
她們與牠們的依附作用,可能是治療作用或是生命的意義,或是心靈慰藉、伴侶<br />
意義,有些甚至在救贖有相當好的回饋。我認識一位憂鬱症很嚴重的狗媽媽,她<br />
秀出手腕一條條的傷痕告訴我,救狗產生某種深刻療效,她找回生命中的意義不<br />
再割腕。我也曾遇過一個愛心爸爸告訴我,車禍時狗趴在他身上救了他的命 10 ,<br />
因此他就開始救流浪犬。花蓮的一個狗媽媽告訴我,她車禍受重傷時,她到十八<br />
10 狗救人這種異常的情況就好比人類才會救人,這是物種間的親屬關係。<br />
68
王公廟求神最後大病痊癒,她開始照顧街頭的流浪犬。以上實例,或許有人覺得<br />
人與狗的事蹟被浪漫化了,但卻是我親耳聽到的事實。<br />
我小孩子長大了都搬出去了,他們沒跟我在一起,我開始將愛放在那些<br />
可憐的流浪犬的身上,那是一種轉移作用,所以我很怕母狗拖著一群小<br />
狗出來找食物,我們做母親的人真的很怕這畫面。(阿丹)<br />
我剛好一生遇到的婚姻都很不快樂,遇到二個死男人對我很不好,因此<br />
我將希望寄在牠們身上,我覺得照顧牠們讓我感到很快樂,我也很高<br />
興。(小可愛)<br />
無論單身與否,她們訴諸感情才有行動力,她們發揮母愛看護照顧牠們。因<br />
此我在訪問狗媽媽常聽到「我的孩子」這類字眼,難怪她們可以為了照顧孩子把<br />
屎把尿毫無怨言。每當夏天我去建國花市時,看到狗媽媽會自備碗以及飼料,準<br />
備給自己的孩子止餓解渴,甚至她們還帶著碎碎的冰塊,放在一旁散熱讓小狗小<br />
貓不會中暑。當有民眾要認養時,她們擔心對方當天沒有立即去買飼料,怕自己<br />
的孩子餓肚子,因此她們自掏腰包附贈一小包飼料。我也曾聽過一位較有財力的<br />
狗媽媽的作法,她在送養小狗時,那儀式彷彿在嫁女兒般的正式,自己購買狗衣<br />
服、狗項圈、狗飼料以及訂作白鐵籠,全部免費贈送給認養人,甚至認養人若居<br />
住在南部,她還會開車親自送達。有些媽媽在選主人時也好像在挑媳婦般的,她<br />
們仔細過濾主人條件,若是不滿意他們就會拒絶,送養後會打電話給認養人,關<br />
切自己的孩子的情況。當我去機場看到狗媽媽送流浪犬到機場準備去德國,她們<br />
在籠子裏鋪好幾塊布,然後放牛皮骨給狗啃,一副依依不捨的樣子,有些媽媽因<br />
為捨不得還哭紅了眼睛。有時,我看到狗媽媽發現狗不見時,那一副發狂不斷地<br />
找孩子的樣子,這就是身為母親的樣態。<br />
人類文化學家康斯坦斯認為,我們與狗深刻的感情,切實地與某特定的精<br />
力有關,藉由狗的能力,能夠重新創造一種孩堤與母親之間的親密感(Knapp<br />
1999:228)。 曾經,我看過狗媽媽幫牠們載上的裝飾品,流浪犬身上竟然載著美<br />
美的天珠或是佛教的保佑符,代表她們對孩子的祈福,她們說如此,民眾比較不<br />
會瞧不起流浪犬。不過,不出所料後來我打聽天珠下落,果真都被人類拿走。無<br />
疑的,牠們對狗媽媽而言不僅是條狗而已,她們傾向將流浪犬當孩子般地照顧,<br />
未婚的毛毛形容這種母親和小孩的依附關係。<br />
我救狗比較偷偷摸摸,怕老闆和家人知道,體力和精神上很累。牠們每<br />
一隻丟出來的都有遭遇的,牠的小狗若在外面出生,我也覺得很心酸,<br />
括風下雨日曬得很可憐,唯一好的地方就是我有供應吃的,至少一天一<br />
餐也肥肥,我在那邊的供應都是吃到飽的,份量都很多。餵狗的人都較<br />
有牽掛和煩惱,不會像別人說要出去玩都玩得很高興,就如同父母出去<br />
69
玩將小孩放在家,心裏會一直想,這時間應當回去餵牠們,我心裏這樣<br />
想,出去玩難免玩地很不開心,下雨打雷就說慘了,不知會淋到什情況,<br />
天氣冷會想明天不知多少隻要感冒了。(毛毛)<br />
社會仍有些人覺得對狗正常與過份的愛之間有一道界線,寵愛狗,花太多時<br />
間在狗身上,與狗太過親近──都會被標示成很不一樣的人:怪異、反社會,然<br />
後成為笑柄(Knapp 1999:174)。我聆聽她們的說法,其實狗媽媽都是心甘情願<br />
照顧流浪狗,倘若無法兼顧人生其它面向甚至為此喪失,這都是她們主動選擇的<br />
結果,我聽到的就是如此的堅持,非關其它。不過,十之八九的民眾卻對她們的<br />
私生活任意做評斷,甚至覺得她們的人生有所缺憾才來救狗。記得已婚的阿瘦,<br />
她告訴我「我在社區餵貓,別人還跟我吵架,然後她還問另一個人說,她到底是<br />
有沒有結婚阿。」<br />
有人說救狗的人都是婚姻有問題,感情有問題,或是人生有挫折。因此<br />
將感情移到動物身上,有也是有,但也是很多沒有,你看也有很多家裏<br />
很好的,我跟你講,那個大陸來的狗媽媽,她先生也反對,她也都偷偷<br />
摸摸,先生罵歸罵,但她該回家時就回家,該做什也做什,還不是沒事。<br />
(寶寶)<br />
外界的謬論展現以下誤解,她們全力地照顧流浪犬代表她們想要小孩。<br />
投注在狗身上的精力與感情,代表對孩子變相的渴望是一種荒謬的說<br />
法。這思維也代表女人一生只有一種方式來貢獻自己,那就是生孩子的<br />
論點。這種將狗與小孩連結的論點,代表母親身份是種正常化的象徵。<br />
(Knapp 1999:186)<br />
我們必須打破這類性別歧視的論調,很多已婚的狗媽媽早有生養小孩的經<br />
驗,後來才救狗,她們投入養狗並不代表想要小孩,也不表示她們只願意照顧流<br />
浪犬,卻捨棄自己的家庭或孩子,這根本不相干的兩回事。黃黃白天餵狗,晚上<br />
在街頭擺攤賣東西,她告訴我擺攤是為了賺錢養一個尚在讀書的孩子,希望供應<br />
到他當兵為止。阿桑有個孩子有點精神障礙,因此她除了救狗之外,還撥空為了<br />
孩子創立協會幫助類似的小孩。阿桑、阿丹、可可、黃黃、芽芽、寶寶、疏洪等<br />
人,她們從沒混淆過動物與小孩的差別,她們對人對動物都無保留地展現關懷倫<br />
理,足以否決關懷動物就不關懷人的無聊說法。這其中伸展的二條路,一條家庭<br />
之路,一條狗兒之路,並不是非此則彼的選擇,這其中的努力有些是很辛苦的和<br />
諧,有些雖是表面和平底下卻波濤洶湧,但她們至少都沒有因此捨棄其一。<br />
二、救或不救? 處境很尷尬<br />
70
到底要不要救?要不要收容牠們?狗媽媽的處境很尷尬,她們的能力有限或<br />
是沒有多餘的收容地方,為此常內心交戰,通常是理智與感性間拔河的試煉。對<br />
大部份的狗媽媽只要看到眼前的生命受難,理性考量就消逝無存,能力不足的問<br />
題往往拋在腦後。不過我發現還是有媽媽受到情感驅動的照顧面,表面瘋狂大量<br />
收容之下蘊含一絲理性分析的邏輯。芽芽收容百餘狗,她曾告訴我面對公與母的<br />
流浪幼犬,她會將母幼犬帶回收容,因為怕母狗長大後,未來在外生小孩。有些<br />
狗媽媽會察言觀色有策略地,察看情勢評估原地餵養的可能性,以及左右鄰居對<br />
流浪犬的接納與容忍程度,而不是一味地通通帶回家,能力為優先的考量。<br />
有私人收容所的狗媽媽,例如咪咪與黃黃,當她們有私人收容所時,總有種<br />
心態浮現,由於有地方因此先暫時帶回收容,最後變成越養越多的景況。<br />
倒霉!救牠回來就一大堆事情,洗澡打預防針結紮,每一隻都理哪有那<br />
個命去理,越理越多越生氣。雖是這樣說我看到可憐的還是撿,我都不<br />
會管以後,只要眼前看到很可憐的流浪犬,我就一定會救,我是沒想太<br />
多的人,都是過一天看一天,結果越撿越多。(咪咪)<br />
有一次我去黃黃賣東西的攤子,她旁邊有個紙箱裝著一隻小狗,我常常<br />
扮演煞車的角色,忍不住跟她說不要再撿狗了。她感嘆地說每當遇到可<br />
憐的狗時,自己能力有限也養很多狗了,年紀大了能養的時間有限,根<br />
本不想再撿了。這是個難題,到底是救也不是,但不救也不是,你看這<br />
一隻小狗在馬路中間亂跑,我不撿牠一定會被車子撞死。我聽了之後也<br />
不知能怎辦,這是個難題,但我多希望她能夠狠心點,不再收容了。(田<br />
野日誌)<br />
她們收容很多流浪狗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多半以她們的經驗值來決定。有些<br />
當初只想要撿來送養,但卻因為送不掉變成自己養,以致於越養越多。有些則感<br />
於大環境的惡劣,原地餵養的狗慘遭不幸或被捕狗隊捉走,因此寧可自己親自收<br />
容照顧牠們,有些情況則不得不收養,例如瞎眼斷腿的殘障狗。在台灣惡劣的大<br />
環境下,請她們控制數量不要再撿狗,對她們而言真的很難。更何況有些是民眾<br />
故意將要丟的狗綁在門口給狗媽媽,這種情形更是防不勝防,叫她們不要管根本<br />
辦不到,這是不得不處理的狗。她們是位於第一線的主要照護者,收容取決多半<br />
先以情感為行動準則,這是一股很強大的温柔力量。<br />
以前我並不知道有這回事,但我發現阿丹、咪咪、安安與寶寶等人傾向將流<br />
浪狗放在私人收容所,這種方式確實和國家體制的撲殺政策有關。<br />
有一次我幫陳僅捉工地餵養的幾隻母狗帶去結紮,工地的人願意讓那幾<br />
隻狗待在原處,陳僅也跟捕犬人員講好了,不要來捉狗。但隔一陣子陳<br />
僅卻跟我說新來的工地主任不准有流浪犬留在工地,限我二天內要移<br />
71
走,她告訴我「那也沒辦法,若我不捉走,狗就要通通被捉去死了,我<br />
要放哪,我根本沒地方放,只有狗場要收而已,我要去開刀住院了,我<br />
以後沒辦法了,真的要快點移走」。本來我很反對將狗放在幾百隻的狗<br />
場,但我知道她也不可能接受安樂,所以我趕緊跟她說,記得要送去狗<br />
場時要打預防針,並且未來一定要多去關心牠,不要放了就不管了。(田<br />
野日誌)<br />
安安曾經看過公立收容所的安樂 11 ,她告訴我親眼目睹後,只要有機會就會<br />
前仆後繼從收容所領很多隻狗出來。<br />
早期的狗媽媽都會拼命去收容所救狗去狗場,因為吳興街時代的公立收<br />
容所從收容到安樂都很可憐。我記得一個籠子都關了快二十隻擠成一<br />
堆,大狗踩著小狗,有些只能站著真的很可憐,實在太可怕了,太可憐<br />
了。連到那邊領自己的狗出來時,只要有多餘的能力,不認識的狗也要<br />
領出來。這樣不斷地領出那樣多隻狗,自己就只能養很多狗,甚至最後<br />
自己成立狗場。(安安)<br />
從前阿丹曾在黃黃的私人收容所幫忙,由於我常去黃黃那邊帶小狗去花市送<br />
養,她曾經勸我不要帶小狗去花市送養,她說了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br />
我曾將一隻流浪犬送給一個客戶,剛開始他們很喜歡,但三個月後,我<br />
去看客戶,他竟說狗不見了。那時我要離去時,忽然在門口那邊看到那<br />
一隻狗,當時牠只剩二隻腳走路,原來是牠已經癱瘓了。我發現牠因為<br />
車禍被撞,血卡住喉嚨,也叫不出來,好好的一隻狗,他們給牠養成這<br />
個樣子,我只好將牠帶回家看醫生。醫生說,若如此何不安樂呢,活成<br />
這樣。我從那時開始接受安樂,若我有地方收容,我也不想將狗送給別<br />
人了,送給別人也不一定會養得好,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阿丹)<br />
以關懷倫理看之,小花花的照顧動力來自於「情感依附」、「敏於他人」、<br />
「責任感」 12 ,這三者皆是女性照顧的核心動力因素,大部份的狗媽媽皆有如此<br />
11 公立收容所號稱「安樂」的屠殺機制一直是件不見光的機密,不過安安坦誠她曾不小心偷看<br />
過。我剛聽到不敢置信地問安安:「那真的是安樂死嗎?」她聽到問題後,聲音越加高亢和堅持,<br />
我可以想像電話的另一頭,她漲紅地臉反駁:「那種並不是安祥的安樂死,狗是在恐懼下被屠殺。」<br />
12 王麗容(1998)將照顧工作的心理論點,歸納為三個部份:(一)「情感依附」觀點:從心<br />
理學觀點,女性照顧動力來自於女性本身對受照顧者之間的「情感依附」。照顧是因為女性的自<br />
我認同、自我特性的能力,以及利他意識所致。(二)「敏於他人」觀點:強調女性有照顧倫理,<br />
顯示出女性「敏於他人」,而且有照顧責任感,發展出親密人格互動關係的能力與需求,以及回<br />
應他人需求的能力。(三)「責任感」觀點:另一種解釋女性照顧的核心動力因素,則是女性強<br />
烈的家庭情感情結,男女之所以有照顧上差別,是因為女性有孝順責任感。<br />
72
的關懷特質。<br />
有一天下午我有事外出,我看到大水溝旁有人用木板圈養很多流浪犬,<br />
我就問正在裏面餵狗的黃黃,結果就開始認識了。我們互留電話後有一<br />
次在馬路中間撿到小土狗,結果我也沒辦法養,就拿給黃黃養。我這個<br />
人就是很有責任,拿狗給別人很不好意思,我就幫忙她去餵狗。那時黃<br />
黃的狗場地上的草長得很高,下班後天黑了沒有電燈,也沒有接水,我<br />
都去附近的池溏提水,也沒有電,我這人怕黑其實很緊張,我是用充電<br />
的電池進去的,只好一進去就一直沖洗和餵食。後來很多人拿狗來丟,<br />
那時被丟的母狗太多,紮也紮不完,牠們一直不斷地生,還有人丟十幾<br />
隻繁殖的名犬來狗場。我本來只是養我停車場後面的狗,認識黃黃後才<br />
會養那樣多,否則根本就不會養那樣多,也是責任感的關係,覺得有摸<br />
狗有感情,捨不得牠們。(小花花)<br />
黃黃是我認識最久的狗媽媽,以前我無法理解她的想法,直到我找她訪問後<br />
才懂得她的思維,原來她用一種自認最穩固安全的養狗方式,至少讓牠們在視線<br />
範圍內生存,對於牠們未來的命運,只好抱著不要強求的心態。<br />
若是將狗放在狗場,我比較放心,因為我看得到牠們,因此一定顧的到,<br />
但在外面生活,牠們無時無刻都有捕犬車和香肉店要捉牠們,真的很危<br />
險。尤其是在車下和大馬路的小狗仔一定要帶走,牠找不到吃的而且跑<br />
來跑去容易被車撞,有些車禍倒在路上的狗,真的很可憐,我若沒撿牠<br />
們,我根本會擔心到睡不覺,但若來我狗場,牠因此得病死亡是件很自<br />
然的事。(黃黃)<br />
疏洪一直強調有能力再救很重要,但我發現,她還是不能拒絶已經接手照顧<br />
的狗。<br />
有人丟母子一窩在我餵養的區域,小狗有人要我就會撿,要是確定很可<br />
愛,我就帶去送,若沒有人要我就無法撿。能做多少養多少,要是每一<br />
隻心軟,全都帶回家隔壁一定會抗議。只要是我能力範圍我才做,不會<br />
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我都會看自己的經濟情況,有些沒有能力想要丟給<br />
我,可憐的就認了。像有一隻狗是殘障狗,照顧起來很麻煩,有個小姐<br />
打電話給我要花錢請我幫忙養牠。我說一日算一百元,包括吃住還要吃<br />
藥等照顧工作,結果那小姐幾個月後就連絡不到了,她丟了就不管牠<br />
了。我覺得沒有本事救,就不要救,她沒想到我也有負擔。不過那一隻<br />
狗真的很可憐,身體有褥瘡,瘦地不得了像伊索比亞也像木乃伊,那一<br />
隻狗真的很可憐,我只好繼續再照顧牠。(疏洪)<br />
73
我曾在動物星球頻道「邁阿密動物警察風雲」,看到某一集內容是動物警察<br />
進去寵物狂的家裏,裏面又髒又濕導致動物交叉染病,警察以破獲的方式捉到三<br />
十隻貓與數隻狗,最後宣判所有的貓都要安樂死。主人在旁邊喃喃自語說:「狗<br />
很忠心,每次看到牠們搖尾歡迎我都很快樂,狗很愛我之類的話。」旁白提到「她<br />
是愛動物的沒錯,但能力不足,以致於照顧品質極差,她有個特徵,不信任將動<br />
物交到動物之家或交給其它的認養人。」當我看完節目時當下想起台灣狗媽媽大<br />
量收容之下人與狗的樣態。我曾去過品質很好以及很糟的私人收容所,我發現取<br />
決因素在於私人收容所的收容數量、資源多寡 13 ,管理知識 14 以及衛生習慣。私<br />
人收容所隨著數目的增加,狗媽媽也不願接受安樂,狗舍很快就會擁擠不堪,爆<br />
發疾病傳染,導致收容品質驟降。另一方面狗媽媽對待動物的方式根源於生活背<br />
景,某些狗媽媽不懂得同伴動物真正的需求,因此我有看過有個狗媽媽將狗當作<br />
雞鴨長期關在籠子飼養,她明顯有給牠東西吃,但同伴動物與人類之間的渴望與<br />
撫摸和愛的互動,她都不重視。記得安安曾告訴我她去探視的一個私人收容所,<br />
她告訴我當時的情景,其實那邊我也去過,踏進去的感覺讓人很沉重。<br />
貨櫃屋裏面沒錢弄電,有好幾群狗,很多狗。那些流浪狗都關起來,有<br />
人進來時會一直撲上來,跳著要你摸牠們。去那裏出來全身都很髒,會<br />
有一種那到底是什麼世界的感覺,好像是地獄。<br />
若從動物的觀點看人,愛與慈悲有時反而成為實踐動物倫理的障礙。將動物<br />
倫理挑戰傳統社會人與動物互動的知識與權力關係,愛與慈悲常是後者的擋箭牌<br />
或外衣,缺乏知識與權力做後盾,動物倫理將空洞化(朱增宏 2003:110)。<br />
以上這段話朱增宏是站在動物的立場,提醒人們實踐動物倫理時,要注意愛與慈<br />
悲外衣下動物被剝削的情形。換句話說,狗媽媽成立私人收容所,倘若她擁有動<br />
物福利的思維以及掌握改變的權力,在實踐動物倫理時就能顧及收容品質。我的<br />
田野筆記可以約略探討台灣脈絡下的衝突。<br />
我每次去黃黃狗場,看到她收了一堆新面孔的小狗,卻因狗場環境不好<br />
感染疾病,由於能力關係,也缺乏妥善照顧和醫療。因為收容數量太多,<br />
沒有做好隔離,還曾發生幾隻狗互咬而死。有一次我看到熟悉的寶貝蓋<br />
上往生背,己經死了,心裏氣到不行,但當看到她辛苦的身影,以及她<br />
的愛心論調:「這些小狗被主人虐待,你叫我怎能不帶走」、「這不是我<br />
主動收容的,是人家丟來狗場門口的,我能不收嗎?」之類的話語,我<br />
之前想要勸她的話語,頓時都吞回肚子裏。說真的,她的當初立意,讓<br />
13 任何生命一定要有資源,才能談得上生命品質。對於缺乏庇護資源的浪貓浪狗而言,根本就<br />
沒有生命的品質,因此收容數量的控制很重要。<br />
14 有些狗媽媽收容眾多流浪犬卻不懂得要分區管理,常造成疾病交叉感染以及狗互咬而死。<br />
74
,我還能說些什呢?猶記得有一隻狗生病後有後遺症,<br />
牠被關在狗場的籠子裏,牠身體不斷一直抖,抖地我看了心裏頭很難<br />
受。牠的行動力不便,很容易直接大小便在籠子裏,黃黃要特地去察看<br />
鋪的棉被有沒有大小便,然後清理。我告訴黃黃:「若我要顧二百隻狗,<br />
我可能會考慮安樂牠。」我知道我的毛病又來了,黃黃笑著說「不行啦,<br />
我顧牠顧很久了,牠還能吃不行啦。」狗生病不是我照顧的,是黃黃照<br />
顧到活下來的,我還有什立場呢?老實說,狗場裏有二百隻狗,牠根本<br />
沒有被好好照顧,有時,我看了很痛苦但無可奈何,黃黃也不可能接受<br />
安樂,因此我真希望牠快點解脫(田野日誌)<br />
朱增宏的一番話比較無法同情台灣的情境之下狗媽媽不得不收留流浪動物<br />
的苦衷。不過卻值得深思一件事,救狗的出發到底為人類中心還是動物為優先考<br />
量?狗媽媽最常碰到的質疑為收容數量太多危及動物福利,此時救狗是不是變成<br />
人類中心主義 15 ,反倒是救自己的情感,撿狗成為解決自己的不忍之情。台灣的<br />
某些私人收容所經營不好並不是件稀奇的事情,在能力不足或是數量無法控制<br />
下,動物能不能有權利獲得一定程度的考量,這時反而成為其次的考量。不少收<br />
容上百隻的私人收容所,最後都變成人狗同病相憐,但直到目前為止,我仍覺得<br />
狗媽媽們已竭盡所能,對於她們我根本不忍還有任何苛求。<br />
收集是一種上癮行為,焦點多集中在個人病理化、問題化的討論。但是社<br />
會環境的影響不可忽略,收集其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Belk 1995)。台灣狗媽媽<br />
是否也在收集流浪動物?指稱台灣的狗媽媽為「動物收集者」 16 若忽略台灣體制<br />
環境 17 及她們資源的匱乏是不符合社會正義的。在台灣社會脈絡的大環境下,責<br />
備她們的收容處境並不公平。她們收容眾多狗後成立私人收容所,起初動念不是<br />
為了收藏動物,而是源於女性的憐憫之情。<br />
在台灣看到流浪動物卻是很二難,要放著讓牠餓在路邊,還是收回去自<br />
己養,或是假裝沒看到呢?動物收集者在台灣的狗媽媽身上是很不公平<br />
的,在德國或許較負面,因為大環境是很好的制度,何必將它弄成如此。<br />
(蔡丹喬) 18<br />
我曾聽一位年輕志工告訴我「我認識一位狗媽媽,她跟我說你只來看一下,<br />
就叫我要改進東改進西的,都沒想到我這樣做已做了好幾年了,遇到事情還不是<br />
這樣走過來了。」安安聽到人家以「動物收集者」批評她時,她很生氣地告訴我,<br />
15 只將倫理原則應用於人類,而且人類的需求和利益具有最高的(甚至是摒除其他生物的)價<br />
值和重要性。<br />
16 動物收集者(ANIMAL COLLECTORS):「動物收集者」的非正式定義,是指一個人長期、不<br />
斷的收集動物,不但越收越多,且數量多過於他或她所能妥善照顧的量(Mullen 2002:28)。<br />
17 詳見第二章第二節的研究背景說明,台灣整個大環境下造就她們收容眾多流浪犬。<br />
18 蔡丹喬為旅德的台灣人士,目前住在德國,她致力於動保志業,是早期推動台灣動保法的一<br />
大推手。<br />
75
批評的人必須跳下來幫忙才有資格批判。<br />
若沒輔導狗場,只是放空炮而己,基本上她們的養狗方式很糟糕,有時<br />
也是因為經濟困窘與資源缺乏,但對動物的心是值得肯定的。不要說是<br />
偉大,也是寛容的,最可惡的是那些丟狗給她的人。自己身體力行去幫<br />
忙才知道第一線的辛苦。要終結狗場?如何終結?如果是送養管道非常<br />
通暢我也很贊成,但有可能嗎?既然是地獄,應輔助他成為天堂不是更<br />
好?台灣的狗場哪有那麼多溫馨小品可談,大多是殘酷的現實。所以我<br />
不會苛責收容很多狗的媽媽,做不好難免,大家都想做好阿。(安安)<br />
阿怪以另一個角度來觀看狗媽媽的收容情形。歐美的庇護所不可能無止盡收<br />
容,而是會接納安樂的選項,維持生活品質,但很多台灣的狗媽媽卻無法接受安<br />
樂。<br />
私人狗場或愛心媽媽的安樂行為,我持正面支持態度,不過很遺憾的,<br />
能在維持狗群生活品質及考量放養風險後,忍著悲痛作此決定的收容者<br />
屈指可數! 多數狗場仍以無限制的大批收容來維持愛心美名,甚至以此<br />
作為募款動機,沒有數量上限的狗場或放養區域,最後招致的是傳染性<br />
疾病蔓延與毫無品質的生存,還有惹來附近民眾抱怨及驅趕下毒等傷害<br />
行為。 最終倒楣的仍是狗,不是以愛心為名的收容者與支持者(阿怪)<br />
19<br />
。<br />
在台灣,狗媽媽用自己愛的方式照顧牠們,她們並不一定是站在動物的立場<br />
著想,其中有幾個衝突的議題,生命的剝奪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看法與作法。例<br />
如為流浪動物決定安樂死 20 以及將大肚狗帶去墮胎 21 。美國的私人收容所比較不<br />
19 見阿怪(2006)。就來談安樂吧。桃園推廣動物保護協會。網<br />
址:http://www.tyacad.org/phpbb2/viewtopic.php?t=6275&postdays=0&postorder=asc&start=230&sid<br />
=54d5b517b33f5b37f8f094b07d2500bc。<br />
20 安樂死爭議不斷,極其複雜,且經常是兩極對立,之所以有爭議,本來就不在於技術的層面,<br />
也不在於主體在死亡過程中有否感受到痛,它的爭議本來就在於社會的,心理的,哲學的,宗教<br />
的層面。見賴芬蘭(2000a)。人與動物的安樂死問題。女人與動物的生態研究室。網址:<br />
http://tw.club.yahoo.com/clubs/Animalwomen/。2006/12/6。我並不反對現階段為台灣受苦的流浪狗<br />
選擇安樂死,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遭致狗友諷刺的經驗,因此目前面對於安樂死的議題,我寧可<br />
保持噤聲。我曾有感而發地發表一篇文章:「因為看了很多,也通通接觸了,我才會說在台灣的<br />
惡劣大環境下,個人的能力有限,以及收容管道遍尋不到的情況下,安樂並不是最壞的選擇,也<br />
不應被汙名。有人若反對安樂,我沒意見,我只希望提出安樂或決定安樂時,能不要受到批判。<br />
本來內心已夠難受了,卻可能要膽戰心驚面對批鬥與冠上莫須有的罪名。只要是站在狗的立場著<br />
想,並且出於愛而安樂狗,應受到基本尊重與設身處地體諒。」<br />
21 墮胎的爭議性很大,端看怎樣看待肚子裏的生命。有些人覺得肚子裏未出生的是條生命,我<br />
們沒有權力選擇拿掉牠們,有些人認為相較出生後的可憐,寧可選擇先墮胎阻攔牠們來到受苦的<br />
台灣環境。不過,我自認為當狗一出生,人類就在為牠們在做選擇了,尤其是流浪犬的處境都是<br />
人類造成的,因此無論是哪一種決定,包括救助可憐的牠們也是一種人類的選擇。<br />
76
會反對安樂死,為了顧及動物的生存品質,他們救援努力後仍無法救助或安頓該<br />
動物,就會傾向安樂,只保留有送養潛力的狗。動物福利是西方的思想,它是從<br />
西方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東方的國情、道德倫理、文化背景與宗教信仰,人與<br />
動物的關係和西方世界竭然不同。以台灣的風土民情而言,大多數人都覺得安樂<br />
死不仁,沒有人能剝奪牠們的生存權 22 。這符合台灣社會上天有好生之德的思<br />
維,文化傳統「好死不如歹活」的慣性思維,這造就放生文化盛行的根源,因此<br />
在台灣到處可在街頭看到流浪的棄犬。<br />
動物倫理或是動物保護,也就是關於人對動物該如何對待,實際上眾說紛<br />
紜,每個狗媽媽各有表述,迴然不同的差異作法。台灣的狗媽媽在實踐與思考動<br />
物議題上,女性情感與宗教思維左右她們的思考模式,因此大部份的媽媽認定安<br />
樂是件殘忍的事,因此她們不一定對西方的動物權,訴求動物權利 23 、動物福利<br />
24 25<br />
與動物解放 概念產生交流對話。因此,不少狗媽媽反對安樂死,縱然牠們身<br />
體殘廢或病重,只要還能吃飯,她們就不吝給一口飯希望延續生命。<br />
有一次我撿到小狗,牠有六個傷口,腳掌、腳根、腳背都爛掉了,一層<br />
皮都沒了,好可憐。我換藥換了二個月,最後訓練牠,只要我一拍牠屁<br />
股,牠就會自動大小便。但我那時工作很忙,根本沒時間照顧牠,因此<br />
我送到一個協會的狗場,後來我不放心有去看牠,結果牠在那邊也很可<br />
憐,那樣多隻狗,由於牠身體癱瘓只能躺著,他們決議要安樂牠,我一<br />
聽很捨不得,心想怎可以,很不忍,當初就是知道他們不安樂才送過去<br />
的,因此我再帶回來。回來後,我帶牠去散步大小便,當我套上輪椅時,<br />
牠很高興地跑,牠會很拼命跑。我會在旁邊說孩子加油,牠就更高興了,<br />
牠前腳一直跳。沒想到某一年冬天很冷,有一天回來牠不見了,我聽說<br />
有二個流浪漢麻布袋一套就帶走了,我想是被拿去吃香肉了。(小可愛)<br />
有些狗媽媽看到大肚狗,會費心地煮好料的食物為牠們進補生孩子。但我發<br />
現越來越多媽媽慢慢地被迫無奈,願意將大肚的流浪狗墮胎,她們看到周遭的惡<br />
劣大環境,縱然不捨甚至有違她們的佛教護生信仰,但卻還是只好接受。黃黃與<br />
綺綺等人都是如此,黃黃篤信佛教,她從剛開始難以接受到最後主動願意:「看<br />
太多了,生下來實在沒什好日子,牠們過得很可憐。」記得綺綺的餵養區域有人<br />
對流浪犬很反感,不時想要驅趕牠們,其中有一隻母狗大肚子了,我很驚訝她轉<br />
22<br />
咪咪的老公曾向一位朋友說:「咪咪收容幾百隻狗,但她身體不好可能也無法活太久。」朋友<br />
馬上回說,「那幾百隻狗要怎辦?你不安樂嗎?」他回答:「我就將那幾百隻流浪狗放走阿,我也<br />
沒辦法,要安樂太殘忍了,我是佛教徒。」<br />
23<br />
提及人類使用非人類動物在原則上即屬不當,我們判斷應當如何對待動物時,人類的利益根本<br />
不應當被列進考慮(Regan 2002:45;引自朱增宏 2003:105)。<br />
24<br />
Regan 認為人類對動物進行各種利用都不算不當,只要做這些事所產生的整體利益高過當時動<br />
物所承受的傷害(朱增宏 2003:105)。<br />
25<br />
《動物解放》一書內容提及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動物均為平等,應予平等考量,其基礎為所<br />
有動物對痛覺的感知,因此,若有其它選擇應避免。<br />
77
變心意,她說「那個真的是沒辦法的事情,那邊的人很討厭牠,生下來很可憐,<br />
一定要捉牠去墮胎。」<br />
看似矛盾的事,我問過許多狗媽媽,她們雖不能接受安樂,但若她們死後由<br />
公立收容所接收她們的狗好嗎?她們一致不信任政府體制內的處理方式,寧可自<br />
己帶狗去安樂死。依往日的接觸經驗看來,此種情況卻罕見,因為她們活在世間<br />
時根本不忍決定安樂,連她們病重臥床時都無法下安樂的決定。因此只要聽聞狗<br />
媽媽死後,遺留了大批的流浪狗無處可去,通常由另一個私人收容所收留,要不<br />
就是交情較熟的狗媽媽緊急接手照顧。更多可見的情況,她的家人違背死者心<br />
意,自作主張將牠們通通送到公立收容所。<br />
三、執著照顧‧至死方休<br />
我研究的對象都是涉入性很深的狗媽媽,無疑的,她們對不歸路的感受特別<br />
深切,她們將救了無法停止越陷越深的狀態,比喻為是一條「不歸路」 26 ,代表<br />
難以回頭。她們告訴我雖然不曾後悔心甘情願,但走到最後陷如此深,當初卻始<br />
料未及。這不是刻意安排的,一旦開始人生即無法重來,若自以為能夠回頭脫離<br />
幾乎很難,因為那顆懸念的心再也放不下了,究竟她們何出此語?難道她們瘋了<br />
不成?<br />
我的受訪者照顧時間都十幾年以上,她們對不歸路的形容大同小異,有一<br />
個狗媽媽感受強烈,她篤定告訴我「我跟你說,會救就不會放棄了,一旦開始沒<br />
完沒了。」記得毛毛有一次也笑著跟我說「這種好像得病,好像末期癌症沒藥救<br />
了,細胞一再擴散,只要切掉細胞,還會再分散,根本沒有切完的一天。」狗媽<br />
媽一旦開始餵養,怎樣辛苦也不忍放手,擔憂放手後要怎辦呢?畢竟只要時間一<br />
到,牠們就會出現等待她們前來餵食。<br />
我以前有工作時,做到累得沒有力氣,回到家裏就軟下來。我累到坐到<br />
椅子上,一下子就閉上眼睛了。但忽然想到還沒養狗,我怕牠們還在原<br />
地等,拖著命還是要去外面餵狗。說也奇怪,這時體力就來了。養狗真<br />
的很難停手,不可能啦!以前在外面餵養就像在吸瑪啡一樣,無論如何<br />
辛苦都無法停手。有人會勸我,現在這一批狗養完就不要養了,但根本<br />
不可能,因為只要出去看到狗,心就會牽動。養狗的人出門眼睛只會看<br />
貓或狗,人站在我面前都沒看到,這不知是什力量一直吸,真的很奇怪。<br />
有些狗媽媽覺得救狗讓她很痛苦,但她還是要去做,其實也沒人逼他<br />
們,做到大家罵死你甚至打你,可是他們還是要做。這真的是很奇怪的<br />
一件事,救狗不但要花費勞力和精神和金錢,做得要死要活,不過大家<br />
還是要一直做一直拼下去。(黃黃)<br />
26 一位年輕志工告訴我:「你怎那樣笨來碰狗,救狗是一條不歸路,還是救貓好了,因為貓只要<br />
實施 TNR 數量就會控制,不會再增加,但狗的問題較多,就算TNR,還是有人不斷得丟狗在<br />
你的區域。」<br />
78
咪咪收養了幾百隻流浪狗,她告訴我,除非困頓到不行或走投無路,才會考<br />
慮安樂牠們,否則會一直養到狗死掉為止,只要救了就不可能再放牠再度流浪。<br />
養狗養了十幾年了,我一直在想這些狗怎不快點死?我就比較輕鬆,我<br />
真得很累,也不是堅持,就是現在放棄這些狗,這些狗要怎辦?要去哪<br />
吃?養了我就不可能再放回街頭不管,那是責任感的問題。這條路真的<br />
是不歸路,因此我會養到我剩最後一口氣為止,當我不能動時就不能養<br />
牠們,到時我會自己選擇安樂。不過我倒是滿希望那一天快來到,我就<br />
能脫離苦海了。(咪咪)<br />
幾位狗媽媽告訴我:「沒辦法,我已經摸到牠了,能怎辦呢?」、「唉!沒辦<br />
法吧,拿自己沒辦法吧!我就是沒辦法看了不去救,除非眼睛瞎了吧!」。從她<br />
們的話就可知道不歸路有個特色,「看見、聽到、摸到」是真實感受的憐憫之情,<br />
只要她們「看見、聽到、摸到」流浪動物,心裏就會難受不得不接手,甚至沒能<br />
力接手,內心煎熬產生掛念與心疼 27 。<br />
「看見、聽到、摸到」也是救狗圈的手段策略,安安講敍當初為何開始餵<br />
養的原因。<br />
當初會開始餵養外面的狗,開始的起因並不是刻意的,因為有個退休老<br />
兵帶我去看某個區域,介紹那邊的八十幾隻狗,叫我過去幫忙。他帶著<br />
我到處介紹,這邊有哪些狗,那一邊有什狗,然後一邊稱讚我,聽說你<br />
很厲害,專門救狗。他說「以後有你加入,這樣子我就可以退休了」。<br />
當時我聽到這句話,我就知道一進去就完蛋了,結果變成都是我在弄。<br />
最近我多了一條路線,那是圈內人狗友請我幫忙餵貓,因為她說真的找<br />
不到人餵了。其實我餵狗已餵到身心俱疲,經過一段時間考量,本來打<br />
算拒絕她的要求的,結果我經過時,看到那區域的躺在地上的貓屍,覺<br />
得牠們可能因為肚子餓覓食時被車撞,真的很可憐。想一想注定逃不<br />
過,我就接手去餵,本來狗事就多了加上餵貓,我更累了。(安安)<br />
我給琴很多錢,我孩子告訴我,她是被我害的,才會有勢無恐地收狗。<br />
她有了經濟的支持靠山,就沒克制的一直撿狗,才會越撿越多。記得有<br />
一次狗舍因為沒有遮蔽,結果大雨打下來,地上都淹水了。琴打給我說<br />
正抱著狗在水裏一直哭,因為一直淹水,狗不知要往哪裏逃。我聽了很<br />
緊張,連忙從我工作的退休金優利裏,拿十萬元蓋雨棚。(阿桑)<br />
27 記得小花花曾跟我說她沒有手機,因此我發現她沒有狗友打來請求援助,她少了「看見與聽<br />
到」這方面的困擾。<br />
79
有一次我半夜一點多,我跟著疏洪去餵養,黃黃打電話來跟我某一隻狗的<br />
情況,希望我前去援助。疏洪聽到後警示我:「十二點後應要關機,不能再讓狗<br />
友打來,你不是超人不能全天侯待命,而且要懂得拒絶別人。」疏洪為了避開這<br />
方面的困擾早就有一套防範措施。<br />
我餵狗都帶口罩等,因為不想和人家認識打交道。這種事情生蛋沒有,<br />
生老鼠屎的一大堆。我的人不麻煩人家,但也不給人家麻煩我,不熟的<br />
人請我幫忙,最後醫藥費都變成我要付的。我認為自己看自己救,我看<br />
到這一隻狗我救,你看到你那一隻自己救。我也懂得拒絶別人,這不是<br />
有錢有閒就可以救,搞得精疲力盡,連人都不如。(疏洪)<br />
這條不歸路該如何解套?我聽到一些有趣的防衛式說法,例如狗媽媽彼此開<br />
玩笑若要出門,最好眼睛都閉下來,不然就儘量不要出門,以免看到街上的流浪<br />
狗。有人形容的更妙,她說不出門都有別人放一窩小狗,或有流浪犬跑到家門口,<br />
等著你打開門看牠。她們常告訴我「不想看了,越看越多,哪有那個能力養那樣<br />
多。」我剛開始聽到這類說法時,感到十分沮喪與辛酸,這反映她們一種集體想<br />
要逃避的心情,以及台灣大環境滿街流浪犬的事實。尤其我的受訪者都養了十幾<br />
年了,眼前不知換了多少張新的面孔,原有的狗死了還有新的棄犬出現街頭填補<br />
原有的空缺,因此根本無法停手。不過還是有狗媽媽不斷地嘗試放手。記得瘦子<br />
曾告訴我為何不可以控制?我和旁邊的媽媽驚訝地問她:「你今天可以停止不養<br />
嗎?」她笑一笑跟我說「沒有啦,我只是說不要再擴大餵養版圖了。」她提出的<br />
方法的確是個保守的辦法。<br />
其它的狗媽媽,例如小秋與自生自滅在照顧的同時,正在想辦法放手。<br />
這是一條不歸路,做到死為止,雖然很難放開,但你沒看我慢慢在放手<br />
了。若有別人跟我說哪裏有可憐的小狗,要我帶流浪犬回家,我就跟他<br />
說你不要告訴我,我沒辦法,我只能幫你送狗,但在送出去之前,你自<br />
己要找地方暫時收容。我最近還聽說有一個地方,有人將一塊工地圍起<br />
來,準備讓裏面的三隻流浪狗無法出來找食物餓死。有個太太一直叫我<br />
去看,我都不想去看。我現在手上有三隻狗,藉由那位太太的關係都留<br />
在我手上,因此我不要跟她去看,她只是要拖我下水而已,我看了會撩<br />
下去。我都跟大家說,我們先講好,你能安置這一隻狗再說,我才會去<br />
看幫忙處理,否則看到可憐的狗後,心裏會一直想著那一隻狗,最後就<br />
變成我的事。(小秋)<br />
救流浪犬何止累,但我累就算了,只是現在不想培養感情了,因為我養<br />
在外面的流浪犬都會被捉走。每次我都會想要不要領回來,帶回來放回<br />
80
去原地再被捉,好像也是白領,因此我現在去餵狗時,不再數有幾隻,<br />
少掉幾隻了,走到這個地步只好裝傻,否則牠們的事情真的沒完沒了<br />
的。但說是這樣說,怎可能不知道,很難啦!只能儘量餵了就走,不要<br />
去摸牠們比較沒有感情,不要去注意有多少隻,才不會掛心牠們怎不見<br />
了。(自生自滅)<br />
博士告訴我,她想要休息停止餵養,她已和老公約定好了:「我一定要搬離<br />
這裏,為了我的生活品質,否則沒完沒了的,根本無法斷絶,唯有搬家才能停止<br />
餵養。」但我卻看到很多狗媽媽,身體雖然不在現場,但一顆心卻因為掛心牠們<br />
還要事先到處打點。<br />
我有一次生病住院都無法去餵養,我花錢請人家幫我餵狗,但也餵地亂<br />
七八糟,讓我很不放心。雖然我遠在金門休養,也只好一直打電話叩人<br />
幫忙,找很多狗友或別人幫忙。(寶寶)<br />
我當初離開台北來到花蓮讀書時,有一絲寄望可以切斷救狗,但繞了一圈卻<br />
還是一樣。因此,切身經驗告訴我,身體雖然遠離,內心若沒完全斬斷,依然會<br />
重起爐灶。芽芽、咪咪和可可曾經有機會切斷養狗,她們因為生病或出國甚至生<br />
小孩,因此暫時放棄救狗,人生繞了一圈,如今她們還是依然在照顧流浪狗。<br />
我覺得我生錯地方了,台灣這種爛環境,我真的待不住了,我很想快點<br />
離開台灣,我曾去過澳洲一陣子,但我知道我根本離不開台灣,就算在<br />
外國我的一顆心也會懸著,不斷擔心台灣流浪犬的情況。這是條不歸<br />
路,依我陷下去的情況,很難再回頭了。(芽芽)<br />
有一次我生了一場大病,是一種很嚴重的惡性腫廇,剛好當時我養的流<br />
浪狗也通通都被附近住戶毒死了,我的狗場也被政府拆掉了,因此就暫<br />
時沒養狗,開刀住院半年養病。我後來生病好了,當時應立即結束不再<br />
弄狗,但沒想到再度回來。現在都在想,早知道當時就趁生病時一次結<br />
束不再碰狗,也不會搞得如此了。(咪咪)<br />
我原本以為她們能持續救十幾年,個性上必然有著某種強桿或毅力。安安與<br />
自生自滅卻告訴我,她們對於其它的事情都是三分鐘熱度,一下子放棄不幹了,<br />
唯獨對救狗卻是頑強的固執。可可告訴我「人家都覺得這件事情,我死都不會改,<br />
很固執,好像是吧。」咪咪照顧幾百隻狗,老公提到她印象最深刻:「她對狗擁<br />
有堅定的意念,那是一種不求回報的精神,一旦踏入,就是全年無休的工作了」。<br />
沙皮從東南亞來到台灣定居,因為曾遇到過性騷擾,因此她連白天都有點怕<br />
出門,但她為了餵養牠們卻得鼓起勇氣出門。<br />
81
我個性異常地膽小,平常外面有風雨時,我待在家裏都會害怕,但現在<br />
我竟然連颱風天也會出門餵養,站都站不穩,有時人都快被吹走了,心<br />
裏會想哭又想笑的想說自己到底在幹什麼,實在太執著了。(沙皮)<br />
我發現當初在建國花市認識的狗媽媽,現在再回去看依然全是熟悉的老面<br />
孔,年輕的面孔卻經常在變換,從中可以知道世代間救狗韌性的差異。外界認為<br />
狗媽媽個性太偏執,我的認知是她們救狗的執著,亦可稱為擇善固執。此事誘發<br />
她們生命中最難放棄的部份,產生極大的關愛力量。她們在這條不歸路為何能一<br />
直走下去?若不是很執著怎能一直撐下去呢?這是她們救動物最大的韌性來<br />
源,否則沒有勇氣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還能一直孤軍奮鬥下去。<br />
動保成員長期以來飽受社會異樣眼光有關,為了流浪貓狗,時常得忍受<br />
許多人的威脅、辱罵。 性格如果不夠強烈,很難以在這條路上走下去,<br />
長期下來造就了大部份動保人的剛烈性格,這種特質幫助了許多狗媽媽<br />
或愛心爸爸撐過了數十年的社會壓力 28 。<br />
28 見小賊(2006)。就來談安樂吧。桃園推廣動物保護協會。網<br />
址:http://www.tyacad.org/phpbb2/viewtopic.php?t=6275&postdays=0&postorder=asc&start=26。2006/2/14。<br />
82
多元田野的足跡與省思-一個漢人教師與蘭嶼學生的生命故事<br />
周建志<br />
這是一個漢人教師與一群蘭嶼學生的故事,是關於他們人生中的一段生命經<br />
驗,這些故事正上演著且仍持續進行著……<br />
1995 年 8 月 28 日下午四點,多尼爾 228 1 的小飛機從高雄小港機場升起,背<br />
著夕陽餘暉盤旋在高屏平原的上空往南飛行,在楓港附近左轉穿過大武山直飛東<br />
邊的小島-蘭嶼。這是我第一次帶著這麼多的行李離開我生長的地方,記得要飛<br />
的那一天家人並沒有來送我,因為我不喜歡送別的場面,而家人也早已習慣我的<br />
離家。雖然從國中開始離家的生活,一路從國高中的台南到大學的台北再到當兵<br />
的桃園,早已習慣帶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奔馳於高速高路或火車上。但這次當飛機<br />
起飛的那一瞬間,我心裡有一種很深很深的感覺,感覺好像這次是我真正的遠<br />
行,要去一個很遠很遠未知的一個地方,心中有許多的不安不捨。<br />
結果在這個小島上一待就是九年,許多親朋好友、蘭嶼人甚至在蘭嶼遇到的<br />
觀光客都喜歡問我為什麼當初會來蘭嶼?為什麼可以在蘭嶼待那麼久?一直以<br />
來我都不去想或不願去面對這個問題,但在田野訪談及論文書寫的過程中,我漸<br />
漸瞭解原來我不僅僅是在寫蘭嶼學生的故事,而是在這個時空中我也是故事中的<br />
一份子,我也參與了遠離家鄉做為異鄉人的演出。<br />
本研究是透過書寫鋪陳描繪出漢人教師與蘭嶼學生離家與返鄉的生命故<br />
事。原本論文的設定是探討有關「蘭嶼青少年在台灣的生活適應」,但在一次跟<br />
受訪的學生說明我的論文方向及訪問他們的理由和原因之後,學生突然說:「很<br />
好阿!老師你來幫我們寫蘭嶼人在台灣的故事。」這給了我一個更明確而清楚的<br />
方向與想法,透過「生命故事」更能清楚呈現他們的生活樣貌並傳達給更多人瞭<br />
解蘭嶼人的困境與適應及在他鄉的日常生活。若以量化的問卷方式或傳統標準化<br />
的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將無法呈現「生命故事」(life stories)的深度。因此<br />
本研究將採用「質性研究」進行田野工作,透過訪談、實地觀察及網路互動,利<br />
用混合研究方法取得豐富多元的田野資料,並透過研究對象與研究者之互動與信<br />
任,使其「主動」述說生命故事,成為合作研究的主體,而非研究的客體。<br />
本文首先將以多元田野場域來做探討,說明什麼是田野、多元的田野場域及<br />
網路是另類田野及在地觀察的場域;接下來提出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br />
架構;最後則是反省研究者的角色扮演及觀看的視野。<br />
1 德國製多尼爾 228 飛機,是目前德安航空公司飛行綠島、蘭嶼、望安、七美等離島所使用的<br />
19 人座小飛機。筆者於 1995 年到蘭嶼時,當時台安航空公司還有飛行 9 人座的更小飛機,可以<br />
直接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上。<br />
83
一、 多元田野<br />
(一)什麼是田野?<br />
人類學者相信知識的生產來自「田野」。根據郭佩宜、王宏仁(2006)指出<br />
「田野工作」(field work)的誕生,是 Malinowski 於初步蘭島(Trobriand Islands)<br />
進行研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殖民該地的英國與波蘭分屬不同陣營,他因<br />
此被迫留在當地超過兩年,因緣際會,發覺長期田野工作對於異文化的研究助益<br />
良多,跳脫「搖椅上的人類學家」之污名。1922 年是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中劃時<br />
代的一刻,Malinowski 出版他在初步蘭島研究的第一本書《南海舡人》(Argonauts<br />
of the Western Pacific)後,長期的田野工作-與當地人共同生活、學習當地的語<br />
言和文化、參與觀察-成為人類學方法論與認識論的核心。「田野」已成為人類<br />
學者的成年禮,沒有經歷超過一年的田野洗禮,就無法「轉大人」,成為「專業」<br />
人類學家。田野研究因此成為人類學領域重要的學術研究方法。<br />
傳統人類學的田野,是研究者依據其研究主題選擇一個地點,花許多時間 2<br />
「蹲點」,與當地人生活在一起、學習其文化,進行訪談、觀察及參與獲得田野<br />
資料。然而「田野工作」就僅限如此嗎?研究者在進入田野之後的「情緒」起伏、<br />
「身分」轉換及「文化」衝擊又是如何呢?筆者將引用「田野筆記」來呈現在這<br />
段田野過程中的情緒起伏、自我追尋與成長的紀錄。<br />
如前所述,原本論文主題是「蘭嶼學生在台灣的生活適應」研究,筆者是站<br />
在外圍俯看的角度來進行。但經過「田野工作」的訪查「洗禮」,我發現與研究<br />
對象竟有相類似的境遇。正如夏曉鵑在《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br />
現象》一書中,提到在研究外籍新娘時「自身反照」(reflexive)的重要性。當研<br />
究他者的同時,對研究者而言似乎也同時在探討自身的生命歷程。夏曉鵑覺得她<br />
遠度重洋的留學經驗與這些外籍新娘處境有些類似,同是為了追尋夢中的更好的<br />
生活,遠度重洋離鄉背井,同樣地面對陌生國度中的複雜情緒。她發現這些「外<br />
籍新娘」不再只是她處心積慮想接近的研究對象,她們變成研究者生命的一部<br />
分,如夏曉鵑所說「我開始看見自己生命歷程和我的研究對象間,不可抹滅的類<br />
同」(2004:15)。<br />
田野從新喚醒我對「自我的認識、自我的追尋與成長的歷程」,也因此才有<br />
「漢人教師與蘭嶼學生的生命故事」之產生。誠如郭佩宜、王宏仁指出「深刻的<br />
田野不只是自外的『工作』,田野或多或少轉化了研究者對知識、對世界和對自<br />
我的認識,也是自我追尋與成長的歷程」(2006:i)。<br />
除了時間影響田野的轉變外,筆者離開蘭嶼,研究對象來到台灣,如此空間<br />
的流動所創造出多元的田野,在筆者的研究資料取得與研究面向都佔有很重要的<br />
位置,因此接下來將以「多元的田野」做分析探討。<br />
(二)多元的田野-蘭嶼、台東機場、台灣流動的「家」及網際網路<br />
2 現今的研究因為畢業的因素,真正的田野工作可能花不到幾個月。當然時間長短不是研究好壞<br />
的唯一判準,但過短的田野就不免讓人對其是否真正瞭解或進(浸)入當地有所質疑?<br />
84
隨著社會與科技的進步,人們已不再「固著」一地,,而是經常在「流動」。<br />
郝明義提到「1990 年 World Wide Web 的瀏覽器軟體將網路與電郵普及到全世<br />
界,使得人類的移動不只在真實世界裡無拘無束,甚至進入到虛擬的空間。以前<br />
出門、出差、旅行、留學、遷徙、漫遊、流浪、移民及朝聖這些種種不同的移動<br />
方式,名稱不同,定義不同,性質也不同。但 1990 年代之後,這些移動方式的<br />
界線卻開始改變與泯沒;移動的起點與目的地,故鄉與他鄉,家與居處,也都跟<br />
著開始產生本質上的混合(2003:4)」。「移動」(mobility)已成為現今社會現象<br />
與趨勢,因此隨著研究對象的移動,「田野」將不再固著於一地而是隨著研究者<br />
或是主要報導人流動。昔日定居不動的報導人,在時勢潮流及科技發展的當下,<br />
也不斷在遷移,從部落到都市、家鄉到他鄉、無以為家或是到處為家。<br />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一直在思索我的「田野」在那裏?事實上,我已經在蘭<br />
嶼「蹲點」蹲了九年,但這樣就夠了嗎?這就是我的田野嗎?因為論文研究的關<br />
係,需要時常與學生聯繫,因此我發現除了蘭嶼中學、他們的住家、海洋、甚至<br />
整個蘭嶼島之外,幾乎只要可以跟學生接觸到的地方都成了我的「田野現場」,<br />
甚至花蓮鳳林筆者的住居、台東及蘭嶼機場、報導人台灣的暫時居住地(高雄、<br />
潭子、八德、南崁及三重)及網際網路,這些不同的接觸場域或所在點都是我所<br />
必須討論的田野所在。以下將針對不同的田野場域分別敘述:<br />
1. 蘭嶼<br />
除了從 1995 至 2004 這九年在蘭嶼的經驗之外,離開蘭嶼後仍然與當地有所<br />
聯繫,並於每年寒暑假回蘭嶼探望或田野資料收集。並於 2005 年及 2006 年暑假,<br />
與幾位同事及蘭嶼社區團體,號召蘭嶼的大專生(都是曾經教過的學生)回蘭嶼<br />
參加「蘭嶼大專青年返鄉服務隊 3 」進行認識蘭嶼及為鄉服務的工作,因此這兩<br />
年的暑假除了協助營隊的進行之外也進行田野的訪調。這兩次的活動共有二十多<br />
人次參與,兩年都參加的約八位,這些參與的學生就成了主要報導對象。第一年<br />
因為負責培訓這群學生及舉辦蘭嶼深度旅遊的活動,因此比較沒有時間進行深入<br />
訪談。第二年服務隊的型態有所調整,因此我能純粹以研究者的身分觀察這些返<br />
鄉學生對蘭嶼的認同與歸屬,進行深度訪談。<br />
2. 花蓮鳳林-筆者的住居<br />
2004 年為了到花蓮東華大學族群所進修請調到花蓮鳳林國中,我沒有選擇<br />
住在學校宿舍而是在外租房子-一層公寓三房二廳,一來是東西太多,二來是希<br />
望將來親朋好友來花蓮有地方可以住。正如預期接待了不少蘭嶼學生,有的是專<br />
程來花蓮看我;有的是來考試借住;有的是來散心紓解;更有一次接待十多個學<br />
生的畢業旅行團。可惜剛到花蓮的前二年,自己的論文方向未定,加上有學生來<br />
訪非常興奮的盡地主之誼,而沒有想到可以進行研究訪談都只是日常生活的對<br />
談。事後發現這種輕鬆自在的交談,反而可以對日常生活進行更多的探討,而這<br />
也成了另一種田野。因為帶他們到花蓮四處走走看看,當他們看到一些社區、民<br />
3 此服務隊由蘭嶼山海文化保育協會蘇瑞清先生及蘭嶼中學陳淑貞老師、林慈翎小姐主辦,筆者<br />
負責支援及協助營隊活動的進行,服務隊的成立及內容於第五章詳述。<br />
85
宿及餐廳都非常有感覺,會聯想到與蘭嶼相關的種種,這是本研究很重要的資<br />
料,給予筆者很多在結構訪談中無法觸及的面向。來花蓮的學生有將近三十人<br />
次,正式訪談錄音三位。<br />
3. 台東及蘭嶼機場<br />
「機場」是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田野現場,包括台東機場及蘭嶼機場。每年寒<br />
暑假筆者都會到蘭嶼進行田野資料蒐集,而在進出機場時常常會遇到學生,也就<br />
順勢坐下來聊聊。在 2007 年寒假,「台東機場」成為筆者訪談的田野。依據多年<br />
的經驗知道學生大概返鄉的時間及他們的習性,不會事先定位且機位不好訂加上<br />
東北季風肆虐經常停飛,於是大多數學生在這段時間要進去蘭嶼都是以補位的方<br />
式,其候機的時間非常長且無聊,所以我有充足的時間 4 「守株待兔」進行訪談。<br />
在機場的好處是可以遇到許多學生,但缺點也因為太多學生,所以要一一寒喧而<br />
不能進行比較正式的訪談。在機場三天共遇到二十多位學生,而正式訪談錄音的<br />
有七位。另外,因每個人的候機時間不同,所以有幾次正聊到重點時卻因為搭機<br />
時間已到而必須中斷訪談,只好下次再找機會。因為蘭嶼的特殊性,所以「機場」<br />
成了一個重要的「田野現場」。如今每次進出蘭嶼,在機場候機不再是看報紙打<br />
發時間,而是我田野訪談的最佳時機。<br />
4. 報導人台灣流動的「家」<br />
以往在蘭嶼中學任教時,每年九月開學總是會跟學生分享討論這長長的假期<br />
大家都做些時候?聽到最多的答案是到「台灣玩」。但在仔細問都玩些什麼呢?<br />
學生的答案可能大多是在家睡覺看有線電視,或是逛逛夜市買些衣服鞋子。雖然<br />
在我們一般人的眼裡這根本不叫「玩 5 」,但每年暑假的「台灣行」卻是蘭嶼學生<br />
樂此不疲的「集體行動 6 」,甚至每年總有幾個學生玩到開學還不見蹤影。實際上,<br />
這些學生的哥哥姐姐在台灣賺的錢並不多,而且每天工作也沒時間帶他們去哪裡<br />
走走,所以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是待在出租的公寓看有線電視。至於沒能及<br />
時回來開學,大多是要等哥哥姐姐領錢才能有機票錢回家,甚至曾經等領錢等超<br />
過一星期學生仍然沒回來,於是老師只好親自去台灣將學生帶回來。因此筆者一<br />
直很好奇,想瞭解學生暑假在台灣的生活到底是怎麼過的。<br />
1997 年首次有機會體驗蘭嶼學生在台灣生活的真實樣貌,那年暑假因為要<br />
升國三留了幾個學生下來輔導,結束之後我要回台灣便順道帶著學生到台中縣潭<br />
子鄉找他的哥哥姐姐,並在那邊過夜。他們租的是大樓公寓一層中的其中一個房<br />
間不到二十坪卻擠了六、七人,大家是蓆地而睡或帶著棉被到大樓屋頂睡,喜歡<br />
睡屋頂的習慣 7 並沒有因為在台灣而有改變;此外,蘭嶼年輕人酷愛打籃球總是<br />
4 2007 年寒假我在台東機場三天,看到一些學生每天一早到機場等到下午,直到第三天才補到<br />
位置進去蘭嶼。除了漫長時間的等待外,住宿及生活費都必須多支出,甚至因不確定補不補的到<br />
位置而不能買一些生鮮食品回家孝敬家人,因旅社及機場沒有冷藏服務,怕壞掉。<br />
5 因為一般人出國會排滿行程,馬不停蹄的到處觀賞,而不會出國去只是看電視或睡覺。<br />
6 幾乎所有的國中生都會到台灣,只是時間的長短不同,所以暑假在島上很少看到國中生。家長<br />
A:「覺得小孩很可憐,一直在島上,所以暑假就讓他們去台灣玩玩、買買東西,高興一下阿。」<br />
7 在蘭嶼,傳統的住屋有涼亭,所以夏天天氣炎熱大家習慣睡在涼亭。但改建成水泥的國宅之後,<br />
不但空間小不透風且散熱不易,所以學生習慣帶著棉被睡在屋頂,等天亮讓太陽自然叫醒。即使<br />
86
在工作下班後到公園的籃球場打球或聚集聊天,這是他們最大的休閒娛樂,我常<br />
問他們下班(他們從事的工作幾乎都是極耗體力的粗工)已經累的要命怎麼還有<br />
體力打球?結果學生回答:「打球是不同的體力,沒有打才累,愈打會愈快樂,<br />
打完回家再沖個冷水澡真的很爽!」結束兩天的體驗再到台北三重找另外的學<br />
生,如果台中潭子學生住的「擠」,那麼台北顯然更居不易,一家人住的「又小<br />
又熱又陰暗」,我是和他們一家五口一起睡客廳地板,很難想像這是他們在台灣<br />
住的地方。這是我的初體驗卻是大震撼,原來他們在台灣是這樣過生活的。<br />
2007 年暑假因為論文的關係,我再度到台中潭子、桃園八德及台北三重去<br />
觀察蘭嶼學生在台灣的生活。這一趟的旅程與十年前不太一樣,當時只是純粹瞭<br />
解學生在台灣的生活,學生還是就學的國中生,而我也還未帶著「研究」的眼光<br />
觀看;而這一次則是刻意去做訪談,學生已經二十多歲成年且在職場多年,其人、<br />
事、時、地、物及心境完全不同,我觀看的內容也有所不同,茲將 2007 年 8 月<br />
22 日的田野筆記摘錄如下:<br />
下班後與忙樂回他和女朋友租房子的地方,在窄小的巷弄穿梭許久,終<br />
於在一堆高樓的後面找到他們的家,是一整排老舊平房的其中一間,應<br />
該是以前眷村的房子-窄小陰暗,前後房子只隔不到 20 公分的距離,<br />
鄰居講話、罵小孩、電視的聲音都可以清楚聽到。他說他們沒裝熱水器,<br />
但有第四台消磨時間。女朋友剛結束前一個工作目前在家做家庭代工,<br />
忙樂在大理石工廠一天工資 1150 元,一星期休一天,如果有加班,三<br />
小時算半天工資(一小時 170),一個月收入 28000 元左右。付了房租、<br />
機車貸款、手機費、水電油錢及吃的,薪水就這樣沒了。連加油的錢都<br />
是先跟公司借 1000 元,再從薪水扣。<br />
在這個流動的「家」,我所觀察到的是十年來蘭嶼人在台灣的生活似乎沒有<br />
太大的改變,他們在都市討生活依舊不容易,生活品質沒有多少的提升,薪資依<br />
然只能溫飽而無法剩餘。但如果他們留在蘭嶼呢?是不是連一天 1000 元都賺不<br />
到而只能在島上閒晃呢?這似乎是一種弔詭但卻是蘭嶼人現實中必須去面對的<br />
問題。透過他們在台灣暫時的「家」之參與觀察,將能提供給筆者更多豐富的資<br />
料去瞭解蘭嶼人在都市生活的真實樣貌。<br />
(三)網路是另一種「田野」,也是「在地」觀察<br />
在這些多元的田野中,「網路」是一開始研究時未曾特別留意的「田野」觀<br />
察現場。但在與學生透過網路即時通、e-mail 及部落格聯繫之後,報導人卻有如<br />
滾雪球般的愈串愈多,甚至許多「失蹤人口」都在網路中「現身」了。因此,許<br />
多豐富的學生資料就源源不斷湧入。以下是幾位學生也是主要報導人,藉由電<br />
冬天只要不是寒流仍然有許多人裹著厚後的棉被睡在屋頂。筆者在蘭嶼任教時,也常在假日跟學<br />
生睡在屋頂,看著星星、聽著浪濤聲、吹著海風進入夢鄉,隔天再被熱熱的太陽叫醒。我們戲稱<br />
這是「滿天星級」的民宿。<br />
87
話、MSN 即時通訊將各種訊息與我分享的部分內容。<br />
「老師,小明要結婚了,另一半是學妹,你有要回蘭嶼嗎?你要來參加<br />
嗎?阿娟也要結婚了,有四個月的身孕了,另一半是學長。還有好多八<br />
卦,下次在告訴你。」(2007/06/22 幸兒的 MSN)<br />
「老師我有小孩了,我傳照片給你看。」(2006/10/20 文生來電)<br />
「老師六月有豐年祭,你要不要回去,很多同學都要回去,我可以幫你<br />
寫補位,你可以睡我們家屋頂,我跟你一起睡。」(2007/05/20 烏細的<br />
即時通)<br />
「我四技二專考的不錯,391 分跌破大家眼鏡,不過不知要填那裡?老<br />
師建議我推甄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域運動管理系」(2007/06/10 豪豪即<br />
時通)<br />
現在的年輕人對網路都非常地熟悉也非常依賴,甚至說寄情或沉溺在網路的<br />
虛擬世界中,當然也從網路中找到慰藉或抒發的管道,蘭嶼學生當然也無法置身<br />
這波潮流之外。反而因大家四散在台灣這個不太熟悉的環境中,「網路」成了非<br />
常重要的媒介-迅速且省錢,聯繫起蘭嶼學生的網絡(network)。他們在雅虎奇<br />
摩網站中設了各屆及各村的家族 8 ,在這裡面互相關懷、互相吐槽、互通訊息,<br />
在其中可以瞭解他們在台灣的生活情形。此外,最近興起的「部落格 9 」更是充<br />
分展露出他們的生活聲息與心情故事,許多人日常生活的「生命故事」就在此延<br />
展,因此成了筆者收集資料了解他們的的另外管道與平台。<br />
「部落格」是目前年輕人的一種心情抒發管道、展現自我、與人溝通方式、<br />
一種心情書寫更是一種文化的書寫。蘭嶼學生彼此散居各地加上對台灣不熟悉及<br />
朋友不多的情況,唯有透過「網路空間」聯繫起「流動空間」與「地理空間」。「網<br />
路」成了蘭嶼學生日常生活打發時間或紓解壓力的重要管道 10 ,因此透過部落格<br />
的內容是一種瞭解研究對象的「在地」觀察。在現今社會趨勢及科技發展下,傳<br />
統人類學的「蹲點」,必須依據現今「移動」的概念而有所調整與轉變。此外,<br />
8 由於網路家族的興起,幾乎每一屆的學生都會有家族作為聯繫與分享的園地。以下列舉幾個網<br />
址:屬於蘭嶼中學 32 屆ㄉ回憶 http://tw.club.yahoo.com/clubs/mehoem/。<br />
蘭嶼中學第 30 屆同學俱樂部 http://tw.club.yahoo.com/clubs/jon_wei/;<br />
蘭嶼中學第 27 屆 http://tw.club.yahoo.com/clubs/h9e8r7o6hero/。<br />
蘭嶼東清聊天室 http://tw.club.yahoo.com/clubs/TBU/<br />
9 部落格藉由網誌、相片、留言、影音、名片與好友等功能,及輕鬆容易操作(相對於網頁製作),<br />
成了現今網路族的最愛。根據番薯藤「2005 年台灣網路使用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有 61.2%的<br />
網友擁有自己的部落格,用網路寫日誌已經儼然形成一股風潮。除了 25.1%是網誌熟手、已經具<br />
有兩年以上的撰寫經驗外,有 64.7%的網友表示是近半年才開始寫網誌。另外,約六成的網友表<br />
示會瀏覽別人的部落格,22%表示會在別人的部落格發表評論,顯示部落格具有社群、互動、串<br />
聯的功能,扭轉了原本資訊僅能由大眾媒體傳播的方式,部落客人人都能是記者與資訊傳遞者,<br />
使得全民媒體儼然成型。(http://survey.yam.com/survey2005/index2.html,2007/10/09 瀏覽)<br />
10 就讀虎尾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經營系的英傑,有天在即時通密我。老師要求他們做一個論文的<br />
作業,但他不知論文要做什麼題目?怎麼寫?於是經過將近二個小時的筆談溝通腦力激盪決定以<br />
「蘭嶼學生在台灣的休閒活動」做主題探討,詳細對話內容見附錄。。<br />
88
在研究倫理中一直「理不清」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關係,在網路中卻是可<br />
以達到一種平衡。因為研究對象是在最安全愉悅下,以自己習慣的熟悉的方式,<br />
抒發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感與情緒,並不是在與研究者面對面的訪談下說出自己的<br />
想法與答案,而是「自然」的呈現,這是最能傳達研究對象的的心聲與他最感興<br />
趣的事物,因此這樣的資料應該更彌足珍貴。雖然網路有真有假、有誇大、有簡<br />
略,這些資料都必須再經過篩選,甚至再追蹤訪談,以便獲得更多元更豐富的訊<br />
息。在此,關於網路資料取得、匿名關係所衍生的問題,因不是本研究之重點故<br />
不予深入探討。<br />
筆者將運用在網路上與學生的互動所獲得的資料,作為理解他們在台灣生活<br />
的另一種「實境」,加上田野訪談及田野筆記作為後面篇章研究論述的重要依據。<br />
二、研究方法<br />
(一)研究對象<br />
在蘭嶼,因為學生三年都住校,朝夕相處,師生的關係與台灣一般的國中相<br />
較是更為深厚。我們的身分除了是老師之外更常扮演父母的角色,所以除了國中<br />
三年的學校生活之外,其畢業後的發展更是關心的延續。至今筆者和 1995 年剛<br />
到蘭嶼所教的學生仍然有連絡,每當學生有機會回蘭嶼都會到學校來看老師,因<br />
此瞭解他們在台灣就學與就業的境遇而萌生此一研究主題。每當與學生談及我想<br />
研究的主題,他們都非常有興趣也願意分享他們的故事與經歷,只是他們會害羞<br />
的說:「不好意思吧!講這些好嗎?我的故事可以講喔!」<br />
田野資料的取得主要有:一、平時的訪談:經由平時的電話聯繫,瞭解學生<br />
在台灣生活的情形,若有相關論文研究方面的資料,筆者會以田野筆記方式紀錄<br />
下來以利將來分析之用;二、在蘭嶼的訪談:2005 及 2006 兩年的暑假舉辦「蘭<br />
嶼大專青年返鄉服務隊」,參與的學生為主要報導對象,進行深入訪談及錄音;<br />
三、在台灣的訪談:2007 年暑假到台中潭子、桃園南崁及台北三重等地方,實<br />
際到其工作或居住的地方進行訪談及錄音;四、網路:2004 年離開蘭嶼之後,<br />
與學生的聯繫透過網路即時通訊的機會大增,因為透過網路可以隨時聯繫上學<br />
生,瞭解其最新訊息,又比較省錢。甚至透過部落格的網誌,可以知道這些學生<br />
的心情心事,因此成了筆者資料收集的重要來源。筆者若認為與本研究有相關的<br />
部落格文章,會徵詢報導人的同意轉貼在論文中作為分析依據。<br />
本研究對象是以筆者在蘭嶼中學任教九年(1995~2004 年)所教過的二十<br />
八位學生為主,目前都在台灣就學或就業,年齡為 15~25 歲之間,女生十二位,<br />
男生十六位。目前他們就學的部分包括高中(台東)、高職(台東)、軍校(桃園<br />
中壢)、護校(桃園長庚)及大專院校(高雄、雲林、台北);至於就業的部分則<br />
集中在台中潭子(朗島部落)、桃園八德南崁(東清、漁人部落)、三重新莊(野<br />
銀)、台北(椰油、紅頭部落)等地方。<br />
在這些報導人中就學的有八位;就業的十四位;服兵役有四位;待業中二位,<br />
89
參加蘭嶼大專青年服務隊的有十位 11 ,透過網路密切聯繫的有七位。這些訪談主<br />
要是從 2004 年至今,訪談時都事先告知受訪對象本研究的主題及訪談內容,在<br />
其首肯下進行錄音。雖然一開始有些不自在 12 ,不過很快就能進入狀況,因為談<br />
的是他們在台灣的情形-自己熟悉的經歷,所以每個人都能侃侃而談,不會支吾<br />
其詞。<br />
每個受訪者情況不同,每次訪談的時間也不一,大部分是二個小時以上。訪<br />
談的目的是透過訪談瞭解個人經驗以及生命故事,在訪談的過程中儘量使受訪者<br />
以說故事的方式去表達。訪談大綱是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回顧歸納整理出的問題<br />
意識擬定,分為三大部分:一、文化差異、城鄉意象、邊緣論述及刻板印象;二、<br />
認同與歸屬;三、返鄉。此大綱主要是訪談前的準備及訪談時的基本主軸,但訪<br />
談時會依受訪者當時的的情況而有所不同,彈性調整並不拘泥於這些問題,甚至<br />
在訪談經驗累積之後,會針對訪談內容做些增減、調整與修正。<br />
訪談地點則依受訪者最自在的地點決定,有涼亭、屋頂、海邊、工作地點、<br />
住家、麥當勞及咖啡屋。在第一次訪談之後,整理完的錄音逐字稿及筆者對當時<br />
訪談情境所寫的田野筆記,都會與學生在做確認與分享,並承諾將來用在論文時<br />
會先經過他們的同意,以避免資料的不當解釋或誤用。<br />
本研究主題透過「離家與返鄉」及「漢人教師與蘭嶼學生」兩個主軸進行研<br />
究提問,書寫生命故事。在兩主軸平行演進中,又可互相對照呼應。<br />
分析架構如下:<br />
蘭嶼學生<br />
研究者<br />
為什麼要離開蘭嶼? 為什麼要離開家鄉?<br />
在異鄉的生活如何?<br />
為什麼台灣不是家?<br />
為什麼蘭嶼是家?<br />
在異鄉的生活如何?<br />
台北是家嗎?<br />
屏東是家嗎?<br />
11 雖名稱為大專青年,但參加資格並不限大專生,有高中生、社會青年、大學休學或重考生等。<br />
12 現在是蘭嶼非常有名的民宿老闆,經常有媒體或遊客採訪,但對於被老師訪問直說:「被老師<br />
訪問,很奇怪。」、「老師不會把我們賣掉拉!」。<br />
90
要返鄉嗎?要透過什麼途<br />
徑返鄉?<br />
返鄉之後呢?<br />
行 動<br />
三、「我」的角色與觀看的角度<br />
為什麼到蘭嶼?<br />
在蘭嶼尋找什麼?<br />
在蘭嶼做什麼?<br />
為什麼要離開蘭嶼?<br />
為什麼又要回蘭嶼?<br />
要透過什麼途徑回蘭嶼?<br />
蘭嶼是家嗎?<br />
Peshkin:「藉著主觀性,我說我所感動的故事。祛除主觀性,我並不是變成<br />
一個價值中立的參與者,而是一個腦袋空空的人」(引自畢恆達 2005:2)。<br />
在田野中與學生的互動及觀察他們在台灣的生活,都讓我「時時有驚喜處處<br />
有感動」,當然也有「無奈與難過」,但這樣的研究者情緒感受到底該不該讓它「現<br />
身」呢?還是必須秉持研究的客觀理性而忽略呢?就我個人而言我很難「視而不<br />
見」,因為它是我在田野工作中的真實感受,當然也影響我的詮釋。與其假裝客<br />
觀,寧將研究者的真實情感呈現,讓讀者瞭解也交由他們判斷他們可接受或不能<br />
接受之處,我想這才是研究者該有的「責任」。正如蔡敏玲(1996)指出「研究<br />
者的感受影響研究者的詮釋,因而不能略去不顧、不寫。」以下是 2007 年 8 月<br />
25 日所寫下的田野筆記。<br />
這麼多年來,時間和空間都已有所變化,學生也都已經長大,雖然畢業<br />
後還一直有電話聯繫或者從家長同學輾轉得知消息,但畢竟已有數年未<br />
見,這樣的時間點與他們相遇真是百感交集。當在台中打電話給小薰約<br />
碰面時,她興奮的在電話中狂跳狂吼狂叫,直說要哭了,久久不能自已<br />
-老師怎麼會在這裡出現?說見面時要抱我,可以明顯感受她的激動,<br />
其實我聽到她如此的反應,我也很欣慰總算從前的辛苦是有代價-他們<br />
並沒有把我忘記,而且還一直惦記著。到了南崁,十年前我帶著到潭子<br />
的學生,如今已是英勇威猛保家衛國的特種部隊一員,聽到我要去找他<br />
更是興奮的說:「老師,你在哪裏?我去接你。」這趟為了論文而跑的<br />
行程,原本是為了蒐集資料,順便看看久久不見的學生,卻意外讓我有<br />
更多的收穫-每個學生都長大懂事已經不是十年前的國中小夥子。心中<br />
91
一直是高興雀躍的,想到從前都是我在服務他們為他們做事,現在卻是<br />
他們在幫我照顧我(要吃什麼、喝什麼、開車……),那個感覺真的很<br />
不同,就好像自己的孩子長大了。此刻真是感覺「我老了,學生長大了」,<br />
但這卻是甜蜜的感動不是哀嘆年歲的無奈!<br />
隨著時空的變換,學生已不再是生活在蘭嶼的十三、四歲國中生,而是在台<br />
灣職場打拼或大專院校就讀的成年人。而我也不再是蘭嶼中學的老師而是花蓮鳳<br />
林國中的老師及東華族群所的研究生。當年看他們跟如今看他們,在蘭嶼和學生<br />
交談跟在台灣和他們相會,其實都是不太相同的。因為十年不算短的時間,蘭嶼<br />
到台灣不算短的距離,這樣的時空交會早已在我們彼此的生命經驗中不知添繪了<br />
多少筆,已孕育了多少豐富的生命故事。這些情緒的起伏、身份轉換、生命的流<br />
轉,都是我書寫論文時真實的感觸與感動,因此我認為這些也是論文的一部分是<br />
應該被紀錄下來的。<br />
在論文書寫的過程,我一直在思索「我」扮演的角色及觀看的角度與位置。<br />
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在這個論文中我是參與者或研究者?我是以「老師」<br />
抑或「研究者」角度觀看?這些研究對象都是我朝夕相處三年的學生,甚至直到<br />
現在仍然在聯繫中,我們有許多生命成長過程的共同參與與體驗,我們關係是長<br />
達十多年,這和一般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關係的建立從零到有的過程是不同的。<br />
我發覺我無法很超脫的看待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題,而是有我多年來對蘭嶼人事物<br />
感情的投注在其中。常常在訪問後回來聽錄音內容做逐字稿,發現我與訪問對象<br />
聊的很愉快,甚至聽到他們對前途的徬徨或無助時,變成了「輔導老師」而不是<br />
「研究者」,我無法客觀的只是聆聽而不給些建議或幫助。這樣的角色混淆一直<br />
是做田野工作的障礙,然而在「反思」為什麼要寫這論文時?我又能釋懷甚至很<br />
享受這樣的田野的工作,因為我的目的就是瞭解他們的故事、寫出他們的故事,<br />
我設定的讀者群就是蘭嶼學生、蘭嶼的教師與蘭嶼的家長。這樣相談甚歡、無所<br />
顧忌、自自然然的訪談不正是需要的嗎?因此我必須承認在這論文中「主觀性」<br />
的盲點是無法避免的。<br />
畢恆達提到在學術研究中「觀點」的重要性,「你所看到的、發問的問題,<br />
都與你的觀點有關;它取決於你認為它有意義或者沒有意義。說與不說都反映了<br />
你的位置與角度,也都造成某種後果。」他也提到主觀性(subjectivity)對研究<br />
者的限制與反思,「主觀性同時是『可能』也是『限制』。研究者應該反省自己的<br />
主觀性,並檢討它對於研究從頭到尾的影響。既然主觀性限制我的認知與體認,<br />
我必須知道什麼感動我,什麼沒有;而我的詮釋中又忽略了什麼」(2005:1- 2)。<br />
以老師的身分進行研究,對田野工作而言,好的方面是可以很快與他們建立<br />
關係,沒有一般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磨合期,並且因為漢人的身分與對蘭嶼的認<br />
識,我比較能與他們站在同一個位置來思考,理解他們在台灣的問題甚至感同身<br />
受-當初我到蘭嶼的情景。但也因為這樣的身分將比較難迴避「客觀」的可能侷<br />
限,常常在訪問中已無法客觀聆聽而是積極介入,可能使得我的觀察與詮釋受個<br />
92
人主觀情感影響,甚至「自以為是」的理解。潘英海(1995:2)曾提醒田野研究<br />
工作者,在田野時所面臨的「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這兩個觀念,這將是未<br />
來田野工作及資料分析時必須特別留意深思的。<br />
2007 年 3 月 24 日族群所辦的「落實田野:中研院田野培訓計畫田野心得發<br />
表會」會後,曾有人質疑我「這些蘭嶼學生都想回鄉嗎?回鄉能做什麼?會不會<br />
是你一廂情願的認為?」當時眞的讓我無力招架,會不會是因為「老師」的身分?<br />
所以他們故意說「我想聽的、好聽的」?這的確是合理的懷疑,甚至我自己也開<br />
始猶疑眞的是如我所想的那樣-他們都想返鄉?「真相」是什麼?他們是否有隱<br />
瞞?我聽到的是不是他們想說的?這個研究有意義嗎?<br />
直到再回到田野及看到學生在部落格的書寫,讓我看到他們對蘭嶼的感知感<br />
覺與感受,才打醒我對「真實」的迷思 13 。如同Seidman(1998)曾說:<br />
我做訪談,因為我對他人的故事有興趣。…說故事是一個建構意義的過<br />
程,在說故事的同時,人們也選擇了其經驗中的細節。…深入訪談的目<br />
的,並不是要得到問題的答案,也不是測試假說,更不是要評估這個項<br />
目是否正確使用,而是要瞭解他人的經驗以及其意義。(引自張婷苑<br />
2002:21)<br />
張婷苑在做青少年離家意義研究時,曾困擾著這些離家青少年跟他說的故事<br />
是真是假?後來她理解到「故事也許會因不同對象而有不同版本,但意圖說出什<br />
麼已不是真假的問題,而是意義如何展現的問題」。她說:「我可以很消極地懷疑<br />
它的真假,但如果他們願意和我談這些經驗,就是交付給我探尋意義的使命。畢<br />
竟對他們而言想說的故事就是這個,也就沒有真實與否的問題了。」(2002:21)<br />
的確,離家青少年可以將他離家的故事說成很英勇、很悲慘、很平實,但畢竟研<br />
究者不是他們這個族群無法得知真偽。但蘭嶼學生的生活並沒有那麼戲劇性的落<br />
差起伏,其生命故事就是平時的敘述不須特別去隱瞞或浮誇,況且筆者對蘭嶼有<br />
一定的認識與人脈,可以從家長朋友處互相印證得知其敘事的真實程度。至於其<br />
對蘭嶼的真實感受?要不要返鄉?無論如何,只要他願意跟我分享在地與離家的<br />
想法感覺,這不就是我研究主要的探討面向?<br />
夏曉鵑在外籍新娘方面的研究經常被問到資料的取得問題,於是她藉由「外<br />
籍新娘識字班」的成立及運作過程做說明。她認為「資料的取得往往必須建立信<br />
任,而信任關係並非靠友善的態度便可完成,更深層的信任必須建立在共同經歷<br />
一個『重生』的過程,亦即,一個共同努力實踐改變的過程」(2004:224)也許<br />
我與蘭嶼學生所面臨的問題不至於到「重生」的地步,但我們有共同的願望與情<br />
感希望蘭嶼有所改變,希望透過「生命故事」的呈現,除了敘說出蘭嶼學生在台<br />
13 曾曾不止一次跟我說:「將來我想回蘭嶼蓋民宿,經營民宿。我家地很多,老師我把地給你。」<br />
這樣的話是真是假已不重要,雖然我知道要把土地給一個漢人是多麼的困難。但這正是他想表達<br />
的「想法」。<br />
93
灣的生活樣貌,最後也能產生「行動」的可能。什麼樣的行動?減少「離家」在<br />
台灣的適應問題及創造原住民青年「返鄉」的可能性。<br />
94
參考書目<br />
夏曉鵑<br />
郝明義<br />
2004 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北:台灣社會研究<br />
雜誌社。<br />
2003 移動在瘟疫蔓延時。刊於黃秀如主編,移動在瘟疫蔓延時,頁 4-5。台<br />
北:網路與書。<br />
郭佩宜、王宏仁主編<br />
張婷苑<br />
畢恆達<br />
潘英海<br />
蔡敏玲<br />
2006 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台北:巨流。<br />
2002 青少年離家意義之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2005 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學富。<br />
1994 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會議論文發表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檢討與前<br />
瞻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1994 年 1 月 12-13 日,<br />
頁 1-26。<br />
1996 教育質性研究者請在文本中現身:兩項重要思慮。國民教育<br />
37(2):21-30。<br />
95
一個行動研究者在部落–南山部落地圖繪製的經驗<br />
陶楷鈞<br />
本文透過筆者參與南山部落的部落地圖繪製工作經驗中,對於部落地圖繪製<br />
行動進行觀察。試圖透過參與觀察該行動,解析部落地圖繪製行動與部落發展之<br />
間的關系。並以該經驗作為出發點,檢視臺灣當今對於部落地圖的論述與作為,<br />
並進行檢討,提供未來部落地圖發展的行動脈絡與方向。<br />
一、前言<br />
「部落地圖」參與到原住民工作,是臺灣近年在規劃原住民部落發展時,常<br />
會被提出的工具。在繪圖工作過程中,參與各方也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與認識。<br />
不僅是跨學門間的認知,政府與部落間也有著不同的想像。<br />
本研究從一個協助部落地圖繪製的行動進入部落作為開始,透過該行動與部<br />
落產生互動,並觀察該地部落地圖繪製行動與部落發展之間的關係。從參與部落<br />
地圖繪製過程經驗裡,檢視臺灣當今對於部落地圖的論述與作為。透過對該行動<br />
在論述與作為上的檢討,提供未來部落地圖發展的行動脈絡與方向。<br />
南山村是中部橫貫公路宜蘭支線上一個兩百二十二戶的泰雅族聚落,高冷蔬<br />
菜的種植為部落在經濟上帶來龐大財富收入。但在高冷蔬菜產業背後的隱憂是<br />
大、中盤菜販對於菜農銷售通路的壟斷以及經濟上的剝削;長期大規模集約式耕<br />
種也造成的地力衰竭以及水土保持等問題。高冷蔬菜為部落帶來財富,也使得部<br />
落概括承受了經濟與環境上的風險。面對產業上的困境,部落開始討論如何在菜<br />
園之外另闢新生計。2000 年開始的馬告國家公園爭議,激起部落裡對於高冷蔬<br />
菜產業存留以及傳統領域土地主權議題的激烈辯論。在部落內外為了國家公園設<br />
立與捍衛部落土地間的爭議方興未艾之際,此時部落也完成第一張部落地圖,向<br />
主流社會宣示對於土地的主權。<br />
對南山部落而言,部落地圖繪製行動究竟開啟了什麼樣的訊息?又與部落發<br />
展和生活脈絡有著什麼樣連結?部落地圖這個行動是曇花一現的政府政策,在結<br />
案報告完成之後便宣告了事。還是可以持之以恆的部落運動?其未來又存在何種<br />
可能性?是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也是筆者在田野中觀察的重點。<br />
二、部落地圖與臺灣原住民<br />
「部落地圖」(community mapping)發展於 1970 年代的五大湖區,緣起於<br />
該區域的印地安人為爭取傳統生活領域之權利,將部落文化中地名、傳說、採集<br />
與狩獵等項目,一一羅列於有限範圍之平面上,形成部落獨有之地圖,成為部落<br />
主張區域生活史的明證。之後除了美加地區原住民部落積極推廣外,世界其他地<br />
區原住民部落也相繼加入繪製行列,目前在澳洲以及原住民部落因部落地圖的證<br />
明而贏得法院判決,取得傳統生活領域之管理權利(台邦・撒沙勒 2001a:130)。<br />
96
簡單地說,「部落地圖」是運用製圖方法,將部落的傳統知識、歷史文化、<br />
自然環境資源、相關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未來的發展願景,透過部落的集體參<br />
與,並從空間的理解方式來記錄以上事務的過程。因此,部落地圖不僅是一張圖,<br />
而是一個有許多不同主題的故事的集合,以及許多部落集體的生活經驗,因此,<br />
部落地圖是一個社群認同的過程。Fox(2001)認為部落地圖所強調的是在政府所<br />
釐定的官方地圖之外的另一種選項。它的主要精神在於透過部落每一份子的參<br />
與,使得部落整體的利益以及文化得以體現的社會過程。<br />
臺灣最早的部落地圖個案與論述,可以追溯到 1997 年台邦・撒沙勒與劉炯錫<br />
在屏東縣霧台鄉的好茶部落的調查行動,但當時因為受限於技術、觀念與經費等<br />
限制,故成效不彰。2001 年,台邦・撒沙勒與劉炯錫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IS)<br />
技術並在部落老人的指導下再度進行記錄,並將調查中所得到傳統地名、禁忌<br />
區、獵區、獵徑等透過 GIS 系統整合與呈現(ibid.:133)。藉由科技輔助的研究<br />
成果,台邦・撒沙勒與劉炯錫皆肯定藉由 GIS 技術進行繪圖是未來的趨勢,並可<br />
以提升地圖之精確與完整性,並可有效降低原住民爭取土地資源權益時與漢人社<br />
會的衝突與疑慮。<br />
在政府政策層面,由於陳水扁總統在競選時的新伙伴關係協定,行政院原住<br />
民族委員會 2002 年起委託學術界進行「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br />
計畫,2003 原民會會同各原住民鄉、鎮、市公所擴大執行,2004 年則持續第三<br />
期工作計畫(中國地理學會 2004)。該計畫係以「部落地圖為主要的研究取向,<br />
以作圖來召喚部落居民對傳統領域、自然資源利用與管理的知識、及傳統的社會<br />
制度等回憶,藉操作程序共同建構部落認同。(中國地理學會 2002:I-2)」總覽<br />
2002 自 2004 年原民會所進行的部落地圖調查計畫執行,可以清楚地看到部落地<br />
圖在該計畫中被視為一種「作圖」(繪製傳統領域)的方法,其作圖目的除了凝<br />
聚部落共識外,與爭取傳統領域擁有權或經營管理權等政治權利緊密相關。<br />
部落地圖另一受到注目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 2001 年時受到森林、保育與原<br />
住民族各界熱烈討論的馬告國家公園籌設案(盧道杰等 2005:5),積極推動馬告<br />
國家公園設立的人士希望能檢討現有國家公園經營管理機制,建立一能增進與原<br />
住民互動機制,讓權益關係者能參與國家公園的經營管理與決策的擬定和執行。<br />
部分保育及關心原住民發展人士認為在國家公園共管(co-management)機制尚<br />
未成熟前,若能先進行部落地圖的繪製工作,則可在過程中整合在地環境資源知<br />
識,並與泰雅傳統制度進行互動,或許可以在馬告國家公園經營管理體制中產生<br />
貢獻(台邦・撒沙勒 2001b;賴俊銘 2004;蕭惠中 2003)。<br />
馬告國家公園設置計畫最終以預算凍結方式被國會束之高閣,但政府對於原<br />
住民傳統領域的修法腳步持續前行。2004 年 1 月 2 日森林法修正案通過,確立<br />
了原住民族在其傳統領域內對森林產物的利用保障與優先權。「傳統領域」從此<br />
正式成為國內法規中的法定名詞與執法依據。2005 年 2 月立法院通過制訂原住<br />
民族基本法,在第 2 條中提及了原住民族土地包括了傳統領域與既有的原住民保<br />
留地。但在這兩項法條當中,皆未說明究竟「傳統領域」的定義為何。該由原民<br />
97
會、學術機關還是部落組織確認領域的範圍?採信誰的調查資料,是由部落地圖<br />
一案中所得到的調查資料,還是透過其他方式所取得的資料為基準?在法律實務<br />
上,載明受用的「對象」與「範圍」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沒有明訂範圍與標<br />
的,則法條的宣示意義大過於實質。然這兩項已經「超越」臺灣原住民社會現實<br />
的立法,突顯出目前部落地圖工作上的矛盾。政府在政策上試圖將部落地圖與原<br />
住民立法作一結合,卻忽略了在現實生活裡,原住民的生活空間早已被現代行政<br />
區域、林務局林班地、國家公園土地以及原住民保留地切割得支離破碎。<br />
透過對於臺灣部落地圖的發展脈絡的整理,可以發現部落地圖的認識與看法<br />
是多重的。改革者的視野裡,部落地圖如馬告國家公園運動裡的角色,被作為「社<br />
會運動」的一種可能,透過繪圖行動以彰顯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向漢人社會爭取<br />
權益的重要依據。在執政者眼中,希望部落地圖的調查結果能夠成為未來原住民<br />
族政策規劃的一部份,「傳統領域」一詞成為法律具文,顯露政策規劃者對於往<br />
後原住民族政策行政疆界劃分的想像。<br />
「部落地圖」若作為社會運動的一種,如馬告國家公園運動,則這場運動的<br />
意義及目標該放在什麼樣的位置及立場上?部落地圖的繪製又具有什麼樣的社<br />
會意義?此外,對於部落地圖所描繪出的資訊,是一種行政疆界劃分的想像,還<br />
是屬於文化及傳統上的意義呢?回到部落本身,前面兩者放在部落的生活脈絡當<br />
中,部落地圖又對部落造成何種影響?<br />
以下將從筆者身為部落繪圖行動參與者以及專業技術提供者的雙重角色作<br />
為出發,從參與 Pynan 部落地圖繪製過程經驗裡,檢視臺灣當今對於部落地圖的<br />
論述與作為。透過對該行動在論述以及作為上的檢討,提供日後部落地圖發展的<br />
新可能性。<br />
三、走入部落<br />
(一)Minbu、Pynan 與南山村<br />
這是初到 Pynan,部落耆老告訴的第一個故事:<br />
在不知道多少代的祖先以前,祖先來自於 Pinsbkan。從那裡出發,一路<br />
經過了 seburoq,來到 Quli sqabu(思源埡口)。他們先後在 Qayawl 和<br />
Sqabu 生活了一段時間,因為族人數目日益增多,三位帶頭的兄弟協議<br />
將人群分散開來。老大 Kbuta 往 papak waqa 方向走,到了現在的新竹<br />
桃園一帶。老二 Kyaboh 穿越南湖大山,往今天南澳的方向前進。老三<br />
Kmomaw 因為身體不好(moyay hi nya),就沿著地形走向較其他兩條<br />
路線平緩的蘭陽溪(llyung minbu)上游出發。<br />
Kmomaw 帶著眾人一路前進,在 hbun sgmi’此定居,這就是南山村最早<br />
的部落。那裡叫做 Sgmi’是因為以前在那塊平臺上長滿了 Qgmi(中文植<br />
物學名為麻六甲合歡)。祖先在 sgmi’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同時也在尋找<br />
更寬闊的土地以利族人生存。幾位族人來到 minbu 打獵,發現這個地方<br />
98
的土地更適合發展,族人們再度展開遷徙,跨越了 gon memutan,來到<br />
了 minbu,就是現在部落的所在地。<br />
到了日據時期,minbu 這個名字被 Pynan 所取代。日本人初到部落時,<br />
在部落入口處煮食,宴請全部落。利用部落聚集的時刻,將族人團團包<br />
圍,令其交出槍械武器,因此不費一槍一彈的控制了部落。因為發生此<br />
一事件,所以這裡被稱為 Pynan,是取自泰雅語 Pinhapuy(意指煮食的<br />
地方)的音變。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將這個部落命名為「埤亞南」,<br />
同時被劃為宜蘭縣大同鄉的一個村治。而後在一次蔣經國先生視察此處<br />
時認為「埤亞南」的名字不雅,便被改名為「南山」。<br />
(報導人,Masing Koyaw、Yukan Buta,2006/10)<br />
這是筆者到 Pynan 進行部落地圖繪製時部落耆老在地圖上所指引出的部落<br />
遷徙路線。透過耆老的口述,不僅僅是點出了地圖上的每個傳統地名,更是描繪<br />
出一幅橫越數百年甚至更久的遷徙史詩以及社群更迭。族人過去經常漁獵的祖居<br />
地 Qayawl 如今已是退輔會的武陵農場和雪霸國家公園管制區域;三兄弟的分散<br />
地—Quli sqabu,現在稱做「思源」。族人所居住的部落 Pynan,從 Minbu 轉稱為<br />
Pynan,再從「埤亞南」人演變至「南山」人。每次的名字轉變,代表著不同強<br />
勢權力來到部落,試圖在此塗上屬於自己的印記,以彰顯對於該地的所有權,卻<br />
忽略了正在這塊土地上紮紮實實生活的族群。Pynan、Quli sqabu 等地名從未顯<br />
現在政府的任何一份正式的官方圖集中,這些屬於泰雅文化與記憶的地名存在於<br />
經常在山林活動的耆老及獵人的記憶裡。<br />
Pynan 是中部橫貫公路宜蘭支線上一個兩百二十二戶的泰雅族聚落,全區海<br />
拔在 1823~950 公尺之間,聚落位於海拔 1150 公尺的蘭陽溪左岸河階臺地上。<br />
高冷蔬菜自民國 60 年代引進部落,在短短二十年間高冷蔬菜的種植為部落在經<br />
濟上帶來龐大財富收入,成為家家戶戶的主要收入。對於部落發展而言,種菜是<br />
當下最該關心的事情。但在高冷蔬菜產業背後的隱憂是大、中盤菜販對於菜農銷<br />
售通路的壟斷以及經濟上的剝削,賴俊銘(2004)對於南山村的產業調查中即指<br />
菜販利用通路上的壟斷優勢,以均一價格收購蔬菜,並以賤買貴賣方式從中賺取<br />
差價以謀暴利,產業單一化也使得在菜農一旦遇到天災人禍或者是菜販不來收菜<br />
時便無以為繼。為了滿足平地市場的需求,長期大規模集約式耕種也造成的地力<br />
衰竭以及水土保持等問題。高冷蔬菜為部落帶來財富,也使得部落概括承受了經<br />
濟與環境上的風險。面對產業上的困境,南山部落成立了產業小組,討論如何從<br />
菜園之外另闢新生計。<br />
2000 年開始的馬告國家公園爭議,南山部落裡激起了對於高冷蔬菜產業存<br />
留以及傳統領域土地主權議題的激烈辯論。贊成興建國家公園的一派人士,認為<br />
藉由國家公園設立,可以促使部落產業轉型,朝向觀光發展。而反對設立一派人<br />
士則是對於烏來和武陵農場的開發案例心有餘悸,認為觀光的發展對部落不會有<br />
任何助益,最後的好處都會落在財團手上,倒不如繼續種菜!在部落內外為了國<br />
99
家公園設立與捍衛部落土地間的爭議方興未艾之際,此時部落也完成第一張部落<br />
地圖,裡頭詳細描繪了在馬告國家公園預定範圍之內,部落的獵場、泰雅地名、<br />
故事。這張地圖的完成,宣示在馬告國家公園議題中,部落發聲的立場與角色。<br />
爾後馬告國家公園爭議隨著預算在 2003 年被凍結之後宣告一段落,但部落繪圖<br />
的工作在政府經費的挹注之下依然持續著。<br />
(二)Pynan 的部落地圖工作<br />
Pynan 是原民會第一期傳統領域調查的重點部落之一,筆者在第三和第四期<br />
調查活動時進入部落。我在部落中的行動分為兩個方向。在技術層面上,透過個<br />
人對於電腦軟體以及地圖判別的資訊,縮短部落地圖繪製過程中因為資訊落差所<br />
造成的隔閡。一是協助操作 ArcView 地理資訊系統軟體,將訪談所獲得的資訊標<br />
記在電子地圖中。另一方面協助判讀 1/25000 紙本地形圖,因能自行判讀等高線<br />
地形圖的居民並不多,很多獵人耆老在山上行走都是憑藉經驗與記憶。筆者利用<br />
彩色筆,先行將稜線、水系、山頭、現在村落位置、公路以不同顏色標示,在不<br />
同顏色區別下,便於判斷相對位置。<br />
另一層面上,則是希望部落地圖的工作可以由部落自行發動。在歷經第一期<br />
與第二期的調查行動後,部落對於部落地圖的概念已經略有了解。在耆老與教會<br />
牧師的協助下,Pynan 組織了一個部落地圖小組,負責推動部落地圖的繪製事<br />
宜。在第三、第四期的部落地圖繪製行動裡,透過部落地圖小組的帶動希望可以<br />
將部落地圖的概念推廣至其他部落以及加深 Pynan 部落的繪製,讓繪圖行動可以<br />
與生活脈絡相互結合產生實用。在這個層面上,我則是以參與者身份置身其中,<br />
透過參與繪圖小組行動,觀察部落地圖如何與部落生活進行對話。<br />
在第三、四期的部落地圖繪製行動裡,部落地圖的調查案從原本的學術團隊<br />
為主軸的調查行動,轉為交由各地鄉公所承辦。Pynan 的部落地圖繪製小組接受<br />
鄉公所的委託,前往前山的英士、松蘿、崙埤等部落進行訪談,筆者則隨同繪圖<br />
小組的訪談進度,提供圖面以及 GIS 軟體技術的支援。而在每一期調查結束之<br />
後,則是由鄉公所出面邀集參與該其調查的部落耆老一同出席期末座談會,共同<br />
確認、分享調查的結果。<br />
四、心得<br />
表面上看起來,部落地圖與恢復部落文化,甚至部落自治有著密切關連,但<br />
必須要體認到的一點則是運用這些繪圖的技術,並非傳統,至少現行的部落地圖<br />
繪製是受到地理資訊系統(GIS)與衛星定位系統(GPS)等科學製圖工具的限<br />
制與影響。這些系統引用於部落地圖繪製行動中,對於原住民傳統空間的觀點產<br />
生一定影響。在部落地圖一案中,筆者常常被承辦人問到的即是究竟傳統領域的<br />
那條領域的「線」該如何畫,那個地名的「點」究竟在哪裡。點、線、面構成的<br />
地圖,是西方科學製圖學上的方法。在南山部落的繪製經驗裡,傳統的地名,是<br />
一個範圍的概念,是以該區域的物產或者事件而名,並非一個精確的座標點;而<br />
領域的觀念則是涉及過往的狩獵行為,部落與部落間領域的範圍常常是交互重<br />
100
疊,互有模糊地帶。因此部落地圖,不是一種恢復傳統的行為,而是以西方科學<br />
知識作為根基的「建構」傳統行動。因此,在地圖繪製的圖面上,是西方科學與<br />
地方社群知識的角力場域,既非傳統,也非現代。<br />
從參與南山繪圖的經驗中顯示,老人家對於傳統領域中地點的記憶與經驗是<br />
具有整體性的,被賦予泰雅地名的地方可能是因為該地有物產(例如 hbunsgmi),或者是發生過什麼故事(例如前述的<br />
Pynan 由來)而得名。這種認識的<br />
過程是具有強烈的實用性,其實用性來自於勞動、狩獵等從實際生活需求中所產<br />
生的,是一種經過相當長期的認識與活動積累而形成的知識體系。<br />
部落地圖在政策論述裡被視為一種「作圖」(繪製傳統領域),輸出的成品、<br />
溝通的介面以各種形式、各樣比例尺的地圖為主。現今的部落地圖調查方式,把<br />
地圖攤開在老人家面前,將長時間所累積的山林知識,記錄在地圖上。並設定了<br />
透過老人家的指認,透過 GIS 軟體的標定,樹立地圖的「工具理性」以及知識<br />
性。在地名、典故一一被記錄於圖紙上之際,受到忽略的是這些知識背後是存在<br />
著一個龐大且悠遠的泰雅生命史與歷史觀,所能看到的僅是一張記滿了地名與領<br />
域線的地圖。<br />
對於馬告爭議時期的南山部落而言,繪製部落地圖代表了他們對於該議題上<br />
參與與發聲的權力。而在馬告事件宣告一段落之後,繪圖行動轉向生活脈絡當<br />
中,在部落居民最關心的產業轉型層面上,透過地圖的繪製,了解到部落有瀑布、<br />
鐘乳石、檜木等自然資源的存在,可以作為日後發展觀光的景點。透過其他外界<br />
資源的配搭,部落開闢了一條簡單的解說步道,嘗試另一種產業的發展。<br />
從「部落地圖」轉向至「觀光產業」,開啟了在國家政策、國家公園運動之<br />
外另一種部落繪圖的可能性。也顯現在部落生活脈絡中,部落地圖是透過觀光產<br />
業與部落對話。<br />
「部落地圖」作為與部落溝通的媒介,筆者藉由參與地圖製作爭取部落的認<br />
同,打開部落觀察的大門,與部落產生互信基礎。此基礎來自於研究者與對象兩<br />
造間相互了解部落地圖的重要性。然而,放置在部落的社會脈絡下,則必須有更<br />
多日常生活的觀察,更多的批判與反省,才能夠深入了解部落地圖的意涵與可能<br />
性。<br />
101
參考書目<br />
中國地理學會<br />
2003 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br />
中國地理學會<br />
員會。<br />
2004 原住民族傳統土地與傳統領域調查研究。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br />
台邦.撒沙勒<br />
賴俊銘<br />
員會。<br />
2001a 畫一張會說故事的地圖。刊於把人找回來--在地參與自然資源管理,<br />
頁 130-138。花蓮:內政部營建署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br />
2001b 設國家公園前,請先畫一張部落地圖。中國時報,論壇版,1 月 23<br />
日。<br />
2004 從部落發展角度看馬告爭議的虛實—以 Pyanan 部落為例。世新大學<br />
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盧道杰、吳雯菁、台邦.撒沙勒、斐家騏<br />
蕭惠中<br />
Fox, J.<br />
2005 誰在詮釋傳統領域。發表於「2005 年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學術研<br />
討會」。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br />
2003 一個抵抗的空間建構-馬告國家公園運動脈絡下的部落繪圖實踐。台<br />
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br />
2001 Siam mapped and mapping. In Cambodia:Boundaries, sovereignty,and<br />
indigenous conceptions of space. Submitted to Society and Natural<br />
Resources.<br />
102
一、前言<br />
台灣原住民樂舞團體與文化環境之研究<br />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藝術展演扶植團隊為例<br />
周家綾<br />
自 1994 年起,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陸續推動「全國文藝季」以及「縣市<br />
小型國際藝術節」,各縣市節慶活動紛紛興起;其後農業委員會的「一縣市一特<br />
色、一鄉鎮一特產」以及交通部觀光局的「每月一節慶」,則更進一步的推波助<br />
瀾(陳嘉宏、范姜泰基 2006)。到了 2002 年,行政院更在「挑戰 2008:國家發<br />
展重點計畫」(2002)中,提出了「觀光客倍增計畫」,目標於 2008 年達到來台<br />
旅客 500 萬人次,透過觀光提昇台灣地方社會經濟發展。在政策的號召下,部分<br />
已打響名氣的地方節慶活動持續舉辦(如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另一方面,文<br />
建會則連結了各縣市的新興節慶,打造「福爾摩沙藝術節」系列活動,將台灣從<br />
南到北裝點得五彩繽紛。這些新興的節慶活動包羅萬象,囊括了傳統節慶再造、<br />
農產品推展、地方工藝展示、人文生態體驗等主題,「原住民樂舞表演」則是這<br />
類活動中經常出現的節目之一,有時是為了暖場演出,有時則是作為活動的主題<br />
(如南島文化節)。透過動感的樂器演奏,歡樂的歌謠,獨特的舞步,再加上主<br />
持人的趣味串場,使得原住民樂舞表演成為吸引人潮、炒熱氣氛的一種方式。<br />
原住民樂舞表演與觀光活動結合的發軔,約可溯及日據時期,包括花蓮阿美<br />
文化村、台北的烏來、南投日月潭德化社等地,都是自日據時期以樂舞展演而享<br />
盛名的觀光景點(趙綺芳 2004:47)。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受到「島內觀光」(陳<br />
揚威 2003:32)的風氣影響,則開始有「九族文化村」(1986 年開幕)、「台灣原<br />
住民文化園區」(1987 年開放,原名「台灣山地文化園區」)以及「布農部落」(1995<br />
開放)等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題的大型觀光機構出現,「原住民樂舞」自然也<br />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展演節目之一。其後隨著新興節慶風潮的出現,原住民樂舞表<br />
演的曝光率大增,除了觀光活動外,筆者同時觀察到原住民樂舞也經常出現在「國<br />
際文化交流」的場合,或在與政府、私人機構合作舉辦的活動中出現。<br />
對於出現在各類場合中的原住民樂舞,筆者相當好奇,穿戴上傳統服飾的原<br />
住民表演團體,站在部落以外的場域,面對來自各方、各族群甚或其他國家的觀<br />
眾時,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角色以及展現的樂舞?因此,為求瞭解當今台灣原住<br />
民樂舞團體與文化環境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將透過田野資料以及文獻的相互對<br />
照,分析已發展成為具有「展演」功能的原住民樂舞團體,如何受到來自族群文<br />
化以及外在環境的影響,並對此情境以及自我身分進行解讀詮釋,發展出應對的<br />
態度策略,從而探討現今原住民樂舞團體的現況,作為理解台灣原住民樂舞生態<br />
環境之參考。<br />
103
有關現今原住民樂舞團體的研究,除了謝世忠對「九族文化村」、「台灣原住<br />
民園區」表演者的研究,游景德(1996)對「原舞者」、「九族文化村」、「布農部<br />
落」的分析,周慧玲(2002)、周文茵(2004)的「布農部落」,陳吟合的「達娜<br />
伊谷鄒族舞蹈團」,江冠明(2002)的「台灣原住民文化園區」,以及梁莉芳對「花<br />
蓮縣原鄉藝術舞蹈團」的研究以外,吳錦發(1999)、胡台麗(1994)以及譚雅<br />
婷(2003)以「原舞者」為對象,撰述原舞者的成立過程、田野採集方式以及舞<br />
台表演經驗,探討部落裡的祭儀樂舞,如何透過現代舞台的元素重新設計,再現<br />
於觀眾面前;黃姿盈(2005)則選取「杵音文化藝術團」為個案,分析其展演場<br />
域、歌舞內涵、音樂風格以及展演形式,以瞭解原住民歌舞團體的發展,與台灣<br />
政治、文化和社會演變之間的關連。上述研究均採取單一或數個案例進行分析,<br />
在量化部分,陳甦蘭(2003)則是以量化問卷輔以部分質化訪談的方式,對台灣<br />
已立案的原住民樂舞團體進行調查,其研究重心放在團體的經費,以及與政府單<br />
位的互動,她建議原住民藝術展演團體應加強自我,提升展演作品的「質」;而<br />
政府機構則應設置專門專業行政人才與單位,建立一套完整公平的補助政策。<br />
經由以上對原住民樂舞團體研究的文獻的概括回顧,筆者發現目前的研究多<br />
偏重於大型觀光地點的「附屬表演團體」,以及「原舞者」,對於非此兩類經營模<br />
式團體的研究不多,且多屬單一個案研究,而陳甦蘭(2003)的研究則是側重於<br />
補助政策的探討,對團體的其他經營面向相對著墨較少。因此,為能更深入瞭解<br />
原住民樂舞團體的各個面向,獲得豐富且足夠分析的研究材料,本研究由 92 年<br />
至 94 年度入選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原住民藝術展演團隊扶<br />
植計畫」之樂舞團體中,選取了「Amis 旮亙樂團」(以下簡稱「旮亙」)、「花蓮<br />
縣原鄉藝術舞蹈團」(以下簡稱「花蓮原鄉」)、「台灣原住民原緣文化藝術團」(以<br />
下簡稱「原緣」)、「杵音文化藝術團」(以下簡稱「杵音」)以及「南島舞集」(以<br />
下簡稱「南島」)5 個團體作為研究個案,進行半結構性訪談分析,以下茲就分<br />
析結果做進一步的討論。<br />
二、原住民樂舞與族群<br />
在本研究所訪談的原住民樂舞團體之中,筆者發現這些樂舞團體的節目取材<br />
來源,經常是與成員以及地緣有密切關係;而其所選擇的樂舞,有些來自於神話<br />
傳說故事,有些是部落的生活片段,最常出現的則是傳統的祭典儀式。趙綺芳<br />
(2004:40)曾提到過去的原住民樂舞與部落的共同生活密不可分,而且部落社<br />
會的傳統儀式,也為經典樂舞提供了滋養的基礎與實踐的情境。當這樣的樂舞要<br />
搬上舞台展演,對於某些部落而言,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新嘗試,他們必須為「傳<br />
統」找到一套新的詮釋方式,而這個詮釋過程則是透過樂舞團體與部落的協調互<br />
動來共同完成,其成果即為舞台上的演出。筆者認為,團體田野採集的對象之所<br />
以與成員組成以及地緣有密切關係,採集的便利以及舞台呈現效果是一部份的原<br />
因,另一方面,同族群/部落的關係,比起外族/其他部落而言,或許因著同胞<br />
的情誼以及對歷史文化傳統的相近理解,而能夠使得協調的過程進行的較為順<br />
104
利,這也反映了同族/同部落的認同感,仍在原住民樂舞團體的運作中,占有著<br />
相當的份量。<br />
作為「部落」以及「舞台」的聯繫者,這些樂舞團體的編舞者、表演者,負<br />
有著詮釋、再現文化的責任,關於何謂「原住民」的樂舞、何謂「傳統」,「原緣」<br />
的團長柯麗美有這樣的詮釋:<br />
傳統沒有一個答案,原住民的東西,由原住民自己做,原住民在部<br />
落成長,看到的那種「真」,他有接觸到那種土質、精神(2006/7/19<br />
筆者訪談柯麗美記錄)。<br />
由以上這段話可以解析出幾個重點—傳統可能為個人各自表述、原住民才能<br />
做出「原住民的東西」、部落經驗是創作的來源。在柯麗美的陳述中,她以「真」、<br />
「土質」、「精神」來描述提供原住民創作來源的「部落經驗」,其所指涉的是一<br />
種來自於個人所感知的社會文化環境。類似的說法也在「原鄉」團長葉芬菊的訪<br />
談中出現,她將每一族的韻味稱為「族韻」,她認為如果沒有在部落長大,那個<br />
「韻」就不對了。由兩位團長的回應,可以看到她們都認為原住民樂舞是無法憑<br />
空創造得到的,而必須與表演者的個人生命、部落經驗相結合。然而「原住民部<br />
落」本身在現在已是個相當難界定的區域分界,隨著交通、經濟的發展,人口的<br />
移動、族群間的通婚,今日所稱的「部落」,早已不若日據時期(或日據時期以<br />
前)有著緊密組織、相對明顯的界分,也並非每一位原住民都有著「部落生活」<br />
的經驗,因此,在欲將原住民文化轉為舞台演出時,這些樂舞團體也必須返身回<br />
歸去找尋族群的「部落記憶與經驗」,對於節目的製作以及團體的自我定位,本<br />
研究所訪談的各團體有不同的作法及詮釋。<br />
團員大多來自花蓮縣光榮村阿美族女性的「原鄉」,由於都是同部落的族人,<br />
傳統樂舞的學習自然也是由村落裡較年長的女性傳授而來,但在新舞碼的創作<br />
中,則是以中生代為主力。團長葉芬菊在描述其與原舞者不同之處時,做了以下<br />
的詮釋:<br />
原鄉的優勢在於背後有個光榮村,原舞者雖然到部落採集,但還是<br />
和部落不一樣…原舞者我知道他們很強調採集,就是一大群人到部<br />
落一住好幾個月,努力做田野筆記,在文史工作上他們是最好的,<br />
但 copy 的不會比原本的好,舞台畢竟是舞台,部落才是真正有生<br />
命的。(2006/2/17 筆者訪談葉芬菊記錄)。<br />
由此可以看到「原鄉」的自信來源,在於她們是目前正生活在部落、與部<br />
落結合的團體,也因此擁有著生命活力。而位居台東,以竹製樂器打擊為特色的<br />
「旮亙」,則是強調樂舞要與部落老人家的記憶連結,團長夫人哈路蔚‧達邦在<br />
回憶創團經過時,提到阿美族的一些樂器失傳已久,團長必須靠著中研院的樂器<br />
105
記錄,將平面資料轉為立體,做好後拿給部落的老人家看,喚起他們的歷史記憶,<br />
一件件的將這些樂器重建製造出來。雖然「旮亙」製作的樂器以及歌謠,都會加<br />
入自己的改編,但從訪談中可以看到他們很重視耆老的認可,「旮亙」的行政助<br />
理陳雅慧在回應樂曲創作從何而來的問題時這樣說道:<br />
編曲都是團長一個人在用,主要是童年的記憶,團長不希望失去傳<br />
統,他編的歌老人家都會唱,像「風箏」就和老人家的記憶有連結<br />
(2006/7/28 筆者訪談陳雅慧記錄)。<br />
在「杵音」的部分,耆老團員是以馬蘭阿美族長者為主,雖然是老人家配合<br />
中生代,視劇情需要加入演出,但在團長高淑娟的陳述中,可以看到她期望的是<br />
以樂舞團體為媒介,讓大眾直接領略部落耆老的歌唱之美,她在受訪時這樣說道:<br />
我們性質不一樣,我們給老人照護,把他們帶出來,讓他們感受到<br />
他們的重要性,他們也會想別族都在傳承,那我們阿美族呢?所以<br />
他們(註:老人家)都把我們當孩子,我爸爸也是在教堂工作,因<br />
為爸爸的關係而和他們有接觸,老人家也很感動有人願意做傳承,<br />
而來幫忙我(2006/3/30 筆者訪談高淑娟記錄)。<br />
「杵音」不只是要讓社會大眾看到原住民的樂舞,更希望原住民自身—包括<br />
原住民的中生代、新生代—也能由長者的演出,瞭解自己的文化、自己族群的樂<br />
舞,其不只需要老人家的肯定,更冀望耆老也能認可自我的價值、重要性,這是<br />
一種雙方向的認同。而「原緣」的團長柯麗美也同樣強調部落耆老的重要性,她<br />
認為這是呈現原住民傳統樂舞的必備,透過這些老人家的演出,才能將原住民的<br />
「氣氛」展現出來,她這樣指出:<br />
我有一個原則,我一定要用老人家,因為整個的氣氛整個的感覺會<br />
出現,如果都是一票年輕人,又不同族的,那簡直是…(2006/7/19<br />
筆者訪談柯麗美記錄)。<br />
柯麗美提到這些老人家都是她在進行田野調查時認識的,她同樣也強調和部<br />
落一起生活的重要性,特別是成員出身來源,她認為原住民樂舞必須要有老人<br />
家,一定要有來自那個族群的成員,她提到「民族舞蹈」就是應該要按照民情風<br />
俗,「沒在那個地方,跳得其實真的是含糊」,她這樣形容。<br />
以單親家庭學生為主的「南島」,同樣也是透過田野調查來學習傳統樂舞,<br />
但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他們是將採集得來的傳說,加上了許多的現代舞元素,其<br />
保留了部分的族群傳統樂舞,另一部份則用「象徵」的方式呈現主題。「南島」<br />
的藝術總監浮漾這樣詮釋他的做法:<br />
106
我自己想在提倡的,例如繪畫,每個時期有每個時期的風格、畫風,<br />
舞蹈和繪畫一樣,都是藝術的東西,這個時代必須找出新的原住民<br />
文化,你說九族文化村難道就是傳統了嗎?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br />
我做出來,我也沒有說要誤導人家還是怎麼樣,所以我強調是「創<br />
作」(2006/4/3 筆者訪談浮漾記錄)。<br />
浮漾以「現代舞」的元素,將原住民樂舞由「部落」認可的部分,轉移到「個<br />
人」對文化理解的象徵層面,並定位為「新的原住民文化」,這反映了新一代原<br />
住民的另種思考方向;然而,他強調舞團新成員必須先由「傳統舞」學起,這也<br />
顯示了其認為「傳統文化」仍是必須先熟習的。<br />
由上述這 5 個團體的訪談資料,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對「原住民樂舞」進行詮<br />
釋、行動,田野的採集與學習是毫無例外的過程,但因著各團的組成狀態、主事<br />
者的解讀,而開展了不同的運作方向。此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老人家」的角色,<br />
在這 5 個樂舞團體裡,從成員、田野採集學習的對象、演出的表演者,皆可看到<br />
耆老的重要性,即便是如「南島」這個以學生為主的團體,在大型展演時,亦會<br />
請到部落耆老進行演出;一來是因為各個團體演出節目的角色需求,另一方面,<br />
耆老也象徵著新一代原住民與「傳統文化」的橋樑,在中青輩紛紛外流至他鄉工<br />
作求學,部落文化出現斷層時,這些老人家便成了文化的守護者。因此,當團體<br />
返回部落向耆老學習樂舞時,代表著他們將藉由這些長者,重新與自己的族群歷<br />
史搭上聯繫,將個人以及部落群體串連起來。<br />
當原住民將自己與族群連結起來時,其同時也承載了族群的現況。根據原民<br />
會最近期的統計年鑑《九十一年臺灣原住民族統計年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br />
會 2004)的資料,筆者歸納出幾個影響原住民樂舞團體較大的層面進行討論。<br />
首先是經濟,在 2002 年的統計中,將原住民與一般民眾的經濟以及勞動狀況相<br />
比,則可以歸納出幾個特點—收入少、薪資低、勞動參與率高、失業率高、農工<br />
職業比例高,這種經濟上的弱勢現象,使得許多原住民難以將人力以及物力投資<br />
在「樂舞團體」這種文化組織上,特別是青壯年的男性。由資料數據中可以看到<br />
原住民的勞動參與率中,參與率較高的年齡層集中在 25 至 49 歲之間,且男性高<br />
於女性,這可解釋為何樂舞團體的組成會有性別年齡不均的差異存在。<br />
其次則是教育程度,在 91 學年度的調查中,原住民學生中,得以就讀高等<br />
教育的人數仍是少數,而整體原住民的教育程度則以小學或以下程度的占較高比<br />
例。雖然教育程度的高低並非參與樂舞團的評判條件,但在與政府單位以及外界<br />
交涉時仍有其優勢,這也形成了大多數原住民團體的團務往往集中在受過較高等<br />
教育的團長或少數幹部的原因。再來則是人口的因素,原住民在台灣為少數族<br />
群,一方面成就其「特別」之處,但另一方面卻也代表著與主流族群之間的懸殊<br />
差距,加上原住民內各族群本身的文化、部落狀況差異,使得原住民在文化傳承<br />
上的人力相當吃緊,在藝術市場競爭中顯得微力。<br />
107
由上述的資料中,可看出相對於廣義的漢族,原住民在經濟、教育、人口的<br />
族群現況普遍較居劣勢,在本研究所訪談的團體成員之中,有幾位都提到了原住<br />
民的「弱勢」處境,部分指涉的是原住民族的經濟、教育層面,有些是指原住民<br />
團體與部落的困境,也有的是文化上的貶抑歧視。王甫昌(2003 15)曾提到弱<br />
勢者的「族群意識」元素有一項是「不平等認知」,他認為這是指成員意識到自<br />
己的群體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這種不公平可能包括了政治權利被剝奪、受教育的<br />
機會比較差、實際可以得到的經濟報酬比較差或是文化受到優勢族群貶抑等等各<br />
類型的歧視待遇;王甫昌認為,弱勢族群的不公平認知,是在建構一種由弱勢者<br />
的立場出發、對應於優勢者意識型態的理解世界之新觀點。若如王甫昌所說,弱<br />
勢族群的不公平認知是在建構理解世界的新觀念,那麼,對於原住民樂舞團體的<br />
成員而言,他們所欲建構的觀念為何?<br />
「杵音」的團長高淑娟認為原住民的團體在人才培育上,本身就是弱勢,成<br />
員的生活經驗、觀念,也使得原住民團體在推展上有其先天上的困難,她這樣描<br />
述:<br />
原住民團隊本來就是弱勢,需要被扶植,更何況原住民人才培育那<br />
麼少,拿去和非原住民團體比較,這不公平,過去台東馬蘭有一萬<br />
多阿美族,但在推動文化的不過 3、4 個人,要長期經營,很難。<br />
部落老人家要走出部落本來就不容易,我好不容易帶他們出來到台<br />
北中正紀念堂、國外,見識到不同的文化,這很不容易,表演還要<br />
教他們走位,去找他們還要自費帶飲料,自己都要倒貼,非原住民<br />
社團是讓人繳費來學,原住民社團已經很弱勢,還要倒貼,一般學<br />
生來,有時還要用拜託的,要給表演費,還要義務教學、友情贊助,<br />
他們(註:學生)就算以後想升學,也沒有藝術學校。原住民的思<br />
考還沒成熟到義務奉獻當團體的志工(2006/3/30 筆者訪談高淑娟<br />
記錄)。<br />
由高淑娟的陳述可以看到她對於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團體差異的情境解讀,同<br />
時也提到了原住民樂舞團體要發展為職業團體的困難處,她認為現在的環境無法<br />
讓年輕的學生長久留在原住民樂舞這個領域,而部落老人家要走上舞台則需經歷<br />
一番心理調適,反映出部落與現代舞台相遇的衝擊。因為有著對原住民人才缺乏<br />
的感慨,高淑娟在提到未來團體發展時,便有了這樣的期許:<br />
有時候急不得,展演是一部份,我還想辦的是台東的研習營,台東<br />
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立案,我們想去協助,培養企畫人才,我們也<br />
是政府培育的,但人數還不夠多,我現在仍想先走藝術教育的推展<br />
(2006/3/30 筆者訪談高淑娟記錄)。<br />
108
高淑娟的期許實際上已超越了一般藝術的推廣範圍,而進入到文化培育的部<br />
分,其一方面認為政府單位應盡力協助樂舞團體的扶植,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自<br />
己的方式,來改善台東原住民整體結構上的人才問題,這更再次顯示了樂舞團體<br />
與族群、文化的連結。<br />
提到「人才缺乏」問題的不只「杵音」,「原鄉」的團長葉芬菊同樣也是強調<br />
「人才」的重要,她認為一個團體要發展的好,一定需要有專業人員,她同時也<br />
提到現今部落影響到了樂舞團體的部分:<br />
原住民部落大多生活也沒很好,要他們常常花時間在義務幫忙很<br />
難,更別說要發展精緻化了。<br />
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人才政策失敗,目前都只是要維護,維護<br />
死的東西做什麼,我們不需要被放在博物館…如果部落的人都有心<br />
有共識,這些不是問題,只是現在部落內部都被利益以及外界的力<br />
量瓦解了,原先部落的活力衰退了(2006/2/17 筆者訪談葉芬菊記<br />
錄)。<br />
葉芬菊的看法提到了兩個與部落現況有關的部分,一個是經濟問題,一個是<br />
部落的分化狀況。在經濟方面,從「原鄉」的例子來看,當一個團體無法提供足<br />
夠的固定薪資時,就僅能依靠成員的義務的付出,然而成員個別的生活經濟壓力<br />
卻又影響義務付出的限度,這在必須擔負家計的中青輩男性中特別明顯;專業人<br />
才、人力以及資源的不足,導致了表演節目精緻化的瓶頸,也連帶影響了市場的<br />
推廣,於是又回歸到了團體的經費收入來源問題,形成了原住民樂舞團體困境的<br />
迴圈。而在部落的分化部分,葉芬菊認為現今部落受到了利益以及外界力量影<br />
響,使得部落的向心力、活力衰退,則亦發削減了樂舞團體的力量。葉芬菊同時<br />
也提到現今台灣有許多的原住民樂舞團體,都是因為經費問題,不到 3 年就便瓦<br />
解,或是一分為二,因此如何讓成員在有限的經費下,願意留在團體裡,就必須<br />
要維持團體的活力有趣、成員互利,葉芬菊表示這是件不容易的事,她自己也在<br />
慢慢思考著團體的未來方向。<br />
「原緣」的團長柯麗美也有提到原住民的經濟問題,由於「原緣」的學生團<br />
員是由團裡提供食宿,使得經費更為吃緊,但她盡量是以較樂觀的心情去面對,<br />
她在描述原民會經費延遲的情況時這樣說道:<br />
原住民已經夠窮了,等於積欠了一堆,因為我們並沒有那些預<br />
備金,沒有金主在後面幫忙,我們不是原舞者,演出團練而已,<br />
我是養人,從零開始,讓他們由不會到會,還有他們的一日三<br />
餐還有什麼就業的,看是做什麼,我這邊很多的方向啦,我這<br />
邊有一些單親的學生,但我不會用那種悲情去跟人家告訴我多<br />
麼窮怎麼樣的,因為我也聽過,我覺得太多的訴苦,會變的真<br />
109
的苦(2006/7/19 筆者訪談柯麗美記錄)。<br />
同樣也在「養人」的還有「南島舞集」,由於成員都是單親家庭的學生,普<br />
遍家庭經濟狀況都不好,為了籌措學生的學費以及生活費用,「南島」也是壓力<br />
極大,但團長莊珍莉也是盡量用積極的態度去面對,「說苦嘛,還是有人比我們<br />
更苦」,她這樣詮釋,所以她們仍然願意去義務支援社區以及學校的教學,希望<br />
多提供一個傳承文化的管道。<br />
在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團體經營的部分,「原緣」的團長柯麗美也有提出了她<br />
的觀察,她這樣描述:<br />
原住民沒有那種存款、少可以積多的那種觀念,因為從小看到一群<br />
長輩們帶著獵槍往山上跑,然後扛了山猪回來,然後就休息阿,吃<br />
山猪,沒有肉了再上去,對財務的觀念是「沒有了再去」的觀念。<br />
這邊學生彼此都不了解,從小就幫爸爸買小米酒長大的,酒對他們<br />
就像白開水,一大早起來一堆酒瓶,所以我為什麼在家裝卡拉 OK,<br />
就是不願意他們在外面喝(2006/7/19 筆者訪談柯麗美記錄)。<br />
由柯麗美的描述,可以看到某些部落經驗,形塑了原住民或是原住民學生的<br />
生活態度,但在團體的經營上卻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難。對於有學生團員的原住民<br />
樂舞團體,其功能不只是樂舞訓練教學,同時也要扮演著類似「家長」、「導師」<br />
的角色,配合團員的個性、生活態度,調整帶團的方式,擔負著比一般團體更大<br />
的社會責任。<br />
除了對原住民弱勢教育、經濟處境的理解外,「旮亙」也提到了原住民在學<br />
術上以及文化上被貶抑的情形,以及他們的反應,團長夫人這樣說道:<br />
他(註:團長)不要像一些學者,做完研究都沒有回饋到社會,所<br />
以他先將中研院的資料由平面轉為立體,拿去給老人家看,老人家<br />
看了很驚訝,這些東西勾起了他們很多的歷史回憶。<br />
我們有過這樣的經驗,在南投表演的時候,有個阿媽說:這就是番<br />
仔阿(台語)!那次表演有阿媽這樣講,也有學者批評不夠傳統,<br />
我問他(註:團長)要怎麼樣,他說不要管他們,做我們自己就好<br />
(2006/3/30 筆者訪談哈路蔚‧達邦記錄)。<br />
由哈路蔚‧達邦的訪談中,可以看到原住民對於過去成為學術研究被動角色<br />
的反感,這也更激發了他們自主研究傳承的動力,並重視與部落的連結,發展出<br />
自己的詮釋應變。此外,由「旮亙」的表演經驗中,也可以看到有些一般社會大<br />
眾對原住民,仍然有著「番仔」這種貶抑的印象與觀念,原住民樂舞團體則必須<br />
要在這樣的環境中,堅持找出自我的認同。<br />
110
三、樂舞團體與環境<br />
除了要找回自我族群的認同外,樂舞團體的生存必須依靠與外界的互動來達<br />
成,在本研究對樂舞團體的資料分析中,發現現今原住民樂舞團體的運作經費,<br />
主要是來自政府單位的補助、觀光活動的演出費、政府以及民間企業活動企畫盈<br />
餘、合作教學的鐘點費以及相關產品的販賣等,較少進行賣票的劇場舞台演出。<br />
為瞭解樂舞團體與不同環境因素的互動情形,本研究訪談了團體對於「原民會」<br />
藝術展演扶植計畫以及觀光場景的看法,以下將分別討論。<br />
為了扶植樂舞團體永續經營,提升專業創作及展演水準,1997 年「原民會」<br />
訂定了「原住民族藝術展演團隊扶植計劃」,其規定近似文建會的「演藝團隊發<br />
展扶植計畫」,但限定為從事原住民音樂、舞蹈、戲劇等藝術展演活動的團體申<br />
請,門檻條件以及評選標準亦較為寬鬆。根據筆者整理近三年的計劃審查結果所<br />
得,在 93 年度的計劃中,原民會自 13 個團隊中選出 10 個團隊扶植,分別獲 20<br />
至 50 萬元的經費補助;到了 94 年度,則由 10 團選出 7 團,扶植金額總計為 325<br />
萬元;到了 95 年度則縮減為 7 團選出 4 團,個別補助金額最高為 70 萬元。由此<br />
可以看到近年來的扶植計劃的獲補團數逐年減少,有走向重點補助的趨勢;另一<br />
方面,根據原民會行政人員的說法,95 年度的預算被砍至 200 萬,原民會希望<br />
縮減獲補團隊數,將補助留給真正需要的團隊,也是形成這個趨勢的其中一項因<br />
素。<br />
在陳甦蘭 2003 年的研究中,曾提到她認為原民會的相關展演補助計劃多無<br />
一定的補助原則以及補助標準,而採取「雨露均霑」、「通通有獎」的方式;她在<br />
研究中亦發現原住民樂舞團體對於原民會的補助以及扶植機制的質疑與意見,主<br />
要是在審查制度、審查時程,以及補助經費的額度。在筆者 2006 年對樂舞團體<br />
的訪談中,同樣的問題依然被提起,特別是扶植計劃審查結果公布的時程,如「杵<br />
音」的團長高淑娟便這樣說道:<br />
企畫是當年要做,而他們(註:原民會)拖到八月仍在審查,九月<br />
才發佈,十月就要表演,有些演出經費都要自己消化,負荷很重,<br />
我們現在也是有經費就做,沒有就算了,但要早點告訴我們嘛!一<br />
般政府計劃案四、五月就會通知,其實很多團隊現在也都是先暫時<br />
不要做(2006/3/30 筆者訪談高淑娟)。<br />
關於時程的問題,原民會的行政人員表示這與立法院的預算、招標的時間有<br />
關,而部分團體的拖延以及補件也是原因之一,該行政人員同時也提到團體不能<br />
單靠原民會的補助,應該要預先設想、規劃,他這樣說道:<br />
原民會的補助不是全額而是部分補助,團隊不能只靠政府,政府的<br />
錢只能作某一部份的加強,而不是沒有補助就什麼都沒有。要規<br />
111
劃,不能一直再等錢,要先設想有或沒有的狀況。今年有先告知團<br />
隊審查結果會延後,應該團隊都習慣了這個時程,我們會盡量快,<br />
但不一定能(2006/3/24 筆者訪談原民會行政人員)。<br />
由此可以看到原民會的立場是希望團體能自立自強,不論是否獲得補助,補<br />
助時程是否延後,都應該有一套維持運作的計劃;但對於本研究所訪談的原住民<br />
樂舞團體而言,原民會的補助仍是其主要經費來源,是否獲得補助、補助金額多<br />
寡,對於團體而言影響相當大,在結果尚未確定之前,團體不敢貿然的做太大的<br />
節目投資,只好存著等待觀望的態度。<br />
另外在補助金額的部分,各團均表示不夠多,「原鄉」的團長葉芬菊即直言<br />
原民會的補助經費,不足以提供團裡聘請專職人員,她這樣提到:<br />
如果你要發展好,一定要有專業人員,如果一個專職行政人員每個<br />
月給他兩萬,一年就要 24 萬,那剩下的十幾萬能做什麼?還要付<br />
水電、燈光、音響、服裝,還有去表演的交通費,這些十幾萬那裡<br />
夠(2006/2/17 筆者訪談葉芬菊)。<br />
對於團體的意見,原民會行政人員在受訪時則是做了這樣的回應:<br />
到底多少夠?所以他們也要去瞭解其他團體是如何經營,例如雲門<br />
和朱宗慶也是慢慢起來,這是要看團長有沒有這個決心,只要(團<br />
隊)有好東西,人家就會來。…有沒有企圖心很重要,一場可以從<br />
50 元開始,但要讓讓有願意花 50 元來看的價值。要有決心,就能<br />
做到,不要只是一直認為自己是弱者,國家就應該資助。<br />
對原民會和團隊來說,只是發錢就沒意義,而是應該好好的運用<br />
錢,自立一點,希望最好能達到政府的錢都不用就能自己營運<br />
(2006/3/24 筆者訪談原民會行政人員)。<br />
由雙方的回應,可以看到原民會和團體的認知上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原住民<br />
樂舞團體自認「原住民」在台灣本身便是弱勢,原民會有義務要提供團體足夠的<br />
援助,讓團體能較無後顧之憂發展;但站在原民會的角度,卻不希望團體過於依<br />
賴補助,期望團體能自行開發財源,減少政府補助的部分。<br />
另在審查的制度上,原民會的行政人員表示以前是採取有申請就給錢,沒什<br />
麼扶植效果,後來就改為招標方式,並配合研習營、行政管理類的課程,加上專<br />
人陪伴的方式,希望能培養團體行政運作的能力。在他的業務觀察經驗中,他認<br />
為目前原住民樂舞團體本身在演出以及經營態度上,存有一些問題:<br />
有些團隊覺得自己很好,有邀約、有觀眾就 OK,但是老師他們很<br />
112
擔心,因為團隊會越來越沒特色,把一些有的沒的加到舞蹈上去,<br />
上次有老師來評審,覺得表演有「衝動」、「振奮」,觀眾也覺得很<br />
熱鬧,但是卻沒有感動。我們觀眾也是以為熱鬧就好,而不瞭解意<br />
涵,觀眾、表演者都不知道,要如何去改變(2006/3/24 筆者訪談<br />
原民會行政人員)。<br />
由上述行政人員的訪談點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創意」的界線在那裡?原住<br />
民樂舞的標準如何評判?如同其所指的—團體「自以為」創意,在筆者的訪談中,<br />
原住民樂舞團體則是質疑外界總以「傳統」來要求,他們認為文化本身即是不斷<br />
變化,並「自認」具有詮釋文化的能力,如「原鄉」團長葉芬菊便這樣說道:<br />
文化就像水一樣,滲透的很快,會一直變,我們不用阻擋,只要保<br />
留住最真的東西—精神。…光榮村有位古金水的爸爸,編了很多<br />
歌、舞,都帶有一些日本的味道,這是因為皇民化的影響,有人會<br />
說,這到底是阿美的還是日本的?事實上有什麼東西是純的,文化<br />
就是這樣搓合的過程,就像水加麵粉成為湯圓(2006/2/17 筆者訪<br />
談葉芬菊)。<br />
「旮亙」的團長夫人亦提到反對博物館式的傳統:<br />
那個竹鐘其實以前是單管,但是他(團長)覺得一次只打一個太浪<br />
費,就把好幾個組合在一起,有些學者就批評不傳統。說實在,要<br />
傳統要去墳墓和博物館找,像台東有展示一個鼻笛,早就不能吹<br />
了,我們的都有加入自己的改編,他們又要展演,又要傳統,他們<br />
自己來打打看阿(2006/2/17 筆者訪談哈路蔚‧達邦)。<br />
「傳統」以及「創新」,一直是原住民樂舞展演始終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也<br />
顯示了原住民樂舞團體不同於一般走純創作藝術團體的「特性」,「活的文化」與<br />
「自以為的創意拼湊」本身並沒有明確的規範界定,今日流傳下來的原住民樂<br />
舞,也有許多融入了其他族群的元素,形成「傳統」論定的困難,經常是審查爭<br />
議的來源之一。<br />
然而,在雙方的角力過程中,政府方面的優勢在於掌握有樂舞團體所需的資<br />
源,若團體需要補助,就必須符合規範,繳交完整的企劃書,聽從評審的意見;<br />
但筆者在訪談中發現團體也逐漸瞭解到與政府交涉的重點,因此,企劃書的撰<br />
寫、培養企劃人才成了團體發展的目標之一,同時也有團體充分利用自身熟習原<br />
住民樂舞的優勢,積極的爭取政府計劃的承辦/協辦,既開拓了財源,也增加不<br />
少曝光機會,特別是近年來台灣積極發展觀光,地方政府努力籌辦活動,更是增<br />
加了原住民樂舞團體發展的空間。這個現象反映了部分樂舞團體已經逐漸掌握到<br />
113
如何製作出合乎上意企劃的技巧,利用政府的資源,拓展樂舞團體以及族群文化<br />
維繫傳承的機會。<br />
除了政府的補助外,在本研究所訪談的團體中,觀光活動亦是團體的重要財<br />
源,在這些團體對觀光的態度中,可以知道他們並不排斥觀光,對於觀光環境的<br />
條件與限制,他們則認為可以透過自我的詮釋來進行編改,如「原緣」團長柯麗<br />
美便提到她對觀光的態度:<br />
觀光是另外的我們文化的一種商機,因為必須提升部落的什麼什<br />
麼,他必須要藉著觀光的東西。... 其實你要分清楚,我不反對觀<br />
光,因為人總是都要吃飯,會接觀光,觀光這個東西其實也不好玩,<br />
要一直變化,重要是觀眾遊客互動的吸引,要創造商機,不只對你<br />
的商機,還有你四周周圍的…其實觀光的東西,遊客來自不同的家<br />
庭,來自不同的階級、身份,他又不是文化學者,只是來歡樂,瞭<br />
解一下東西,我是覺得不要太商業化,10 個舞碼至少有 3 個舞碼<br />
是傳統的,7 的舞碼是帶動觀光比較 high 的,讓觀眾遊山玩水累了<br />
來這邊抒解,看到很美的東西,聽歌,等於是種休閒,表現不要很<br />
低俗,要有個層次,有個味道(2006/7/19 筆者訪談柯麗美)。<br />
柯麗美認為觀光客本身僅是為了休閒娛樂的目的而進行觀光活動,她認為樂<br />
舞團體就應該提供一個抒解的情境,有個「味道」就好,重要的是達到與觀眾的<br />
互動,並為團體以及邀請單位創造商機。柯麗美同時也提到了在不同表演場景下<br />
的調整,譬如在國外演出時是以現場演唱為主,但在國內的觀光場合,因為經常<br />
需要重複唱跳,便改以事先錄製好的 CD 播放,節省體力;另在表演節目以及服<br />
裝上,她認為國外的演出可以安排多一些族群,穿著各族群的服裝,以讓外國的<br />
觀眾欣賞到台灣原住民多族群的美,在國內分界就必須清楚,傳統或創新也要對<br />
觀眾說明,不可混淆。<br />
「南島」則是提到「創新」要比「傳統」有助於在原住民的樂舞團體中凸顯<br />
出來,其藝術總監浮漾這樣描述他的觀感:<br />
我們本來也做傳統的表演藝術,可是後來發現大家都認為原住民的<br />
舞蹈,進場是很吵、很熱鬧,很外放,後來許多原住民團體都成為<br />
一樣,所以我們還是走創作,找原住民表演新的元素,在服裝上面,<br />
雖然走創作風格,但還是不離開傳統,還是原住民服裝,把傳統和<br />
創新結合在一起。…我們也出去接很多案子,北中南都跑,階梯數<br />
位 30 週年也是我們去開場,當我們轉型做創作以後,場子變多了,<br />
路變廣了(2006/4/3 筆者訪談浮漾)。<br />
浮漾提到「南島」會依照邀請單位的需求,創作符合主題的節目,但其也仍<br />
114
然強調會讓團員先熟悉傳統的樂舞,之後再學創作,以免誤導。而在「旮亙」的<br />
部分,其同樣也表示會因應場合調整演出,但會堅守底線,不讓商業破壞團體的<br />
自主權:<br />
我們表演很有彈性,吃飯的當然就熱鬧一點,給學者的就會傳統一<br />
點。我們絕對不讓別人牽著走,所以我們不要財團介入,這樣會失<br />
去自主權(2006/3/31 筆者訪談哈路蔚‧達邦)。<br />
由上述的團體經驗,可以看到原住民樂舞團體如何在觀光場景中,創造出給<br />
予觀光客的「舞台性真實」(MacCannell 1973:593),其對於台前、台後,以及各<br />
個場景的轉換,均有自己的一套詮釋想法。雖然有一部份論述(史邁克 1991;<br />
瓦歷斯 1992;孫大川 1991)指出原住民的觀光對部落組織、文化、族群尊嚴造<br />
成傷害,憂心強大的資本體制逐漸侵蝕了原住民傳統的價值觀,使其為了追逐外<br />
界的認同或是利益,而放棄傳統信仰、改變自我,但筆者認為,無論如何,就現<br />
實層面而言,觀光的確提供了樂舞團體經費上的資源,而且在大型觀光活動中的<br />
曝光,也為團體帶來國外的演出機會,擴展更廣的表演場域。<br />
四、小結<br />
透過上述的資料分析,可以看到台灣原住民樂舞團體在性質上與一般專職展<br />
演的團體有相當大的差異,其與部落的關係,除了展現在樂舞藝術的成就,也塑<br />
造了各團體的特色。而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部分,筆者認為,對於原住民樂舞團<br />
體而言,所謂的「前台」不僅出現在「觀光場景」,其與外界互動的各個場合都<br />
可被視作是另一種意義的「舞台」,觀眾可能是民眾,也可能是政府官員、學者、<br />
評審,樂舞團體配合對方的需求,調整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做出合理程度的妥協。<br />
但是,對於後台的空間,團體則各有堅守的原則,抗拒外界的干涉,筆者認為這<br />
些原住民樂舞團體正努力的想反轉外界所加諸的刻板印象與唯一標準,而導向認<br />
為團體具有詮釋自決的能力,建構起團體獨一無二的價值。<br />
115
參考書目<br />
王甫昌<br />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br />
史邁克著,廖碧英譯<br />
1991 觀光事業與台灣原住民。載於林美瑢編,原住民與觀光—從社區主<br />
瓦歷斯‧尤幹<br />
江冠明<br />
權、文化尊嚴、經濟價值談起,頁 23-36。台北:永望文化事業有限<br />
公司。<br />
1992 荒野的呼喚。台中:晨星。<br />
2002 創新的認同—三地門文化產業中的現代認同與變遷。國立東華大學族<br />
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br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br />
吳錦發<br />
周文茵<br />
周慧玲<br />
胡台麗<br />
孫大川<br />
陳揚威<br />
陳甦蘭<br />
2004 九十一年台灣原住民族統計年鑑行政院。台北:原住民委員會。<br />
1993 原舞者:一個原住民舞團的成長記錄。台北:晨星。<br />
2004 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實踐與反思—以布農文教基金會為例。國立政治<br />
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br />
2002 田野書寫、觀光行為與傳統再造:印尼峇里與臺灣臺東「布農部落」<br />
的文化表演比較研究。臺灣社會學刊 28:77-151。<br />
1994 從田野到舞台—「原舞者」的學習與演出歷程。當代 (98):30-47。<br />
1991 久久酒一次。台北:張老師。<br />
2003 現代舞與文化認同—當代臺灣原住民編舞者研究。南華大學美學與藝<br />
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br />
2002 我國對原住民藝術展演補助政策之探討—以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br />
為例。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br />
出版,台北。<br />
陳嘉宏、范姜泰基<br />
2006 政治掛帥 淪為選戰配角。中國時報,A3,3 月 6 日。<br />
游景德<br />
1996 文化行銷—臺灣原住民文化展現之經營行為初探。國立東華大學企業<br />
116
黃姿盈<br />
趙綺芳<br />
譚雅婷<br />
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br />
2005 原住民歌舞團體的演出形式與音樂內容-以「杵音文化藝術團」為<br />
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br />
2004 臺灣原住民樂舞與泛原住民主義的建/解構。臺灣舞蹈研究<br />
1:33-62。<br />
2003 原住民樂舞與文化展演的探討-以「原舞者」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br />
MacCannell, Dean<br />
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br />
1973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br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3):589-693.<br />
117
微弱的歷史聲音,美麗的寶島之歌—<br />
原住民女性社會運動者的記憶拼圖<br />
馬昀甄<br />
一、我知道的你看不見—尋求她的過程<br />
從 1984 年到現今的原住民街頭運動,近 20 年間,抗議的行為讓原住民問題<br />
從邊緣浮現。而要瞭解原住民社運史的讀者,只能在學者論述的不約而同?以事<br />
件或議題性的方式建構出當年的歷史概要與評斷找到知識性的建構。觀察現有原<br />
運的相關文獻資料可見,以社會運動事件時間序列、集體性行動為主要探討的書<br />
寫方式佔原運敘述文章有很重的數量 1 。而這些被書寫的歷史的「主體」是誰呢?<br />
被呈現的主體又是誰?社會把「原住民」想像為一個同質的範躊的結果,就是在<br />
對立的前提下,使得「主體」的論述再度忽略了雙重弱勢者的聲音,特別是女性<br />
(劉紹華 1994)。排灣族女作家阿女烏(1993)談到她的田野經驗時寫道:「在<br />
部落史的調查中受訪的都是男性,女性卻常常在背後竊語,私下指正男報導人的<br />
錯誤,女性有另一種與男性不同的記憶與歷史角度,連對地名的命名也不同。但<br />
是,她們卻不願站出來同男性侃侃而談。」<br />
若從社會結構面與歷史殖民的角度來談原住民社會運動。卑南族學者孫大川<br />
(1989)說:大環境的紛紛擾擾,固然是一種歷史的真實;小場面的邊緣世界又<br />
何嘗不是真實的?是以身處邊緣的小場面帶來的是變遷中人的情感、階級等異<br />
動,呈現不同於歷史觀點的微觀思考。而在建構大型知識客體的權力女性無法掌<br />
握,亦無機會重思自己的地位時,女性只好利用其他的形式的表現來保存她們自<br />
1 回顧原住民街頭運動從 1984 年到現今,近 20 年間,官方、民間研究者、原運參與者所出產相<br />
關文獻與書籍評論,與原運相關論述主題粗略分類如下 :探討族群與自我認同有謝世忠(1987,<br />
2004)、許木柱(1990),孫大川(1992,1995),陳茂泰(1993),張茂桂(1995,2002),王甫<br />
昌(2003)。以 原運議題事件、媒體報導與社會結構探究為主的有陳秀惠(1985),黃美英(1990,<br />
1995),鍾青柏(1990),李慈敏(1991),黃宣範(1993),周瑞貞(1998),張岱屏(2000),田<br />
春綢(2000,2006),黃修榮(2001)。原社運回顧與省思有台邦‧撒沙勒(1993),瓦歷斯‧尤<br />
幹(1992),麗依京‧尤瑪(1996),路索拉門‧阿勒(1999),夏曼‧藍波安(2000),陳俊明(2002),<br />
汪明輝(2003)。運動路線理論建構與實踐有夷將‧拔路兒(1987,1993,1994,1995),高德義<br />
(1991),魏貽君(1996)。原運與法令、政策有林淑雅(2000)等。我粗略的用這五大類將原運<br />
主要知識生產的來源,羅列出來。因本文著眼於女性運動者個人生命敘說與細微觀點為主,在此<br />
就不詳細討論以社會運動事件分析陳述的相關論點。綜合前述為文的內容與分類項目發現,各作<br />
者的敘事主體與關照層面都以大環境社會互動下的影響、團體集體行動為主,間或夾雜少許個人<br />
獨特感思,但仍不脫大敘事、整體面思考的範圍。以社會運動事件時間序列、集體性行動為主要<br />
探討的書寫方式佔有很重的數量。而屬於原運裡微觀的個人省思與主體認同部分常一同併入大論<br />
述、集體觀點裡,顯現足跡。那被男性作者視為個人、獨特、小場面的女性經驗書寫,涉及原運<br />
部分,如利格拉樂‧阿女烏(1996,1998)、麗依京‧尤瑪(1996,1997,2001)、劉湘吟(1997)、<br />
鍾寶珠(1998)則穿插在原運文獻資料中,曇花一現。對於當年女性運動者行動抉擇與運動內部<br />
文化可以窺知的面向極少,所知有限。女性運動者經驗的可貴,生命歷程裡面的歡欣與痛苦掙扎,<br />
實是根植於不同於眾多學者與男性運動者文章裡著眼的政治面取向之外。<br />
118
。歷史脈絡中的原住民女性在原住民社會制度裡,既無番刀(知識<br />
生產的個人),也不是獵人(經濟生產的個人)。原住民知識份子書寫歷史只有男<br />
性的份,只有強壯獵人的份,而女性未享菁英位置的歷史仍再度被淹沒(劉紹華<br />
1994)。不過,她們參與過那段歷史的事實,是不能被否定。儘管是小場面的歷<br />
史,但卻能真切的表現對立的結構,強調差異性,使女性的被淹沒的歷史位置重<br />
現。<br />
為能更瞭解女性在原運時期的作為,我試圖藉由訪談女性原運者,重構不同<br />
於歷史大場面敘述的原住民社會運動片段的個人記憶。女性自我生命的述說,是<br />
直接將細微的個體起源作更完整的敘述,輔以個體在社會運動中的表現,個人的<br />
日常生活因為社會運動產生的變遷與影響。在廣大的歷史中由男性扮演陳述的部<br />
分,究竟是History?Herstory?還是Humanstory?現今受到社會、文化複雜多樣<br />
性的影響,女性在歷史的建構論上開始占有一席之地。<br />
本文以生命敘事的方式,訪談五位原住民女性運動者各自敘述片段原運歲月<br />
(1980-1995)的過程,重塑片段原運觀點。在那段參與原運的時光中,如何觀<br />
看這個世界,詮釋自己的生命?發掘出原住民女性運動者不可見的另一面 2 。試<br />
圖擺脫理論的模式將女性生命述說對號入座,先讓「她們」說最後才換「我」說。<br />
再則透過敘事探究的分析方法,從查訪到的女性原運者名單裡,先電話說明<br />
來意後,從中找出受訪意願高的五位女性運動者進行敘事訪談。但此說明的是,<br />
此樣本並非經過普查研究再取樣,進行深入探討,所有受訪者不一定能涵蓋所有<br />
原運面向。就個人生命敘事而言,從有限的受訪者的個人記憶綴補與大環境的歷<br />
史相襯,對部分女性原住民社運者的生命歷程以能提供讀者一個原社運女性形<br />
象,對於社會運動的情景背後,能出脫於其他書寫呈現。<br />
這五位受訪的原住民女性運動者當年進入原運的時間點前後時間差距不<br />
大,約於 1984-1987 年之間,各自從不同面向加入原運的腳步,所以五位女性運<br />
動者的生命歷程裡互有共同的經驗在流動與,而在對話內出現不同的解釋。先以<br />
她們各自的生命故事圖 3 ,來說明受訪五位女性運動者在原運內所見與所聞的角<br />
度與立場:<br />
1. Afan‧LEKAL,為Amis(阿眉族 4 ),年齡 5 44 歲,宗教信仰為基督教,出生於<br />
台東縣長濱長光部落,現為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秘書。Afan的生命故事圖(見圖<br />
一)以直線時序鋪述。虛線大箭號是她人生主要時間。其人生幾度重大的變遷,<br />
從丈夫投入原運的那一刻始,就與原運脫離不了干係,幾乎是原運就是她生活的<br />
全部。她青春的黃金時期,是隨著原運的開展與衰落起伏者,因為愛情使她與丈<br />
夫共同面對這一切。她生命的敘事,是圍繞著愛情與原運而展開述說。我將她的<br />
2<br />
在以下的行文裡,顧及行文便利。我將以「她們」來指稱我的受訪者們—參與 1980 年代以後<br />
的女性原住民籍的街頭原住民社會運動者。而原住民社會運動有時也會簡稱為「原運」,原住民<br />
社會運動者則簡稱為「運動者」。<br />
3<br />
本五式生命故事圖,採集五位受訪者敘說至 2006 年。<br />
4<br />
訪談過後,我用電話分別求證受訪者,她們各自族群識別要如何註解而得。<br />
5<br />
受訪者各自年齡紀錄至本文寫作時間,2006 年。<br />
119
愛情與原運之間的關連,以圓形線條(代表原運)包圍愛心(代表愛情)作解讀。<br />
圍繞在虛線大箭號兩旁的弧形方框則是她自我看待生命每一事件的感受與想法。<br />
2. Sayung‧Losing,為 Tayal,年齡 46 歲,宗教信仰為基督教,出生於桃園縣復<br />
興鄉。Sayung 的生命故事圖(見圖二)從牧師家庭開始,用矩形框鋪述幾個重<br />
大的轉折點凸顯原運與她生命的關係。並利用灰色彎曲箭號壓圖,將重大轉折點<br />
鑲嵌其中。神學院就讀、婚姻、丈夫入獄是她對於自我與原運思考的轉折。為了<br />
方便對照,某些轉折點也加上時間標記。弧形虛線方框說明的是 Sayung 童年背<br />
景以及發現族群差異的事件。彎曲箭號連接到 Sayung 的家庭背景。弧形方框解<br />
釋 Sayung 在轉折點上的心情與處理方式,並可依循方框各尖端接續閱讀相關事<br />
件。Sayung 的運動生命隨著丈夫職位的遷移,在過程裡慢慢耳濡目染。在敘述<br />
上面,Sayung 平鋪直述的以童年、求學經驗、各地服務、運動場合上如何到至<br />
今,階段性的講述來塑造她人生的旅程。從事情本身,行動者的反應,讓 Sayung<br />
間接的找到自己母職角色與運動者的認同角色。<br />
3. Sankilj‧Vacesan,為 Paiwan,年齡 39 歲,宗教信仰為基督教,出生於屏東縣<br />
來義鄉文樂部落。Sankilj 的生命故事圖(見圖三)以中心的黑色方框圍繞敘述。<br />
從這個事件開始,Sankilj 講述她的家庭、學習生活、生命的態度、運動場上親人<br />
的顧慮。我用弧形方框來表示。閱讀順序則以中心點圓形灰色箭號環繞閱讀。<br />
Sankilj 的敘事從找出疑惑的根本開始講述,因為不瞭解所以尋找原因。家庭環境<br />
的單純讓她沒辦法接受神學院的議論,透過運動身體實踐跟家鄉經驗的對照讓她<br />
接受事實,並且開始傳播原住民角色的困境以及反擊的能力。在很多方面的論述<br />
上,我發覺到她是從自己的角度反思、搜尋相關的線索來告訴自己「事實」是「真<br />
實」的現象。<br />
4. Lipay‧Sinsi,為 Amis,年齡為 57 歲,宗教信仰為基督教,出生於台東縣成<br />
功鎮八翁翁部落。Lipay 的生命故事圖(見圖四)是以雙箭頭為主線,粗箭號表<br />
示她主要找回文化身份的事件,細箭號則是參加原運的開始與顧慮。鑲嵌在左右<br />
的箭號以圖形大小來表示找回原住民認同的先來後到。而下弦月的原運托盤,是<br />
包圍她在原運裡面的感情掙扎,長橢圓框裡面以她的觀點說明對方怎麼陳述,而<br />
上方箭形的四角框則是她自己理性所見與解釋。弧形方框陳述個人背景與自覺認<br />
同事件。直角矩形方框特重她接觸原運的時機與重要事件回憶。雙軸線進行於裁<br />
縫編織與原運的鎔鑄。教會牧師的影響使 Lipay 接觸信仰的實踐,在原運場上爭<br />
取權益。而裁縫編織則是讓她找回族群文化的開端。<br />
5. Laya‧Namoh,為 Amis,年齡為 44 歲,宗教信仰為基督教,出生於台東縣真<br />
柄部落。Laya 的生命故事圖(見圖五)從童年經驗到玉山神學院是一個階段。<br />
玉山神學院以後開始投入黨外運動,粗虛線分成兩端在雛妓與勞工、原運兩者間<br />
遊走。灰色箭頭的導引可見她移走的原因與解釋。爾後雙線發展到現在立法委員<br />
的身份。弧形方框引述的是她自我的想法與生命經驗,可依從框線的尖端連結閱<br />
讀到下一方框。直角矩形方框則是將社會運動的論述與個人批判著重標示。矩形<br />
加粗方框則更進一步的強化她作法的原因理由。可以由她的敘事發現,整個時間<br />
120
序列下來是呈現她個人的權利自覺史,從覺醒到力爭。<br />
學者 Clandinin & Connelly(2000)將其分成為敘事探究的三個向度:1.個人<br />
與社會,內在與外在的「交互作用」;2.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續性」;3.在地<br />
情境的「地域性」。透過這些探究,敘事探究裡的故事所描述的不只是在顯示「尋<br />
找和聽故事」,它也是一種生存的形式,一種生活的方式—嘗試在被視為理所當<br />
然的事物之外思考,「讓尋常的事物變得陌生」。進而可以看見敘事者生存於種種<br />
不同的生活壓力底下,強調身份(identity)和活生生經驗(lived experience)的<br />
「生命政略(life politics)」(范信賢 2003)。Goodson and Sikes(2001)指出:「訴<br />
說關於我們生活和我們自我的故事,它做為一種詮釋性反省的手法,讓我們有一<br />
種觀點去理解我們是誰、是什麼,以及種種加諸我們身上所發生的事物。」<br />
而「故事之所以值得講、值得理解,其價值就在於有那難題<br />
(trouble)存在。……『難題』不只是主角和境遇之間的錯配,<br />
而更是主角在建構該境遇之時的內在掙扎。……敘事裡的難題,<br />
其造型並非歷史或文化上的『一了百了』,它所表現的是一種時代<br />
和一種環境。所以『同樣的』故事會一再改變,而對它的理解也<br />
會在同情之中與時俱變,只是其中總會有些先前的優勢處會再餘<br />
留下來」(Bruner 1996;宋文里譯 2001:215)。<br />
但這種個人的獨特性並不是因此就將其視為個案,它的「個人性」是嵌鑲於<br />
「社會脈絡」中的。換句話說,發生在敘述者身上的「故事」,它也可能在其他<br />
人身上發生;發生在「過去、現在」的故事,它也有可能在「未來」發生。因此,<br />
故事即不是個別的故事,放置於社會脈絡中,它可能也反映著此特屬族群的集體<br />
命運(Riessman 1993)。而葉雅玲(2004)認為原住民女性所要面臨的多面向自<br />
我與環境問題,也正是要到了女性真正能提筆思考寫作,方能奪回「詮釋」女性<br />
自我與族群的權力。<br />
121
我是生長在台東長濱長光這個一個小的部落它是算是<br />
阿美族的一個聚落的一個部落。我們是背山面海的。通<br />
常人家就是說ㄟ你們山地人住在山上。我說那我們住在<br />
海邊那應該是不是叫做海邊人。多少都會這樣子回應一<br />
些朋友的一些看法。那我是從小在那邊長大,一直到十<br />
五歲國中畢業之後離開家鄉然後到大都會來求學。其實<br />
剛開始我是直接到工廠去工作,因為家境不是很好,那<br />
就到桃園的一個針織廠工作。<br />
第一個工作五惠實業是針織,國中畢業就來那裡工<br />
作,建教合作,但並沒有讀書阿。我較長的是在五惠<br />
及台麗成衣廠工作,之後較短的大概兩三個月在<br />
RCA(八德路)工作,我去 RCA 的時候就開始唸育達(夜<br />
間部)。<br />
上了一學期,我覺得都市跟鄉下的那種程度相差很<br />
多,而且我又輟學了兩年,我根本就 我覺得我跟不<br />
上同學他們的那種 那種程度,我覺得我的成績太差<br />
了,那時候我就變得好瘦好瘦。<br />
後來,第一年考二專的時候沒有考上,我就來這裡(長<br />
老教會總會)打工,從那個時候打工到現在,二十二<br />
年。後來就上了那個二專的夜間部。畢業後,我又去<br />
唸一個夜間部,讀一個那個基督教的學院,那個時候<br />
二十出頭吧。前前後後大概讀了十年的夜間部。<br />
其實我的民族意識應該是比他們強烈,但是那時候我們,<br />
因為我在教會裡面成長,然後所吸收的資訊都是來自於教<br />
會,後來又進到教會來工作。所以我就覺得,沒有離開過<br />
那種社會的關懷。<br />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一股力量要去,做這樣的事情,因為愛<br />
情嗎?還是對自己族群的熱愛?我想這雙方面都有。從我<br />
自己的母語來看,我的母語講得非常好,而且我也是母語<br />
老師。因為母語給我的影響,然後整個環境周遭的影響,<br />
對我很深刻。所以我覺得應該自己要站出來。因為生命然<br />
後再加上我自己的宗教,生命本來就是要活出它的亮光。<br />
從這個部分我們就會去思考這個問題,怎麼會這樣,當然<br />
那個時候還沒認識夷將,原運還沒開始崛起的時候也不敢<br />
有多大的表達。但是因為長老會的關係,從過去他們對這<br />
個整個社會的影響,連帶的我們在這邊工作的人也會有些<br />
影響,那個是最直接的一個。<br />
我跟夷將是在 1988 年 6 月 4 號結婚。那之前其實我們已<br />
經對整個原運的工作都有很大的那種決心跟抱負。能說<br />
抱負嘛,應該是說為著原住民的權利或者是為著原住民<br />
的理想而戰嘛。那當時有人稱我們是『革命鴛鴦』。<br />
我們應該是還沒結婚就已經他要投入這個原運的工作,<br />
雖然我們知道這是一項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我還是很支<br />
持他這麼做。因為我覺得他對整個原住民有一種責任,<br />
所以就毅然決然的要去嫁他。那…當時就是被這個喜愛<br />
原住民的那種熱忱吸引跟投入整個生命。<br />
結婚,其實跟他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因為我<br />
知道他為了原住民的工作走來走去跑來跑<br />
去,根本就沒有辦法很顧家。可是我還是很<br />
愛這個男人愛到沒有他會死掉的那種。<br />
【圖一】 Afan 生命敘事圖<br />
國中畢業離家<br />
教會總會工作<br />
愛 情<br />
原<br />
丈夫入獄<br />
離婚<br />
運<br />
你說我的信仰喔,我的信仰應該是說從小就一直到現<br />
在,家庭的關係。從小,因為我們家就在教會旁邊而<br />
已。我覺得父母親的帶領也很重要。我受我的母親那<br />
種信仰,受蠻大的一個影響。因為我的母親他本身信<br />
仰相當的好。而且鄉下什麼資訊都不知道,以前最遠<br />
國小的時候只有到成功去吃那個-切仔麵加滷蛋,就<br />
覺得很棒..<br />
我對我的同學,我不會跟一般人一樣說。啊!我就<br />
說你是山地人,那個時候都還是說山地人。我覺得<br />
像我是阿美族,我都會很大方。我不會 care 說,我<br />
就說你是山地人,好像被鄙視。不會,那個時候我<br />
都覺得原住民有什麼不好,山地人有什麼不好。我<br />
就說一樣啊,我工作得比你賣力,我做什麼事情我<br />
不一定會輸給你。那時候就是有那樣的一個心態,<br />
想說我不一定輸於他嘛,只要我能力好,我一定比<br />
你做得還棒這樣子。<br />
其實在對人這個部份,我是覺得我們怎樣去尊重自<br />
己,也要相對的去尊重一個人。<br />
在這裡我們一年一聘。在過去,大概有長達十年的時間<br />
我的生日剛好在五月。每年五月我生日的願望就是繼續<br />
留在這裡。我已經把長老教會總會當作是我生命的,幾<br />
乎說是全部,因為我用心在投入這個部份很久了。<br />
在過去有人要逼迫,要我離開這裡,無所不用其極,那<br />
是夷將那時候在監獄的時候,我本來要換單位,可是某<br />
種原因讓我不能換單位。後來是聽其他同事在講說要把<br />
所有的阿美族全部趕離開總會,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可<br />
能他們那時候的策略吧,那時候我覺得我盡心盡力在<br />
做,而且原宣那時候也像現在一樣,就我一個人工作著。<br />
總務是那個時候剛好離開一些原住民的工作,因為說總<br />
務剛好跟原住民沒有什麼直接關係。<br />
因為當初我給自己的承諾就是我這一生就是要奉獻給教<br />
會,所以那時候想法只要留下來就好。<br />
我們不想讓,讓家人擔心嘛,所以我們就<br />
不會跟他們講,講一些事情,不過後來他<br />
們也很清楚說我們的理念是怎麼樣。<br />
而且我的家人也是非常的投入這個部分(運<br />
動)而且非常的挺他,因為他們看到我這樣<br />
相挺,他們也高興願意這樣子挺他。<br />
原運十週年的時候,我的父親那個時候剛好在台東馬偕<br />
住院啊,然後那個時候就跟夷將回鄉下去,然後那天晚<br />
上夷將就被警察帶走。<br />
在夷將入獄的那段期間,我現在回想起來我幾乎天天都<br />
去,我兩天就去即使會面的時間只有半小時。而且只能<br />
一個禮拜一天。<br />
我們真正分開的理由不是因為有小孩,我想說不要讓這個孩子一出生就沒有爸爸。<br />
我那時候決定說離開的理由是這一個。其實感情的事情你本來就並不是說你有錯或<br />
者是我有錯,或者是雙方都有錯。是我跟他主動提出的問題因為我受不了那樣子的<br />
一個壓力。<br />
上帝說神愛世人,要愛人如己,我怎麼可能把她當情敵,她是我男朋友的女朋友,<br />
122<br />
怎麼可能把她當情敵。
123<br />
我是泰雅族,但是是嫁給阿美族。過去就是在山上長大,桃園復興鄉。一直到國小畢業之後。才知道什麼<br />
叫做社會,在鄉下長大在鄉下那個村子就是我的世界。國小畢業之後,我到淡江中學去唸書。這時候我才<br />
知道,原來原住民有分這麼多種。我以為我在鄉下只有泰雅族,我用的語言都是泰雅族的語言。我到淡江<br />
中學時候,發現有其他的原住民,我還用我自己的語言,泰雅族的語言去跟他講話,他就….你是不是別<br />
的..他就完全就聽不懂。那個時候國小的教育也沒告訴我們說,原住民有在台灣有幾族幾族,國小那時候<br />
教育哪會談到這些。後來,到國中那時候才知道說,哇,原來原住民有這麼多種,而且是分佈在各個縣市<br />
阿,我以為那個時候的原住民只有我們呢,我那時候真的是天真到那種地步。<br />
牧師家庭<br />
我是出生在一個牧師的家庭,我爸爸<br />
是牧師。從小就是完全是看不到爸爸<br />
在家裡。就是他到處跑去做傳道,去<br />
做福音的工作。那有沒有影響到他的<br />
一些想要服務人群的那種任務,那種<br />
工作。有沒有影響到我到最後想要從<br />
事這樣的工作,多多少少會有。<br />
神學院時期<br />
1981 年在玉山神學<br />
院結婚。隔年大女<br />
兒在神學院出生<br />
我蠻早熟的,因為我覺得進入神學院之後逼得自己<br />
的年齡就成長。我們是畢業前結婚的,還生了那個<br />
老大,而且那時候神學院還很好笑喔,沒有所謂的<br />
夫婦宿舍。就是我們是第一個,在學校結婚的學生。<br />
所以哪時候,學校的董事會決議要蓋一棟那個夫妻<br />
宿舍,我們算是先鋒者。所以那些後來的學生,其<br />
實他們要感謝我們,哈哈哈...那時候夫婦宿舍我們是<br />
第一對住進去的。而且老師們,都已經預備好,就<br />
祝福這對學生。因為將來我的老公要作牧師,我要<br />
作師母,那時候學校就應該要,就覺得要好好栽培<br />
學生。就這樣,那也很幸福,成功在學校生下孩子。<br />
偏遠阿美族<br />
部落服務<br />
隨老公轉往高雄<br />
漁民服務中心<br />
1982-1984<br />
1984-1987<br />
丈夫入獄<br />
都市原住民<br />
違建戶問題<br />
參選新店市<br />
平地原住民<br />
市民代表<br />
2006<br />
1987<br />
原住民有一個神<br />
學院就是玉山神<br />
學院。因為我一<br />
直想要瞭解這到<br />
底原住民有哪<br />
些。而這些原住<br />
民個個不同,文<br />
化、背景到底不<br />
同在哪裡?我就<br />
選擇性的考玉神<br />
那個教會就是很單純,沒有受到任<br />
何那個社會上的污染。就好喜歡那<br />
個地方,真的好喜歡。就跟著教會<br />
的會友就下田,種田,跟著會友到<br />
處去,他們去哪裡抓魚就跟著去,<br />
他們去採箭筍我們就跟著去.<br />
看著老公就這麼忙自己同胞的事<br />
情,很多情況是你看的東西多了<br />
就會耳濡目染。<br />
到台北才知道,原來我們的挑戰<br />
更大。那個時候違建戶的問題又<br />
比那個漁民的工作又多了很多。<br />
1995<br />
幾乎看到我的人就是講說,啊!你就<br />
是馬耀太太。從來不知道我叫什麼,<br />
我叫做 Sayung‧Losing。就是說民眾他<br />
們只認識馬耀,我開始反省,有很多<br />
民眾,在任何場合 如果有人刻意介紹<br />
我,他只能介紹我是馬耀太太,那時<br />
候我的感覺就是 ㄟ..怎麼會是他的附<br />
屬,我有名我有姓。<br />
就因為我老公被關 那段時間我就很認真的就去學開車。然後帶人家去<br />
看一下我老公。常常去法務部去探獄,都是我帶頭。<br />
我要安排他們的行程,因為我覺得我跟我小孩子的時間不要被剝奪,<br />
我那時候在想我老公他主要看的是孩子。可是 那個時候很多外面的團<br />
體一直要來看,又不能阻止他們去看。<br />
人。<br />
我老公被關之後我才開始在台面上,慢慢的被人家…也不是說被人家<br />
拉過來或什麼,我以前就一直在做了,只是說大家都不知道,因為不<br />
得已阿,我老公進去了,沒人帶了,那時候我就變成參加原運的政治<br />
犯家屬的召集<br />
那個時候我去洗頭,然後那個美容師跟我講,小姐你這邊有禿,兩片,<br />
好大。我竟然都沒有發現,一年多。後來去醫院去檢查,才知道說原<br />
來是那個壓力太大。導致內分泌失調,可能以前從來沒有那麼緊張過,<br />
那麼累過。<br />
時候時機剛好我大女兒生病,兩<br />
天就跑馬偕醫院打針。<br />
為了教會的工作,我女兒的身<br />
體,我老公的事情,還不是就這<br />
樣,為了原住民所有的權益,我<br />
還帶頭去抗議,然後就是在那一<br />
年當中喔,我也開始想說我幹嘛<br />
那麼累呢?但是你說不做這些<br />
事情也不行阿。如果自己顧到自<br />
己孩子也就算了,還得顧老公<br />
阿,顧教會,還得顧原住民。<br />
經營二<br />
手服飾<br />
原運<br />
我覺得是我年齡到了,可以穩重一<br />
點成熟一點,而且這是種面對的事<br />
情。就是我,自己有必要對自己工<br />
作的一個交代。以前那個時候為了<br />
小孩子,什麼事情都不能做,綁手<br />
綁腳。那現在孩子大了,我覺得我<br />
可以去發揮自己的工作,可能會寬<br />
廣一點。<br />
我這次出來參選代表,他跟我講說<br />
你會不會太累?我說我不會,我不<br />
是要證明說我的能力一定不輸<br />
你,而是說我要自己規劃我自己的<br />
事,我將來。兩年前我跟他講說新<br />
店市要有一個名額,我們的人數的<br />
總數已經達到。我們有一個名額,<br />
我要選代表,我老公那時候說這樣<br />
子好阿,我支持你。<br />
我覺得我就是參與。我覺得參<br />
與最好的就是對原住民,就是<br />
對自己的同胞最好的一個交<br />
代。不一定要用什麼位置,從<br />
以前我就是參與者,我又不是<br />
領導者,我也不是先鋒者,我<br />
甚至沒開過會,但是,只要他<br />
們議決開會丟過來之後,我就<br />
會幫忙動員。<br />
我的人生就這麼平<br />
凡,就是跟著老公後<br />
面走,參與原運。然<br />
後到最後我自己要出<br />
來參選代表就這樣,<br />
我就是這樣不想要什<br />
麼。<br />
【圖二】Sayung 生命敘事圖
124<br />
圖<br />
因為我習慣從小就在教會裡面聚<br />
會,家族聚會的時候就很習慣的<br />
跟爸爸、媽媽去教會,教會的公<br />
佈欄就看到玉山神學院在招生,<br />
就這樣子考進來了。<br />
考進來以後,進入到這個學校,<br />
發現到學校他的環境,還有他所<br />
談的一些言論啦,跟我以前的學<br />
生生活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也<br />
慢慢的接觸說,學校有一些學<br />
長、學姊就開始講原住民的議<br />
題,甚至於說原住民的一些社會<br />
的問題,原住民的教育問題,就<br />
開始在談。<br />
在一年級的時候,我覺得我很害<br />
怕,我好像來到一個我完全不知<br />
道的地方,那個時候就很單純,<br />
而且真的是非常的單純,一張白<br />
紙…<br />
那我自己很大的衝突是,因為那<br />
時候我哥是憲兵中校,剛好鎮暴<br />
部隊也是他在管。他那時候就把<br />
我找回去,被他訓話,我哥哥還<br />
跟我講:「你知不知道你這樣<br />
做,你會誤了我的前途,影響我<br />
升官。」可是我沒有去在乎他的<br />
感受,我只是跟他說:「那你知<br />
不知道,跟我們一樣流著這個血<br />
的原住民,有很多人無家可歸,<br />
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完美。」我就<br />
這樣跟他反駁。所以那時候我哥<br />
哥認為我在造反,他覺得說我在<br />
反抗當時的執政者,他覺得說我<br />
那個時候是混亂,他很擔心說,<br />
如果我被抓,我被關。<br />
甚至於我的父親也覺得說,為什<br />
麼我會去參加,我父親也跟我講<br />
說,去念神學院,為什麼回來就<br />
變了個樣子?我就說我不是變<br />
了個樣子,我就說這種運動是我<br />
們原住民的問題。<br />
甚至有一次我家裡面的叔叔曾<br />
經跟我講說,做這個到底對你有<br />
什麼好處?我就說:「沒有什麼<br />
好處呀。」<br />
其實那個時候的社會運動,實<br />
際上,我覺得我是一個參與<br />
者,只是我不知道整個在帶的<br />
運動一個策略的人,在計劃的<br />
人,這個我都不知道。然後去<br />
了以後,真的自己的意識,自<br />
己的認知,還有一些自己的看<br />
法,真的一點一滴的就被改變<br />
了,那個就是整個參與運動。<br />
其實那個時候真的時很惶恐,因<br />
為覺得就是說那些問題,好像不<br />
是自己的問題,有一種感受。甚<br />
至於我們班有幾個女同學就哭<br />
啦,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接受他必<br />
須知道這樣的問題。<br />
有一次參加完活動後,一個人在想的時<br />
候。我就會想說,我這樣子做到底有沒有<br />
什麼意義?有時候我會這樣問我自己。可<br />
是我會想說,如果沒有參與的話,我怎麼<br />
會曉得我們現在的處境呢?<br />
我都是在有必要的時候,我就會講話,我<br />
覺得我不太像是運動者,我覺得我比較像<br />
自己在參與自己事情,我也不是當幫原住<br />
民說話那樣的人。<br />
那個時候(學校參加運動時期),我<br />
並沒有用信仰去看。我那時候只是想<br />
要瞭解台灣原住民的處境是什麼?<br />
我就覺得說我為什麼不自己去跟他<br />
們走一次,去瞭解這種實際的情況是<br />
怎麼樣,特別是參加雛妓的那種街頭<br />
運動,我看到很多原住民所謂的精<br />
英,當時後,一個一個的上去宣傳<br />
車,有的哭,有的吶喊,也有的是為<br />
自己的家人而哭,那個時候給我的感<br />
受很大,因為我從不去想這些問題,<br />
然後我也是生長在那種比較嚴謹、單<br />
純,比較完整的家庭。<br />
現有的反省是在要畢業的那個時<br />
候,自己實際去了陽明山,也去了總<br />
統府,也去了立法院,實際的參與社<br />
會運動走街頭,開始自己發傳單的時<br />
候,我可以有那個心反省。<br />
很多人都不敢走,那個時候我可以去體會<br />
說,為什麼不敢。因為那時候台灣的局勢,<br />
沒有像現在這麼開放。<br />
那個時候還是有所謂的言論(限制),雖然說是<br />
言論自由,但是那個時候還是被禁止的。有<br />
時候我會接到很多的電話。<br />
我還跟他講說:「如果你自己關心,你為什麼<br />
不跟我們走呢?」我說你不要想從我這裡得<br />
到什麼?<br />
我實際的去彩<br />
虹婦女事工中<br />
心工作,然後<br />
起初跟那些個<br />
案接觸,然後<br />
去排時間,真<br />
的實際去關心<br />
這些所謂的不<br />
幸婦女的時<br />
候,那個心情<br />
又是另外一種<br />
轉化。<br />
那個時候我都不敢照相勒,因為我哥哥那<br />
個時候是憲兵中校。我每次,兩次從現場<br />
被拉走啊~然後被訓,我根本不知道誰是<br />
誰,我只知道阿兵哥把我架走,等到坐上<br />
車,我才知道他叫他阿兵哥抓我回去的。<br />
我們家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是第六個。然後我們家經濟上比較辛苦,<br />
因為孩子多呀。我出生在排灣族的聚落,屏東來義鄉文樂村。其實<br />
我的童年的成長很單純,從小學、國中、高中受的教育,完全是從<br />
學校知道的一些事情,就是老師啦、教科書這樣,我根本沒有想過,<br />
關於自己原住民的問題。<br />
然後比較深的印象是,只要是出去啦,跟昔日的同學在一起,或者<br />
離開自己的村莊,就可以聽到我們原住民以外的人就會一直笑啦、<br />
在那邊講。你知道那個時候,還不是那麼在乎說,他們講的那種番<br />
人啦,或者是那種山地人啦,還不是那麼意識到有被歧視。可是一<br />
直到,大概是國中的時候,出去參加一些學校的活動比賽這樣子,<br />
才知道說原來那樣子就是被歧視。<br />
然後那時候也不是很清楚自己原住民的問題,根本一片空白、白紙。<br />
到了高中以後,就感受到自己是少數,因為國小國中我們大部分是<br />
原住民學生,到了高中以後,我們班只有三個原住民,其中只有我<br />
們三個是原住民,然後那時候才感受到~我們真的是少數。然後一直<br />
到選幹部、選班長什麼的厚,才知道說,我們真的是少數勒。我們<br />
班剛好是,客家人跟漢人的比例是一半一半,所以我們這三個人是<br />
關鍵人物…<br />
那個時候在籌備的時候,是在總部嘛,他們在分配一些工作的時候,的確都是男性在主導,女孩子<br />
還是可以提供一些意見。我覺得我們女孩子,為什麼都不敢講話什麼的,可能是跟自己受過的教育<br />
有關係。其實就像我呀,那個時候他們就叫我負責什麼什麼,我就不敢,就是很出鋒頭的事情,檯<br />
面的事情。我們有很多的包伏,我們會認為說,應該先看男孩子怎麼做再做吧,就像說,我認識的<br />
幾個前輩女孩子,有時候給她們工作的時候,她們就說,我寧可做什麼做什麼這樣~<br />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女性的角色,你說被動嗎?也不是,因為當時的那個局勢,他們就是要保護我們,<br />
我覺得男生就是要保護我們,不允許我們遭受到危險。<br />
在外地念高中,高中畢業以後,去工廠工作一年。<br />
對於想要讀的學校,家裡的經濟不是很好,就去<br />
工廠工作一年。在工廠工作的時候就想說,難道<br />
就這樣過一生嗎?就有一點就是說,不太願意就<br />
這樣認命。<br />
就在工作的那個時候,因為我祖母過世,我回家。<br />
以前我在想信仰的事情的時候,我只是把<br />
它放在教會和我個人的生活裡,那就是我<br />
對信仰的看法。後來在學校經過這兩年的<br />
訓練、栽培、洗禮之後,我瞭解到信仰它<br />
的泛圍很廣,後來才覺得說原來信仰也關<br />
心政治,也關心各方面的議題,那個時候<br />
的覺醒,然後我才知道信仰是要去做公益<br />
的事情,不是個人利益的事情,是群眾,<br />
特別是弱勢族群的事。<br />
【圖三】Sankilj 生命敘事圖
我在台東成功鎮,八翁翁一個小小的小故鄉長大出生。成功鎮,那裡有很多部落,而且是好小<br />
的部落,在那邊出生。一直到四五歲就搬到關山,我等於是在關山長大的,等於是兩個故鄉。<br />
應該是 63 年的時候就嫁給我先生。我先生的工作在台北市,所以就過來,這兩個小孩子是在台<br />
北市出生的。到現在已經 32 年了吧,來台北已經 32 年。<br />
因為看到自己族群都沒有工作,所以才把代工給他們,讓他有工<br />
作。本來是從時裝,後來又發覺到說有很多原住民的圖騰,就先<br />
從包包開始,把一些圖騰弄上去開始。有人說我作的東西民族風<br />
那麼有,我說,我作的東西是只限於在原住民的圖騰。<br />
我們附近學校老師,他們要做民族舞蹈,學校要比賽。他們就<br />
想說,只要有原住民他們就有辦法跳舞,他們想要嘗試用原住<br />
民的方式來做,結果找我。我說你們找錯人了,因為我從小就<br />
在教會的家庭長大,我比較沒有接觸有什麼豐年祭什麼祭的我<br />
都沒有參加過。<br />
那當時你知道嗎,教會他等於是在,破壞我們自己傳統的東西,<br />
你信教以後,你就不能(參加),那個是不好的。所以我們都<br />
沒有接觸自己的文化。甚至我爸爸他很喜歡講神話故事,但是<br />
他真的很喜歡,他也會講很多過去的東西。但是就不准參加祭<br />
典。所以,要跳出什麼活動,根本就要去問老人家。我那個本<br />
來是拒絕,後來經過他們這樣子不斷的遊說,我說我試試看,<br />
我先問問看。就開始產生興趣,好奇然後興趣…<br />
我現在還在做原住民<br />
阿美族傳統服的運<br />
動,為了這個,我先<br />
生跟我鬧過彆扭。辦<br />
喪事,配戴(穿著傳<br />
統服)。他們說場合<br />
不對,那我認為沒有<br />
什麼不對。我覺得對<br />
死者是尊重的最高敬<br />
意。我們配戴的方<br />
法,一般是右往斜斜<br />
到左邊,喪事是左邊<br />
到右邊,我認為我是<br />
尊重我的朋友。為了<br />
這個,我先生跟我鬧<br />
彆扭,甚至不參加。<br />
因為在北部,的確都<br />
沒有再弄這個,傳統<br />
祭儀的精神,他們還<br />
沒有這個認知。<br />
那一定要讓他們(孩子)知道,我們做任何<br />
事情要跟他們做說明,讓他們去認同。當時<br />
我兒子,他也跟著去衝撞(抗議的時候)。<br />
那時候發覺,ㄟ 我兒子,真的也很勇…<br />
125<br />
我爸爸!他很喜歡說傳說神話故事,我這一對兒女,他們每次回去,<br />
吃過晚飯以後,我爸爸就在那邊講,然後我就在那邊做翻譯什麼的<br />
我媽媽就在旁邊編織,那個竹籐編,有時候就跟其他同齡或其他小一<br />
點的三個或五個就圍在她旁邊,問她說媽媽這個怎麼編?斜織或直<br />
線,她說這個是你外婆的眼睛。那個時候我就印象很深,啊!原來那<br />
個叫菱形的東西就是祖靈的眼睛,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裡。<br />
剛開始原運抗爭因為媒體報導的真是負面的。很暴力,而且把交<br />
通弄得什麼混亂,什麼的。第一印象是這樣子。然後,慢慢的接<br />
觸到馬耀牧師他們,我覺得沒有錯,為了要爭取自己的權益。<br />
我先生是吃公家的飯,等於說我的孩子也是說吃政府的,他當時<br />
在刑事組。所以一有什麼原運,他們去蒐證。我所謂擔心是擔心<br />
我先生這裡。因為政治發言當時沒有說出來,他們(原運)是對<br />
的,我聽到的都是負面的。他們去蒐證,我是很擔心我先生。所<br />
以背著他,偷偷去。<br />
我跟他講這個事情的時候,他說,唉啊,你早說嘛,我是很認同<br />
他們的動作,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可是我不方便出面。但他說,<br />
你不要太露臉,因為是公務人員的家屬,擔心影響到他的工作。<br />
【圖四】Lipay 生命敘事圖<br />
他們吼,都是同質性很高。有的人就說,噢!你在台面上,都是,那個名利都是你的。當時我真的<br />
很左右為難。怎麼講呢,這邊一直聽他講這裡,那這裡的只有挨打。他們自己很清楚,會講說我們<br />
沒有這種心,沒有怎麼樣。我夾在中間,過去大家一起親嘛,又聽到個人的反應太強烈…<br />
原 運<br />
他們排他心態太強烈,那個是,說你不要光是聽他們講什麼,然後我就說,我沒有聽到他們這樣子說<br />
你們,我的確沒有聽到他們在攻擊她們阿,都是她們在攻擊他們。後來她們就把我歸類,害我聽了很<br />
難過。我真的很難過,那時候真的很難過,<br />
都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因為他們年紀都小,我把他們當作自己人來看待。因為她們作的事情,我真的<br />
很心痛。我一直努力想讓他們復合。<br />
剛開始我還在努力,可是我的努力沒有用。那我乾脆就放棄了。(馬耀)入獄後,當天她們有來,以<br />
後,就慢慢的開始有聲音,她們對內有聲音了。那我是覺得她們不應該去講這個東西,我覺得,為什<br />
麼是他們那樣?她們當時也掛上名字領導,領隊。他們也不願意,可是他們在召集,他們也不是要為<br />
什麼心,他們也是要負很大的責任的。因為大家都沒有那個表示,放馬耀牧師這個人去,你看他們入<br />
獄了,還講他們什麼呢。<br />
那時候我是抱一個 erden(母語)的孩子,那時候還很小,那孩子很黏我。剛好在抱,他<br />
要把我們趕。我就想說,ㄟ 我在抱一個孩子,不至於敢動我。我就背著它,我萬一有<br />
什麼事,我就把小孩子傳過去。結果他們還是不敢。因為大家都已經向前了,我用我<br />
的肉身去擋,唉啊,那應該不是怪手,是他們軍人的東西,是大型的工具。後來那個<br />
孩子的媽媽,就 哇!那麼一下就在那邊哭。如果它再有動作,我一定會把孩子往前送,<br />
我就自己擋在那邊。我那時候真的眼淚,因為看到我自己族群,受到這樣的待遇。<br />
真的從前政府,太歧視我們原住民。我們越走,心就越來越強烈,要如何爭取自己。<br />
那當時我們經濟還<br />
很好,所以有一些<br />
(運動)需要什麼東<br />
西,我都會用金錢去<br />
幫助。總是要用到一<br />
點錢,要買什麼東<br />
西。就想說自己能<br />
夠,喔,有錢出錢,<br />
有力出力。
126<br />
醫療經驗<br />
反雛妓<br />
勞工運動<br />
原<br />
運<br />
童年經驗<br />
學習經驗<br />
我一到九歲是部落的孩子,我所有原住民知識<br />
在快六歲的時候,我因為一個醫療的過失,被我們的這個附近的醫生打到小兒麻痺。我有<br />
的既定,是在真柄,我所有的生命養成的人格<br />
奠定是在真柄。對我來說,那個部落的圖像是<br />
我延續以後很多事情的一些角度與看法。我是<br />
老五。所有兄弟姊妹裡面就我發展的很不一樣。<br />
一個不一樣的父親,他覺得說這個應該是要行使法律的訴訟。因為我的父親的勇敢極力的<br />
要去要求一個公道,那時候在部落第一個敢直接的面對漢人,然後告漢人。這是我父親給<br />
我在我的生命歷程很深很深的影響,我六歲時候就進法院。<br />
這個童年的訴訟的一些震撼,雙方協議說一定要把我醫好,醫到我能走。我開始意識到一<br />
個狀況說原來權利是這樣的。<br />
我每天,我記得我必須要做一些水療,那部落的老老少少時間一到就會圍著我,我的記憶<br />
是我是很方便的檳榔咬器。你就開始聽很多老人家講部落的一些恩恩怨怨,講很多部落的<br />
很多很多大人世界的一些事情。那當然你開始在耳濡目染的討論裡面看到大人的世界,所<br />
以也就變成比較早熟。<br />
到漢人的圈圈裡面讀書,<br />
文化上的衝擊、語言使用<br />
上衝擊,很多的衝擊。頓<br />
時有很多不知道要怎麼因<br />
應。高中開始有些困難,<br />
我那時候功課很差,大概<br />
我後面只剩下兩個一個,<br />
變成不是很快樂。心態上<br />
面一直有一些困境,一直<br />
沒有辦法得到解決。覺得<br />
好像什麼事情都不對。<br />
我有一個很清楚的印象是高中時候不是都要寫週記嗎?<br />
週記是我一個很大很大的知識價值平台。我很喜歡在週<br />
記裡面表達我的想法。老師都會批一個說有思想,這是<br />
三年來老師給我的評價,不同的老師,都會出現過這個。<br />
玉山神學院<br />
黨外<br />
運動<br />
教會給我很大的一些平衡心態上面的一個窗口。<br />
我在教會我可以作領袖。我可以做我幾乎在學校<br />
辦不到的狀況。還好有這樣,我在教會就發展得<br />
非常傑出。我完全繼續我神學院那個宗教的經<br />
驗,我開始整個人在神學教會這個部分脫胎換骨。<br />
我大學的教授一直就是依循我這個有思想<br />
的特質。很喜歡跟我講運動,概念,很多狀<br />
況,很多學校的一些點點滴滴,老師把我當<br />
作是他很好的忘年之交,願意講學校的很多<br />
狀況。也累積了很多對成人世界的一些看<br />
法,做學問的一些方法。就很自然的留下一<br />
些刺激跟訓練,一直到我為什麼毅然決然的<br />
選擇寫雛妓這個研究的畢業論文,是那個時<br />
候整個黨外運動非常非常蓬勃的時候,就在<br />
一九八三年那個參與的時機跟你參與的整<br />
個歷程,已經在豐富我在這個題目上的一些<br />
處理。<br />
我是唯一在整個運動的初期,唯一參加決<br />
策、路線討論、整個運動型式的表達,應該<br />
要怎麼去規劃,初期我是唯一一個原住民女<br />
性進入到這個運動的討論,主要是因為這個<br />
我作的娼妓研究的題目。<br />
我個人選擇運動完了以後,就離開,我從來沒<br />
有想要去會後會!去建立新的人脈網路,我要<br />
為我的運動累積什麼,我的腦袋裡面沒有這個<br />
東西。我的腦袋裡面只有,我為原住民可以做<br />
什麼,我做了,我已經算完成了。<br />
那個時候這些男性慢慢覺得說女性議題在外界<br />
有一定的共鳴,也有相當程度的歷練。所以我<br />
們就在無形當中遭到莫名的排擠,莫名….這就<br />
是一個很自然,無形當中你就會有一些排擠的<br />
狀況,但是你完全沒有這種意識。<br />
大概有五六年的時間,我在這<br />
個運動的場域裡跑到幕後,我<br />
不再去參加它的決策,不去路<br />
線表決,我不參加。因為我覺<br />
得你每次講的任何建議,沒有<br />
任何人採信的一些必要性也沒<br />
有直接的幫助。我就拒絕這樣<br />
的遊戲規則,就開始退居幕後。<br />
因為我自己那個<br />
時候在勞工的場<br />
域裡面,還有這個<br />
娼妓這個議題下<br />
面琢磨,我並不需<br />
要聚焦在原住民<br />
上面。所以我就有<br />
我自己選擇上的<br />
立場,我就自己離<br />
開這個場域裡的<br />
一些決策。<br />
之後,在每一個運動的設<br />
計,我不再是決策的成員。<br />
我不再討論這個運動裡面<br />
很重要議題的代表,而是在<br />
遊行時候出現。<br />
這個運動可能有人要遞請願書,要跟最高<br />
的領導人互動,這個角色,都不會是由女<br />
性擔任。媒體不會是有你去說話的地方,<br />
(他們)不會讓你去在那個畫面出現<br />
經歷過那麼多不<br />
同的場域與位<br />
置,看原住民問題<br />
的一些角度比一<br />
般人還要深刻,我<br />
走到這裡來更深<br />
刻。所以運動對我<br />
來講那個是一個<br />
很重要的一種看<br />
整個原住民在整<br />
個主流社會面臨<br />
的一些困境造成<br />
的結果。<br />
我所有知識經驗告訴我,這個事實跟我得到的<br />
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宗教教育是兩件事。基<br />
於這個理由,我一定要把他弄清楚。所以就捲<br />
入了這個娼妓研究裡面,因為觀察到很多事實。<br />
你對人的基本關懷,他跟生理無<br />
關跟階級無關,跟金錢無關。這<br />
個權利是,只要他是人都應該要<br />
被分享。假如有這樣很深刻的人<br />
權內涵的一些態度,那當然就沒<br />
有所謂的原住民的權利,就沒所<br />
謂的女人的權利。<br />
我應該是倡議者,<br />
這個定義上面對我<br />
較恰如其份。因為<br />
你必須透過演說去<br />
影響,你想影響的<br />
事情。運動是任何<br />
一種形式達到改變<br />
的目的,都叫運<br />
動。<br />
現在這個運動目前是冬眠<br />
的狀態。大概沒有一個很強<br />
的說這是大家都同意的主<br />
張,永遠都有一群個別性<br />
的,被人在那邊,好像打出<br />
一定的號召。<br />
【圖五】<br />
Laya 生命<br />
運動的夢想是一定要<br />
有,就是說,你如果太利<br />
益導向,你少了那個理<br />
想,你就沒有動力,沒有<br />
瘋狂的動力。你太瘋狂,<br />
太熱情,你少了這種知識<br />
裝配的這種理性與現實<br />
的烘托的話,你這運動會<br />
受到一定的傷害。這是兩<br />
敘事圖<br />
立法委員<br />
造之間缺一不可。
二、美麗島小運動<br />
在 1980 年之前,整個台灣是一個非常威權的時代。全部社會的力量,<br />
社會力的支配都在一個政黨的手裡被概括,那是種獨斷、專斷、威權的<br />
那個年代。所以那個時候所有對這個社會的有一定的正義的信仰都積極<br />
聚在一起叫做黨外。而國民黨,好大好大的一個國家機器,都在它手裡。<br />
當時原住民的運動,也是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下面被孕育出來的。〈Laya〉<br />
這段話串起當年整個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大環境背景。原運,可以說是從各個<br />
社會議題裡,抽出原住民的部分,來加以凸顯。它是從大環境的影響下,被刺激<br />
出來的眾多社會運動之一。而這些參與原運的行動者,是由很多團體聯盟組合而<br />
成。雖然彼此的訴求點不盡相同,但是都以原住民議題為主要,所以被歸類成原<br />
運的行動者。以我訪談的女性運動者來說:Afan 是以原權會為中心、Sayung 跟<br />
Lipay 以都市原住民問題為主、Laya 主要的運動場合是雛妓跟勞工問題、Sankilj<br />
則是各個原住民議題場合都會見到她的身影。<br />
原運的開展,除了受到黨外環境的滋養外。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 1 ,在裡面<br />
也扮演著啟蒙 2 與動員 3 的角色。原運依靠著長老教會全台教會網路,發佈消息與<br />
提供資源,包括人才與資金。而主要由長老教會組成的原運團體,在運動場上,<br />
則分佈於每個議題中參與討論與策劃。<br />
而原住民族早期的知識菁英份子,除了台大的原住民大專生外,幾乎都是從<br />
長老教會體系學校裡出身或有相同的基督教信仰 4 而結識行動。位於花蓮的玉山<br />
神學院 5 ,是一所專門培養原住民宣教人才的學校。原運在台各地的議題開展,<br />
玉神畢業的牧師與傳道們,扮演提供原住民同胞們知識自覺的角色 6 。五位受訪<br />
者中Sayung、Laya、Sankilj三位即分別為玉山神學前後期的學姐妹。<br />
玉山神學院的學生,最早與原運開始產生關係,是來自一場學生與學生間的<br />
1 詳細請參見 周怡君 1997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與其社會運動參與》,頁 48-56。東吳大學社<br />
會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2 多數的原運人士都曾參與過 URM(台灣城鄉宣道會)草根組織訓練。URM 最早是由加拿大<br />
Dr. Ed. File 創始,民主人士林哲夫策劃為台灣人量身訂做的訓練班,進而成為台灣城鄉宣道會<br />
(TURM)。此一組織者訓練機構為配合國內社會運動的需要,培育了近千名的組織者,與台灣<br />
民主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主張以「愛」與「非暴力」帶來改變,許多主張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份<br />
子都曾受過此訓練。早年政治情勢的緊張,參與訓練的人士都被國民政府列為「黑名單」,受到<br />
國民黨嚴密的監視。而原運早期事件裡,一群年輕人合力拉倒阿里山吳鳳銅像,造成吳鳳神話的<br />
瓦解,就是第九期 URM 原住民學員的行動(吳佩蓉、黃懿翎 2003)。URM 六大精神:<br />
●對抗邪惡的勇氣 ●為義受苦的精神 ●創造性的少數<br />
●相互成為資源的結盟 ●愛與非暴力 ●爭取被壓迫者的尊嚴<br />
3 詳細請參見李慈敏(1991)對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參與社會運動過程,有對其立場與訴求作整<br />
體回顧歷史。<br />
4 本研究女性受訪者,基督教為其共同的宗教信仰,在成長過程裡普遍接受過教會宣道與神學院<br />
教育。<br />
5 詳細請參見鍾青柏(1990)的碩士論文研究,內有精闢討論。<br />
6 原住民運動發展中,玉山神學院作了一件任何自稱是原運領袖者所不能的事—覺醒教育(陳俊<br />
明 2002:12)。<br />
127
座談。座談舉辦的立意是良善的,期望原住民學生可以多了解社會環境的政策<br />
面,內容是針對政府與社會對原住民問題所做的批判與討論。不過長老教會從<br />
1977 年到 1980 年間一連串爭取民主人權的運動事件 7 ,使得基督教長老教會在<br />
國安單位裡面,早已被列入黑名單。Sayung的丈夫當時是學生會會長,替玉神學<br />
生舉辦這場座談。國安單位事前得到消息,早已部署人員,包圍玉神進行監控,<br />
當時氣氛很緊張,卻也為原住民運動立下一里程碑 8 。<br />
1987 年,社會的娼妓問題正吵的沸沸揚揚,而原住民雛妓更是嚴重,佔其<br />
中案例絕大多數。要說明的是,娼妓問題長久一直與社會經濟結構問題緊密相<br />
扣,是恰好當年黨外運動鬆動了社會觀念,而促成以平地婦女為號召,原住民團<br />
體一起響應的救援不幸少女 9 的反雛妓大遊行 10 。<br />
雛妓議題是Laya投入運動的主因之一。在玉神時期,師長待她如忘年之交,<br />
讓她暢所欲言的學習生涯,無形使她具備了基礎的學術訓練與觀察。黨外運動蓬<br />
勃發展,直接促成了Laya以娼妓研究為主題,完成她的神學院論文 11 。Laya的論<br />
文發表後,受到當時很多人的異樣眼光。因為娼妓問題不容於當時社會風氣,可<br />
以被公開談論。<br />
而除了原住民雛妓問題、勞工、土地問題亦是原運運動的場域。<br />
當年(1984 年)Sayung的丈夫Mayaw牧師接受了代理長老教會高雄漁民服<br />
務中心 12 主任的邀請從花蓮鳳林教會離開,夫妻倆風塵僕僕的轉往高雄接掌漁民<br />
服務中心,處理高雄的原住民漁工問題 13 。<br />
漁民問題跟雛妓問題一樣,都與社會結構複雜的糾纏著。原運的先鋒者胡德<br />
夫曾經說過,原住民處在:「最高的鷹架,最深的地底,最遠的海洋,最重的背<br />
負物以及最暗無天日之空間」,勞工、礦工、漁工、娼妓,這些處在社會底層的<br />
原住民,是台灣奇蹟不可抹滅的邊緣小人物。不過因著許多外在條件的限制,族<br />
7 基督教長老教會在 1977 年,同年發表了國是聲明和人權宣言,造成國民政府很大的震撼與不<br />
諒解。1979 年美麗島事件,國民政府後續逮捕相關人事,總會三位傳道因而被判刑。1980 年總<br />
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以藏匿施明德為由被捕入獄(陳俊明 2002:6)。<br />
8 座談會以後,玉山神學院的學生就開始陸續參與原住民社會運動。以學生會領隊、各族團契或<br />
個人方式參加原運。三次還我土地運動的遊行,玉山神學院更是全校師生一起動員 8 :那一次的<br />
會(座談會)之後,玉神的學生就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參加原運的工作。在那當時我們也不是很積<br />
極一定要帶動什麼,動員什麼人,都沒有。就是說要讓這些同學,回到教會那個同時,能不能也<br />
帶著這份使命,對自己同胞的權益、福利,能帶著使命回到部落。〈Sayung〉<br />
9 玉山神學院由童牧師領隊參加救援不幸少女。參見,陳俊明〈玉神參與主要原運示意圖〉(陳<br />
俊明 2002:10-11)而基督教長老教會底下專責於教會與社會福利的機構,設有六大關懷福利<br />
機構:分別是 1. 原住民社區發展中心 2. 彩虹婦女事工中心 3. 台北婦女展業中心 4. 勞工關懷<br />
中心 5. 海員/漁民服務中心 6. 身心障礙關懷中心(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總會網頁 網址:<br />
http://www.pct.org.tw/ ,快取日期:2006.6.20)<br />
11<br />
陳秀惠 1985《對山地婦女充當妓女問題的牧養關顧之研究》。花蓮院玉山神學院畢業論文。<br />
未出版。<br />
12<br />
Sayung 的丈夫 Mayaw 服務的單位屬於長老教會底下的社會福利機構:〈海員/漁民服務中<br />
心〉,早年即以處理原住民漁勞工權益糾紛為主。<br />
13<br />
當時,還有許多不同角度來從事原住民問題的團體,包括土地、環境、正名、憲法…等。在<br />
此以她們述說的事件與各自著力點為主,其他面並不多作解釋。<br />
128
人可從事身體勞力工作居多,利用勞力賺取微薄的薪水。男性行業從建築業的板<br />
模工到遠洋漁工,礦區採礦工…,女性則是到工廠當女工、作業員、家庭代工…<br />
都有。這些在都市工作的族人,因為工資只能勉強溫飽,並不足可以負擔都會區<br />
高價的房租與地價。族人只好圍著無人居住的山邊或河堤自行蓋屋,圈居而住。<br />
這群在台北謀生活的族人們,被稱做「都市原住民」。而他們所居蓋的房子,被<br />
政府稱作「都市違建戶」。但 Sayung 認為應該是要稱他們叫作「暫住戶」:<br />
他們(族人)是上一代的,當初年輕力壯的時候就來台北工作。然後他<br />
(族人)來台北工作找不到房子,繳不出房租,就只好自己在那邊搭工<br />
寮。那搭了工寮,那時候沒水沒電,他們還可以生活。那段時間,又到<br />
處都是灰塵,都沒有水泥地,什麼都沒有。他們搭工寮,也沒人告訴他<br />
說你侵佔我的土地,你的地在這邊是不合法的,沒有人告訴他。〈Sayung〉<br />
為了處理違建戶安家的問題,Sayung跟丈夫兩人帶人到處陳情,奔走而替都<br />
市族人爭取到國宅與地上物賠償。最遠還到省政府(南投)抗議,綁布條。爭取<br />
到現在住的中正國宅,讓族人以優惠的價格承租,但違建戶的問題並不因此而退<br />
場,移居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反而因為台北縣都市開發計畫而出現更多的變數<br />
14 。<br />
而雛妓、漁工、違建戶的問題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產具有關連性。然而,<br />
在都市以外的族人,只要有高山與海洋,就可以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過去族人<br />
利用耕種、漁撈、打獵等傳統生活形態,不需要與外界有太多的接觸就能生存。<br />
而現今國家以經濟開發為考量,族人長年賴以維生的土地,在國民政府出現以<br />
後,被規劃為國有用地。從此,族人不能在其上任意打獵與耕種。<br />
土地問題關連著全台原住民生活居住的問題。較於其他議題,土地議題是原<br />
住民族從國家體制裡,衝破統治結構的覺醒 15 。原運裡面規模最龐大的遊行,就<br />
是與土地議題有關 16 。當時三次還我土地運動大遊行在新聞媒體上獲得許多關<br />
注,而後因為原運者之間對於運動議題的核心價值認同不一,原運便逐漸以各種<br />
不同操作手法延續,在街頭抗議的場面便逐漸消失於媒體報導中。<br />
以上,是原運在街頭運動時期(1984-1995)的操作議題,下面就來談談處<br />
於原運底下的原住民女性都在做些什麼事、以及她們在思考什麼。<br />
三、原運裡的女人<br />
14<br />
詳參見楊士範 2006《阿美族都市新家園:近五十年的台北縣原住民都市社區打造史研究》<br />
一書,內有歷史脈絡與針對現況的探討。<br />
15<br />
還我土地運動的形成緣起於多奧在玉山神學院的一篇論文…深感原住民土地流失的嚴重…花<br />
費相當時間深入調查研究及統計…完成受獲得大多數牧師認同及深受感動,並一直決議協助根據<br />
多奧這篇「四百年來殖民統治者之土地政策,探討原住民流失」的論文,策劃及發動四十多年來,<br />
原住民最大規模的抗爭—還我土地運動(Lyiking‧Yuma 1996:180)。<br />
16<br />
「還我土地運動」大遊行的相關論述請見李慈敏(1991)。<br />
129
我曾經在訪談裡問女性受訪者們,她們以為運動是什麼?原住民運動又是什<br />
麼?她們說:<br />
Laya:運動是任何一種形式達到改變的目的,都叫運動。<br />
Sayung:其實主要是跟原住民問題有切身關係的都叫做原住民運動。不<br />
管是爭取什麼呢或者是提倡也好。只要是牽涉到我們權益問題<br />
這都叫做原住民運動。<br />
Afan:運動就是集合大家的理念去做有意義的事,大家的共識形成之<br />
後,努力而做的事。<br />
Sankilj:你要讓別人知道我們現在的處境,真正關心台灣這個多元的一<br />
個族群,原住民不能一直認為我們是弱勢族群,已經不允許這<br />
樣了。<br />
Lipay:(原住民社會運動)沒有錯啊,為了要爭取自己的權益。<br />
社會運動在她們各自的定義裡面歸納有:「達到改變、做有意義的事、讓別<br />
人知道、爭取權益、正義的。」原住民社會問題,一直都是在公理與正義的面向<br />
打轉。街頭活動在覺醒教育的層面上,除去媒體初期的負面報導,越來越多的原<br />
住民同胞是透過新聞媒體,開始注意自己週遭的問題與有損權益的政治政策。<br />
幾次在陽明山的抗議的活動,Sankilj回憶的是肢體衝撞時同伴緊密聚在一起<br />
的感受:「我當時覺得蠻感動的是,那個時候在陽明山吧。鎮暴部隊開始潑水,<br />
就是用那個管子,潑水的時候,我覺得那個時候很讓我(有)那個(感覺),生命,<br />
就是大家緊密在一起有沒有。水再怎麼潑,你就會覺得是生死與共,那個時候我<br />
心想是這樣。」「生死與共」一詞道出在直接面對政府公權力的現場裡,每個人<br />
共同的意念。<br />
Lipay也有過這樣的場面,這個場景對她來說,是為自己族群問題感受上,<br />
心中永遠的痛:「我那時候真的眼淚那個(流下來),因為看到我自己族群,受到<br />
這樣的待遇。「(原住民運動)沒有錯啊,為了要爭取自己的權益。」場景起因是<br />
法院判決調查員撞傷原住民車禍的刑責過輕。原運團體認為法官歧視原住民,所<br />
以發起這場抗議事件 17 。<br />
在眾多不同類型訴求的社會運動遊行的隊伍裡面,要顯示原住民成員性質高<br />
的遊行方法,除了遊行穿著的傳統服鮮明標誌,Sayung 說原住民的臉要被政府<br />
與媒體直接看到,所以原住民一定要站在前幾排。另在遊行隊伍的前進中除了布<br />
條與傳統服外,嘹喨的歌聲也是另一種凸顯身分的方式。Afan 說:「在抗議的時<br />
候有時候是拿大聲公在那邊唱歌,因為我們有時候沒有車子啊,就是背著那個大<br />
聲公在那邊唱。」唱出心聲,唱出認同感:「oh ㄟ~央,歐嗨ㄟ央,歐嗨央~…<br />
17 1994 年 12 月 9 日調查局屏東調查站調查員張連松,在花蓮海岸公路因超車糾紛槍擊花蓮壽<br />
豐鄉原住民范玉雄致下半身癱瘓案。原權會等 11 個團體,一百多名原住民趕抵花蓮地院抗議地<br />
檢署不以殺人罪起訴張連松(山海文化 1997:29)。<br />
130
這首歌一定唱、「原住民全勝利」,還有「我們都是一家人」這三首是必唱的歌。」<br />
那時以母語或是國語演唱的歌曲,是經過挑選,簡單易學。母語旋律的吟唱引起<br />
鄉愁與部落回憶,而國語歌詞裡「原住民全勝利…、團結起來,相親相愛,因為<br />
我們都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算是另一種的精神喊話,也是原運者期盼<br />
政府別讓台灣的一家人,家破人亡。<br />
不過這些在遊行場合常出現的臉孔,理所當然的也成為情治單位監聽與監視<br />
的目標。每每在遊行的開始與結束Sankilj都會接到許多電話,對她進行試探,讓<br />
當時單純的Sankilj覺得驚訝與不解,為什麼他們都知道?接了多次電話後的她,<br />
某次鼓起勇氣的告訴對方,如果關心的話,為什麼不一起參加:「有一次,那時<br />
候剛從陽明山下來,我就要回去了。那個時候在下雨,時候很晚了,大家就覺得<br />
說已經派幾個人去跟李總統對話了,大家就都解散。從陽明山坐公車回來的時<br />
候,剛到工作的地方的時候,電話就來了。我就覺得很驚訝,然後(調查局)就知<br />
道我,說有看到我在那邊做什麼。我還跟他講說:「如果你自己關心,你為什麼<br />
不跟我們(一起)走呢?」我說你不要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而Sayung與Afan在<br />
受訪中也表明情治單位的情蒐與接到不明電話的感受。不過她們也都明確表明了<br />
「習慣就好」,事情一樣要堅持下去的決心。<br />
從事原運的歲月中,她們身為自己(家庭、職場)與運動者(公眾)的角色<br />
之間,應該怎麼拿捏與扮演,才可以「完美」演出?Sayung 因為丈夫入獄而一<br />
肩挑起丈夫的工作,但她的孩子當時正生病著。Afan 在丈夫入獄的時候,一再<br />
被調動職位,工作上飽受許多壓力。Lipay 與 Sankilj,參加遊行的時候面對吃公<br />
家飯的親人,心裡擔心影響他們前途與堅持行動的兩難選擇。Laya 夾在運動者<br />
間的男女角色的選擇。她們,都是怎麼解決這些梗概?<br />
當然原住民運動,你說有什麼甘苦?我們努力的有成果,就是我們最<br />
大的成就,就是我們覺得最喜樂的事情。苦,做任何事情,當然苦都<br />
會有。<br />
〈Sayung〉<br />
一直以來, Sayung認為全家一起參加原運的遊行才有意義,也才能讓老公<br />
無後顧之憂的放心的策劃原運,然而丈夫的入獄最是讓Sayung擔心,政府用「違<br />
反」集會遊行法的理由,要起訴她的老公 18 。<br />
丈夫入獄後,往後一年的教會、家庭、原運活動等事務 19 讓Sayung身心都受<br />
18 但是 Mayaw 卻對 Sayung 說:「好,沒關係,你們就不要再一些無謂的抗爭,讓我進去也好。<br />
但是要在外面的媒體上,一定要曝光(看)我們原住民多弱勢。一方面就是要凸顯我們被迫害,<br />
國民黨政府怎麼樣對待我們原住民。(原住民)更好欺負的感覺。」而 Sayung 也贊同丈夫的說<br />
法,只好帶著不捨與不甘,目看丈夫入獄。她自己也一肩的挑起照顧子女的責任,並且接手丈夫<br />
全部的工作,包括原運帶頭抗議者的角色。<br />
19 當時 Sayung 丈夫入獄期間,大女兒也正患病治療中。每週固定幾天 Sayung 必須帶著女兒,上<br />
醫院打針治療病情。為了在獄中的丈夫,Sayung 又要妥善分配好每週探監的時間,讓家人與外<br />
面關心的單位團體的探視,錯開在兩次會客時間裡。<br />
131
到了影響。她的身體出現壓力過大的反應,而在她的心裡又經歷另一個認同迷<br />
惑,她是誰?是Sayung‧Losing還是Mayaw師母?或者兩者皆是?<br />
丈夫在獄中,Sayung 在外面忙著發新聞稿與帶頭抗議,結合更多的原住民<br />
族群的力量,他們負責的原運的工作沒有因此停頓下來:「那時候我老公沒有在<br />
作的事,我都要做。」然而在過程裡,她發現大家見到的,與認識的,還是先從<br />
丈夫 Mayaw 的認識後,連帶知道她是師母的身份:「可是那時候(大家)還不知<br />
道,我叫 Sayung‧Losing,只知道我是 Mayaw 師母。大家看的,他們認識的還<br />
是 Mayaw 師母。」<br />
以 Mayaw 師母為開場白的介紹,多次經驗讓 Sayung 開始反省,她當時感覺<br />
到她不是 Mayaw 的附屬。雖然身份是他的妻子,但也有名有姓,是一個獨立的<br />
個體:「我開始反省,在任何場合 如果有人刻意介紹我,他只能介紹我是 Mayaw<br />
太太,那時候我的感覺就是,我怎麼會是他的附屬。我有名我有姓阿,我即使那<br />
時候沒有改名字,我好歹也叫做宋惠珍。那時候,好歹也說宋惠珍女士什麼。喔,<br />
不是,他們介紹說這是 Mayaw 太太、Mayaw 師母,從來不稱我說,你是<br />
Sayung‧Losing。我想說,算了。」<br />
但是 Mayaw 認為這是一種疏忽,因為介紹方式的問題,讓別人對 Sayung<br />
的認識,還是停留在 Mayaw 太太的稱呼上。然而在他入獄的期間,Sayung 也參<br />
加不少大大小小政治性的會議跟抗議活動,早就自己走出一條運動的路線來。倘<br />
若沒有刻意的在介紹 Mayaw 太太後,接著說明她叫 Sayung‧Losing,使人記住,<br />
那 Sayung 下次還是不會以自己的名字出場:<br />
以前還沒有想過,出獄過後他一直慢慢在想說,其實我參與了很多政治<br />
的部分,為什麼大家不認識你的名字。那時候開始,他覺得疏忽了。因<br />
為介紹就是說,我太太,就這樣子,就沒有報我的名字是誰。所以他那<br />
個時候,他也在反省。以後我出去的時候,(他就會這樣介紹)這我太<br />
太,而她的名字叫Sayung‧Losing。很注意到這個,他介紹我的時候會<br />
介紹我的名字。她是我太太這是 很必然 ,而是 她的名字叫<br />
Sayung‧Losing,不是Mayaw太太或是Mayaw師母。〈Sayung〉<br />
所以遇到不知道 Sayung 跟 Mayaw 的關係的新朋友,Sayung 很直接自我介<br />
紹,告訴別人:「我叫 Sayung‧Losing。」直接表現出個人獨立的形象。<br />
教會的工作、兒女的健康、獄中的老公、原運的工作,這四者,瓜分了 Sayung<br />
全部的時間。Sayung 自認她大可不做原運的這些事情,丈夫入獄了,小孩生病<br />
了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說服她放棄原運的工作,只要專心於她的教會工作與家庭就<br />
可以了。但是 Sayung 的心就是放不下,放不下成長經驗裡面那些為人服務的精<br />
神體會。<br />
一年半以後,Sayung與原運團體的努力,讓她的丈夫終於能在聖誕夜前夕釋<br />
放。繁忙的一切讓Sayung沒有時間,沒有好好的照顧自己。連壓力過大產生頭髮<br />
132
上的禿塊也是髮廊的小姐發現,她才驚覺,鐵打的身體好像出毛病了 20 。<br />
治療圓形禿的過程裡她也瞭解到,該作的事情要作,但是照顧別人的同時,<br />
也要關心到自己。事後 Sayung 回憶起這段往事,還是不能相信自己當初那股任<br />
重道遠的勇氣。從花蓮教會到高雄漁民問題、台北違建戶的各項工作,都沒有像<br />
Mayaw 牧師入獄那時的辛苦,讓 Sayung 感到力不從心卻有要硬撐下去的苦衷。<br />
那在運動場上一起奮鬥的同伴們,沒有人曾主動詢問 Sayung 需不需要幫<br />
助?原運團體只看重每星期的會面時間,討論、關注的只有原住民政治性的局<br />
勢?Sayung 老實的說,這些事情他們幫不上忙。教會工作的事、小孩照養方面,<br />
最清楚流程與方式的是 Sayung,團體友人們縱使關心插手可能也不得其門而<br />
入:「我自己教會的事我一個人做,因為他們幫不了忙。我小孩子的事情我也一<br />
個人做。很多的事情就是需要我做,要處理。」<br />
那時讓Sayung心裡難以拒絕的幫助就是丈夫Mayaw對獄友的愛心關懷。<br />
Sayung丈夫的牧師的身份,在獄中大家都知道。苦惱的獄友找他訴苦,請他排解。<br />
當然也包括了經濟的困難,而Mayaw都會想辦法當作自己的事情解決。從親疏關<br />
係上來說,很顯然的,可以提供支援的就是她的妻子Sayung:「不是只忙我自己<br />
的事情,我還得忙我老公交代的事情。」寄錢、送花、水果探望這些行為,為期<br />
一年多的牢獄生涯,Mayaw幫助了許多獄友,也讓Sayung多了幾根白髮。<br />
一直到丈夫出獄以後,Sayung 才發現自己的壓力在身體上的反應。而她也<br />
知道丈夫對她的心疼,很想要好好彌補過去她的辛苦。她說那是她應該做的事,<br />
利用分工也好還是團體戰也好,該作的事還是要完成。少了丈夫的這段時間,<br />
Sayung 一個人也可以把兩個人的事好好做完,帶孩子、教會工作、原運等,就<br />
是不要讓暫時休息的丈夫擔心。<br />
其實 Sayung 有認真想過放棄的時候,可是當小孩子左一句「媽媽,還好喔,<br />
你們那一代,爸爸他們那些人一直在為原住民爭取,不然現在哪來的可以改名<br />
字。」兒子說。右一句「媽媽以前好辛苦喔,而且辛苦都有代價。」女兒說。這<br />
些話語傳來耳際時,原運與子女這兩個最甜蜜也最沉重的負荷是 Sayung 拋卻不<br />
下的寶貝。<br />
1990 年代街頭原運時期,有兩位原住民男性運動者因為違反集會遊行法入<br />
監服刑。Sayung 的丈夫 Mayaw‧Kumod 是第一個,第二個則是 Icyang‧Parod,<br />
也是 Afan 的前夫。當年,部落的長老們還在司法院前面,為 Icyang 舉行部落公<br />
審,判他無罪。隔天(1995/10/24)的抗議「反司法迫害,還原住民人權」大遊<br />
行還拆下立法院的招牌。<br />
前夫入獄的期間,Afan與Sayung擔心丈夫的心情是相同的。雖然監獄規定每<br />
週只能會面一次。但是Afan到處拜託認識的立委們,寫傳真去向法務部要求,讓<br />
她可以會面。回過頭來,觀看因為前夫入獄,連帶使Afan工作環境受到波及。雖<br />
然長老教會對於社會運動採開放支持的態度,也曾發表公開的聲明與行動支持原<br />
20<br />
那時候我覺得真的一天的時間(忙到)都不夠我睡眠。哄孩子,顧孩子什麼的,好辛苦。那<br />
段時間,都一個人,完全沒有人幫我。〈Sayung〉<br />
133
運某些議題。不過當時正值原運抗爭的高峰期,每週都有遊行抗議活動,猜測長<br />
老教會遭到一些社會壓力或是保護政策使然。讓Afan在當時的工作上,面臨幾次<br />
去留的問題,還好事後都是有驚無險,依舊在長會總會工作,只是工作單位轉換,<br />
離開原住民議題較遠的業務 21 。不過在同一個地方工作了將近 20 年,Afan也曾<br />
因為複雜的人事糾葛想要離開。曾試著應徵其他工作,在外頭轉了一圈以後,她<br />
發現同樣是工作,在這裡可以讓她展現宗教服務的熱誠,外面的工作只能冷冰冰<br />
的上班下班,對她來說沒有任何意義。<br />
Afan 在面對熟悉的環境的各種責難,以戒慎恐懼的心度過,在原運與工作<br />
之間,終於取得了平衡。而 Lipay 在抗議遊行的時候,除了議題訴求以外,心裡<br />
想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擔心丈夫對她作為的看法,害怕她的舉動會影響到丈<br />
夫工作的前途導致丈夫的不諒解與不支持。當然,Lipay 最終還是希望得到家人<br />
的支持。<br />
Lipay 對原運的第一印象除了來自於媒體與教會 Mayaw 牧師的陳述,另一個<br />
窗口則來自擔任警務人員同為阿美族籍的丈夫,雖然丈夫對原運的動機與訴求表<br />
示肯定,但是丈夫的認同並不能表示也贊同 Lipay 出去參加遊行。警察身份的顧<br />
慮是原因之一,個人安危也是。Lipay 每次去遊行總是戰戰兢兢的怕被丈夫發現。<br />
而真正讓 Lipay 開始擔心自己的安全,感覺到害怕,是面對面與鎮暴警察對<br />
峙場面。回想那天,Lipay 說有超過三倍的警察在包圍著她們,試圖驅離遊行者。<br />
漫長時間的對峙下,警察把她們架離抗議地點。在專門收容抗議份子的保安大隊<br />
裡,待上六小時。最後透過立法委員與各方的幫忙才得以被釋放。當時,已經接<br />
近半夜了。獲得自由的 Lipay,她的心境又轉向擔心丈夫是否因為她的晚歸而正<br />
在生氣。已經半夜十二點了,而她卻還沒回家,怎麼不會讓家人擔心?她待在保<br />
安大隊的事,警務人員的丈夫知情嗎?這樣多的猜測,讓 Lipay 一回家,見到端<br />
坐在客廳等她的丈夫,Lipay 緊張的低著頭不發一語,趕緊洗澡整理家務。而那<br />
天晚上丈夫卻什麼也沒問 Lipay,就這樣過了一晚。<br />
過了一陣子,Lipay 才告訴丈夫那天發生的事情。原先 Lipay 以為丈夫會勃<br />
然大怒,還好策略運用得宜,沒料到丈夫的反應讓她出乎意料:好一陣子然後再<br />
告訴他的。我跟他講這個事情的時候,他說:「唉阿,你早說嘛,我是很認同他<br />
們(原運)的動作,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可是我是警察)不方便出面。」他<br />
說:「你不要太露臉,因為是公務人員的家屬。怕這邊(Lipay 參加遊行),擔心<br />
影響到他的工作。〈Lipay〉<br />
此後Lipay去參加遊行不再需要擔心丈夫的想法,而且當時正值青春期的一<br />
雙兒女而言,她們的媽媽作了最好的榜樣,有遊行活動也一起去參加 22 。<br />
21 Afan 的工作本來是在原住民宣教委員會,在解聘的最後關頭,她被調去總務處當總機。之後<br />
就從電話總機小姐到總務處助理,再到發行室,負責編輯刊物。工作職務都與原運的教會運作扯<br />
不上干係。最後還是因為待他如親人的牧師相助,終於讓她回到原宣繼續服務,直到現在。回憶<br />
起那個場景,與那些讓她傷心難過的話,還記憶猶新。<br />
22 這些動作是為了什麼,那一定是要讓他們知道,因為我們做任何事情要跟他們做說明,讓他<br />
們去認同(Lipay)<br />
134
Lipay 在行動上有家庭的支持,讓她從此原運路上不孤單。Sankilj 則有陷在<br />
親情的壓力伴隨她運動的熱情的消長。<br />
「真的我忘了,到底遊行幾次,我算不起來了,我還好幾次被罵共匪。」Sankilj<br />
說。在那個未解嚴的時代,大家對匪諜的定義就是會來擾亂台灣社會治安,煽動<br />
反抗政策的遊行。所以常在集會遊行場合出現的Sankilj,就被圍觀的民眾罵共匪。<br />
但實情是當時Sankilj有一個現役的憲兵中校兄長。而遊行場合上的跟原運團<br />
體針鋒相對的鎮暴部隊,就是她的哥哥在掌管。Sankilj遊行的一舉一動都有人在<br />
監視著:那個時候我都不敢照相,因為我哥哥那個時候是憲兵中校。我兩次從現<br />
場被拉走啊,然後被訓,(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誰是誰,我只知道阿兵哥把<br />
我架走,等到坐上車。我才知道他(兄長)叫他阿兵哥抓我回去的。我哥哥真的<br />
很厲害,從現場把我驅離,在現場把我抓到,我覺得他是不是跟在我後面。<br />
除了有被在運動場上被兄長拉走的經驗,Sankilj還被哥哥找去訓話。哥哥告<br />
誡她,她遊行的行為會影響到他的升官與考績。其實哥哥的另一層用意是擔心她<br />
的安危,Sankilj當時沒有聽出弦外之音。甚至在Sankilj以替原住民爭取權益反駁<br />
哥哥的禁止時,她的哥哥還以為Sankilj是在造反,很擔心Sankilj會因此陷入牢獄<br />
之災:「我只是跟他說,那你知不知道,跟我們一樣流著這個血的原住民,有很<br />
多人無家可歸,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完美,我就這樣跟他反駁,所以那時候我哥哥<br />
認為我在造反,他覺得說我在反抗當時的執政者,他覺得說我那個時候是混亂,<br />
他很擔心說,如果我被抓,我被關。」Sankilj說。<br />
夾在兄長與運動的熱情之間,Sankilj 每次遊行的時候心中都充滿矛盾與衝<br />
突,很怕哥哥又會在場上把他拉走。然而親情的壓力還不止於此。遠自屏東家鄉<br />
的也認為 Sankilj 去念了神學之後怎麼變了個樣子,而擔心不已。<br />
所以 Sankilj 花了很多時間去向關心她的親友們解釋跟說明,父親才漸漸明<br />
白。偶而出現在地方抗議活動,也與 Sankilj 為原住民議題而走,開始慢慢從瞭<br />
解到支持 Sankilj 的志業。兩年後,Sankilj 的哥哥退伍了,當時她也完成神學院<br />
學業,就前往台北的長老教會機構工作。往後台北街頭有什麼遊行活動,下班後,<br />
Sankilj 就常去參與。<br />
兄長的退伍對 Sankilj 來說是心情壓力頓時減輕,而神學院畢業後,在長老<br />
教會彩虹婦女事工中心工作的機會,讓她有時間接觸原運以外的社會運動議題。<br />
此時的她從原運的議題上得到成長,進而成為對各個面向投注關懷的社會運動<br />
者。也曾跟著原權會的幹部一同到泰國參加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會議。<br />
Sankilj在運動場上當然也有緊張的時候。在遊行的分工上,對自己作為很有<br />
想法的她,是不可能老擔任發傳單的角色,而不會被其他領導者發現她的優點。<br />
有許多場合,很多人都想要推她上台發言,不過Sankilj卻不敢答應:「我顧慮到<br />
我的大哥,那個也是我不敢的原因,因為有親情的壓力。」除了親情以外壓力,,<br />
敬老尊賢的禮貌也是她選擇不上台,寧願發傳單的原因 23 。<br />
23 我那時候有想過。因為有那麼多的前輩,就覺得自己不是什麼東西,就不願意去。就寧可去<br />
發傳單,要去發一些東西呀。有什候要面對那個鎮暴部隊的,也是很甘願的站在最前線,只有上<br />
135
在台北街頭運動場上,Laya 也在很多的場合中觀察到除了親情以外的男性<br />
運動者與女性運動者之間問題。<br />
Laya 算是早期的運動者之中,在原住民議題裡打轉的少數女性領導者。與<br />
其他運動者雖然是站在民主情感的立場的結盟。Laya 以為每個人想傳達的理念<br />
不盡相同,總是有相異之處。她說在原運初始時:<br />
初期希望能夠結合這樣一個系統,就是說你從工農,從婦女有很多的原<br />
運的結盟。在這個運動的過程,我是唯一的女性。有很多在對原住民的<br />
問題跟困境的認知上跟這個壓力(身為女性)的侵害感是一致的。<br />
當時有一些狀況我也意識到男女有別的問題。譬如說那些意見,女人的<br />
意見會不會被同意,那些主張,女人的主張會被同意?那些我有觀察到<br />
他的端倪。〈Laya〉<br />
她觀察所見,當時許多的女性角色是處於輔助性的地位,像是情人、朋友<br />
等,協助男性運動者作簡易的剪貼或文宣的製作,遊行前雖有分派工作職務,但<br />
是與政府官員遞交陳情書的重要鏡頭,都見不到女性的身影:<br />
媒體是有你去說話的地方,不會讓你在那個畫面出現。在第一線裡面,<br />
有鎂光燈的、有政治的積累這種成果,女性是絕緣的!〈Laya〉<br />
Laya 所見的兩性問題,各個女性運動者間看法不一而論。她談論的牽涉到<br />
運動內部的分工,還有女性運動者各自對傳統女性與現代女權觀念的認知差異,<br />
在眾女性間產生許多的討論。<br />
Afan說:「在當時啊,原運的女生大部分都比較少浮到檯面上,大部分都是<br />
做幕後的啊!」但也不能以「作幕後工作」而全面認定多數女性運動者行為,應<br />
是鮮少出現在遊行車的講台上,登高一呼。如Laya所言:「媒體是女性絕緣體的<br />
角色。」較多時候,運動場上可以看到Sankilj在發傳單與前線衝撞、Afan拿著擴<br />
音器高歌前進與負責繕打文宣品、Sayung跟Lipay忙碌的動員婦女、Laya為關注<br />
的議題在衝刺,演講。分工方式的不同讓她們的工作散落在各大小事情上。<br />
但是她們還是用「幕後工作」來形容自己所做的事。有沒有參與核心會議、<br />
發表演說與意見的行為,也是她們以為自己擔任「幕後工作」的原因:<br />
Sayung說:「真正的參與原運我從以前就有在參與,沒有斷過,既使我<br />
是在做幕後。老公在前面,開會也是他們開會。那就是他們開會決議怎<br />
麼樣,我就配合。」Lipay說:「有過跟他們一起討論。跟原權會的一<br />
些幹部。麗依京、Icyang、MayawKumod、麥村連,不少喔,還有幾位<br />
牧師。那自己就在那邊(開會)。那我不是最核心的。他們有他們一些<br />
台講我不敢。因為看到很多前輩在,就會覺得自己的份量不夠。(Sankilj)<br />
136
細節討論的一些人(幹部)。」<br />
由此可見,當時在她們的瞭解裡,有哪些女性才符合「幕前」運動者的定義:<br />
Sayung 說:「有啊,有幾個,好多啊。我們就跟原運,幾乎都是在做幕<br />
後的工作,幕後比較多。還是有幾個站在第一線的。那個,麗依京‧尤<br />
瑪,還有巴燕‧達魯的太太,露妮,她們都是站在第一線的。」<br />
Sankilj說:「也有很多女性在講話,那時候在講話的,像陳秀惠現在的<br />
立委,陳美珠,還有那個麗依京‧尤瑪,大概就是這幾個在講話吧。然<br />
後還有幾個我不知道名字,但是我知道人。」<br />
Lipay說:「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那我沒有口才。只要是有能力的<br />
人(口才好),你可以在上面。所以當時女性也是,麗依京啊,她也是<br />
(有能力的人)。」<br />
會「講話」等於有能力,在台上演說的女性,才算是幕前的工作者。其他大<br />
小事務的分工,處在媒體光環外的,常被認為是誰都可勝任,顯得不比在台前說<br />
話的事情重要。而對自己被其他人歸為在台上說話的女性角色, Laya 自己發出<br />
了這樣的觀察:「說這個運動可能有人要遞請願書,要跟最高的領導人互動,這<br />
個(重要)角色,都不會是由女性擔任。」<br />
Sankilj 更進一步的描繪在開會分工時候的情景:「在籌備的時候,是在總部<br />
(原權會)。他們在分配一些工作的時候,的確都是男性在主導。可是女孩子還<br />
是可以提供意見。」原權會員與教會傳道人,雙重身份的她跟 Lipay 一樣,都不<br />
是最核心的幹部群,只是參加開會的義務資助者:「我是原權會的會員,又是長<br />
老教會的傳道人,所以有兩個身份。兩個身份的我就去參加(開會),但我並不<br />
是幹部。原權會他有本身的幹部,長老教會也有本身的幹部。我那個時候的角色<br />
比較像是義工,在那裡提供資料。」<br />
我在參與的時候,像那個尤哈尼,或者是麥村連,那個時候 Icyang 也<br />
有來。我就會覺得說他們都很尊重各方的意見,而不是單單把女性搬出<br />
來(分配工作)。沒有,我們是大家一起討論的。有的時候他會點呀,<br />
會點呀,(叫你說)你的看法怎麼樣?因為(開會的時候)女孩子不講<br />
話的話,都會被點嘛,真的會這樣子。〈Sankilj〉<br />
他們很尊重(我們女性)。我參加了幾次的籌備會,我覺得很(受)尊重,<br />
以我的角度。他會要聽我的意見怎麼樣,很多時候是我們很被動(不自<br />
己主動開口)呀,他們並不是不給(發言機會)。〈Sankilj〉<br />
男性運動者主持會議程序,涉及議題討論的時候,與會的人都被男性要求要<br />
發表看法。Sankilj 認為男性會聽她的意見是一種尊重的表示,但她也說出了會議<br />
137
的主導者是男性。但是 Sankilj 以尊重會議的角度去思考,開會的每個人都有表<br />
達意見的權利。其他男性用「點」的動作告訴她,不要忘記這個權益。有的時候,<br />
反而是自己太過被動的發表意見。<br />
而幾乎沒有參加過開會的 Sayung,事後被告知分配的部分,她也認為這是<br />
一種分工,開會的人決定事項,像工廠一樣外包出去給有門路的人。這樣的模式<br />
的過程裡,Sayung 覺得較不會干涉各自工作的處理:「因為我有我的工作,他有<br />
他的工作,既然開會完畢,告訴我有這樣的決定就可以了。」<br />
對於在籌備會議發表意見,為何女性總是少言的問題,Sankilj 自有一番解<br />
釋。她以自己作例子說明,從小受的教育教她比較保險的作法,習慣性的先看別<br />
人怎麼行動。在社會觀念裡,她說女性的行為被框上固定的框架,嚴格地被檢視<br />
著,常莫名的背上社會包袱。再者,女性運動者面臨責任背負時,她同時也扮演<br />
在家庭與工作上的眾多主角。女性細膩的特質與社會賦予的衿持印象,也讓她們<br />
顯得踟躕不前。<br />
當然,Sankilj 認為當時的情勢波動也是很大的因素。而從小受到男性必須是<br />
強壯勇敢形象的知識輸入,讓她覺得男性有保護女性的義務:「當時的那個局勢,<br />
他們就是要保護我們。我覺得男生就是要保護我們(女生),不允許我們遭受到<br />
危險。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女性的角色,你說被動(不去爭取工作)嗎?也不是。」<br />
女性被動的感覺在當時的她來說,是籠罩在男性保護傘的下方。「當時的局勢很<br />
危險。這些男生為了要保護我們,他們都不太願意讓我們站在最前線。可是在籌<br />
備當中,我的感受是很(受)尊重。」Sankilj 說。<br />
Sankilj再拿她當作例子,繼續敘述女性在社會運動場上自我、家庭、與倫理<br />
框架交互思考的天人交戰場面:害怕說話不得體、長幼輩份的倫理、親情的告誡<br />
都是Sankilj的難言之隱,因為當時不能完整的表達。這個衝突的形象,還被其他<br />
男性視為膽小懦弱 24 。<br />
而詢問男女分工的內部文化時,Sayung 就很明白的說,參與就是一份心,<br />
要什麼樣的位置或者角色都不是最重要,如同 Lipay 與 Sankilj 一樣:「我覺得參<br />
與是最棒的。你人參與,就是一份心。不一定要做到什麼位置,我覺得說我帶人<br />
來會更好。」而她和 Lipay 透過教會工作的關係,常常負責婦女動員的工作。她<br />
們利用電話聯絡的方式動員,長老教會系統樹狀的通訊網路及公報可以方便掌握<br />
人數。<br />
較於 Lipay 與 Sayung 的婦女動員模式,Sankilj 以她自己所見去解讀女性心<br />
裡內部的難為,原運的男性伙伴們對女性的偏見說法不是絕對。不同於她,Laya<br />
透過她的觀察,用性別的二元概念與傳統教育的影響,提出一套女性權利觀的見<br />
解。她認為傳統父權的觀點,實是完全移植到某些原運者的男性與女性身上。<br />
Laya 是其他人口中在幕前講話的工作者,而她說用倡議者來形容她的角色<br />
會更合適,主要是因為她在娼妓研究上的貢獻。在原運裡,她自覺為:「應該是<br />
24 他們那個時候一直推我說,去呀!我沒有去(台上),那時候我就被他們一直罵我說:「你怎麼<br />
那麼膽小,那麼懦弱!為自己講話,為自己想。〈Sankilj〉<br />
138
倡議者,這個定義上面對我特別較恰如其份。因為你必須透過演說去影響,你想<br />
影響的事情。」從初期就全程參與原運的工作,在核心的幹部群裡面打轉的她。<br />
又有什麼原因使她後來選擇離開核心的決策者,轉變成幕後的遊行支持者。運動<br />
者彼此間認知差異與內部文化的情感連結是離開的線索:<br />
經歷過那麼多不同的場域與位置,看原住民問題的一些角度比一般人還<br />
要深刻,我走到這裡來更深刻。所以運動對我來講那個是一個很重要<br />
的,一種看整個原住民在整個主流社會面臨的一些困境造成的結果。為<br />
什麼會這樣?我找到那種串連困境的一些解釋的一些線索與工具那個<br />
成分。〈Laya〉<br />
這些串連困境的線索與成分,Laya 把身為原住民女性在整體社會的困境,<br />
兩者解釋結合相似的地方,發出了如此的感嘆:男性的習慣與女性自己體認的從<br />
屬意涵思想互相輸送下,造成原住民婦女運動在原運當時主題涵蓋裡內部缺席的<br />
原因。<br />
從加諸了女性身份的原住民角度出發,她又把焦點放在整體社會對女性養<br />
成教育的窠臼之中,詳細說明:<br />
原住民婦女運動為什麼會缺席?是故意的呢?還是我們的男性非常習<br />
慣,這是我們的場域跟你們無緣也無份。這可能是,呃..多半的我們如<br />
果從一個教育去養成這樣的認知。整個既成的教育的價值就是告訴我們<br />
女人應該是附屬品,女人是依附的,女人是不應該反對,女人不應該說<br />
話。〈Laya〉<br />
Laya 用「打天下」的方式形容當年籌備的辛苦,卻也發覺大眾社會價值所<br />
建構的男性慣習,讓她在發表事件的建議時,受到其他運動者的漠視與不採信。<br />
於是五年後,Laya 決定離開核心討論圈,作自己堅持的議題運動。<br />
大眾男性慣習讓 Laya 無法接受女性為何一定要處於乖巧柔順的角色。一直<br />
為議題發表意見與要求的女性,對團體裡男性權威帶來很大的衝擊。而操作事務<br />
性工作的女性,在團體間的關係,則會受到男性較多的眷顧:「這些運動裡面就<br />
是說,很自然的這個價值建構出來的女性對待的一些慣習,所以,你如果每次就<br />
是幫忙他(男性)剪剪東西,做做後援部隊(男性就會很滿意)。」問題出在發<br />
表眾多意見的女性運動者,對男性主導人物產生了威脅性的危機,使得有男性意<br />
識的產生排除心理?<br />
若假設如此,那麼女人表現出她的主體性,就會被男性視作情緒上的歇斯底<br />
里。社會營造的守舊氣氛導致,女性的思想與見解無法被男性所採納。Laya 說:<br />
他(男性)連承認你(女性)的主體能力,你的主體見解,你的獨立思想,都不<br />
會!所有女人的勇氣都把他解釋成神經病、情緒化。他(男性)不會容忍你的自<br />
139
主性,不會容忍你的獨立見解的。他不會,整個社會營造的氣氛是這樣。<br />
一個巴掌拍不響,這也不是單方面的認定,多半的女人也習於傳統社會慣習<br />
約束。Laya 認為女性傳統所受的知識生產,也是促成男性刻意淡化原運裡面原<br />
住民女性運動者成就的幫凶:「因為多半的女人也接受這樣的制式教育,只是暗<br />
示,自我暗示這種角度來看。當然這個運動裡面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女性的參與與<br />
貢獻。當然全部就被稀釋掉、被淹沒掉。」<br />
而女性面對表達意見時候,要尊重男性面子的自我暗示教育,使得女性殉道<br />
者的形象被無比推崇,女性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觀念,連帶工作與家庭的地位被<br />
拋卻,還順勢丟了男性對女性的尊重。而男性卻不用受到這樣的犧牲形象背負:<br />
這整個運動的歷程,是很多女人的犧牲,包括工作。你不工作,你不盡<br />
男性家庭背負責任的那種待遇。因為父權社會給女性一個犧牲的形象,<br />
那你在這個形象的要求之下,你願意這樣子作(犧牲工作與家庭搞原<br />
運)。這是很自然的。你不會懷疑是這是一種不對。〈Laya〉<br />
Laya 以上的批判,都是事後才慢慢發覺有這樣的脈絡在運作。而當下的她,<br />
腦中雷達並沒有偵測到諸多原運男性的作法。當時男性的態度可以主觀的歸因在<br />
大環境下的近墨者黑使然。關於原住民婦女議題在當時原運的訴求裡面表現得很<br />
微弱,原運還是不脫主打政治上的平等與揭發不公的事實。原住民雛妓問題是初<br />
期的曇花一現,熱潮很快就被其他社會問題掩蓋過去。<br />
更大的癥結是處在媒體前曝光的領導者,Laya 說女性都消失了,都是男性<br />
的角色,而她們卻還是犧牲的形象,被男性利用著:<br />
媒體不會是有你去說話的地方,不會讓你去在那個畫面出現。在整個運<br />
動的軸線裡面,我們被擋。所以在第一線裡面,有鎂光燈的、有政治積<br />
累這種成果,女性是絕緣的!〈Laya〉<br />
再回頭落到傳統女人處事分類的習慣上來說,Laya 認為女性的處事邏輯,<br />
老是被主觀的男性以偏概全的否決,整個運動的路線會偏動,不連貫,很多原因<br />
在於處事者的態度問題。傳統女性常利用分段的方式,多方面處理某一件事,並<br />
確認每件事情妥當無虞,女性嚮往的是一個可以掌握情況的環境。而男性主導的<br />
路線規劃上,太過利益導向就會變成製造個人英雄、不確定衝突的局面。她認為<br />
她作了很多原運中應該要被注意的事情,但是其他男性運動者所操弄的原運路<br />
線,使她的努力被埋沒了。<br />
最終 Laya 還是回到人權的議題,用實際的成果來努力她與人民都同意的主<br />
張。努力爭取人權自由,雙方分享對人的基本關懷就是良性利益的輸送。Laya<br />
肯定原運中女性參與者的貢獻,但她觀察到的諸多的因素,表現出女性在原運的<br />
氛圍底下自動、被迫的無法與男性分享運動成果:<br />
140
這個運動整個發展的過程有很多不同的女人參與過。但是這個運動分享<br />
給這些女性什麼東西?沒有。(Laya)<br />
而在當時參與的女性運動者除了已婚、夫妻同行以外,未婚女性運動者也存<br />
在於原運之中,Sankilj 與 Laya 當時即是未婚女性運動者。而她們兩人對於原運<br />
伙伴兩性之間的對話與立場,仍留有許多待為文討論的空間。<br />
四、走進自己的田,看見自己的門<br />
這是最最遙遠的路程,來到以前出發的地方。<br />
這是最後一個上坡,引向家園絕對的美麗。<br />
你我需穿透每場虛幻的夢。<br />
最後才能走進自己的田,自己的門。<br />
------胡德夫〈最最遙遠的路〉<br />
光亮的生命也是會被小小的阻礙,稍微減弱些許光芒。不過阻礙反而會讓生<br />
命展現更多的韌性。遊走在眾多原運團體裡面的女性,或許在她們的回憶裡面有<br />
許多怨懟和歡欣,也有許多辛酸和掙扎。但也因為這些的歲月人事糾葛,才構成<br />
原運政治面以外的溫情時代。因為這些對立的事件,才見的到彼此為自己的立場<br />
在奮鬥的模樣。<br />
受訪者女性個人在面對橫逆時,傾向「靠自己」解決問題,自助的想出應變<br />
方案,以過當下。像是 Sayung 在丈夫與女兒間忙碌穿梭,尚能努力於自我實現<br />
來說。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若沒有苦心堅持也無法如此。她巧妙的將原本屬<br />
於丈夫的實現,轉移到自己身上,強化自己自我實現的微弱因子。使她在丈夫入<br />
獄、女兒病情雙頭燒的當下仍可以透過意志努力達成,社會運動、教會工作、家<br />
庭之間的平衡,並且走出一條自己的原運路線。Sayung 從幕後浮現為政治犯家<br />
屬的開端,模擬代夫出征意涵很重,進而在互動的過程裡面,逐漸由被動的責任<br />
感(暫時代替 Mayaw 的角色)轉向主動的自我實現。Sankilj 與 Lipay 不也是在<br />
自助的情境底下,解決自己夾在人際關係與親情裡的為難,在她們的人生歷程<br />
裡,無時不是朝著此「自我實現」的目標前進。<br />
在運動內部文化上的討論,當女性運動者在男性主導場合裡「回話」,是否<br />
造成了男性對主導地位產生危機感,致使男性無意識對「回話」的女性運動者採<br />
取排除政策?以確保自我核心地位的優越,而沈默的女性運動者卻又會被「點」<br />
起來發表意見,「點」的動作有支配的意味,若本為男性促使會議結論出現的好<br />
意,因為作法不夠尊重,便落入了傳統性別主義的批評。那麼女性在運動的內部<br />
文化中,對於運動者男性而言,從她們敘說來看,是不可或缺的依附性角色。在<br />
媒體公眾的前台展現時,女性形象還要適時的退居,成就男性。由此可以看見女<br />
141
性若處在傳統社會的期望下,犧牲的形象常連帶著女性的圖像,一同扮演「阿信<br />
25 」般吃苦、識大體的社會角色。而當家庭發生變故或出現裂痕,女性真要把自<br />
己排除在外,以家庭為優先處理,奉獻自己,忽略自己的感受。然而家庭角色遇<br />
上社會運動的自我實現,公私領域的角色轉換時,母職角色的完成使得已婚女性<br />
運動者認為自己是「兼職」運動者,故以「幕後」作為自己原運行動位置的表示。<br />
因為非「全職」運動者,對自己能力上面呈現否定自我,卻告知我們一個實情:<br />
女性運動者身上帶有許多牽掛,所以不如男性可以全心一意維護運動的神聖性。<br />
而女性運動者對於不確定事物表現出無法預測的不安,也讓她們在失去支持(入<br />
獄或者運動路線不明確)產生惶惶無助的飄零感。就像 Laya所言,女性處理事<br />
件的方式採分段計畫,步驟掌握,遇到困難必先解決。而不似男性以最終目標為<br />
整體營運方案,面對未知狀況仍能執行。這是性別氣質上的問題,Sankilj所認為<br />
「男生要比女生勇敢、男生就是要保護我們女生」的說法是以受到傳統規範的教<br />
育思考。但這種作法卻使得原運內部文化裡也複製了一群受到階級壓抑的人。再<br />
回歸「能力」判定問題上來說,女性自我肯定的價值,在傳統社會觀點下呈現來<br />
自於他者的讚賞;而在現代社會新女權觀念影響,女性能力實來自於自我肯定的<br />
成就,女性運動者間對此討論所持的立場因各方援引與啟迪觀念不同導致。而前<br />
文裡提到Laya與Sankilj所持的觀點,也正是大眾對傳統與現代女性形象立場的不<br />
同解釋面。<br />
愛人同志情感的Afan與Sayung、中間螺絲釘路線的Lipay與Sakilj、公共正義<br />
的Laya於各敘事主題比重上或有不同與缺乏,造成材料使用上的失衡現象,這或<br />
可認為是個人著重與注目的記憶不同所致。也表現了:在她們生活中,原住民社<br />
會運動交織在公領域與私領域當中。不過也告訴閱讀大眾,有些聲音必須被限<br />
制,才可創造出某種特殊的和諧,並且真實的呈現出她們自我的面貌,如同交響<br />
曲般的共鳴。<br />
針對女性運動自主性的討論,多數女性運動者在運動場合中,行動角色依附<br />
於(丈夫)而顯現。Sayung 自我覺察「我是誰」的例子來說,她也是在場合中<br />
找不到屬於「自己」稱呼,而感到附屬於丈夫形象的現象。「Mayaw 師母」與<br />
「 Sayung‧Losing」由名可見,選擇發出招呼的人是以一個人或是兩個人的雙<br />
重印象來與 Sayung 對談。除可當作結識時間點的辨別,也可當作他人肯定 Sayung<br />
的努力是否連同丈夫 Mayaw 的形象一併考量。這也是當時夫妻共同從事運動的<br />
女性運動者,一個受到雙重檢視必須背負的不成文規定,已婚女性運動者的言行<br />
還必須為丈夫成就形象負起責任,我們可由 Sayung:「丈夫若不是那麼有名,自<br />
己的名字才會被其他人記住」的說法得到驗證。可見運動團體內部慣常使用延伸<br />
印象記住他人的方式:誰先被注目,相關他人就連帶成為依靠的角色。<br />
女性運動者在原運的內部文化上,建立的原運、族群、個人的自我認同感是<br />
25 《阿信》為日本 90 年代長紅連續劇。主角〈阿信〉小時候被當賣幫傭,年輕時受婆婆的虐待,<br />
終年遭逢戰爭,喪夫喪子,到老年開超商而重新開創生命的另一春天,一生曲折坎坷。作者橋田<br />
女士綜合日本各地女性的故事編寫而成「具有日本阿媽性格」的女性生命小說。而「阿信」一詞<br />
也轉化為吃苦耐勞、為人奉獻的意象。<br />
142
交雜於個人歷史和社運歷史,呈現複雜多元形象。也呈現了她們所述說之原運內<br />
部文化,本是多方各自表述,卻又資源共享互助的實況。<br />
Kiecolt(2000)認為社會運動的參與有可能帶來自我觀念的轉變。一種可能<br />
是參與者認同階序的調整,使得某一種認同晉升到更主導的位置,因而貶低了原<br />
先的主要認同。另一種自我觀念的轉變,是在既有的認同上建構新的意義。經由<br />
運動的參與,以往被貼上負面標籤的身份特徵或是生活方式,反而可能成為群體<br />
驕傲的來源(何明修 2005:86)。若從教育程度與受教地點來說,當年處於 19-26<br />
的女性受訪者群,屬於原住民知識菁英的一環。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就讀神學<br />
院的她們比其他在部落與都市生活的同年女子,取得知識培力的方法更直接且有<br />
實踐的場所。甚至她們運動生命從神學院學生時代,即受到學院風氣影響,開始<br />
加入原運組織,以街頭遊行作為,形成當時社會環境裡一股不同於其他群體的驕<br />
傲。並在其中將民族的認同透過原運更強化,而帶出自我、身份的再認同。處在<br />
原漢文化邊界遊移的她們,各民族間不同的社會制度傳統和外來文化浸濡的交<br />
錯,也為其自我實現影響因子。但在本研究的呈現上,礙於敘事資料的取得與印<br />
證上,並無做更深入的討論,僅能隱約從各自參與原運時期經驗、工作、家庭、<br />
神學教育中看出端倪。<br />
對於女性在社會運動者非全職參與的討論裡面:「母職角色」是已婚女性運<br />
動者必須兼顧的重心。在家庭時間以外她們可自由支配時間的有無,成為影響已<br />
婚女性運動者參與的關鍵。但角色可說是社會對於某一地位的行為期望,是佔有<br />
地位者應該表現的行為。是文化的、是人為的、與個人的人格特質無關(張承漢,<br />
1994)。Wiltfang and McAdam(1991)指出:年紀輕、未婚、沒有子女的人,有<br />
比較多的可支配時間投入社會運動(轉引何明修 2005:81)。而本研究發現:少<br />
數未婚女性運動者雖比已婚女性運動者擁有更多運動機動性與自主,但卻仍得承<br />
受社會規範影響,自我暗示為「屈就」的角色。受到原漢文化傳統性別觀念影響,<br />
少數女性運動者成了幫凶,使男性為中心的道德觀更加壯大,因而造成與接受現<br />
代新女權觀念的女性運動者間嫌隙的開始。Laya談到個人主體建立與運動者互動<br />
部分,即援引女性主義者維護自我權益的立場,以此觀點批判運動內部文化中傳<br />
統主義的窠臼。女性運動者藉由從男性印象角色傳遞,投射到自主意識「我是誰」<br />
的過程,由「自助」的行為,在家庭與公共角色裡面排除困難,藉以維繫個人(與<br />
丈夫)原運的熱誠和家庭健全的結構,兩者雙重夾攻底下,仍努力於自我實現。<br />
勢必委屈忽視自己,自我忍耐,身不由己的建立一個「吃苦」的女性意象。畢恆<br />
達(1996)認為女人與男人同樣需要追求自我的成長與實現。女人的表現應該受<br />
到肯定,不是懷疑;女人也不應該因為她的性別,注定要犧牲自己去照顧男人或<br />
成全男人的事業。工作中如是,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不過從敘說裡發現,委屈過<br />
後,一旦可以真正自我掌控生命的步伐時,女性運動者所表現出來的積極與樂<br />
觀,才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意義,在感受與行動力上不由得讓人肅然起敬。<br />
范雲(2003)以為過去的社會運動研究,不僅忽略運動者及其生命背景的重<br />
要性,也往往假設同一個社會運動中的運動者必然是同質的。即是在同一個社會<br />
143
運動中,運動者整體的生命傳記背景的組成,也是會隨著時間而變動的。運動者<br />
可能自願性地加入或退出,其來源也可能受到整個大環境的影響。生命的意義並<br />
不一定是在事情發生的經驗,而是後來發生的事情開啟了當年的意義(余德慧<br />
1998)生命敘事的主要的目的是在瞭解受訪者在訪談時,在經驗裡如何賦予條理<br />
及次序,使得他們生命裡的事件和行動變得有意義(Riessman 1993)。<br />
不過,就算我們承諾站在女性立場,也未必就能讓經驗發聲。解釋經驗牽涉<br />
到再現真實,我們在研究過程裡,創造並一再地重複創造聲音,這個事實再也沒<br />
有比研究個人敘說更為明顯的(Riessman 1993)。Labov(1972)所有的敘說都是關<br />
於過去某件特定事情的故事,它們有共同的特質,並且表示他們希望如何被瞭<br />
解,以及重點是什麼。而形成敘說的不只關於我們過去的行動,同時也包括個人<br />
是如何理解這些行動,也就是意義。敘說者把他們的生命澆灌到這些典型的形式<br />
裡,也訴說他們選擇如何去解釋這些行動(引自 Riessman 1993)。<br />
以上,從她們的生命敘說可見,女性原住民社運者在運動與生活的交互穿插<br />
進出生命時,「自助」是她們所採用的生活攻略。處在原運脈絡下的她們,受到性<br />
別主義的規範、運動者印象角色的傳遞、同性姊妹情誼的立場殊異與自我生命經<br />
驗的交互影響,都造就原運歲月理她們的樣貌,同時也發現到怎於眾多的家庭、<br />
社會、公眾的角色的扮演下,原住民女性在不同的時間裡,針對不同主題的關心,<br />
透過原運,得到經營自己田畝的力量。在自我概念上獲得肯定,經過原運的生命,<br />
擷取新型態的認同模式,形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動能量。<br />
144
參考書目<br />
山海文化雙月刊編輯部<br />
尹象菁<br />
1997 台灣原住民社會大事記。刊於山海文化 15:22-46。<br />
2002 原住民文學中邊緣論述的排除與建構—以瓦歷斯‧諾幹與利格拉<br />
樂‧阿女烏為例。靜宜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王甫昌<br />
2003 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br />
王明珂<br />
2001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br />
台北市原住民委員會<br />
2002 山海子民的心靈謳歌:台灣原住民族女性的奮鬥歷程。臺北市:北市<br />
玉山社編輯部<br />
原住民委會。<br />
2004 台灣女性故事(共五冊)。台北市:玉山社。<br />
瓦歷斯‧尤幹<br />
1992 番刀出鞘。台北:稻鄉。<br />
多奧‧尤給海(黃修榮)<br />
2001 四百年來殖民統治者之土地政策—探討原住民土地流失。原住民報<br />
13:27-41。<br />
Icyang‧Parod<br />
1987 讓台灣原住民擁有文化地位。原住民 4:4。<br />
1993 我們為什麼選擇「台灣原住民族」這個稱呼。收於族群關係與國家認<br />
同,張茂桂主編,頁 187-190。台北:業強。<br />
1994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發展之初步探討。山海文化 4:22-38。<br />
1995a 「原住民」正名運動十週年前夕─我在「平安夜」拘留所內「紀念」。<br />
山海文化 10:88-91。<br />
1995b 從「山胞」到「原住民」的正名運動史。台灣史料研究 5:114-122。<br />
何明修<br />
2005 社會運動概論。台北:三民。<br />
何穎怡<br />
1997 女人在唱歌—部落與流行音樂理的女性生命史。台北:萬象。<br />
余德慧<br />
1998 生命史學。台北市:張老師文化。<br />
利格拉樂.阿女烏<br />
1993 我所知道的原住民婦女。清華大學兩性研究室演講。11 月 9 日。<br />
1996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台中:晨星。<br />
1997 紅嘴巴的 VuVu—阿女烏初期踏查追尋的思考筆記。台中:晨星。<br />
1998 穆莉淡-部落手札。台北:女書。<br />
吳天泰<br />
145
1997 婦女與原住民。刊於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42:1-2。<br />
吳佩蓉、黃懿翎<br />
2003 以愛與非暴力帶來改變的故事。台灣教會公報。<br />
網址:http://www.pctpress.com.tw/news/essence/people/p2635.htm. (網<br />
頁快取日期:2005.12.20)<br />
吳書昀<br />
2001 性別意識的發展歷程—以婦運參與者為例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br />
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李慈敏<br />
1991 族群動員—以台灣原住民族二次還我土地運動為例。清華大學社人所<br />
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江寶月<br />
1993 期待阿女烏使十族女性原音再現。刊於誠品閱讀 12:70-72。<br />
汪明輝<br />
2001 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回顧與展望。<br />
汪明輝個人網頁:http://www.geo.ntnu.edu.tw/faculty/tibu/<br />
論 文 全 文 網 址 :<br />
http://www.geo.ntnu.edu.tw/faculty/tibu/%E5%8F%B0%E7%81%A3%E<br />
5%8E%9F%E4%BD%8F%E6%B0%91%E6%97%8F%E9%81%8B%E5<br />
%8B%95%E7%9A%84%E5%9B%9E%E9%A1%A7%E8%88%87%E5<br />
%B1%95%E6%9C%9B%E7%99%BC%E8%A1%A8%E6%90%9E.htm<br />
(網頁快取日期 2005.06.20)<br />
周怡君<br />
1997 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與其社會運動參與。東吳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br />
文。未出版。<br />
周瑞貞<br />
1998 台灣原住民族社會運動之意義建構與媒體策略分析—以「還我土地」<br />
運動為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林亦晨<br />
2001 原住民女性之族群與性別書寫—阿女烏書寫的敘事批評,輔仁大學大<br />
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林春香<br />
2003 我是誰?原住民女性教師 Nikar 的生命故事。國立臺東師範學院教育<br />
研究所論文。未出版。<br />
邱貴芬<br />
1997 原住民女性的聲音:訪談阿女烏。中外文學 26(2):130-145。<br />
胡幼慧主編<br />
1996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br />
146
范信賢<br />
2003 尋找一種親近性關係的教育研究:經驗、敘事與探究。發表於質性工<br />
作研究坊:敘事研究與教育實踐。花蓮師範學院多元文化與教育研究<br />
所主辦,未出版。<br />
范 雲<br />
2003 政治轉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台<br />
灣社會學 5:133-194。<br />
夏曼.藍波安<br />
2000 原運再起與省思。原住民 1:7。<br />
孫大川<br />
1991 久久酒一次。台北:張老師文化。<br />
1992 原住民文化歷史與心靈世界的摹寫─試論原住民文學的可能。收錄<br />
於山海世界 (2000):107-137。台北:聯合文學。<br />
1995 夾縫中的族群建構─泛原住民意識與台灣族群問題的互動。收錄於夾<br />
縫中的族群建構。台北:聯合文學。<br />
2003 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台北:印刻。<br />
徐正光、宋文里<br />
1989 台灣新興社會運動。台北:巨流。<br />
時報文化出版<br />
2002 山海子民的心靈謳歌:台灣原住民族女性的奮鬥歷程。台北:台北市<br />
原住民委員會。<br />
高雅雪<br />
2000 族群認同與生命的交織~四位原住民青年族群認同之生命經驗與民<br />
族誌電影。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高德義<br />
1991 與黃昏搏鬥:原住民運動初探。山地文化雙月刊 21。<br />
曹愛蘭<br />
1996 女性與社會運動。刊於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 40:1-3。<br />
梁莉芳<br />
2001 召回我們的力量—一個阿美族部落舞團女性的生命經驗。國立花蓮師<br />
範學院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畢恆達<br />
1998 社會研究的研究者與倫理。刊於危險與秘密:研究倫理。嚴祥鷥主編<br />
台北:三民。<br />
許木柱<br />
1990 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認同運動:心理文化研究途徑的初步探討。刊於台<br />
灣新興社會運動。徐正光、宋文里合編,頁:127-156。台北:巨流。<br />
部落工作隊<br />
2000 原住民族。自 2002.07 起改以電子報發行《原住民族電子報》。網址:<br />
147
http://web.my8d.net/m5a07/ (快取日期:2006.3.20 )<br />
郭苑平<br />
2003 眷村台灣媽媽的自我與認同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br />
文。未出版。<br />
陳秀惠<br />
1985 對山地婦女充當妓女問題的牧養關顧之研究。玉山神學院畢業論文。<br />
未出版。<br />
陳俊明<br />
2002 玉山神學院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神學與反省。玉山神學院神學研究所<br />
道學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畢恆達<br />
1996 找尋空間的女人。台北市:張老師。<br />
游鑑明<br />
2000 台灣地區的婦運。刊於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陳三井主編,頁<br />
403-554。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br />
2002 傾聽她們的聲音─女性口述歷史的方法與口述史料的運用。台北:左<br />
岸文化。<br />
黃心雅<br />
2004 原鄉、土地、身體、記憶 當代原住民女性之遊徙詩學與認同政治—<br />
以安莎杜娃與阿女烏為例。收於性別、流動與主體建構學術研討會論<br />
文集。高雄:高雄縣文化局。<br />
黃美英<br />
1990 台灣文化斷層〈文化評論集〉。台北:稻鄉。<br />
1995 文化的抗爭與儀式。台北:前衛。<br />
葉雅玲<br />
2004 原住民女性身份認同與(被)書寫的面貌—從沙鴦、綢仔絲萊渥到<br />
利格拉樂‧阿女烏。刊於文學新鑰 2:91-105。<br />
葉漢明<br />
1999 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析論。香港:教育圖書。<br />
詹素娟<br />
1997 族群關係中的女性—以平埔族為例。婦女與兩性研究 42:3-7。<br />
路所拉門‧阿勒(胡德夫)<br />
1999 大武山的吶喊。台北:國際特赦雜誌。<br />
2005 匆匆專輯。台北:野火樂集。<br />
劉紹華<br />
1994 去殖民化與主體重建—以原住民三份文化刊物為例,探討歷史再現中<br />
的權力問題。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劉湘吟<br />
1997 原住民的女兒─麗依京‧尤瑪的使命與實踐,新觀念 102:<br />
148
謝世忠<br />
18-29。<br />
1987 認同的污名—台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台北:自立晚報。<br />
2004 族群人類學的宏觀探索—台灣原住民論集。台北:台灣大學。<br />
鍾青柏<br />
1990 台灣先住民社會運動研究—以還我土地運動為個案分析。台大社會學<br />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br />
魏貽君<br />
1996 另一個世界的來臨─原住民運動的理論實踐。國立清華大學社人所碩<br />
士論文。未出版。<br />
麗依京.尤瑪(Lyiking‧Yuma)<br />
1996 傳承─走出控訴。台北:原住民史料研究社。<br />
1997 迷思的傳承。百合台灣(4)。網址:<br />
http://www.taip.org/document/lily/v4t20.htm (網頁快取 2005.11.28 )<br />
2001 原住民女性的社會參與。收於第一屆原住民婦女福利會議文集,頁<br />
104-105。<br />
楊士範<br />
2006 阿美族都市新家園:近五十年的台北縣原住民都市社區打造史研究。<br />
台北:唐山。<br />
顧燕翎、鄭至慧主編<br />
2001 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br />
Afan LEKAL<br />
2005 一堂美麗的課。刊於耕心週刊 480:5。<br />
Bruner, Jerome<br />
2001[1996] 教育的文化‥文化心理學的觀點(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br />
宋文里譯。台北:遠流出版社。<br />
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br />
2003[1993] 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王勇智、鄧明宇譯。台北:五<br />
南。<br />
Hooks, Bell<br />
2001 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曉征、平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br />
社。<br />
Marcus, G. E. and Fischer, M. J.<br />
1998[1986] 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科學的實驗時代。王銘銘、<br />
藍達居譯。北京:三聯。<br />
Rosemarie Tong<br />
1996[1989] 女性主義思潮(Feminist Thought: A comprehensive<br />
introduction)。刁曉華譯。台北:時報文化。<br />
149
White, M. & Epston, D.<br />
2001[1990] 故事、知識、權力-敘事治療的力量。廖世德譯。台北:心<br />
靈工坊。<br />
Wolcott, Harry F.<br />
2001[1990] 質性研究寫作(Writing Up Qualitative Research)。顧瑜君譯。<br />
Bruner, J.<br />
台北:五南。<br />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r />
2000 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n<br />
Francisco:Jossey- Bass Publishers.<br />
Cohen, J<br />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mtemporary<br />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4): 663-716.<br />
Conle, C.<br />
2000 Narrative Inquiry: Research tool and Medium for Professional<br />
Develop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3(1), 49-64.<br />
( http://global.umi.com/pqdweb?Did=000000056880417&Fmt=3&Deli<br />
=1&Mtd=1&Idx=13&Sid=1&RQT=309 Date: 2006.05.20 )<br />
Goodson, I. F. and Sikes, P.<br />
2001 Life History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Learning from Lives.<br />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br />
Labov, W.<br />
1982 Speech Actions and Reactions in Personal Narrative. In Analyzing<br />
Discourse:Text and Talk. D. Tannen, ed. Pp. 219-247. Wsahington, DC:<br />
Gerogetown University Press.<br />
Rosenwald, G. C., & Ochberg, R. L.<br />
1992 Introduction: Life Stories, Culture Politics, and Self-understanding. In<br />
Storied Liv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elf-understanding. G. C.<br />
Rosenwald & R. L. Ochberg , eds. Pp. 1-18. New Haven, CT: Yale<br />
University Press.<br />
Spivak, Gayatri Chadaravoty<br />
1993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br />
Theory. A reader. P. Williams & L.Chrisman, ed. Pp. 392-403. New York:<br />
Harvester Wheat Sheaf.<br />
Tajfel, H.<br />
1972 Experiments in a Vacuum.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Psychology:A<br />
Critical Assessment . J. Israel & H. Tajfel, eds. London: Academic Press.<br />
150
下禮拜記得回來—大同大禮部落的生活回憶<br />
陳永亮<br />
『我愛太平洋,相連到天邊,東台灣廣播電台,107.7,拉近你和我彼此的心......』<br />
收音機的喇叭中傳來了輕快的台呼。<br />
這是八點的台呼,我看了看剛帶起的錶,時針在 8 的位置,長針則停留在 6<br />
的數字上,顯然手上的這隻錶快了幾分鐘。我把右邊的旋鈕拉出,朝逆時針的方<br />
向轉了幾圈,將時針與分針調回”應有”的位置。這樣做完之後,錶面上兩根針所<br />
劃出的形狀突然讓我想起小時候玩的一種叫「小精靈」的遊戲,遊戲的核心是缺<br />
了一角,不完整的圓所表示的精靈,空缺的那部分成了他的嘴巴,張的大大地不<br />
停開閡,沿著看起來像是某個人腦圖案的曲折路徑吃著其上的小點。當中會有類<br />
似守門員角色的侍衛,不斷追殺試圖阻止精靈的工作,他必須注意閃躲,並完成<br />
將所有小點咀嚼乾淨的任務,然後進入另一個更複雜更蜿蜒的圖形路徑,繼續做<br />
著唯一、重複的工作:移動、躲避、蒐集、咀嚼、蒐集。<br />
●<br />
五點,天空已呈現一種將清醒的白,在這個採完箭筍後的七月早晨。<br />
教堂在和它一樣有著歷史性、時間性的光線中出現,彷彿彼此都想把自己的<br />
等待往對方身上疊加般的結合在一起,那個在《追憶似水年華》裡的貢布雷教堂,<br />
大概也是以這樣子的姿態出現在Marcel Proust眼前吧。突兀的高度,石灰水泥堆<br />
砌出的帶點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西式外觀,在僅餘六間 1 木屋與鐵皮屋的大禮部<br />
落中,讓人一眼就發現它與周遭幾戶建築的不同。三十幾年前,就在這片Sachi<br />
父親提供的土地上,居住於此的大禮居民共同出錢、出力,完成了眼前的這座建<br />
築。那時,教會是整個部落的信仰中心,90%以上的大禮居民會在六日的時候來<br />
到這做禮拜,然後在前方的大草原上聊天,舉辦活動。如今,雖然教會和整個部<br />
落已搬遷下去,但他們仍然在週日時—如果時間允許的話—聚集於山下教堂聽牧<br />
師傳道做禮拜,他們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在有任何需要時祈禱,他們是信奉<br />
耶穌的基督教徒--除了正睡在教堂裡的Sachi。<br />
Sachi(47 歲)在這天色已泛白,但太陽還未升起的時刻起來。這時候的天<br />
空看起來似乎不是因為太陽照射的關係而出現,反而比較像是因為我們張開眼<br />
睛,經由眼神發出的光而使得天空得以被看見的好像還比較接近一點。這麼說起<br />
來,是泛白的天色喚醒了 Sachi,還是 Sachi 打開了這樣的天空?<br />
1 實際長時期居住的只剩三戶<br />
151
她從木床上起來。這是屋內僅有的幾樣「家具」之一,一張長約六、七公尺,<br />
寬兩公尺,七、八十公分高,可容納七、八人睡的木床。床看上去有十幾年的歷<br />
史了,由許多木板和木柱組合釘製而成。當鄰居進入屋內串門或老公 Buya(64<br />
歲)農作後,總習慣將手上或背上的物品放在這張床,然後舒服地或坐或臥於其<br />
上,躬著腳聊天休息。因此,說是「床」其實並不太正確,室內除了飯桌和放著<br />
瓦斯爐的“流理台”外,這也是唯一的一張「桌子」,和常被用來坐的「椅子」了。<br />
而在它右邊靠牆壁的地方,擺了 199 大賣場常可看見的附有滾輪的塑膠整理箱,<br />
箱子的作用有點像是抽屜,裡面裝著衣服、衛生紙、牛皮紙袋、一些書面資料、<br />
電池等物品的。床底下因架高而騰出來的立體空間,則擺滿了烤火用的樹枝、搭<br />
建用的木頭、各式各樣的農用工具、除草機、飯鍋蒸籠、玉米飼料以及怕鄰居發<br />
現後,會一下子被喝光而藏起來的米酒。<br />
Sachi 換下棉質 T 恤的睡衣,穿起有著大領子,衣身由紫紅、深褐等暗色條<br />
紋交叉連結,看起來頗為正式的絲質上衣,底下則是修改過褲長,有著彈性的深<br />
黑色針織褲,這是在基隆賣衣服的女兒寄給她的,深色讓 Sachi 不擔心農作勞動<br />
所造成的髒污,領子則讓她覺得自己穿的是正式的衣服,因此女兒總是買給她有<br />
領子的深色衣服。而 Buya 還在這床上繼續睡著,懷裡抱著 Bilaq(原住民語是「小」<br />
的意思),腳下則躺了另一隻叫 Barvi(豬)的狗。<br />
Sachi 拿出床底下裝著玉米粒的桶子,舀了三四盆出來,摻些小雞專用的飼<br />
料,走至屋後面的雞舍。原本在雞棚裡的雞看到她走近,彷彿餓了許久似的紛湧<br />
而出,但在接近 Sachi 時,卻又不是毫無保留的靠近,而是帶著一點謹慎小心、<br />
亦步亦趨似的在旁觀看,直到 Sachi 做出舀玉米的動作時,牠們便群起擁近。玉<br />
米並非整個倒在雞飼料盆中,由於養的雞將近五十隻,Sachi 將手上的玉米分成<br />
好幾堆的錯開,堆疊在一定間隔的地上,才不致讓雞有搶食或擁擠的情況發生。<br />
大部分的時候 Sachi 會留下一些盆中的玉米,然後抓起握在手心中,配合著口中<br />
呼出「咕咕咕咕」的雞聲,灑在附近的土地上,好幾隻雞因此圍在她腳下身旁,<br />
她就這樣站在雞群中,帶著看起來像滿足的微微笑容,注視著底下不斷伸縮著脖<br />
子啄食玉米粒的雞。<br />
●<br />
那是 1961 年, Sachi出生的年代。Sachi是受過日本教育的父親幫她取的名<br />
字,有著濃濃的日本味。父親叫著她時,總會在名字後發出”ko”的尾音,念起來<br />
便成了Sachiko。出生七、八個月的Sachi體弱多病,母親因為農作繁忙,小孩子<br />
眾多 2 無法專心照顧,使得Sachi常常咳嗽發燒。雖然如此,母親為了醫治她的病,<br />
還是常常抱著她抓著一隻雞下山,將雞賣給平地的族人後,有了錢帶她去看醫生。<br />
「我媽媽說,那時候賣雞都是要給我看病」。<br />
但 S achi 仍是時常生病,好幾次送到山下時,因路途 遙遠,病況變的很嚴重,<br />
2 Sachi 共有九個兄弟姊妹,她排行第六<br />
152
甚至 蔓延到肺部。於是,母親將她送至秀林嘉明村一個由外國人開設,補助原住<br />
民看診的醫院。在那她獲得了不同於山上的醫療的照顧,有專門的醫生治療她的<br />
疾病,也有照護人員隨時看顧。一直到病好出院時,已是三歲,一個會講話的年<br />
紀了。那時的她嘴巴呢喃說著的並不是族人的太魯閣語,而是「台灣人」(她這<br />
麼形容)的國語,因為照顧她、和她講話的,是一個用國語說話的台灣人。<br />
出院後的 Sachi 並沒有馬上回到山上的大禮。她在加灣的阿姨見她身體 不<br />
好, 回到山上無法受到照顧,另一方面自己唯一的女兒又在台北工廠作女工,家<br />
中沒有小孩,因此便與 Sachi 的母親談好,要將 Sachi 留在加灣這陪伴她,也讓<br />
她可以在山下看醫生、唸書。<br />
「生我的是媽媽,養我的是 我的阿姨」。這位 Sachi 口中的阿姨,成了影響<br />
她生 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小時候的她得以在山下的景美國小唸書,並且受到較為<br />
完整的醫療照顧,都是因為這位阿姨的堅持。Sachi 很喜歡與阿姨聊天,除了分<br />
享內心的感覺思緒外,更可以從阿姨的口中聽到許多關於道德規範、做人處事的<br />
道理,這些觀念到現在她仍覺得深深的影響著;她的姨丈常常買冰給她吃,當她<br />
生病時,更是騎著那時重重的腳踏車載她去很遠的三光社區看病。這一切的點點<br />
滴滴當 Sachi 回憶起來時,總是格外的感激與感動。<br />
但 Sachi 並非完全與山上斷了聯繫。在國小的寒暑 假期間,她仍是會回到山<br />
上, 幫忙母親洗衣服、掃地、養雞、照顧底下三個弟弟等,直到開學再回到加灣<br />
的阿姨家繼續生活。對她而言,回去山上幫忙是應該的事,這並不會令 Sachi 覺<br />
得難受或辛苦,但她多少也感受到,有種與阿姨比較親,比較想黏著阿姨的感覺,<br />
並不是不喜歡她媽媽,只是單純地「覺得與阿姨有比較多的話可以聊」。<br />
在加灣唸書的生活讓她懷念,有著喜歡聊天的阿姨和疼她的姨丈照顧她 ,也<br />
有一 些與青梅竹馬同學之間的濛濛情愫,但那時在自己的道德觀念中以及阿姨的<br />
勸誡下,她始終認為是不妥的,因此也沒發展過什麼。雖然對 Sachi 而言,這並<br />
不是問題也未曾困擾,但她還是認為自己的家是在稱為「哈魯閣台」的大禮山上。<br />
那裡有她的家人,有十分嚴厲卻又特別親近的父親,有平常可以一起嬉鬧、出事<br />
了會幫她出氣的兄弟姊妹和年齡相仿的鄰居。<br />
「小時候我二哥很喜歡嚇我們,有一次他為了要叫我們睡覺,故意騙我<br />
們說鬼在晚上七點就會出來了,八點就在房子邊繞啊繞的,你看,現在<br />
都在外面了。結果我三個弟弟嚇到晚上都不敢出去尿尿,早上起來三個<br />
都尿床,我媽媽早上發現就說你們三個為什麼不會出去尿尿,現在又是<br />
冬天,棉被要怎麼曬?......我和我哥哥在旁邊都笑死了......」<br />
「我們會和大同那邊的小孩或者這邊比較不好的在樹林裡打架,拿樹<br />
枝、石頭一些有的沒的丟來丟去的,然後到了中午才回家吃飯,我媽媽<br />
看到我們都會罵說你們在幹嘛,是不是又跑去亂玩了,都不會幫忙家裡<br />
ㄋㄟ...」<br />
153
「...五歲時姊姊就嫁出去了,家裡沒有女孩子,只有我和我媽媽,所以<br />
我爸爸特別喜歡我,和我特別有緣...他有心事還是都跟我講,不會去找<br />
他其他兒子講...」<br />
她 喜歡回到山上和哥哥弟弟在一起的感覺,這讓她有一種歸屬感,不再是個<br />
寄人 籬下的小孩;她喜歡和兄弟姊妹以及鄰居在山上玩樂的感覺,這讓她覺得很<br />
愉快。現在,這些她口中的兒時玩伴大都住在山下的太魯閣閣口附近,他們偶爾<br />
也會上山來整理在大禮的土地。<br />
Sachi 讀完國小後,母親原本 是要希望她繼續念,可以成為那時在部落裡公<br />
認是 高收入且地位頗高的職業-護士,但父親認為女孩子終究是要嫁出去,念那<br />
麼多書沒什麼用,且考量當時家庭經濟情況並不好,無法供應 Sachi 繼續唸書,<br />
便讓她回到山上家裡幫忙。<br />
回到大禮不到兩個月的時 間,父親從教會牧師得知,台北教友需要一個可以<br />
照顧 嬰兒、整理家庭環境的原住民小孩。母親哭著不希望這身旁僅剩的 13 歲女<br />
兒要離她這麼遠,但在父親的堅持和牧師的安排下,剛回到山上的 Sachi,再次<br />
離開還來不及好好熟悉的「家」,在對方「老闆娘」的親自陪伴下,從花蓮到台<br />
北,開始了兩年多保母和女傭的生活。<br />
「那時候大概 13.14 歲了,我自己都是小孩還要看小孩ㄟ......我媽那時<br />
不肯讓我去,她就哭啊,說我一個女兒離我這麼遠,但是我爸爸還是要<br />
讓我去台北工作......妳知道嗎?我從花蓮坐國光號時還經過秀林這條<br />
路,車子停站在太魯閣那邊,我看到這些山,想到我爸爸媽媽,我整個<br />
人都哭了......要不是我的老闆娘坐在旁邊,我差點要衝下去呀......」<br />
她 始終記得那一幕的場景。<br />
●<br />
眼前的這些雞是一個半月前Sachi從山下買上來的半土雞,所謂的半土雞是<br />
混了 外來洋雞的血緣,比起純土雞,會長的較為大隻,可食用的肉也更多點的仿<br />
土雞。這些雞除了偶爾供自己食用外,絕大部分是要賣給山下的其他族人。當社<br />
區中的人逢聖誕節、收穫節或過年時,亦或是結婚、喪事或偶爾想吃,總是會跟<br />
他們購買。雞不只是他們山上的肉食來源,更是主要的經濟收入。初期拜訪的幾<br />
次經驗裡,遼闊的玉米田景象總讓我印象深刻,這裡的土地種植著大片的玉米<br />
田,但沒有一根是要拿到山下販售的,玉米收成後被晾在屋簷下、帆布上或屋頂,<br />
曬著太陽好幾天,待呈現一種金黃脫水的乾燥後,用手或起子將玉米粒剝下,視<br />
情況決定是否搗碎供給幼雞或直接讓成熟的雞食用。在大禮大同這不到十戶長期<br />
154
留在山上的住戶中,雞是每一戶人家都會養的家禽。當他們在山上有了自己的土<br />
地和房子後,下一步往往便是開始計畫種植玉米來養雞 3 。<br />
再過兩個月左右這些雞便成熟至可以吃的大小,足以供應上山遊客以及入冬<br />
後山 下對雞增加的需求了。Sachi 計畫下個月要再買五十隻的幼雞、火雞、鴨等,<br />
以應付聖誕節這個對山下信奉基督教的族人而言,極為重要也必須殺雞慶祝的日<br />
子。「再過幾個月,我就有雞可以賣給山下了。」她驕傲的說。<br />
Sachi 認為養雞要分批養,不能只養一批,就像種高麗菜一樣 ,一大片土地<br />
要分 開分期種,這樣才不會全部擠在一起:一來怕菜收不完會爛掉,二來又怕採<br />
完一批,等下一批要好幾個月,如此期間的空檔將沒有東西可賣。因此她計畫一<br />
批一批的養,這樣什麼時候都能有大雞可以賣給需要的人了。<br />
要不是幾年前為了就讀高職的兒子需要學費和零用錢,Sachi<br />
其實不需要在<br />
現在 還計畫著這些,她早可以像這的其他幾戶一樣養雞養了好幾十年而有數量豐<br />
富且不同時期成熟的雞,她早可以像其他幾戶人家一樣,有了自己在山上的固定<br />
房子和土地。但那時她為了供應孩子的花費,將山上的雞全部賣掉,原本計畫要<br />
開墾定居的立霧山土地也暫時擱置,與老公下山去作臨時工,蓋墳墓、除路邊草、<br />
作泥水工等。直到一年多後,他們覺得蓋墳墓的錢不吉利且孩子休學當起修車學<br />
徒後,便又回至山上繼續整理、開墾土地。等到玉米收成,有了飼料來源,繼續<br />
這樣養雞種菜的生活。<br />
Buya 從床上醒來,手中抱著的狗 —Bilaq 也跳了下來,和另一隻早已起床的<br />
Barvi<br />
在外面用他們的頭和耳朵一邊嘶磨一邊追逐。牠們是 Buya 夫妻倆養了好幾<br />
年的寶貝—巧克力—和野狗所生,巧克力一共生過十幾隻小狗,Sachi 都將牠們<br />
分送給其他人,獨留下這兩隻看起來特別有緣的 Bilaq 和 Barvi。今年二月在一<br />
場平靜的睡夢中,或許是年紀到了,巧克力安詳的死亡。他們在屋外的邊坡上挖<br />
了巧克力體型大小的坑將牠放入,兩側抹上水泥,覆上土後用水泥在上面立起一<br />
塊長橢圓型的石頭,石頭前方放了一個印有巧克力和一群年輕女性合照的馬克<br />
杯,這是照片裡那群每年會上來拜訪 Sachi 的朋友所送的。順著埋葬巧克力的方<br />
向再過去約三百公尺林木圍繞中的低陷草叢,則是以往埋葬老人家們的地方,她<br />
曾在山上某個夜晚見到的已逝去奶奶也葬在那。巧克力死後的那段期間,Sachi<br />
整整哭了三天三夜,而 Buya 則是生了一場就他們形容莫名所以的病,這場病持<br />
續了一個禮拜才漸漸康復。如今巧克力的兩個小孩受到相同的喜愛,無法生育的<br />
Buya 甚至將牠們當成自己的小孩,總喜歡將牠們抱在懷裡,嘴巴喃喃自語地說<br />
著:「乖乖喔,爸爸愛你,嗯,Bilaq(Barvi)」。<br />
蓋這樣的墳墓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不過是幾 年前他們在山下靠著蓋墳墓賺<br />
了不 少錢,然而這錢「像水一樣會溜出去」,雖然賺了許多,但那時 Buya 常常<br />
生病,小孩子也出了些事,錢就這樣不知不覺,無法掌握的花在許多莫名其妙的<br />
3 Sachi 的四哥之前在山下從事勞動性職業,後來因病開刀以及經濟不景氣,他失業回到山上。<br />
由於酗酒、抽煙以及賭博,使得家計更加困難,最後老婆離婚,兩個女兒和前妻離開他自立生活。<br />
他回到山上,住在已過世的二哥竹屋內,整理後方土地準備種玉米。預計之後採收玉米飼料有著<br />
落後,開始蓋雞舍養雞。<br />
155
用處去了。如今秀林鄉的公墓中,仍有許多他們所蓋的上方有著十字架的基督教<br />
式墳墓,這十字架在巧克力的墓上,並沒有出現。<br />
Buya 將棉被摺好,放在靠牆壁的位置後,下了床穿上過於寬鬆,使得必須<br />
繫上 紅色塑膠繩,但繫緊後褲頭卻又形成好幾個皺摺的咖啡色休閒褲。無數次的<br />
勞動所積累出的污痕與傷口在這褲子與白色麻質內衣上歷歷可見。他喝了口水,<br />
走到雞舍旁抓了隻雞像在跟人說話似的手掌夾著雞的兩頰喃喃自語。Sachi 叫他<br />
不要這樣,告訴他去把屋內已脫粒但還未曬乾的玉米拿出來曬。Buya 悻悻然地<br />
走進屋內,將折起來的藍白條紋帆布拖至戶外,打開後用耙子一耙一耙地將玉米<br />
粒攤平,使得每粒都能受到陽光的照射。這樣做的同時,他還得不時地驅趕那些<br />
走近啄食的雞。<br />
我被一陣竹支 摩擦地面的聲音給吸引,此時Sachi已拿著竹支做成的掃把在<br />
室內 的水泥地上掃地。上個禮拜她才將室內的地板整個洗刷過,因為當小雞剛運<br />
上來而雞舍尚未完成時,他們將 50 幾隻的小雞放在屋內一起生活了好幾天<br />
還算乾淨,沒有多少灰塵,只殘留一些昨晚鞋底下的<br />
泥土<br />
4 。直<br />
到雞群們稍微長大,而雞舍也略具雛形後,才將牠們移至戶外,並打掃雞群們所<br />
留下來的排泄物與氣味。<br />
早晨的水泥地看起來也<br />
、玉米脫粒的碎屑和晚餐後狗所啃過的骨頭碎片。但是這已經夠讓 Sachi 有<br />
拿起掃把的理由了。每早起來,她總是會花上好幾十分鐘將地上的「垃圾」掃至<br />
室外,然後繼續到戶外已被踩踏數十年而緊實平坦的泥土地上,同樣用一種緩慢<br />
且固定的速度,以不超過兩種方向的揮動角度,將雞屎、枯葉等掃至邊坡上。那<br />
「唰...唰...唰」的聲音雖然刺耳,但因為節奏和緩且規律的關係,聽久了反而讓<br />
我有一種心情安定的感覺。<br />
●<br />
那 是戶有錢的人家。老闆娘的父親開一間貿易公司,而老闆本身則是開鞋<br />
廠, 民國六十年代初期,這戶人家就有兩部轎車,對 Sachi 來說足夠稱的上是很<br />
有錢的人家了。他們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離中國電視公司很近的地方,因為每<br />
次接小孩時,Sachi 總會看到那個很大的電視招牌。<br />
在台北工作的日子裡,Sachi 其實有著像加灣一樣 ,還算愉快的回憶。她負<br />
責照 顧三個小男孩中最小的一個,是個還不會走路的小嬰兒,而另外兩個小孩(最<br />
大的國小二年級)或許是年齡相近的關係,也很喜歡和她玩在一起。有時候她需<br />
要幫愛吃宵夜的老闆出門買食物,但老闆娘對她很好,總是會罵她先生說「你自<br />
己不會下去買啊!你一直叫她出去,她是一個女孩子晚上出去萬一被人家怎麼<br />
樣,你敢負責嗎?你會還給人家一個女兒嗎?」他們甚至為了這樣的事吵架,而<br />
之後老闆便不曾叫 Sachi 去買東西了。<br />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原因,Sachi 到現 在總是特別害怕夜晚出門,那讓她感<br />
4 颱風天時,他們也將所有的雞都抓入屋內,整整待了兩天。<br />
156
覺自 己隨時都會有被人侵犯的可能。晚上她絕不一個人騎車出門,一旦整個家裡<br />
或部落只剩她一人時,突然的敲門聲也總讓她胡思亂想,害怕該不該開門。<br />
沒有生女兒的老闆娘將Sachi看做自己的女兒般疼愛,甚至告訴Sachi直接 稱<br />
呼「 媽媽」就好了,但Sachi覺得自己的媽媽在大禮,就算是生命中極為重要的<br />
阿姨,她也始終依照著部落的稱謂習慣 5 ,直接稱呼阿姨的名字,而不曾叫過她<br />
「vuvu」(母親),因此Sachi始終沒有這樣對老闆娘開口過。儘管如此,老闆娘<br />
還是會帶Sachi去百貨公司買衣服,但Sachi一進去看見穿衣服的人體模特兒,卻<br />
誤認為是真人而嚇了一跳;她會帶Sachi去自己妹妹家學鋼琴,但Sachi始終學不<br />
會,也彈不好;她會幫Sachi塗指甲油,但是一旦塗抹好,Sachi便會趕緊將它洗<br />
掉,因為部落裡的老人家說過:「會擦指甲油的女人是妓女、是風塵女!」<br />
一年多的時光匆匆流過。Sachi 與「台灣人」似乎特別有緣,小時候生病被<br />
台灣 人照顧,畢業後卻換她到台灣人家裡照顧對方的小孩,「好像我生命中跟台<br />
灣人是有緣住在一起的」。但正當 Sachi 逐漸適應台北的工作與生活時,鄉公所<br />
辦理身份證的通知讓她又回到了花蓮。<br />
回到山上的心情就像之前一樣,並沒 有任何不開心或複雜的感受,彷彿只是<br />
扮演 好自己的角色,盡該盡的義務來來去去。就算經過台北生活的洗禮,她也從<br />
不認為自己與部落裡的其他族人有何不同。她依舊在家裡幫忙,做著和台北一<br />
樣,屬於女人應該作的「家裡」的事情:洗衣服、帶小孩、掃地、煮飯......等,<br />
而哥哥們則負責與父母到一個小時路程外的立霧山去開墾。然而族人畢竟感受到<br />
她的不同,「唉啊!你回來啦,你怎麼變那麼白...」「你怎麼變漂亮了...」「你的衣<br />
服怎麼那麼美麗...」等話語在那段時期總是不斷出現在一些玩伴和長輩的口中,<br />
這並非是嘲笑或排擠,他們真的覺得 Sachi 已經是個漂亮的女孩子了,而這也是<br />
她前夫喜歡上她的原因。<br />
部落從以往到現在一直 沒有電力到達,到了夜晚常常都是點起自製的柴油燈<br />
方能 照明。當男生和女生於夜晚一起坐在床上,甚至只是單獨的處在屋內時,對<br />
於部落裡的老人家而言,就代表男女已經發生關係,而這是很嚴重也是老人家很<br />
忌諱的事。<br />
前夫是他 三哥的好朋友,那時為了接近 Sachi,便常常到家裡來找他三哥和<br />
Sachi<br />
聊天。不久後,鄰居間便有了耳語,認為他們之間有曖昧的情愫。那時住<br />
附近的姨丈—許通成向正在立霧山開墾的 Sachi 父親說,他常常看見 Sachi 和那<br />
時大他五歲的前夫晚上在屋內共處,認為他們之間已經發生關係。父親聽到這事<br />
後,隔天拿著木棒回到大禮,沒有講任何一句話地便朝不知情的 Sachi 打去。<br />
「這麼大的木頭啊!要不是我媽媽抓住爸爸,跪著求他,我的腳早就被這樣<br />
打下 去了...」。一頭霧水的 Sachi,根本不知道父親為何如此的大發雷霆。父親是<br />
個很嚴肅的人,很少講話,一旦講話或罵人,都是很嚴重或重要的事,如今這舉<br />
動顯然讓 Sachi 瞭解自己已犯下了天大的過錯,但她仍不知道到底錯在哪裡。<br />
「妳要結婚了,妳知道嗎?」「咦!我要結婚?我要跟誰結婚?」Sachi 的四<br />
5 太魯閣的傳統習慣除了父母和爺爺奶奶外,其餘的親戚多是直接稱呼名字。<br />
157
嫂告 訴她這件事後,她終於明白自己的處境。但她完全不能接受,因為身為小孩<br />
子的她根本沒做過那些事,也不懂那時的禁忌。她跑去和即將結婚的丈夫理論,<br />
澄清她根本沒和他發生關係,為何亂講話。她甚至拿石頭丟他,一直到前夫流血<br />
被三哥喝制,她茫然無措的呆立在現場,任情緒與委屈化作眼淚流淌而出。「我<br />
們要結婚了喔,妳就不要一直哭一直哭啊...」但事情還能怎樣發展呢?儘管父親<br />
不捨 Sachi 這麼早結婚,儘管 Sachi 那時未達法定結婚年齡,但身為部落的一份<br />
子,父親遵守規範準備殺豬事宜,而母親也通知各方親戚他們要結婚殺豬的事了。<br />
「我就這樣嫁給他了...」Sachi 為這段回憶下了註腳。那是 1975 年,Sachi15<br />
歲。<br />
●<br />
Sachi<br />
簡單的炒了在邊坡上採的紅菜,並加熱昨晚所熬煮的一鍋混著豬肉、<br />
竹筍 和雞蛋的滷味。豬肉是昨天 Buya 帶上來的,由於沒有冰箱的緣故,帶上來<br />
的肉第一天都會先煮熟過以便能久放。他們所買上來的肉以豬和魚為主,大部分<br />
的時候用滷或水煮抹鹽的方式吃上好幾天。有時因為個人食慾或某些緣故必須晚<br />
幾天才會吃肉時,便會將肉以塑膠袋包起來,放在不斷流著低溫山泉水的浴盆中<br />
保存。<br />
餐桌 突兀的是張比木床還低,比和室桌略高的方桌。椅子則是烤肉或演講會<br />
場常 見的那種靠背和扶手一體成型,可堆疊起來收放的塑膠椅。低矮的桌椅所要<br />
求的坐姿與他們在屋外烤火喝酒時的高度相同,除了 Sachi 外,旁邊幾戶人家,<br />
甚至是他們所搭建的涼亭下竹製的桌椅,都以這樣的高度出現。<br />
桌上放著早上炒好的兩盤菜,和昨晚燒了一半蠟燭的木製燭台 。Sachi 拿出<br />
維士 比倒入杯子裡,她總在早餐時喝上幾杯,剩下的便在上午農作時的空檔喝<br />
光。「這樣工作才會有力量」她說。Buya 在旁邊慢慢喝著從保特瓶倒出的透明液<br />
體,幾乎沒說什麼話,也沒有拿起筷子夾菜。「你怎麼都不吃飯呢?」「這也是米<br />
啊,我也有吃飯啊。」他還算清醒的回答。Sachi 對 Buya 有點交代似的討論今天<br />
要做的工作,並叫他不要再喝了,而 Buya 沒多說什麼,好像在向 Sachi 確定一<br />
樣的重複了幾句工作內容後,蓋子蓋上,喝完杯中所剩的酒。<br />
吃完飯,Sachi 將滷汁倒入吃剩的稀飯中,夾幾塊豬肉進去 攪了攪倒在餵狗<br />
的盆 子。Bilaq 和 Barvi 從飯桌旁跑了過去,爭相搶食著,散落在外的飯粒則成<br />
了雞的點心。她將碗筷盤子等收至家中唯一一條流著山泉水水管的浴盆中,就像<br />
這邊其他的幾戶一樣,他們自己尋找水源而非與他人共用同一個水源,水源是幾<br />
年前回到山上所接的,或許位置並不是太好,以致於水流不若其他幾戶來的充<br />
沛。幾隻雞在浴盆旁低著頭尋找這慣常出現的米粒菜渣。<br />
Sachi 請我從整理箱旁拿出收音機,一種放入乾電池後 便不需插電,可以聽<br />
CD、 錄音帶、廣播的手提式音響。由於 Buya 亂操作的關係,如今只剩下廣播可<br />
聽,不過這也足夠滿足她的需求了。廣播中主持人正透過訪問,請來賓介紹花蓮<br />
158
當地的私房密境,我聽了一陣子,心裡暗自竊喜身處的地方並未被提及。不久主<br />
持人播放孫淑媚的這首「空思戀」,Sachi 跟著哼了起來。<br />
風在吹 吹在我的心肝底 想起伊對阮的一切 你講過的話 親像風在飛<br />
經過了後 找別個<br />
雨 在落 落在我的心肝底 親像一蕊窗外的花 誰人照顧阮 可憐玫瑰花<br />
雨落風吹 我是沒人的<br />
你 傷我傷甲這呢重 我等你等甲目眶紅 對你的關懷最後當作一場夢<br />
是我一直做暝夢 我會感動你來疼痛 對你全部付出攏是沒採工<br />
你傷我傷甲這麼重 我等你等甲目眶紅 這款的等待起起落落嘸願 放<br />
是我一直做暝夢 想欲收回已經無望 只有一個人 惦惦空思戀<br />
「 啊!你傷我這麼重.....有夢......無望......」她哼著唱,表情已不像早起時的<br />
輕鬆 。<br />
Sachi<br />
將放在旁邊的水桶提來,拿出浸在泡沫水裡面的衣服,在同一個浴盆<br />
和水 流中,繼續洗著這幾天來的衣服,昨晚和早上的碗盤鍋瓢則已洗淨放到室內<br />
水泥做的講台上。做著這些事的同時,廣播中繼續介紹旅遊景點,也播放了蔡小<br />
虎的「夢中的探戈」、李翊君「負心的人」、江蕙「紅線」...等歌。除了幾首最新<br />
的流行國語歌曲外,Sachi 都能跟的上廣播中播放的國台語老歌哼上好幾句。<br />
Buya 走到教會後面的新雞舍旁,繼續做著這幾天仍未完成的雞舍圍網工<br />
程。 若不將這些雞圍起來,Sachi 這幾天剛種下去的菜和玉米都將被他們給翻出<br />
咬壞了。不過由於圍起來的地有一分多的面積,而 Sachi 的預算又不夠買足夠用<br />
的圍網(一捆六百,她已買了三捆,還差兩捆),因此雞舍的一面仍有著廣大的<br />
缺口,雞群們也就這樣四處亂晃。<br />
●<br />
「從我嫁給我前夫開始就苦了」,Sachi 這樣回憶自己的婚姻生活。<br />
就在教堂上方 30 公尺處如今種著高麗菜的平台,是她 30 幾年前的 夫家所<br />
在。 那時為了迎娶 Sachi,他們付出一定的聘金,殺豬、請客、送禮(豬肉)等,<br />
Sachi 的婆婆四處向別人借錢來應付這場婚禮。婚禮圓滿結束了,但 Sachi 的夫<br />
家卻因此而背負了債務。此時還沒嫁出去的小姑因為感受到家裡經濟情況的不<br />
好,認為一切都是嫁來的 Sachi 所引發,因此對 Sachi 有著深深的怨恨。她不斷<br />
在母親—也就是 Sachi 的婆婆耳邊言語,說 Sachi 為家裡帶來了厄運,使得原本<br />
便對大媳婦較為偏心的婆婆更是對 Sachi 有著不好的印象。而 Sachi 的丈夫在婚<br />
後一年多,大女兒才四個月大時,入伍兩年當兵去了。Sachi 必須獨自照顧女兒,<br />
159
與婆婆一起工作,去山上背著木材、竹子等。「而她的大媳婦就指甲那麼長的在<br />
家裡」她說。<br />
丈夫當兵的兩年,Sachi 形容自己的生活像是被虐待一樣。但是從小看到村<br />
子裡 一些婦女的情況以及聽長輩聊天談論,使得她知道,嫁出去的女兒不應該再<br />
回到娘家來逃避或要求幫忙,這會使得村子裡的人到處議論紛紛,也讓父母面臨<br />
尶尬的處境。因此從小 Sachi 便有一種個性,不論在外遭受什麼困難或打擊,她<br />
也不會回家向父母訴苦。<br />
但父母親還是知道了Sachi的處境,原因不出意外的依舊是鄰居的閒聊。疼<br />
她的 父親帶著氣憤的心情來到親家理論,由於丈夫還未退伍的關係,Sachi的父<br />
親找到了婆婆,向她質問:「我的女兒從嫁來妳家,受什麼委屈、從來不會下來 6<br />
跟我們訴苦,但是聽人家這樣子講,你為什麼要這樣虐待她?她雖然年紀小但是<br />
她很懂事,今天不是你兒子當兵她不守規矩,每天跟你一起出去工作的也是只有<br />
她一個而已,我們不是沒有眼睛看,沒有關係,如果妳不要我這個女兒,孫女留<br />
給你們女兒我帶走,當初你在我女兒身上花多少錢,我就一毛也不會給你少的退<br />
給你,我今天要把我的女兒帶走......」。<br />
父親不可抑制的說著,Sachi 的公公 出面勸他不要那麼生氣,但身為 Sachi<br />
的父 親還能怎麼樣呢?「我不是生氣,我的女兒那麼小就嫁到你們家,我很心疼,<br />
很不甘心呀......」Sachi 重複著她父親當時說的這句話。<br />
經歷過這次事件以及丈夫退伍返家後,Sachi 的生活 暫時得以恢復正常,她<br />
的丈 夫代替了父親,成了那個會保護她的人,這其間他們陸陸續續生了四個孩子<br />
中的三個。但套句 Sachi 說的:「天有不測風雲,月有陰晴圓缺」,幾年後,因為<br />
學校廢校的教育問題、政府興建房子輔導他們遷移至山下的民樂社區,Sachi 的<br />
命運也在此時有了決定性的改變。<br />
搬下山的Sachi依舊和公公婆婆住 在一起。如同那時搬遷下來的許多人家一<br />
樣, 兒子與父母在同一塊土地上蓋了兩棟彼此獨立卻又相鄰的房子,有著同一個<br />
庭院,以及共用一個門牌 7 。對Sachi而言,或許是之前在加灣生活和台北工作的<br />
經驗,另一方面也因為她仍舊可以跟生命中最重要角色的丈夫、小孩一起生活,<br />
離開山上搬遷至民樂社區並沒有多大的不捨與難過。她在天祥招待所 8 找了份服<br />
務生及清潔員的工作,那是她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刻,有相處融洽的同事和長官,<br />
不管有什麼煩惱,到了招待所她總可以忘記一切,帶給同事和客人歡樂;而她也<br />
利用休假時的空檔,至崇德的海鮮店做著同樣的工作貼補家用。除此之外,不同<br />
於部落中「今日事今日畢」「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族人,Sachi有濃厚的儲蓄保險<br />
概念。她將夫妻所賺的錢分別以對方的名字存入郵局定存、互助社 9 等,也幫小<br />
6<br />
指位於大禮教堂下方 30 公尺處的老家,在 1980 年遷村後因年久失修而今只剩水泥地基。<br />
7<br />
Machi、Yaya 在民樂社區的房子也是如此,在主體建築外加蓋一相鄰的房子,然後自己住到 旁<br />
邊加蓋的屋子,主要的建築則由兒子居住。<br />
8<br />
招待所於 1994 年拆除重建,如今為天祥晶華 酒店。<br />
9<br />
互助社是那種只能存入不能提領的設計,若需用錢則是以借貸 的方式向互助社借錢,如此的規<br />
劃是希望對部落居民強迫儲蓄並減少花費。<br />
160
兒子(前三個是女兒)從出生起便存放保險教育基金。看著小孩子在自己的照養<br />
下長大,她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對Sachi而言,這已是最大的幸福了。她是<br />
個稱職的老婆、媽媽、媳婦和服務生,而老公承包小型營建工程的順利與成就,<br />
也讓她與有榮焉。<br />
「葉太太啊,為什麼每次你老公過來提前領薪水的時候,你不過來一起提<br />
呢?」工程公司的會計問到。<br />
「你就是這樣太照顧家裡,太照顧小孩子了,你的時間都花在家裡,你老公<br />
在外面幹什麼你都不知道!」母親曾這樣提醒她。<br />
「那不是你老公嗎?他怎麼喝醉酒被一個女孩子載走了?」目睹的海鮮店老<br />
闆娘這樣跟她說。<br />
Sachi 的丈夫比起其他族人,有著頭腦清楚、反應快的特質,懂得如何與外<br />
面的人打交道,他結交了許多營造廠的老闆,並承包了大大小小的工程。然後,<br />
丈夫瞞著她在外與女子發生婚外情,公司會計的暗示、親朋好友的耳語,甚至當<br />
對方都已登堂入室向她拉保險時,三年多的時間 Sachi 渾然不知。如今回想起來,<br />
暗示的話語只能徒增 Sachi 的無奈與哀嘆,因為她始終不相信這樣的事會發生在<br />
自己身上,她沒有做錯任何事,對不起任何人,她不相信自己會遭受到這樣的對<br />
待。<br />
Sachi 一如往常地在天祥招待所開心地與同事工作,並且領取了好幾個月的<br />
年終獎金及過年津貼。她開心地打給婆婆,約好會搭哪一班客運從天祥下來,請<br />
婆婆在公車站搭上同一班車,並一起至花蓮市區看醫生、幫婆婆買藥、買衣服等。<br />
出門的婆婆撞見了自己的兒子與其他女人正在發生的事,她生氣、難過,但並沒<br />
有直接拆穿兒子或怒斥這樣的行為,婆婆甚至在想,該不該告訴 Sachi 這樣的事?<br />
坐上車的婆婆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難過的流著眼淚。<br />
「你幹嘛哭,你眼睛不好嗎?」<br />
「你生病嗎?今天是我生病ㄟ,你是太高興我幫你買衣服嗎?」<br />
Sachi 一頭霧水,一直安慰婆婆不要哭,甚至還跟婆婆開玩笑,但婆婆依舊<br />
不說,只是淡淡的陪 Sachi 走完市區的行程,然後在回程的車上眼淚直流。<br />
那時 Sachi 正好放假三天,她有一個習慣,會在放假的那天,把家裡整理過<br />
一遍,用的很乾淨,然後將門反鎖,鞋子收進室內讓人以為她不在家,便可在家<br />
裡好好地休息一整天。隔天一早,當丈夫一晚徹夜未歸,而 Sachi 獨自在屋內睡<br />
覺時,婆婆走了進來,把 Sachi 搖醒,決定告訴她這件事。<br />
「媳婦啊,有一件事要跟妳講,請妳不要嚇一跳...」<br />
「什麼事?」<br />
「是這樣……」<br />
「什麼?你再說一次!」<br />
161
婆婆重新再說了一次。<br />
「怎麼會這樣?」Sachi 楞在那,不知發呆了多久,然後哭了出來。<br />
「我沒有出去哭,就在屋內哭,哭很久,婆婆抱著我叫我不要哭,但是<br />
我還是一直哭,抱著棉被一直哭……」<br />
●<br />
將 衣架套進衣服,Sachi 把洗好的衣褲晾在用竹子搭起的曬衣竿上,進到屋<br />
內整 理環境,做著她口中最喜歡做的工作-家事。<br />
室內其實還算乾淨。地在早上已經打掃過了,但 一些雞仍舊從門縫、窗戶等<br />
跑進 屋內而使得地上多了一些雞屎和風吹進來的枯葉等,因此 Sachi 拿起掃把再<br />
掃一次。<br />
她從屋 內最深處的水泥台階開始打掃起。這高起來的台階曾是教堂的講台,<br />
牧師 在這堆砌出的高度上,向底下坐著的信徒傳道。如今木製的講桌和長板凳早<br />
已不見蹤影,信徒們和牧師搬遷至民樂社區,屋內只剩這講台和另一面水泥牆壁<br />
上掛著的「IN MEMORY OF MRS. BARNES」<br />
圓孔的石膏板拼裝而成,在當<br />
時應<br />
10 木牌讓人嗅出宗教曾存在過的痕<br />
跡。台階的上方靠近天花板的地方,一根孟宗竹橫梗在兩邊的窗戶上,掛著Buya<br />
已清洗並晾乾過的衣服,下雨時,這五公尺長的竹子也成為室內的曬衣竿。台階<br />
的左側堆放了預備用的瓦斯筒、鍋具、碗筷、醬油、香油等廚房用品和調味料,<br />
另一側的地上則風乾散落著即將要下種的蕗蕎。<br />
屋頂的天花板是一片片類似隔音牆,有著細小<br />
該是頗為先進的材質。天花板的兩側與地面呈水平,中間部分則彷彿被上面<br />
尖聳的屋頂拉起一般,朝天空突起。幾片板子因為滲水的關係,已經老化腐蝕並<br />
有著從淺黃到深褐色的水漬。在教堂兩側的門邊,一側是單口快速爐的活動流理<br />
台,這是 Sachi 清掃的重點,因為底下總是容易散佈著炒菜時的碎屑;另一邊則<br />
擺著一個 42 加侖的大鐵桶,上面除了一些香菇、麵條、麵輪等乾貨外,還有一<br />
個雜貨店常見裝糖果的塑膠盒,裡面是女兒知道 Sachi 腸胃不好,買給她的有助<br />
消化、排毒的酵素粉。整個室內的“大型家具”,除了這兩樣外,就剩之前所提的<br />
低矮飯桌和異常寬大的木「床」了。由於室內物品簡單的可憐(除了木床底下擺<br />
滿的各式農用工具和飼料),因此 Sachi 打掃起來並不費力。她熟練地將細小瑣<br />
碎的“垃圾”往大門掃去,把早餐坐的椅子堆疊起來,然後跳上床擦拭雞所留下的<br />
腳印,並將枕頭和棉被重新折疊整理好。做著這些事的同時,她仍跟著木床上收<br />
音機所播出的國台語音樂哼唱。她喜歡這樣做家事聽音樂的感覺,這讓她覺得好<br />
像可以忘記些什麼,同時間卻又想起些什麼。<br />
10<br />
木牌中的 Mrs. Barnes,據 Sachi 說並非是來這傳教佈道過的牧師,而是當初其他教會的牧師到<br />
教堂參訪時,送給教會掛上去的。<br />
162
「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電台宣導著行車安全。<br />
「在山上可以盡量喝,因為山上沒有車不會車禍。」Sachi<br />
說。<br />
屋 內看得出歷史的水泥牆壁上,除了無數深淺不一的污痕外,竟有著 4 個當<br />
時建 造時便已嵌入的電源插座和開關,在這沒有電力到達的地方,顯的格外突<br />
兀。原來當初建造教堂時,居民曾預期會有電力通達的一天,於是做了這樣的插<br />
座。誰知道日後電沒有來,而部落的人卻下去了。<br />
Sachi不習慣太亮的夜晚,只有幾次會接上發電 機讓上方垂掛著的日光燈發<br />
出難 得的亮光,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當兒時玩伴—美麗和夏蘭 11 上來整理土地時,<br />
他們會開燈打上幾圈麻將。<br />
他們打的是 16 張麻將,固定的牌友除了 Sachi、Buya以及長時間待在山上的<br />
Sachi表弟-Hogan<br />
12 (32 歲)外,就是這些偶爾上山的朋友了。勝負的判決一樣<br />
是胡牌或自摸,但他們不以金錢當作籌碼,因此花色和台數很少也沒有必要去<br />
算,遊戲的目的只是必須有一個贏家出現,然後其他三家都是輸家,必須眼睜睜<br />
看著贏家獨享戰利品──一杯酒。大部分的酒是由「招賭」的人所提供,有時是<br />
啤酒,有時是高梁,更多的時候是山上常見的米酒,完全視當時有什麼而決定。<br />
若是自摸的話,酒則會比單純的胡牌再多一些。有時他們會玩著沒有戰利品的麻<br />
將,不過總是顯的意興闌珊,而過程中如果酒已經喝完,遊戲也會在接下來的幾<br />
輪草草結束。Buya玩牌時顯的特別專注,不多話,和總是唱著暗示性歌曲 13 的Sachi<br />
呈現明顯的不同,而結果常常是Buya或Hogan喝了最多的酒。不過Sachi並不以為<br />
意,她還是喜歡大家一起打麻將的感覺。<br />
Sachi 把收音機關掉,在床上躺了一會後,走出去 看看 Buya 的工作情況。她<br />
總是 不放心 Buya 的工作內容,因為 Buya 常常一股腦地悶頭去做,沒有像 Sachi<br />
想到材料充足與否、事後的使用方式、細部規劃等,因此每當 Buya 工作時,Sachi<br />
總是得不定時的查看,深怕那個地方弄錯了,就會使工作的成果與她的計畫有著<br />
極大的落差。此時 Sachi 發現 Buya 把支撐圍網用的鋼筋立在錯誤的位置,不僅<br />
使得已不夠的圍網更加捉襟見肘,也讓規劃中的菜田被劃分進去。因此 Sachi 重<br />
新跟他解釋了一番,並向 Buya 說明她要的雞舍門位置和開關方式。Buya 沒說什<br />
麼,悻悻然的拔起鋼筋照著 Sachi 的意思修改。<br />
看著 Buya 重新立了幾根鋼筋後,Sachi 轉身進 入屋內,戴起斗笠並用棉布熟<br />
練的 包起兩頰後頸,套上防曬用的工作衣袖,將蕗蕎放入自製的塑膠簍子裡繫在<br />
腰間,往灑藥除草過的邊坡走去。<br />
「她好忙喔,這麼勤勞,做這麼 多事,都是因為你來要表演給你看的。」<br />
11 夏蘭是 Sachi 以往在大禮的鄰居,在山上有一塊土地,偶爾會上來除草整理;美麗則是夏蘭的<br />
弟妹,銅門人,偶爾也會與丈夫(夏蘭的弟弟)上來整理已辦休耕的土地。上山時他們都住在教<br />
堂上方的老家,午餐和晚餐會帶著幾盤炒好的菜或飯到 Sachi 這一起食用。<br />
12 曾是職業軍人,後來不習慣軍中勾心鬥角和上級壓榨下級的生活,以及職場和社區的環境,<br />
而待在山上。主要在山上養雞、種菜、幫父親管裡的流籠頭運輸等,偶爾會做背負重物、協助高<br />
山避難木屋興建的零工。<br />
13 如等不到想要的牌時,Sachi 會唱:「等啊等啊望啊望…」<br />
163
Buya 這樣對我說。<br />
●<br />
「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你對我有什麼不滿意,你就直接說啊。這個家你有<br />
幫小 孩子洗過澡,進廚房煮過菜嗎?我這個太太做的怎樣,還不夠為你犧牲嗎?<br />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我?……沒有關係,我們離婚,你不喜歡就離婚嘛,你也不<br />
用這樣糟蹋我……」。丈夫沒有說什麼,走了出去。<br />
事情爆發後 Sachi 雖然覺得難堪,但離婚的念頭卻 也只是在心中淡淡掠過,<br />
畢竟 她還有四個小孩,對孩子的責任、認為自己不應該回到娘家求助,加上公婆、<br />
小姑和同事的勸說,使得 Sachi 繼續維繫著這段婚姻。<br />
「你就是這樣太照顧家裡,什麼事你都用的好好的,讓你老公沒有後顧<br />
之憂,他才會在外面搞東搞西……你就不要工作了,待在家裡不要管<br />
事,讓你老公自己去煩惱……」<br />
「可是我不工作怎麼行?郵局還有 定額定存的錢要繳,還有小孩子的保<br />
險基金,我沒有工作就沒有錢可以付了啊…」<br />
「你就不要管,讓你老公去操心好了」<br />
Sachi<br />
辭掉在天祥招待所的工作。雖說是要回家當少奶奶,但不習慣無所事<br />
事的 生活,又必須繳納定存保險,Sachi 還是在社區台八線的馬路邊,白天賣起<br />
了挫冰,晚上則擺起麵攤。<br />
而老公繼續在外面與對方 糾纏,甚至將女子帶回家中和 Sachi 吵架。公公和<br />
小姑 見家裡情況愈來愈混亂、不安寧,拿了一大筆錢載著 Sachi 至花蓮火車站,<br />
請 Sachi 離開至台北,找個地方睡覺,暫時不要回來。他們希望讓 Sachi 的老公<br />
看看沒有她的話,這家裡會是怎麼樣子。而早已陷入混亂,不知如何解決家裡困<br />
境的 Sachi 雖然百般的無奈、不捨、疑惑與難過,但她還是順著他們的建議,坐<br />
上往台北的火車。<br />
「我要去哪裡? 我到底要去哪裡?」一路上她不停的這樣問自己。窗外風景<br />
由熟 悉變為陌生,十幾年前坐在國光號上的心情隱然浮現,只是更加的茫然與無<br />
助。她不知要去哪裡?沒有人安慰她、帶著她,不知道這樣的離去是否會讓問題<br />
解決,未來變好?以為自己已經著了根,一再妥協讓步的結果卻是必須在這監禁<br />
又不知目的地的火車上。「我要去哪裡?我到底要去哪裡?」忐忑的心情一直到<br />
了台北,提著裝了錢的大皮箱,一個人的 Sachi 出站時已淚流滿面,小時候幫傭<br />
的地方無從找起,整個台北對她而言全然是個陌生的環境,根本不知有哪裡可以<br />
落腳。路上擁擠的人群掛著和家鄉不一樣的臉孔,車站外則是快速流轉的馬路與<br />
街道;耳中傳來不熟悉的對話和車站播報聲,但沒有一個人能給她答案,更多的<br />
人群帶來的是更大的恐懼,計程司機的詢問也只是讓她更加的迷茫。於是 Sachi<br />
164
躲回車站,打電話給遠在花蓮太魯閣的小姑。<br />
「你先找個旅社睡覺,『旅社』兩個字你會看嗎?」<br />
「我看的懂……」<br />
但 她擔心的卻是小孩子現在在幹嘛,放學了有人煮菜給他們吃嗎?那個還沒<br />
入學 的最小兒子有人幫他洗澡嗎?他們的衣服沒人洗怎麼辦?明天早上誰要給<br />
他們零用錢?她煩惱這些每天做的工作,要照顧的人,根本無心在此多待一秒<br />
鐘。她掛上電話,「連天橋都沒有過」,回頭搭上往花蓮的火車。<br />
「你不要回家裡讓丈夫看到你,你一定要離開,再坐火車回去 …」「我要回<br />
哪裡 ?我才剛坐火車回來而已」。公公和小姑接到通知到火車站找她。但他們還<br />
是認為 Sachi 必須離開一陣子,才能使家裡情況有所改變。Sachi 並非不願意配<br />
合,只是她放不下小孩,也找不到人可以投靠,「我要去哪裡?」成了「我能去<br />
哪裡?」。最後她想起了楊梅做汽車輪圈的表哥,在小姑答應會好好照顧小孩後,<br />
Sachi 在這一天內,第二度坐上往台北的火車。於表姊的指導下,到了台北車站<br />
換搭往新竹的國光號,然後拿著楊梅的住址給計程車司機。<br />
「你是原住民喔?」司機問。<br />
「對啊,怎麼樣?」<br />
「你不怕嗎?」<br />
「我怕什麼?我長 的不怎麼樣,身上也沒有錢,你想把我怎麼樣?你把<br />
我賣掉人家也不要我。」<br />
「我看妳是原住民,你那麼 有膽子叫我一個人載妳,妳知道妳要去的地<br />
方路很遠嗎?」<br />
「你就把我載到那 邊,然後放我下來就好了…」<br />
從 台北到表哥家的路上,陌生的環境和言詞總讓 Sachi 恐懼不安。好幾次她<br />
告訴 自己,如果最後找不到地方或發生了什麼事,她就這樣死掉或自殺算了。但<br />
就像她說的:「天公疼憨人」,最後她還是順利到了楊梅表哥那。而老公也在兩天<br />
後,在姨丈等人的陪同下,親自開車到楊梅接回 Sachi。<br />
丈夫依舊無法切斷與女人的關係。當他在外發生不快時 ,也總是會將怒氣轉<br />
往 Sachi<br />
身上發,好像是 Sachi 造成這樣處境似的(事實上這男的確實是受到極<br />
大的壓力,在部落中受人議論紛紛或抬不起頭)。他曾經在某次返家後,拿起 Sachi<br />
非常喜歡,用來插花的日本酒瓶朝 Sachi 砸去(第一次砸煙灰缸並沒砸中),嚴<br />
重到 Sachi 被公公送醫檢查後,有輕微的腦震盪;他曾經像發了狂似的,騎著機<br />
車朝 Sachi 急衝而去,想要讓 Sachi 受到嚴重的傷害。這些事 Sachi 都並未向家<br />
人訴苦,但一如以往地經由口語傳到同一社區的父親耳中,他生氣的到對方家,<br />
掐住女婿的脖子,將他架到牆上,就像之前對親家同樣的質問,問他為何要如此<br />
165
對待他的女兒。<br />
這些事件後,對於離婚 Sachi 終於有了堅定的打算,「我不離婚他總有一天<br />
會把 我打死,我怎麼死的都不知道」,然而丈夫依舊不答應,因為對他而言,這<br />
彷彿宣告他是個失敗的男人,這讓他難以在眾人面前抬起頭,雖然他已對 Sachi<br />
和這個家沒有感情和責任感,但他仍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失敗的男人。<br />
事發後 Sachi 坐計程車到對方女孩子位於榕樹村的部落理論,她氣憤 地出手<br />
打了 對方(雖然認錯人而誤打了她妹妹),並扯著對方頭髮要將她帶到社區中來<br />
理論。後來在村長的見證調解下,對方答應不再和 Sachi 老公往來,而公公也替<br />
自己的兒子求情,請 Sachi 不要離婚,再給他兒子一次機會。「這個家不能沒有<br />
你。你走了孩子怎麼辦?我們年紀大了無法照顧小孩了…」<br />
Sachi 再次的妥協。她跟著老公,開始做起小包的工程。<br />
「幾點了?阿亮。」邊坡上的 Sachi 向我詢問。<br />
●<br />
「快 12 點了。」我大聲地說。同時間我看著 Sachi<br />
和 Buya 手腕上沒有<br />
手錶的身影。<br />
「時間差不多了 ,我要去弄飯菜了。剩下的下午再種。阿亮,你不要再<br />
煮麵了,我看你很可憐,都一直吃麵,那個很容易餓,中午你不要再煮<br />
了,跟我們一起吃吧」。<br />
「嗯」。<br />
她 將早上的那鍋滷肉加熱,用自己種的蕃茄炒了蛋,並倒上一盤醬油醃製的<br />
山胡 椒。這樣的菜量夠他們吃到晚上了,傍晚時只要簡單的熱一熱,一天三餐對<br />
他們而言,總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與金錢準備。<br />
Sachi 煮好菜,叫 Buya 休息進來吃飯。但 Buya 仍 繼續地做著,過了一會兒,<br />
直到 雞舍的門完成後,他才帶著工具,緩慢的邁著步伐走進屋內。「好熱,太陽<br />
好大,以前山上沒有那麼熱,現在天氣怎麼那麼奇怪...」。他把帽子脫下,拿起<br />
綁在腰間的衣服擦拭著臉上和身上的汗,然後拿起碗喝了杯水後盛飯吃了起來。<br />
Sachi 說她吃不下,叫我先吃,當客人來時,她總是習慣等所有人吃飽再將剩下<br />
的菜收拾乾淨。她走到門外看 Buya 剛完成的雞舍。住附近的 Hogan 和他媽媽(與<br />
Sachi 的爸爸是表兄妹)吃飽飯也走了過來。Hogan 前陣子正替自家幾十年歷史<br />
的雞舍主體完成重建工作,屋頂是鐵皮,其他部分則仍舊是木頭,在支柱下塗抹<br />
了柏油防止腐爛。重建後的雞舍縱深更深也更為堅固,內部多了許多讓母雞孵蛋<br />
的空間。現在他過來看看 Buya 他們所搭建的雞舍,但並沒有一起幫忙。<br />
Hogan 的媽媽請 Sachi 和 Buya 晚上到家裡吃雞酒,因為整個上午她已 將蕗<br />
蕎都 種下去了,心情很輕鬆高興,要殺隻雞來吃。「那我們再帶幾盤菜和米酒過<br />
去。」Sachi 說。幾個禮拜前 Hogan 在苗栗的姊姊決定將大禮的部分土地賣給國<br />
166
家公園,而他媽媽陪著鑑價人員清點完補償的地上物後,也煮了一鍋雞酒,除了<br />
招待鑑價人員,也像完成了一件重要事般的犒賞自己。在這裡,若是為了慶祝或<br />
開心而殺雞煮了雞酒,總是會請另一戶的人家一起來吃。<br />
兩隻火雞沒有動靜的躺在地上,Sachi 請 Buya 過來看,確定他們都已死掉。<br />
Buya 說他前幾天看到兩隻火雞脖子搖搖晃晃,一副全身無力的樣子,於是昨天<br />
餵食他們山下買的感冒藥,怎知道最後還是死掉。Buya 向我表演雞搖晃的樣子,<br />
Sachi 無奈又氣憤地罵著他不該亂餵雞吃藥。<br />
我看了看牆上的鐘,指出的時間是 3:27,而且錶面上的針始終一直維持著一<br />
種獨 特而非正常的速度在走,你永遠不知道它現在是快幾分鐘或慢幾小時。「時<br />
鐘壞了,不是沒電,我換過電池了,它還是一直走,但是走了走了就是會亂掉,<br />
我後來乾脆就不管它了,反正也沒在看。」「那你怎麼知道時間呢?」「反正天亮<br />
了就起來,吃完飯就工作,工作累了休息,餓了就吃飯啊。」Sachi 走進屋內拿<br />
出碗筷輕鬆地說著。此時 Buya 在旁邊立定起來,兩腳併攏,低著頭手指著靠在<br />
一起的腳,帶著點酒意和還算良好的國語說:「我工作的時候,如果有太陽的話<br />
只要看下面的影子就行了,影子沒有的時候,就是中午了。」聽著他們敘述的同<br />
時,我想著早上調整手錶時間的意義。<br />
飯後,Buya 依慣例去餵食他的兩隻心 愛寶貝,Sachi 則將碗筷拿去浴盆中準<br />
備晚 上一起清洗。<br />
「Hogan 還這麼年輕就待在山上實在很可惜,他應該出去工作賺錢、結<br />
婚生小孩,年輕人應該出去闖一闖,不應該在這裡…他們父母也拿他沒<br />
辦法……」<br />
「你不希望兒 子回來留在山上嗎?」我問。<br />
「要看回來山上是要幹什麼。做農太辛苦了, 年輕人應該要出去賺錢,<br />
我這裡的地有一塊絕對不會賣要留給他,錢我沒有,但至少會留一塊<br />
地,現在我在山上就是要整理和拿到這塊地,以後要幹嘛就是看他,至<br />
少我這個作母親的沒有對不起小孩了…」<br />
最 小的兒子是 Sachi 目前最放不下心的小孩。他同居的女友已懷孕幾個月<br />
了, Sachi 一直計畫著結婚方面的事情,Buya 則完全不想參與。一個多月前 Sachi<br />
請在三重做捷運工的兒子趕緊回來,一起至秀林對方家中提親。那時她在對方和<br />
自家各殺了一隻豬,宴請雙方家中的主要成員,因為 Sachi 相信男女雙方若未結<br />
婚而發生關係,必須殺豬避免厄運的降臨。但(未過門)媳婦日漸隆起的小腹,<br />
使得結婚儀式必須等到孩子出世後再舉行。偶然的算命經驗讓她對預測命運的事<br />
感到好奇,她常懷疑是否名字不好使得自己命運如此多劫,也一直替將出世的孫<br />
子尋找一個好(命)的名字。<br />
天氣熱,原本四散在外的雞 都已跑回雞舍躲避正午的太陽。Sachi 將雞舍的<br />
門關 了起來,回到木床上休息,從以前她就有著睡午覺的習慣。但 Buya 則是隨<br />
167
性,有時到別戶那用餐,只要有酒往往可以待上個半天。不過現在的他看來顯得<br />
無聊且有點疲憊,他抱著 Bilaq 上床,離 Sachi 約一公尺半的距離,躺平睡著。<br />
我成了無事可作的人,於是組合起昨晚 Sachi 找出來的帳棚,這帳棚是以前<br />
的遊 客留給她的,Sachi 知道我睡覺時不習慣被熱情的 Bilaq 和 Barvi 給簇擁包<br />
圍,因此特意找出這帳棚,讓我可以安心的在裡面睡覺、「做功課」。<br />
我在外面搭起帳棚,走近棚內盤腿坐了起來。拉開門的拉鍊讓自己與 外界仍<br />
有著 視覺上的聯繫。然後開始想像自己是那個在初步蘭島的馬凌諾斯基、新幾內<br />
亞的瑪格麗特或是南美的李維史陀,想像著這裡擺滿了我的器材、筆記,而外面<br />
的土著正帶著陰莖霄忙碌地做著我沒見過的新鮮事。擣芋頭、甘暑、磨箭、織布<br />
等。想著想著不自覺地躺了下去。(不知過了多久)直到棚內悶熱的空氣將我喚<br />
醒,才迫不及待地鑽出帳棚外,看著屋裡的人們仍然繼續做著我進入帳棚前所做<br />
的事。<br />
●<br />
這 三年多丈夫悠遊兩人之間而沒被察覺的日子,也是 Sachi 身體最虛弱、承<br />
受許 多莫名病痛,常常需至醫院報到的時期。白血球過高、胃潰瘍、心臟方面等<br />
的疾病,整整困擾了她好幾年。事後的她回想起來,總相信是丈夫在外面與其他<br />
女子有關係後,再回來動她的身體所導致。<br />
由於老公手上工程頗多,Sachi 成了老公 的分身,帶著一群工人從北花蓮、<br />
奇美 甚至是屏東,四處做著丈夫承攬的工程,老公則在另一地監工。這給了老公<br />
又一次婚外情的機會。丈夫在某日帶了女子至屏東向 Sachi 索取工程餘額,說是<br />
要支付其他款項。但 Sachi 不再相信。她帶著工人越帶越有心得,也替老公賺了<br />
不少錢,堅持不在工程未完成前將錢交給丈夫,這使得丈夫勃然大怒,拿起玻璃<br />
杯等物品丟向她並作勢毆打,完全無視現場其他工人。幸虧力挺 Sachi 的工人們<br />
出面保護,最後她並未讓丈夫將錢帶走,卻也因此受了輕傷。<br />
工人們帶 Sachi 到海邊散心解悶,希望壯闊的海洋與聲浪能 平復她憔悴的身<br />
心。但 望著整片大海,卻更加深心裡的茫然與無助,她不解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br />
對不起任何人,為何會遭受此對待?她不懂自己的命運為何這麼悲慘?她找不到<br />
方法能改變這一切,再也受不了一再地背叛及爭吵,不知道這樣活著還有什麼意<br />
義?於是她趁著其他人不注意時,走到人跡罕至,一塊突出於岸邊的大石頭上,<br />
一躍而下。<br />
「幹!要 跳也不會走遠一點,賣吼吻看到…」兩名釣客發現將 Sachi 救起,<br />
是她 口中從小就有緣的台灣人。怎麼被救起的她根本想不起來,只記得當醒來睜<br />
開眼時,對方向她說了這句話。<br />
從花蓮趕到屏東,大女兒的探 視讓 Sachi 找到了活著的意義,「媽媽,你不<br />
要難 過,不要想不開,我們四個小孩都會支持你...」她決定不再自殺,只希望此<br />
生盡最大的努力讓小孩子受到照顧、好好成長。如果這段婚姻還有意義,那就是<br />
168
她要給孩子一個完整,有母親的家庭。<br />
語言的力量有多大?帶來了怎樣的影響?<br />
在外做工程的期間,曾有好幾個男生或者是 憐惜,或者喜歡 Sachi 堅毅活潑<br />
的特 質,租車行老闆甚至是為她看病的醫生都對 Sachi 表示好感,想要追求。但<br />
Sachi 從不考慮,因為她相信,一旦不守規範在外面「亂玩」,和不應該在一起的<br />
人玩樂,那她的兒女將會受到詛咒,她簡直不能想像因為自私的享樂,而讓子孫<br />
承受她所帶來的報應,這讓她一輩子都不會原諒自己。因此她一直謹守著自己的<br />
分際,也從沒有讓公婆或部落裡的其他人說話過。<br />
直到 Buya 出現。<br />
Buya(1944 出生) 是一位熱心、憨厚不多話卻做事認真的人。因為家庭窮<br />
困, 不同於其他男性族人,Buya 在婚姻中入贅給大他近 20 歲的老婆—1910 年<br />
代出生,在日本文化教育下長大的 Taroko 族人。雖然年紀有如此的差距,儘管<br />
入贅的方式在當時算是特例,且是一樁墊基於經濟現實的婚姻,但 Buya 知道自<br />
己在這場交換中的身份,為了表示對老婆的忠誠,他在手腕上刺上了老婆的日本<br />
名字。<br />
二十 幾年的打拼,加上老婆經濟上的支持,Buya 成了一位擁有工程車輛與<br />
機械 的管理者。當工程有所需要,工頭會向他調派車輛,也因此他總是會出現在<br />
一些工地的現場,他喜歡買啤酒請工人們一起共飲,Sachi 和她的丈夫因此也認<br />
識了他。<br />
不知是 有心還是無意,Buya 似乎常常將目光停留在 Sachi 身上,Sachi 雖然<br />
不知 情也沒與他往來,但這樣的耳語經過他人的敘說已沸沸揚揚。流言傳到了<br />
Buya 老婆耳裡,她跑到 Sachi 家向 Sachi 的公公婆婆訴說,一時間 Sachi 成了不<br />
規矩的女人,從一個婚姻受害者變成不守婦道的人,「原來妳自己在外面也是這<br />
樣...」,社區中的人對她議論紛紛,公婆指責她將為家裡帶來厄運,她覺得所有<br />
人對她的眼光已經不同。Sachi 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在家裡無立錐之地,在社區裡<br />
也不被認可的人。<br />
當知道已無法繼 續待在這個家中時,Sachi 決定要離開這個家了。她開始暗<br />
地裡 向朋友借錢,總共借了十萬,其中五萬存在四嫂名下,託她照顧自己的小孩,<br />
另外五萬則是預備離家後的先期支出。一切安排妥當,是澄清也是報復,她來到<br />
了 Buya 的家裡,向他老婆理論。<br />
事情的演變彷彿小時候與丈夫 因流言而結婚的事件一般—當然,事情遠比當<br />
初更 為嚴重。15 歲的女孩子已是 30 歲的人妻,丟石頭的動作成了言語的威脅,<br />
而從丈夫變為比自己媽媽還要年長的 Buya 老婆。結果,同樣是離開原來的家庭。<br />
「...我跟你老公沒有關係、沒有瓜葛,妳竟然跑到我婆婆那邊這樣說我<br />
的事,讓我在那沒有辦法生存,好,沒有關係,這個老公是你給我的,<br />
妳不要後悔,我要把他帶走就一定會把他帶走...」<br />
169
她繼續轉身向 Buya 說:「現在妳老婆跑到我家裡這樣子鬧,讓我沒有<br />
辦法生存......你如果今天不跟我走沒有關係,明天報紙登出無名女屍就<br />
是我,我會讓你們全家人不得安寧...」<br />
她 在太魯閣叫了輛計程車,包車到了台北,卻不知該落腳何處,最後請司機<br />
載至 淡水。在學校附近 Sachi 租了間木板隔間的雅房,旁邊住著小她十歲,叫她<br />
姊姊的大學生。不知能做什麼,她整天到海邊閒晃,那景象帶來的卻總是迷茫。<br />
回到房間後嘴巴始終叼著未點燃的煙,一罐米酒酒量不好的她強迫自己喝了三天<br />
才喝完。隔壁的女學生們知道她心情不好,總是請她過來一起聊天。然後她買了<br />
一台小電視,開始看起當時只有三台的電視節目。而 Buya 在幾天後,放棄太魯<br />
閣的事業與家庭,北上和她相見。<br />
●<br />
Sachi 已起床在邊坡上種著蕗蕎。這是她從小時候到現在山上常吃到的食<br />
物, 葉子像蔥,根部像蒜,但味道卻比較像洋蔥一樣稍微刺激嗆鼻。大部分的時<br />
候 Sachi 將蕗蕎直接洗淨沾上混著山胡椒的醬油生吃,偶爾也會放在瓶罐裡醃製<br />
過食用。自從平地開始流行所謂的風味餐,並傳出蕗蕎是健康食品,有排毒減肥<br />
的效果後,他們便開始大量種植。這是 Sachi 除了雞和箭筍外,另一個會拿下山<br />
去販售換取金錢的農產品了。主要是賣給認識的餐廳業者,其餘的則拿至山下部<br />
落或社區中販售。她很自豪有辦法找到管道賣給大量進貨的餐廳業者,不用像其<br />
他幾戶必須在社區中或路旁一袋 50 元的零賣。今年的蕗蕎讓她有三萬多塊的進<br />
帳,這超乎了她的預期,因此在這片剛整好的土地上,沒有像其他幾戶先種短期<br />
可採收的甘藍或包心結球之類的菜種,她優先種下明年春天才能採收的蕗蕎。<br />
Buya 將雞舍的門打開,不懂得從缺口出來的雞全都跑了出來,幾隻雞跑到<br />
Sachi<br />
旁邊用嘴和爪子翻弄著土,她害怕這些雞會將剛入土的蕗蕎翻出,不時的<br />
驅趕著牠們,一方面她也生氣的罵著 Buya,但雞已無法被趕進雞舍,且圍網本<br />
就仍有缺口未補足,因此 Sachi 也只能讓這樣的情況繼續,而 Buya 依舊悻悻然<br />
地走進屋內準備下午的工作。<br />
Buya 拿起除草機,倒入柴 油。他要去幫夏蘭的土地除草,因為對方給他一<br />
天一 千五的工資,請 Buya 幫忙整理那片已雜草叢生的土地。昨天下午的一場雨<br />
讓 Buya 只做了半天,因此今天下午他要繼續做著昨天下午的進度。只要不喝酒<br />
的話,一旦 Buya 拿起工具開始工作,他總是會做到一定的進度才會休息回家。<br />
但另一方面,整個工作並沒有明確的期限,進度會因為很多天然(下雨、颱風等)<br />
或人為因素(酒醉、下山、生病等)往後延,Buya 很少會在事發後的隔天加把<br />
勁補足,換句話說,落後的進度並不會加快他除草的速度;一切視他何時完成,<br />
並向對方申請幾天的工資。<br />
眼前 Sachi 種菜的土地、 居住的教會以及教會後雞舍的範圍,屬於過世的二<br />
170
哥所 有,由他的小孩共同繼承。Sachi 從立霧山回到大禮後,經過外甥們的同意,<br />
暫時居住在這發展。簡單的幾樣「家具」,沒有其他幾戶專用的廚房和烤火用地,<br />
甚至連洗澡也是在唯一流著水的浴盆旁露天進行,雞舍則是在教會後面以往廁所<br />
的水泥地基蓋上棚布而成,這一切似乎說明了這只是個暫時的居所,卻也是如今<br />
花上最多時間居住的地方。<br />
Sachi 站在邊坡上,彎著 腰熟練地揮動著小鏟子,把土翻開後拿出竹簍中的<br />
蕗蕎 放進去,視大小一次大約放進 3~6 個。接著將鏟子橫握,利用側邊水平的一<br />
面將翻起的土推下,再用鏟子底部壓實。一個動作循環不用一分鐘,然後繼續間<br />
隔約幾十公分翻土種植。Sachi 見我在邊坡上無事可做的樣子,請我下去隨便拿<br />
個東西驅趕圍繞在一定距離旁翻土的雞。我拿著竹掃把揮舞,也撿起小石子往遠<br />
處翻土的雞丟過去。<br />
受不了炙人的陽光 ,我回到屋內休息。走到教堂外時,望了望在太陽底下顯<br />
得有 點冷清的山坡,然後轉身看著眼前的建築。門口上方經歷時空洗鍊,釘在那<br />
已經好幾十個年頭的「禮拜堂」三個字吸引了目光,那不是一般常見的標楷體,<br />
而比較像是一種象形書法,因為「禮」的部首看起來像是「犬部」,而右側的豊<br />
則像是一隻坐著的狐狸。但對他們而言,這三個字或許不如上方那比它本身更具<br />
象徵意義的符號來的更具有力量吧——垂直交叉的兩根木條高聳其上,目空一切<br />
的鶩自矗立著。在它後面是兩側向中央突起的屋頂,木製的屋樑鋪上了日式風格<br />
的黑色圓拱型瓦片,兩側的一端是混揉了閩南以及日式屋脊常可見的趨吉避凶圖<br />
騰,又像西方中古世紀某個雕刻的屋頂裝飾。灰白地衣和慘綠的苔蘚像是吸取這<br />
座建築的歷史方能存活般的,在已顯粗陋的外牆上蔓延;幾個不知原因產生的裂<br />
縫與凹痕,彷彿吸進了幾世紀的黑暗般凹陷,讓我有與最後一幕,<br />
想往洞裡望進去的深深渴望。錐形的窗戶使得這座建築更加立體,牛奶白和蛋黃<br />
色的玻璃在木條的安排下表現出十字圖形;無奈幾處以木片遮掩或破了未補的空<br />
缺,卻讓留下的褪色玻璃看起來像是就地取材的隨意拼湊。與窗戶下方切齊的壁<br />
身鋪上毛毛小小的洗石子,讓人極不協調的想起慈濟的建築外觀。教堂前方立了<br />
兩個與窗戶同樣形狀的三角水泥柱,像是鳥居似的鎮守著台階的起點。沿著台階<br />
而下是以往花圃的所在...。<br />
Buya 醉醺醺的回來。原 來是遇到雇他除草的夏蘭老公,以及要到大同的族<br />
人。 他們在流籠頭那喝了酒,回來時走路已經搖搖晃晃,滿臉潮紅。他走到邊坡<br />
上,向 Sachi 喊餓了,請她上來煮飯。Sachi 看了看天色,以及簍子裡的蕗蕎,<br />
不耐煩的回答太陽還那麼大,且晚餐要去 Hogan 那吃雞酒,所以不準備煮了。<br />
Buya 覺得有點自討無趣,走進屋內將幾天前採的竹筍剝皮放入滾水中,把佛手<br />
瓜和掛著的香腸拿下來切片,放在桌上好像等著 Sachi 回來處理似的,然後走到<br />
雞舍,一會兒用手搖盪著早上的鋼筋是否牢靠,一會兒走進雞舍的棚架下看飼料<br />
和水盆的情形。這一切動作都在眼神呆滯伴隨著踉蹌的腳步完成。<br />
竹簍裡的蕗蕎沒了,Sachi 終於完成這幾天的工作。她走上來,問 我幾點了,<br />
然後 看著鍋子裡正在煮的竹筍和桌上凌亂的菜餚,一邊善後一邊氣沖沖地罵著<br />
171
Buya。<br />
「你不是我老公,你沒望啊......答應人家的事情,就要幫人家做好,哪<br />
有人像你這樣做半天休息一天的,你不要跟人家拿工錢了...」<br />
「你怎麼會請到這樣的工人,比你還早下班,四點多就下來說肚 子餓了<br />
叫我煮菜,你以後不要叫他幫忙了...」Sachi 轉身向喝了酒正準備離開<br />
的夏蘭老公說。他沒說什麼,一副不在意又彷彿理虧似的走出去。<br />
躺 在床上的Buya抱怨為何要讓他這麼累?他已經老了,不想再工作了。上<br />
禮拜 他才因此和Sachi鬧脾氣,因為Sachi下山辦事情,留他一人在山上工作。他<br />
沒做什麼事,只是整天到鄰居那喝酒,訴說著Sachi給他那麼多的工作,而他Baki 14<br />
有那麼多小孩,卻只會叫他去立霧山幫忙除草開路。那時Sachi聽到鄰居打電話<br />
來告知,又氣又難過的整晚睡不著,隔天趕緊辦完事上山。如今同樣的爭執又要<br />
重演。<br />
「為什麼你那麼不喜歡工作?跟我爸爸差那麼多,我爸爸那麼老了,還<br />
是一直在山上作事情,在他的土地上工作,你怎麼那麼懶惰?...好!你<br />
說你不要工作,那我叫你下山去辦事情,你又說你不會,我下去辦,你<br />
又在上面鬧脾氣喝酒不做事,你到底是想怎樣?巴達岡<br />
16<br />
,我為什麼要那麼拼<br />
跟你說過孩子是我最重要的,我跟你在一起也是為了我的小<br />
多錢<br />
你管好了...... 上次你找外<br />
15 的土地我花了<br />
多少時間金錢才要拿到,你什麼都不管,你有幫過我什麼嗎?現在雞在<br />
這邊,你跟我下去了誰要照顧?我下去幫你買煙、買酒、買肉上來,你<br />
如果不工作那你就整天喝酒喝到死算了,拜託你死乾脆一點,不要拖在<br />
那邊那麼久,還要我照顧你,花那麼多錢...」<br />
「我那麼努力幹什麼?那些小孩是姓葉不姓江<br />
命?我的土地不要給他們,我已經老了,我不要那麼累,不想再工作<br />
了...」<br />
「我早就<br />
孩,你現在有可能叫我不去管那些小孩,不替他們想嗎?上次我去台北<br />
幫忙顧外孫一個禮拜,你就聽那個姓葉的 17 講,懷疑我是去跟其他男生<br />
亂搞……我女兒的婆婆生病住院,我去基隆幫忙看小孩都不行嗎?好,<br />
那我以後都不下去,待在山上事情都你去辦,你會辦嗎?……」<br />
「...你不要想那麼多事情給我那麼多工作,我已經老了,我賺那麼<br />
幹嘛,你會把我的錢拿去給你的小孩用...」<br />
「你這麼不相信我,那你的事情、你的錢都給<br />
14<br />
太魯閣語「長輩」的意思,指 Sachi 的父親。<br />
15<br />
巴達岡位在大禮對岸的山腰上,於日據時期已被遷移至平地,Buya 的父母是巴達岡人,Sachi<br />
向鄉公所申請土地測量及過戶手續,將於會勘後取得土地權狀。<br />
16<br />
Buya 無法生育,沒有小孩。<br />
17<br />
Sachi 前夫的哥哥,現仍長住在大禮山上。<br />
172
甥女來查帳,懷疑我把你的錢用給我小孩,結果呢?我有動你的錢嗎?<br />
你不管我的小孩,我總要管,我對不起他們,我會活到現在就是因為小<br />
孩子,我不放心他們,到我死之前都一定會替小孩子想…」<br />
Buya<br />
依舊沒什麼回應似的採取消極的抵抗,他很少回嘴,只是喃喃地重複<br />
說著 自己不想工作了。十幾分鐘後,這番「爭執」有了結果,Sachi 決定明天起<br />
讓 Buya 下山放五天假,得到他所謂的「休息」。<br />
然後她走至新建好的涼亭下坐著,看著眼前好 幾十年的熟悉景象。<br />
●<br />
Sachi 和 Buya 在台北做起熟悉的工程,只不過已從小包變成工地的版模工、<br />
捆工 、拔釘工和廚師。那時正好是台灣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營建業有許多的勞<br />
動工作。他們把握每一個機會,幾乎整個月都「滿工」,板橋、泰山、林口都有<br />
他們工作過的足跡。Buya 是所謂的工地師父,而 Sachi 負責拔釘以及炒菜給工人<br />
吃。一天的薪資兩個人將近五千,一個月下來賺個八九萬是常有的事。<br />
兩年多的日子 Sachi 始終想念著小孩。她常獨自一個人走在傍晚疏洪 道的堤<br />
防上 ,想念著這個時刻小孩子放學了正在做什麼;得知小孩子生病受傷,她會包<br />
計程車甚至坐飛機回去只為帶小孩子看醫生,然後睡在花蓮市;當兒女思念母<br />
親,Sachi 會跟他們約在台北的火車站見面,一起逛街,一起分享著彼此的心情。<br />
不同於幾年來的病痛纏身,這幾年是 Sachi 身體最好的時候,她認為是老天爺和<br />
孩子冥冥之中給予力量幫助她,支持她。這段期間 Sachi 和 Buya 存了不少錢,<br />
她利用這些賺來的錢償還了當初借的十萬塊,而每個月也都固定匯款二萬五給四<br />
嫂,支出小孩子的學費和零用金。甚至當丈夫請徵信社找到他們,並向法院控告<br />
通姦時,是幸或不幸,18 萬元的易科罰金對他們而言已是可以支付的數字了。<br />
「你不用套我的話,我把事情都跟你說,沒錯,我有和這個男的在一起,<br />
因為我的老公在外面玩女人不顧家,從來沒拿錢回家,沒有錢我要怎麼<br />
教育我的四個小孩子?為什麼我要離開花蓮來到台北?就是因為他容<br />
不下我,讓我沒辦法待在家裡......今天外面生活要租房子、水電、吃飯,<br />
我還要給小孩子教育費,這個月錢如果不夠,我就跟這男的睡,他跟我<br />
睡一次我拿 3000 塊...」Sachi 坦率又氣憤的向做筆錄的警察說。<br />
Buya<br />
則死不承認。做完筆錄和簡易審訊已經接近中午,將近 10 個小時沒睡<br />
了。 大女兒在 Sachi 的通知下,和奶奶(Sachi 的婆婆)從花蓮來到板橋。<br />
「奶奶,你看我媽媽這樣子,出去以後我不要姓葉了...」即將高中畢業 的女<br />
兒看 到母親憔悴的樣子放聲哭了出來。<br />
「不要銬我媳婦的手,她沒有做錯事 ,是我兒子不好,她是我最好的媳婦,<br />
173
是她 養孩子的...」婆婆看到 Sachi 被銬上手銬的一剎那,跪下去對警察說。有一<br />
種難以形容的感受,無奈混雜著溫馨,這是 Sachi 第一次感受到婆婆對她的肯定。<br />
頻繁的出庭和爭訟讓不懂法律的他們緊張不安,生活徹底打亂。丈夫雖然控<br />
告通 姦,卻不願意和 Sachi 離婚。為了解決多年的糾葛,Sachi 回到秀林租了房<br />
子,在同情她的檢察官建議之下,誘使丈夫在警察面前對她施暴,並於深夜包了<br />
計程車,確定丈夫與第三者在家同處一室後,帶著警察破門而入。兩項證據的支<br />
持,她終於訴請法院判准離婚。<br />
離婚後的Sachi仍不願回到娘家 居住,她與從台北回來的Buya在民樂社區租<br />
房子 ,並找到蓋墳墓的工作。身為嫁出去的女兒,Sachi的父親當初並沒有要留<br />
土地給她,父親將土地分給五個男生,其中最小的兒子按慣例負責照顧父母,和<br />
他們同住,因此擁有老家也分得最大部分的土地 18 。而嫁出去的女兒屬於另一<br />
家,是不能將祖先的土地帶走的 19 。直到Sachi和丈夫離婚,又尚未與Buya結婚時<br />
20 ,父親對她說:「妳現在沒有先生了,沒有辦法從先生那拿到土地,妳沒有土<br />
地以後怎麼辦?妳的小孩子不能沒有土地,地是我們的根,沒有土地就好像是流<br />
浪的人,也會讓人懶惰,這樣是不行的...」於是,趁著那時鄉公所的土地重測,<br />
父親將Sachi納入他的戶口,將自己在立霧山新開墾的土地撥給Sachi一部份,而<br />
大禮的地則堅決不給,因為這是祖先的地,不能給女兒帶到別人家去。後來父親<br />
見所有小孩只剩Sachi願意留在山上發展,在Sachi的數度要求下,幾年後將大禮<br />
邊坡的一塊地分予Sachi。<br />
由於蓋墳墓所賺的錢總是不 易留下,且身體又常出現莫名的疾病,他們決定<br />
上山 開墾,一方面協助父親採收高麗菜,一方面整理父親給予的土地,準備申請<br />
權狀。直到族人因各種原因檢舉違建砍伐的作為後,他們回到大禮繼續尋找出路。<br />
●<br />
「可能上輩子欠他的,所以這輩子要這樣折磨我...」她長長的嘆了一口氣,<br />
用一 種慣有的方式解讀自己的人生。<br />
黃昏像一張薄膜似的淡淡吹著風, 草地上兩隻狗不停地廝磨追逐。Sachi 在<br />
涼亭 下訴說著過往種種回憶,我彷彿跟她分擔著某種共同哀愁似的東西,但那是<br />
什麼呢?<br />
狗兒跑了 過來,那雙做過女侍、清潔員、女工,蓋過墳墓、房子、各種工程,<br />
戴過 手銬,種過蕗蕎、玉米、青菜和養雞的手,如今正摸著 Barvi 毛茸茸的耳朵<br />
與身體。Hogan 的媽媽說雞酒煮好了,請我們過去吃。Sachi 將曬了一整天的玉<br />
米拉至屋簷下,用帆布蓋上。等到雨天或飯後的空閒時間,或是與上來整理土地<br />
18<br />
若父親死後,母親也會分到家產的一部份,而這部分是要留給照顧她的小兒子。<br />
19<br />
Sachi 認為也正因為她是嫁出去的人,所以大同的人認為她不應該回到這山上開墾,沒有權利<br />
擁有立霧山這塊有爭議的土地。<br />
20<br />
Sachi 和前夫在 1993 年離婚後,與 Buya 一直到 2003 年才公證結婚,之前一直是以同居的方<br />
式在民樂租房子,後來在秀林鄉公所附近,Buya 的土地上搭起的「鐵皮木屋」居住。<br />
174
的姊妹淘坐在屋簷下聊天時,再用手或一字形起子將玉米粒剝下。Sachi 今天是<br />
沒時間處理這些了,她進到屋內,將 Buya 煮的竹筍炒上豬肉,並叫醒他一起過<br />
去。<br />
Hogan 坐在自家的屋簷下,腳踩著使用了 10 幾年的ㄇ字簍,用手抽掉已斷<br />
裂或 破損的藤枝,然後穿入在屋頂曬了好幾天的新藤。這些在平地已少見的藤簍<br />
是要讓母雞孵蛋用的。旁邊的矮桌擺著一大鍋的雞酒,以及高麗菜、山胡椒等幾<br />
盤青菜。Bravi 和 Bilaq 高興的在桌下四竄,低頭尋找掉落的食物。這裡一個月<br />
總會有 4、5 次這樣的「party」,以心情愉快的原因居多。天色漸黑,Hogan 打開<br />
發電機的引擎,將有著各樣電器插座的延長線接上,四周瞬時被日光燈照亮了起<br />
來。他把收聽中廣新聞網的廣播關掉,當時正播放各種物品(麵粉、沙拉油、石<br />
油等)漲價的消息。電視打開後,轉到四個無線頻道中,收訊較清楚的「民視」。<br />
此時播放晚間新聞,畫面中陳水扁總統在某個場合發表談話,Buya 見著大聲的<br />
說:「幹 XX,王八蛋!騙肖ㄟ...」。其他人沒說什麼,好像各自都陶醉於手中那<br />
碗雞湯似的專心啃著雞肉,喝著濃濃酒味的湯,然後將吸允過的骨頭丟到地上,<br />
一旁立即蜂擁而上。他們臉上帶著輕鬆滿足的表情,配合偶爾的談話,這頓飯的<br />
節奏比起其他餐總是來的緩慢許多。<br />
三戶人家 來了,他是Sachi前夫的大哥,也是Sachi<br />
口中<br />
家都可以在私底下向你抱怨另一戶哪裡不好,有哪些令人討<br />
厭、<br />
他們習慣收看的節目—「愛」。<br />
整個<br />
21 中的另一戶—葉先生也<br />
愛說他人閒話的「不好的人」。他曾經向Buya耳語,懷疑Sachi下山是跟其他<br />
男人在一起,也曾經嫉妒Sachi某季的玉米豐收,而奚落這些玉米如何的不好,<br />
不適合養雞等。<br />
這裡每一戶人<br />
自私自利的事情至少半個小時以上,聽完抱怨的你以為他們有著什麼深仇大<br />
恨或水火不容,但只要待上個幾天,加上些幸運,你就會發現,那些他們嘴裡多<br />
麼令人憎恨的對象,卻也是見面會寒暄幾句,一起坐下來聊天喝酒,吃飯打麻將<br />
做禮拜,或是在物品上互通有無的親友。當他/她忿忿不平地說著某人如何占他<br />
/她便宜或對其他人亂說他/她壞話的事時,隔幾天你又可以看到他們正喝著酒<br />
開心地聊天,批評當下不在場—往往是幾天前才和他/她一起談過別人是非—的<br />
人,於公私領域上 22 的處理失當或別有意圖。<br />
關心了明日天氣的好壞,開始播放幾個月來<br />
劇情是由意圖奪產的不孝媳婦、陰沈狡猾的善變人士、改過自新仍講義氣的<br />
流氓、單純善良的盲女、隱藏自己等待報仇的中年男子、仗義執言的甘草角色、<br />
敦厚慈悲的傳統女性、操縱他人為己謀利的父親、介入他人婚姻的劈腿男女等各<br />
種角色與各種恩怨交織糾葛而成。但不管是片名或是節目網站的劇情介紹 23 ,都<br />
強調一切由「愛」而起。<br />
21 目前大禮約有五戶,常住山上的則是 Sachi、Hogan 和葉姓人家。<br />
22 大部分是農事、家事、教會事物等<br />
23 在電視劇的網站裡,劇情介紹如下:這是個「愛」的故事…他們都為了「愛」付出了一切…親情的愛、<br />
友情的愛、愛情的愛…都在這些人物中蔓延開來…,愛帶來了溫暖、陽光,愛帶來了衝突與矛盾,這一切,<br />
都只因為「愛」...。http://www.ftvet.com.tw/Drama/8love/layout.asp?LL=story<br />
175
葉先生看了一半後便離 開,帶著電瓶式頭燈準備去打飛鼠。Hogan 的媽媽用<br />
手和 起子將一定數量的玉米粒剝落後也入房睡了。剩我們四人繼續專心地看著電<br />
視。Sachi 和 Buya 不時地隨著劇中人物的作為,說著:「這個最壞了」、「她又要<br />
害人了」、「有這樣的女兒就有這樣的父親」、「她竟然對自己婆婆這樣」、「活該,<br />
害人結果害到自己」、「她要害他他還不知道」等。有時劇中人物只是因煞車失靈<br />
不小心撞上仇家,他們也會認為對方是故意的而更加責罵。「他等一下會叫人去<br />
打她」、「他不會成功的...」他們不時地當起自稱的編劇,認為劇情下一步應該怎<br />
麼演,然後期待著之後的發展。<br />
第一百多集的電視劇差不多與 酒杯中的米酒同時結束。他們將酒喝光並看著<br />
預告 注意明日劇情的線索。Buya 穿上衣袖繡有國旗和「反共救國」的東引島黑<br />
色棉質運動外套,Sachi 張開手臂伸伸懶腰,嘆了一聲。在月色的照明下,兩個<br />
人不用手電筒的走過黃土小徑回到家裡,兩隻狗一前一後的跟著。Sachi 走到屋<br />
後的露天浴盆洗澡,洗後的舒服感容易讓睡意降臨,因此她習慣等到上床前洗<br />
澡。Buya 走到雞舍巡視,此時雞群們早已回到棚架下,在習慣的地方休息。他<br />
看了看四周,確定了雞的位置和數量後將門關上,然後走至教堂前方把那扇滑輪<br />
鏽蝕,基座溝槽也已變形的大門推至定位。不久後 Sachi 從側門走了進來,吹熄<br />
蠟燭。她不喜歡 Buya 抱著狗睡,因此在距離幾公尺的老位置上躺平,Bilaq 被<br />
Buya 抱著,Barvi 則不時移動,找尋牠想要的溫暖。我睡在靠窗的位置上,從沒<br />
有關上的窗戶望出去,天空乾淨的讓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滿足和感動。遠處 Hogan<br />
關掉發電機,四周一片寂靜,窗外唯一能聽到的,只有緩慢而低吟的蛙鳴聲,以<br />
及滋滋的冬蟖聲....<br />
176
近代都蘭部落社會變遷與地方自主性之發展<br />
陳佩儀<br />
本論文主要以居住在都蘭部落之阿美族人為敘事主體,一方面探討都蘭部落<br />
在歷經不同外來政權(日據時期到國民政府時期)的影響下所產生之多項改變。<br />
在國家權力架構下,都蘭部落阿美族人逐漸失去原有廣大的生活空間,其社會組<br />
織與規範逐漸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外來政治性的介入與運作。這些政策往往是<br />
國家機器「由上而下」進行,忽視了當地居民的參與和固有文化之特色,造成與<br />
部落之間的種種衝突。關於國家霸權的運作,本研究著重分析不同時期外來政權<br />
在政策與經濟的考量下,於部落內逐漸築起的殖民地景所顯示出之空間霸權,並<br />
說明這樣的空間霸權到處存在。筆者以 pagifalan(都蘭鼻之阿美族地名)開發案的<br />
過程為例,分析目前國家政策在空間規劃上仍然漠視當地居民之文化權、生存權<br />
及充分參與的權力,主要的規劃與決策權仍在政府、設計公司與財團之間運轉,<br />
形成一股「內部殖民」權力不平等之宰制。<br />
另一方面筆者也觀察到在長期一連串外來政策壓制、文化斷層等結構性的改<br />
變下,近年來受到世界原住民潮流及國內原住民運動所引發之部落主義、社區營<br />
造之影響,都蘭部落阿美族人的族群認同與主體性也逐漸恢復。都蘭部落阿美族<br />
人如何重新發掘出自身內在還蘊含的文化潛力、元素,尋回對自我族群之認同?<br />
進而發展出另一股「由下對上」、企圖去殖民化的群眾力量與部落自主發展歷程,<br />
以對抗長期以來的國家霸權?筆者認為固然都蘭部落曾面臨人口外流、文化接續<br />
斷層之困境,然而部落文化之本質、元素與精神卻一直深藏在部落耆老們心中,<br />
成為部落本體力量之根源。透過耆老們之熱心配合及部落青年之自我覺醒,發自<br />
部落內在之文化傳承運動逐漸喚回更多族人的回流與認同。2003 年這一股部落<br />
力量進一步結合外部相關團體和媒體,成功地阻擋了國家政策對當地都蘭鼻開發<br />
案之進行,展現在地人對部落空間之自主性、強化更多人對部落、族群之認同與<br />
信心。筆者期待都蘭部落的經驗與歷程可以作為其他地區之相關參考。<br />
關鍵字:殖民去殖民,空間霸權,族群認同,部落主義,東管處,都蘭鼻,自主<br />
性<br />
177
一、問題意識<br />
近年來隨著相關政府單位各項公共建設的陸續動工與私人資本家買賣土地<br />
的頻繁,蔚藍深邃的東海岸開始暗潮洶湧,即將產生重大的變化,也將改寫原本<br />
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生活版圖。這些現象讓我想探究東海岸土地變遷的始末與對當<br />
地居民、環境的影響。我以位於東海岸的都蘭部落為例,分析其在不同時代下之<br />
環境變遷、土地使用的改變、外來政治權力的運作及近年來在社區內部逐漸發<br />
展、凝聚的部落群眾力量,以作為其他地區之對照與參考。<br />
本篇論述主要以都蘭部落阿美族人為主體,因此將部落以外的政治力量皆視<br />
為是部落主體性以外之外來政權,以凸顯這些外來政權及政治力量對部落的影響<br />
力及政治霸權。本論文將從時間與空間兩大主軸來分析,在時間軸上將按照年代<br />
先後順序分為日據時期前、日據時期、國民政府時期、近代、與未來發展等五大<br />
時期。我將一方面以田野訪談為主、相關文獻為輔,由當地居民的描述重現不同<br />
期間都蘭部落的面貌與發展。另一方面以當地人的生活經驗為例,分析在不同時<br />
代政權下,其主體性地位之消失與生活的變遷。<br />
在空間軸上首先從早期都蘭阿美族人的傳統領域 1 、部落地圖 2 的角度論述,<br />
紀錄過去日據時期前都蘭阿美族人的生活面、生態面、文化面、與部落歷史等面<br />
向,企圖重現昔日都蘭部落傳統生活的樣貌,並且將特別著重部落一些儀式空<br />
間、神聖空間之重要性。由此,從都蘭阿美人的文化邏輯中耙梳出傳統部落對土<br />
地的認知、與環境之緊密關聯。突顯原住民在生活環境中之主權地位及其特殊之<br />
傳統知識與生態平衡觀。<br />
其次隨著外來政權(從日本政府到國民政府時期)的進入,整個部落體系便<br />
籠罩在國家範疇之下,進行殖民地式的政治、經濟與教育模式。在此階段下,除<br />
了田野訪談外,我想以部落裡現存的一些地景來加強分析在不同外來政權之下,<br />
環境的規劃與土地使用背後制定的機制與掌政者之殖民心態與空間霸權。在殖民<br />
政策之下,都蘭部落的土地如何開始產生變化?都蘭阿美族人對土地的主控權如<br />
何開始慢慢移轉、甚至喪失?一棟棟象徵外來殖民政治、空間霸權、由上而下推<br />
動的建築地景如何龐然地出現在都蘭阿美族人的傳統土地上?在不同時期之<br />
下,都蘭阿美族人又是如何因應時代洪流改變對土地的使用與認知?此外,我將<br />
以交通部觀光局之都蘭鼻開發案為例,說明主流政權在民意的形式包裝與帶動地<br />
方經濟的美麗口號下,枉顧地方文化特色、破壞當地自然環境與生態。在台灣這<br />
些頻繁可見的建設案,當主流價值與地方主體產生衝突時,到底最後真正獲利的<br />
1 依據立法院審議的「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以及仍在內政部研修的「原住民族土地法」草案所<br />
定義的「傳統領域土地」是指舊部落、舊部落周邊耕墾地、傳統獵區、祖靈聖地,而其認定需要<br />
經由族群與部落內部的確認,具體操作方式就是要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和衛星定位系統<br />
(GPS)調查測定其確切位置與面積,據以繪製部落地圖。<br />
2 依據立法院審議的「原住民族發展法」草案以及仍在內政部研修的「原住民族土地法」草案所<br />
定義的部落地圖,標示的不僅是各種地形、地貌、地名與方位,更要將與土地有關的口碑(如神<br />
話傳說)、使用該土地的傳統經驗,以及各類相關的知識、記憶等曾經確實擁有、管理、使用的<br />
證據,詳細記載和呈現,俟資料完備,則可據以主張該土地的傳統權益。<br />
178
人是誰?<br />
第三、近年來隨著原住民族群意識抬頭,在部落主義、社區營造的帶動下部<br />
落族人也開始思考政府的政策與各項開發案在都蘭產生的影響與衝突,究竟是誰<br />
在規劃我們的家園?我們發現當權者的思考邏輯往往和當地人的文化邏輯相矛<br />
盾,長久以來當地人也無從充分參與部落空間之規劃與政策,當地人的意見與文<br />
化長期被政府忽視。政府單位在部落公有土地上的種種規劃常常獨立在部落之<br />
外。而在面臨一連串的變化,透過部落地圖的調查、口述歷史的紀錄與各種地方<br />
性活動的進行,我也觀察到都蘭阿美族人日漸形成、由下而上的部落凝聚力,都<br />
蘭部落的阿美族人重新產生對土地的認同,並且將過去的生態知識運用在部落的<br />
建設與發展,開始從文化的角度重新在自己的土地上展現出具有族群主體性的規<br />
劃與發展願景。以上這些都是本論文急欲探究的主題。<br />
二、田野對象與研究方法<br />
現今在都蘭部落還有完整的男子年齡階級組織,將部落男性依年齡大小分<br />
組,從青少年開始,差距五歲為同一階級,每五年晉級一次。通過成年禮之新進<br />
階級,頭目和長老會開會決議,以晉級當年發生之大事作為新階級的名稱。例如<br />
其中一組「拉贛駿」階級名稱的由來,即是以當年第一位上太空的華人-王贛駿<br />
而來。目前在都蘭部落還能追溯的最早階級為拉唗嚕活(Ratodoh),若以四至五<br />
年晉級一次,則都蘭部落可以追溯將近兩百多年的歷史。從不同時代階級的名稱<br />
來看,從早期的阿美族組名、日本組名、國民政府時期的組名等,可以看出一個<br />
時代變遷對部落的影響,而都蘭部落年齡階級的演變就是一個部落史。<br />
本研究之田野對象即以都蘭部落阿美族人為主,分老、中、青三代。耆老組<br />
以都蘭部落老頭目為中心,帶領訪問相關長者;中年組以都蘭年齡階級拉國中、<br />
拉建設、拉元簇、拉贛駿之族人為主;青年組則以拉中橋、拉監察、拉千禧、拉<br />
立委之族人為主。為顧慮到當事人之隱私,本論文中所有受訪者都將以匿名表<br />
示,以免造成當事人不必要之困擾。目前筆者在都蘭部落定居已有六年多的時<br />
間,部落耆老們也給予筆者一個阿美族的名字:Lameru(都蘭部落阿美族語:<br />
小米),希望筆者像小米一樣結穗美麗。同時在部落朋友的帶領下,筆者目前為<br />
都蘭部落年齡階級-拉贛駿之一員,也是部落團隊-都蘭山劇團之執行長兼藝術<br />
行政組長與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之一員,有機會常常與部落族人接觸,一起<br />
協辦各項部落活動。平日筆者即協助申請部落計畫並執行、參與社區活動、每年<br />
之 kiluma’an(俗稱豐年祭),進入部落之人際網絡。在參與的過程中筆者也逐漸<br />
了解大家的想法與族人之間的互動模式,對於本論文之訪談對象皆有一定的接觸<br />
與認識,因此不會有陌生、尷尬之疑慮。唯耆老在接受訪談時,仍以阿美母語為<br />
主,仍需借助部落族人代為翻譯。本論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如下:<br />
(一)民族誌研究法<br />
Malinowski認為民族誌(ethnography)的主要目的在瞭解當事人眼中的另一<br />
種生活方式,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是要「掌握當地人的觀點、他與生活的關係、<br />
179
了解他對他的世界的看法」(胡幼慧 2005:174)。民族誌知識的產生基本上依賴<br />
兩種文化經驗的對照。研究者以自我原有的「背景知識」-即個人的生活經驗、<br />
文化價值、觀念體系等-為基礎,對被研究世界裡觀察及學習到的新經驗進行理<br />
解詮釋(胡幼慧 2005:175)。筆者是一位漢族學生,生長背景是一個福佬家族,<br />
但是研究的田野地點與對象則是一個阿美族聚落。雖然筆者已經在都蘭定居六年<br />
了,但是和族人聊天時,他們所使用的字彙、句法邏輯、祭典儀式、生活方式等,<br />
每次都會引起筆者的好奇心。筆者想透過訪談,耙梳出都蘭人的思維邏輯與文化<br />
意涵。再加上近年來政府公部門在部落推動各項規劃及建設往往成效有限,也令<br />
筆者質疑是否公部門的思考邏輯和部落族人的思維模式是相衝突?筆者也想透<br />
過民族誌的方式為族群思維之間的差異做進一步的比較。<br />
(二)焦點團體法<br />
焦點團體法多了團體成員的「互動」和討論。研究者在此法中往往扮演了中<br />
介者的角色,其所收集的資料,便是以團體間互動討論的言詞內容為核心。訪談<br />
的問題通常集中在一個焦點上,研究者組織一群參與者就這個焦點進行討論(陳<br />
向明 2005:285)。根據筆者在都蘭部落進行訪談的經驗,當地族人常常喜歡聚集<br />
在一起聊天、歌舞同歡樂,很多家族也仍保有每一至二個月進舉行 pabisin(親<br />
戚會)的習慣,此外都蘭部落傳統領域地圖的製作也已在 2003 年完成,都蘭部<br />
落透過部落族人主動、積極的參與製作地圖,培養互動的默契與共識,並對自己<br />
的部落環境更加認識。筆者將針對特定參與的團體成員進行訪談,了解背後的過<br />
程與意義。若能擅用焦點團體法,將具有主題相關經驗的族人聚集起來,不僅可<br />
以避免陌生、不熟悉的尷尬場面,團體之間個人的言論也容易刺激其他人的經驗<br />
回想與集體記憶,是非常實用的方法之一。表 3-2 是筆者論文期間焦點團體訪談<br />
的時間、對象、與主題內容,針對每一個主題內容進行 3-5 次之焦點團體訪談,<br />
每次約 8-10 個受訪者,受訪時間為 2-4 小時。<br />
表 1:焦點團體訪談的時間、對象、與內容<br />
時間 訪談對象 主題內容<br />
2006 年 1 月、 前任頭目、 都蘭部落遷移史、傳統地名、傳統領域範圍、社會組織、祭典儀式、年齡階<br />
2006 年 7 月 部落耆老 級、過去土地使用狀況等<br />
2006 年 8 月 老婦人數位 傳統禁忌、施巫術、祭典、傳說故事等<br />
2007 年 2 月 老獵人數位 狩獵範圍、狩獵方法、動物分布、生態觀等<br />
2007 年 2 月 中年族人數位 都蘭灣及都蘭鼻捕魚和射魚之生活經驗、魚貝類習性及分部、海濱自然環境<br />
之認識、生態觀等<br />
2007 年 3 月 中年族人男女<br />
數位<br />
不同時代都蘭部落之產業變遷<br />
2007 年 4 月 老漁民數位 漁獵範圍、漁獵方法、生物分布、生態觀、環境變遷等<br />
2007 年 4 月 頭目、耆老 日據時期都蘭部落之社會變遷、男子集會所之遷移等<br />
2007 年 4 月 耆老數位 外來地景的出現(警察局、神社、學校、活動中心等)、外來宗教(天主教、<br />
基督教、真耶穌教、民間信仰等)在都蘭之發展<br />
2007 年 拉金馬、拉傳 部落人口流失、在外跑船之經歷、重回部落的心情<br />
1 月-4 月 廣、拉建設組<br />
180
員數名<br />
2007 年 拉贛駿、拉中 過去都蘭部落年齡階級之斷層、文化流失、重新認同族群之歷程。<br />
3 月-5 月 橋、拉監察、<br />
拉千禧、拉立<br />
委組員數名<br />
2007 年 村民數位 對都蘭鼻開發案之看法<br />
3 月-5 月<br />
(三)個人深度訪談<br />
個人深度訪談以預先告知受訪者,尋覓適當時機、登門造訪、攝影錄音的方<br />
式進行,依照訪談的進度與內容實施 2-4 次之深度訪談。訪談的對象主要有:<br />
1. 焦點團體訪談中的特定人士。焦點訪談適合聚集一群具有共同經歷、記憶的<br />
族人,透過聊天、訪談的方式,刺激、回憶、多方面呈現主題內容。然而焦<br />
點團體訪談進行的過程中,礙於時間的限制及參與的人數,某些對於特定主<br />
題有深入認識、深刻經歷的受訪者便不容易暢所欲言。此時筆者都會留意這<br />
些特定的受訪者,請對方寫下詳細之聯絡電話、地址,另覓適宜的時機登門<br />
拜訪,進行更深入之個人訪談,以補述更詳細之內容。<br />
2. 部落中有特殊生命/生活經驗或生命/生活故事、僅存之耆老。這些耆老為數不<br />
多,且多屬於個人特殊之經歷與生命史,不適用焦點團體法。例如部落僅存<br />
一位之竹占師,現年七十多歲,對於驅除疾病、驚嚇、或不順遂等儀式仍然<br />
非常熟練,至今也仍有許多族人尋求他的幫助。針對此人之個人訪談,可以<br />
讓筆者更了解都蘭部落傳統泛靈之信仰觀念,增加對傳統生態觀、環境觀之<br />
完整性。<br />
3. 在地團體之負責人。近年來在都蘭部落陸陸續續成立許多地方性團體,彼此<br />
之間的屬性與發展重心皆不太相同,然而對於部落文化之傳承、文化產業之<br />
研發與對自我族群之認同都有一定之貢獻與意義。針對這些地方團體之負責<br />
人進行個人深度訪談,可以更了解他們對部落現況之看法、未來發展之願景<br />
及對部落之使命感。<br />
4. 特定藝文及環保團體人士。2003 年都蘭鼻開發案抗爭運動的過程中,除了部<br />
落頭人、族人之參與外,還有藝文及環保團體的支持與協助。針對特定的相<br />
關人士進行個人深度訪談,可以增加對都蘭鼻開發案環保面向之見解,加深<br />
事件的廣度與深度。<br />
5. 特定政治人物,主要以廖國棟立委為主。廖國棟立委即為都蘭部落阿美族人,<br />
除了提供其個人對都蘭鼻開發案之看法外,也分析現行法律上或政策上對於<br />
部落發展之衝突與建議。<br />
(四)參與觀察法<br />
參與觀察提供研究者「被信任者」身分的機會。透過參與觀察成為社會情境<br />
中的一員,可獲得第一手資料、看見受訪者之行為模式、並激發受訪者說出原本<br />
隱而不說的資料(Corrine Glesne 著,莊明真譯 2006:61)。筆者目前身為都蘭部<br />
落「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的一員及都蘭山劇團執行長兼藝術行政組長,這<br />
181
幾年來持續直接參與部落每年一次青少年文化傳承訓練營及其他活動計畫之規<br />
劃與執行,在每一次的規劃與執行過程中,筆者都親身感受到部落族人在經歷過<br />
訓練營之後再一次的成長與對部落文化的認同感、向心力、及自信,這樣的直接<br />
參與有助筆者分析族人對自我部落認同感的滋生,並進而由自我出發,產生部落<br />
的主體性發展。<br />
三、結論<br />
台灣原住民是目前最早居住在台灣的住民,原本擁有對自然環境的使用權與<br />
主權,然而在外來政權-日本政府與國民政府相繼進入台灣後,他們也逐漸喪失<br />
其原有之權利與地位。本論文欲解釋都蘭部落阿美族人如何從早期自給自足的部<br />
落生活到納入主流經濟、政治體系架構之過程;外來政權如何藉由空間霸權所建<br />
立之殖民地景改變都蘭部落阿美族人對土地環境的主權、傳統經濟型態的運作、<br />
與部落社會組織、教育文化之延續;並分析長久以來被他者化的都蘭部落阿美族<br />
人如何透過一連串部落文化活動之推動與對國家政策抗爭之社會運動,慢慢產生<br />
對自我族群之認同、恢復民族自信心、創造部落文化產業之歷程。<br />
本論文主要以都蘭部落之阿美族人為敘事主體。首先從部落傳統上對土地所<br />
有權與使用之認知、土地與農耕相關之禁忌與儀式、泛靈(kawas)之傳統信仰、<br />
以及族人和周邊其他族群之互動,說明都蘭部落之阿美族人與自然環境、傳統文<br />
化之間的緊密關聯。早期阿美族人感受到自然環境之無常、天然災害之頻仍、與<br />
農業作物之不穩定,逐漸發展出一套耕作模式與「靈」(kawas)的概念。對阿美<br />
族人來說 kawas 無所不在,有自然環境之 kawas、動植物之 kawas、施巫術之 kawas<br />
以及各種好的與壞的 kawas 等,並衍生為一系列繁複之禁忌與宗教儀式,如祈雨<br />
祭、祈晴祭、海祭與 kiluma’an(豐年祭)等。農作物之好壞、獵物之豐收、個<br />
人之病痛與部落發展之順遂,都環繞在這些 kawas、祭典、禁忌之文化產物中,<br />
形成自然環境、阿美族人與部落文化之間緊密之結合。<br />
西元 1895 年日本殖民政權正式進入台灣,隨著在台勢力逐漸穩定下來,日<br />
本多項殖民政策也隨之在台灣展開。為了便於控制,日本政府首先將原本分散的<br />
部落集中、遷徙,建立其行政區域之活動範圍。行政界線一旦劃定、確定,也限<br />
制了族人的活動範圍。原本都蘭部落阿美族人散居在目前興隆以南,經過羊橋、<br />
八里溪、都橋、都蘭本部落、漁橋及北郡界山區一帶,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慢慢集<br />
體聚集、形成現在之都蘭村。在土地制度上,族人之間約定成俗的「土地先佔法」<br />
也改採用「土地登記制度」,使得原本廣大之傳統領域,除了一些長期使用之農<br />
耕地登記為私有地之外,其餘廣大之狩獵山林、河濱、海濱等地區則劃歸為國有<br />
地:花東地區成為殖民政府地大物博之可用之地。此外,灌溉系統之建立與水稻<br />
種植之引進,改變了原本圍繞小米成長週期而形成之傳統祭典與禁忌;日本神道<br />
教的傳入也改變了部落原有之泛靈信仰,族人對土地、對環境的價值觀逐漸物化<br />
了。<br />
其次,為了加強掌控部落族人之生活,日本殖民政府施行一系列非常嚴謹之<br />
182
社會組織制度及殖民知識體系。誠如姚人多所指出:日本殖民的治理性表現在兩<br />
方面。一方面是科學性,國家機器利用科學觀察、調查、分類及計算等;另一方<br />
面是結合權力與知識之生物政治,二者從中發展出規訓式控制人身的方法(姚人<br />
多 2001)。這套規訓制度在社會秩序方面,日本政府建立了天羅地網之警察制<br />
度、帶進日本學校教育與神道教信仰,都蘭部落阿美族人在生活面、教育面、信<br />
仰面逐漸異化,至今部落內的耆老們對於日本政府時代警察大人、老師大人威聲<br />
赫厲的印象仍然歷歷在目。在經濟方面,部落不再廣泛地種植小米、芋頭等糧食<br />
作物,取而代之的是日本殖民政府所需要之熱帶栽培業,大片大片的甘蔗園與矗<br />
立的糖廠象徵了殖民地式經濟的來臨。派出所、學校、神社、糖廠等殖民地景陸<br />
續出現在都蘭部落的土地上,都蘭部落自此進入到外來政權之政治、經濟體系當<br />
中。<br />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隨之而來的國民政府在許多政策上仍依循、接收日本殖<br />
民政府所霸佔之土地與所有權,部落土地並沒有因此而「光復」、「回歸」。此階<br />
段在都蘭部落明顯的改變就是西洋宗教的進入、部落社會與經濟再次的改變。本<br />
論文第四章的後半段說明此時都蘭部落的傳統聚會所(sfi)徹底瓦解原有之教育<br />
與訓練功能、manayaw(大獵祭)獵場之改變與禁止、以及在 1960 年代因為大<br />
環境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部落年輕人大量舉家遷移到外地工作與居住,形成部<br />
落文化嚴重之斷層。本論文主要列舉日據時代及國民政府時期陸陸續續出現在都<br />
蘭部落之重要殖民地景,突顯出在這些空間霸權背後,外來政權對部落之掌控與<br />
影響。2003 年,由東管處策動、顧問公司規劃、預計由外地財團 BOT 經營之「都<br />
蘭鼻開發案」再次粗劣地暴露出國家政權對一個地方部落環境權與文化權之漠<br />
視、權力之不對等之空間霸權。<br />
從東管處對都蘭鼻開發的說詞與空間規劃來看,國家政策是將都蘭鼻視為一<br />
風景絕佳之「荒地」,藉由開闢此荒地、建設觀光飯店及遊樂設施,一方面紓緩<br />
都會人口擁擠、緊湊之生活步調,提供、滿足都會人士休閒旅遊之需求;另一方<br />
面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然而在筆者的訪談中,都蘭鼻不只是都蘭部落傳統領域之<br />
一部分,更是蘊含部落祭儀、海洋生活技能與文化傳承之重要據點。依據筆者長<br />
期在部落之觀察及耆老的談話中深深學習、領悟到「部落文化、教育並不是局限<br />
在僵化的學校制度中,反而是極生活化、自然而然發生,小孩子是從做中學!」<br />
之道理。這樣的教育方式是學校所沒有、也是學校不可能教的,這些部落知識技<br />
能、社會生態與人際網絡就是這樣一個階級一個階級傳承下去。如今,東管處國<br />
家政府一個政策就要這樣霸道式地將正在都蘭鼻進行之部落文化完全抹煞掉,無<br />
視地方部落對環境、土地之主權與傳統使用方式,當然激發出部落抗爭的力量。<br />
歸結都蘭鼻開發案與部落衝突之始末,筆者認為第一點是政府與部落族人雙<br />
方對土地認知之差異。雖然歷經不同外來政權、思想觀念之改造,傳統部落的一<br />
些思維,即人、自然環境與文化彼此之間緊密的關聯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是可<br />
以隨時從耆老們及年輕人之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蛛絲馬跡。例如筆者常與部落耆<br />
老、年輕人上山採樹皮製作樹皮衣,耆老們仍然會用米酒、檳榔,口中念念有詞<br />
183
地說:土地神呀!樹神呀!請讓我拿取一些祢的樹幹、樹皮,讓我製作衣服、不<br />
必受寒,我們用石頭與祢交換,請祢賜給我們。這樣簡短的儀式與祭詞常常讓長<br />
久以來生活已經科學信仰化與物質化的筆者非常感動、驚訝與驚嘆,原來在目前<br />
這樣一個 E 化的世代中,在部落、在族人身上還是可以深深感受到純粹的自然<br />
與萬物共存的真理。雖然歷經外來宗教、政權之影響與生活型態、社會結構之轉<br />
變,一些部落傳統的精神與思維模式仍然深深烙印在一些族人心中,影響著其生<br />
活模式與對事務之價值觀及看法。這樣子萬物共存的土地觀、環境概念與後來國<br />
家政權「物化」的土地觀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極大的差異和衝突。第二點<br />
就是國家政策對於地方部落仍持續存在著殖民霸權及一手掌控之心態;鼓勵地方<br />
民眾之參與、保留地區之文化特色、促進部落經濟之發展等等往往仍然只是政客<br />
的口號而已。政府一聲令下的決策、顧問公司的規劃、財團的進駐,馬上就可以<br />
一筆勾消當地居民對土地的集體記憶、情感與權利。開發得宜,政府與財團獲利;<br />
開發失敗,當地居民承擔殘局與環境破壞之後果。政府與財團之短視近利與霸道<br />
心態展露無疑,當地居民與自然環境處於被支配、宰制之狀態。<br />
隨著國際逐漸重視原住民的權益與聲音的時代趨勢下,為了打破長期以來<br />
「國家-部落」權力不均之狀態與脫離被宰制之地位,都蘭部落阿美族人重新凝<br />
聚、整合內部之力量,向外界發出自我的聲音。都蘭鼻開發案抗爭成功的原因筆<br />
者歸納如下:第一、在都蘭鼻開發案說明會之後,部落耆老在短時間之內就繪製<br />
完成都蘭部落傳統領域之地圖與傳統地名之由來,遠比隨後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br />
委託學界執行、鄉公所協助之官方版傳統領域更詳細、清楚,搶得先機讓部落年<br />
輕族人及早認清部落傳統領域之範圍,藉以作為初步抗爭之依據。第二、部落頭<br />
人之有效領導與對土地之認同。都蘭鼻開發案發生在都蘭部落前頭目 P 任職期<br />
間,為了充分表達出部落族人對開發案之反對心聲,前頭目 P 常常帶領族人不辭<br />
辛苦前往都蘭鼻現場、鄉公所及東管處等地陳情、說明。筆者印象最深刻的就是<br />
前頭目 P 在接受訪談時曾說:若在我有生之年、都蘭部落頭目任內,能夠解決部<br />
落土地、與族群之間的爭紛,我就能夠安心的回到天上去。短短的幾句話,展現<br />
出一個部落老者對於土地開發之憂心、保護部落之責任與族群共融之智慧。第<br />
三、與部落以外之團體有效結合。一個部落的力量有限,然而結合其他相關團體<br />
則力量無窮。誠如 Anderson 所言:一旦疆界、侷限被打破之後,隨著印刷術、媒<br />
體的普及,所有遠方的群眾將因共同的集體記憶而串聯起來(Anderson 1999)。整<br />
個都蘭鼻的抗爭力量包含部落本身、藝文團體、環保團體、政治團體、及媒體之<br />
有效運作,一波又一波向社會大眾發聲,形成群眾的力量,成功阻擋東管處對都<br />
蘭鼻之開發。<br />
然而追根究底筆者認為還必須從更深層的角度來分析整個都蘭部落族群認<br />
同的發展。筆者認為都蘭部落能夠發出這麼大的力量,主要原因仍在於部落本身<br />
過去長期深層耕耘、推動、栽培年輕人有關。1960 到 1980 年代,都蘭部落如同<br />
其他部落般嚴重面臨青壯年人口外流、文化斷層、部落瓦解的狀態,甚至 1990<br />
年代初期都蘭部落的 pakanunay(青少年)只剩下一位在旁邊觀看而已。這樣的<br />
184
狀態在 1993 年受到國際原住民年的刺激與國內原住民運動的推動下,部落意識<br />
逐漸覺醒,一些有識之士體認到文化傳承之危機,終於在 1995 年重新舉辦將近<br />
消失五十年之巴卡路耐訓練營。由自願擔任講師的老人家帶領青少年穿梭在部落<br />
山林裡,砍竹子、採野菜、製作傳統手工藝、傳唱部落歌謠、訓練海上技能等,<br />
pakanunay 從學習中探索服從、敬老等傳統精神與文化,重新踏上祖先走過的足<br />
跡。從此以後,巴卡路耐訓練營慢慢得到族人的認同,每到 kiluma’an 前夕長輩<br />
們都會聯絡在外地之青少年回部落參加,逐漸恢復過往、成為每年舉辦一次的常<br />
態訓練。<br />
此外,近年來部落在地性團體對於地方文化之傳承與創新也有很大的貢獻。<br />
由部落族人組成之都蘭山劇團除了肩負紀錄、保存部落傳統樂舞之使命外,更進<br />
一步將採集到之部落歌舞、神話故事及社會現況等狀態與現代舞臺劇結合、創<br />
新,用更多元的舞台表演方式抒發族人對部落不同之觀點。另一個由部落族人組<br />
成之阿美文化團則是以文化產業為主,訓練青少年舞蹈團、推動當地阿美族風味<br />
餐、手工藝品創作、及部落生態體驗等等。近期阿美文化團在週休二日的下午還<br />
增加部落黃昏假日市集,鼓勵部落村民舉辦跳蚤市場、販售自採的野菜、月桃編<br />
等手工藝品,增加居民日常生活之收入,並且還計劃與當地民宿業者合作,共同<br />
創造出具有阿美族風格之民宿就業商機。從這些活動看來,筆者發現阿美文化團<br />
已經逐漸改變以往只純粹保留部落文化之階段,隨著多年來族人田野調查成果之<br />
累積,近年來阿美文化團慢慢將這些原有之部落特色、資產與現代商機結合、創<br />
造出深具在地風格之商業契機,逐漸在經濟上獨立自主發展。此外,如阿度蘭阿<br />
美斯文化協進會、藍星文化藝術團、SiKi 工作室、小米文史藝術工作坊等其他部<br />
落在地團體在部落文化推廣上也是不遺餘力,都是推動部落發展上旺盛之生力<br />
軍。由上述這些現象我們得知目前都蘭部落的成果並不是一夕造成的,而是在族<br />
人長期默默耕耘下、共同努力開花的結果。<br />
本論文筆者應用後殖民主義與族群認同等觀點來分析在經歷多次外來政權<br />
的轉移與制度影響下,都蘭部落阿美族人對土地主權慢慢喪失的歷程及部落自我<br />
重新展現的主體性發展。其中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注意:<br />
(一)國家政策與部落思維之衝突<br />
早期傳統部落受到農業技術、環境、天災等之限制,作物產量不穩定,藉由<br />
農業歲時祭儀與各種禁忌之進行,一方面祈求作物之豐收,另一方面也合理化許<br />
多不可預期之災變以穩定社會秩序與民心。雖然目前許多傳統的祭典、禁忌、與<br />
社會規範都已經逐漸消失,然而一些生活習慣、方式與對事物之認知、思維仍然<br />
潛移默化、潛藏在部落族人的生活中,影響著一些行為。部落思維與國家政策、<br />
主流觀念之間常常存在極大的差異與衝突。<br />
(二)從殖民主義的角度,分析外來政權對土地認知的差異及空間霸權<br />
1895 年日本政權進入台灣,開始確定各鄉鎮之行政界線與範圍,部落正式<br />
進入到國家行政體系之中。首先在日據時代外來政策下的集體遷村,將原本分散<br />
的都蘭阿美族人集中居住在現行村落的行政範圍裡,縮小了阿美族人傳統的活動<br />
185
範圍。其次為了確定土地權限範圍,國家不再採用阿美族傳統之「土地先占認定<br />
法」改由政府調查無誤之土地登記制度,減少了阿美族人傳統的土地使用範圍,<br />
生活方式從不定居之游耕轉變為定居之水稻農業,也改變了傳統的小米農業祭儀<br />
與禁忌。第三,政府為有效掌握當地資源與控制當地居民,著手進行環境調查、<br />
教育與警察監控制度。日據時代殖民地景之都蘭公學校、神社、派出所陸陸續續<br />
出現在都蘭部落的土地上,象徵殖民政權強而有力之掌控。最後,為累積殖民政<br />
府財富、滿足日本內地之所需,在台灣本土大力推廣殖民地式之經濟,即熱帶栽<br />
培業。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外地資本家在都蘭興建之糖廠,開始大規模種植甘蔗,<br />
徹底改變都蘭部落之農業地景與經濟結構。<br />
國民政府時期,對於原住民發展政策某些程度上仍延續日本政府,在部落土<br />
地之認定與空間規劃建設上仍然忽視當地文化之特色與延續,使得在日本時期改<br />
革之下都蘭部落尚存之文化特色與社會規範更進一步地中斷、消失。象徵傳統都<br />
蘭部落阿美族聚落最重要之 sfi(聚會所)就是在不同政權制度與外來宗教之影<br />
響下,失去原有之樣貌,甚至轉讓、轉賣給他人。1960 年代開始,隨著西洋宗<br />
教之禁止、台灣農業價格低落、經濟結構轉變,造成部落大量青年外流,sfi 也<br />
逐漸沒落下來,甚至改頭換面成為了都蘭社區之活動中心,失去 sfi 在部落教育<br />
傳承上之功能。外來政權枉顧地方文化之獨特性與主體性所形塑之「空間霸權」,<br />
以自我想像塑造各種外來地景與地名,造成地方文化之改變與中斷,直接、間接<br />
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經濟產業型態的改變也改變了部落原有的<br />
價值觀與信仰,造成部落族人與土地、環境、文化之脫離與斷層,成為被異化之<br />
「他者」。<br />
(三)由「內部殖民」的觀點分析近年來「國家政策-地方民眾」權力不對等之<br />
關係<br />
縱然當前台灣政府高喊保育自然、人文資產,推動國土規劃、永續經營,然<br />
而在這些口號之下,仍然存在了許多執政者「中心-邊陲」、「中央政府-地方民<br />
眾」權力不對等之內部殖民心態,忽視了當地自然資源與人文文化之特色,也漠<br />
視民眾參與之重要性。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政策與外來財團的經營下,本研究發現<br />
這些所謂的「觀光產業」發展其實與當地居民的關係是非常疏離、脫節,並且在<br />
不尊重、重視當地環境特色的前提下,一個個樣本式的觀光建設其實多是外來模<br />
式的仿造與外地人對花東地區的想像,不僅無法發揮花東地區獨到的地方特色,<br />
反而還破壞了當地之自然環境。這些現象說明了國家政策一如往昔仍然枉顧地方<br />
環境特色、當地住民文化與民眾參與之權利,依舊霸道式地依照其「想像」制式<br />
開發地區之建設與發展,展現出一種「空間霸權」之姿態;本研究所探討的東管<br />
處既有之公共工程設計與都蘭鼻開發案之過程就是一個個明顯的例子。此外<br />
BOT 的開發方式,將原本屬於大眾之公共財與自然環境交由財團私有化經營,<br />
顯示出空間霸權中被漠視的民眾權益和參與。<br />
(四)都蘭部落阿美族人對土地、族群之認同及部落主體性之發展<br />
在上述的情況下,當地居民若要突破「內部殖民主義」的宰制,顛覆這種國<br />
186
家政策「由上至下」之霸道形式,本研究觀察到最重要的還是被宰制者必須先有<br />
所知覺、覺悟、破繭而出。都蘭部落在 1960 到 1990 年代之間,雖然人口大量外<br />
流,造成部落文化嚴重之斷層,所幸部落耆老之堅持、自願熱心擔任年輕人文化<br />
傳承之老師、協助部落文化之延續,以及年齡階級與各家族宗親會之潛移默化,<br />
才讓都蘭部落的青少年了解部落文化之精神內涵、得以延續傳承下去。此外,1993<br />
國際原住民年,在大環境之改變與趨勢下,透過報章媒體之散播,台灣原住民族<br />
之境遇與世界其他原住民族之狀況相連結,產生 Anderson(1999)所指稱跨越<br />
時空之結合,也刺激青壯年民族自覺、自信心、認同感之產生而回歸部落。這些<br />
回歸部落之青壯年更可藉由同年齡階級同儕之關係吸引更多族人回流,形成一股<br />
良性循環、部落內部主體性發展之力量。<br />
都蘭鼻開發案暫緩施工成功的原因除了部落內部自我的力量外,筆者認為也<br />
和外部相關團體的有效結合相關。自從都蘭鼻開發案在部落爆發衝突之後,部落<br />
與相關之藝文團體、環保團體、政治勢力之結合與媒體的報導,讓台灣更多的群<br />
眾因為環保意識之抬頭、環境汙染破壞之共同經驗,而將彼此相隔遙遠的群眾串<br />
聯起來,凝聚一股跨族群、跨區域、更強大之力量,終於成功阻擋開發案之進行。<br />
隨著大眾對部落的認同感逐年增強,部落裡的一些族人及在地民間團體也慢<br />
慢重新找回過去文化的特色與光榮,並將這些文化特色重新融合在部落社區總體<br />
營造當中。在文化創新方面,地方藝文團體都以各種方式致力於「去殖民化」;<br />
在部落產業經濟方面,阿美文化團也持續推廣部落生態旅遊、發展部落有機產<br />
品、假日市集及阿美族風味餐,企圖走出一條部落自主、經濟之路。<br />
都蘭部落的經驗在台灣原住民社會中並不是唯一,長久以來國家政策、開發<br />
與法令在部落發展上之不公義與糾紛,近年來陸陸續續爆發出來。2005 年 9 月<br />
初在新竹縣泰雅族司馬庫斯部落發生之「風倒櫸木」事件,部落族人在海棠颱風<br />
過境後,為搶修崩塌道路將倒塌之櫸木擱置路旁以備部落他用。然而事隔一個月<br />
後林務局員工就逕自將櫸木鋸斷、運送處理;相反的事隔數天之後,部落族人撿<br />
拾櫸木剩餘之殘枝預做使用,卻被當地警察依違反森林法,以「加重竊盜罪」移<br />
送法辦。同樣的行為與事件發生在林務局與部落族人身上卻有兩種不一樣的處理<br />
標準。2007 年 4 月底第一期已接近硬體完工之台東杉原「美麗灣渡假村」開發<br />
案,由於業者長期任意傾倒工程廢棄土、水泥、石塊在沙灘上,當地阿美族人終<br />
於無法忍受其生活環境、自然海灘長久以來受到財團開發之破壞與污染而向媒體<br />
發出深沉的控訴。2007 年 6 月當台灣其他地區遭受連日豪雨淹水災情,宜蘭縣<br />
大同鄉泰雅族寒溪部落卻因無水可用而煩惱。原來是十幾年前該區上游之水源地<br />
在沒有知會部落的情況下,已經被自來水公司接收管理,導致下游的部落常常無<br />
水可用。以上這些原住民部落社會案件一再突顯出國家政策、政權與部落傳統精<br />
神、習慣法之間觀念之差異與衝突。這些例子在在說明了隨著部落意識的提昇以<br />
及族人對部落權益之重視逐漸增強,未來國家與部落之間的爭紛將更加明顯。都<br />
蘭部落抵制國家開發案進行之成功案例正可以作為未來其他部落社會抗爭之經<br />
驗。<br />
187
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台灣飲食習慣標榜無農藥殘留、有機農業,無化學污染<br />
之野菜逐漸受到大眾的重視,而原住民之飲食習慣正符合這股潮流,非常具有發<br />
展潛力。目前在台東縣魯凱族的達魯瑪克部落結合勞委會多元就業服務方案,已<br />
經慢慢發展出原住民有機飲食。無獨有偶,在大環境消費飲食習慣的改變下,都<br />
蘭部落的阿美族人也正在進行部落美食風味餐,食材皆採自大自然。另外,原住<br />
民對於自然資源之使用也非常具有環保、永續等概念。目前在都蘭部落以前任頭<br />
目為首的一批老人近年來開始在山林裡採集雀榕與構樹的樹幹,拿著木槌敲敲打<br />
打,重新製作、恢復都蘭部落失傳已久的樹皮衣。在老人家堅持保存、恢復文化<br />
特色的執著下,也有一些部落青年受到感動,慢慢延續部落原有之樹皮文化並加<br />
以創新,成為一件件具有巧思又有地方特色、創意之手工藝品。筆者認為抗爭激<br />
情過後,更須深思部落現有之資源與特色,如何有效結合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br />
發展更具部落自主性之地方經濟產業,如此才是真正的獨立自主、茁壯。此外,<br />
都蘭部落阿美族人對自然環境之熟識、與海洋魚類的魚汛週期、狩獵文化等在地<br />
生態知識也是未來部落發展生態旅遊之潛力。如何重新尋回祖先的文化智慧、生<br />
態智識,並加以創新、結合各項活動與產業發展,這些都是部落族人必須思考的<br />
方向。筆者相信每個部落都有其獨特之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可以善加運用,唯有<br />
在文化與經濟同時並行成長下,部落才能有效地走出自我主體性之發展之路。<br />
188